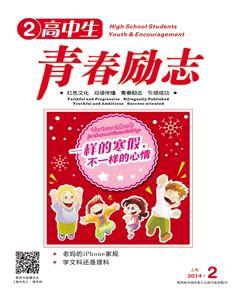给《诗经》涂上一抹色彩
张睦远
那是一条从西周发源的河,见证着三千年的沧海桑田。它时而潺潺而过,时而汹涌奔腾。它把沿途的一切都带走:战乱、国破、人亡、饥荒,还有爱情、亲情、友情。它卷着几百年的历史,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直涌向今天。河边有青郁的植物,淡然平静地任凭人们不断地给它们变更名字。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别忘了芦苇也曾是水畔的贵族,它们在有风的天气里拂动裙裾,说着情话。它们见证过脚下的河流因一位伫立在岸边的痴情人而变得忧伤的往事;它们凝视着河面上自己青色的身影,听着那似悲似喜的一唱三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求之不得的心境该是怎样一种忧伤呢?被芦苇染青了的河流那边伫立着一个我,正在细细地饮啜着这条名叫“诗经”的河。
那时人类正处于牙牙学语的时期,用着今天看来生僻的词汇。“蚩”就是“嗤”,“说”就是“脱”。可是幼稚的人类却懂得贴近自然,他们祭拜着想象出的万能的神,日夜劳作着采薇菜、葛菜、荇菜。人类是河流的子女。一个个质朴的诗人、歌者泛舟河上,为简单枯燥的劳动创作着号子,顺带抒发着人生境遇的种种情感。于是这世界上就出现了一首《采葛》,饱受争议的一首小诗。今人们啊,不要再纠缠于什么主旨中心了,且把那小诗细细品读,只要满足于它的文字美就可以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固执的重复,微妙的变化,一张薄薄的纸就能把我们带回遥远的岁月,和采葛人一起凝视着那青青的古老植物,且歌且叹。没有任何矫情的宣泄,反倒为小诗增添了朦胧美,于是一腔绵绵的情意和黯然的咏叹跨越千年,来到了我们心中。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从《诗经》的河里,我们窥探着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辛勤地劳作着,从不思考地球的奥秘。天真的人们对一切都敬畏,土地、山川、生物、生老病死,都是造物的安排。纯良恭顺的人们服从着命运,恪守着从远古时期承袭而来的纯真质朴。请看看那些刚刚出生的小动物吧。它们的眼睛乌黑清澈,闪耀着人类早已失去的天真无欺。我想,三千年前那些大地的儿女也一定拥有这样的眼睛吧。他们有远超过我们的智慧,因为他们懂得大自然神秘的呓语里蕴藏的真理。他们从不忤逆自然,正因如此,自然从不惩罚他们。可是,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思想。弃妇喟叹着氓的反复无常,那一声从古代传来的忠告“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闪耀着杰出的智慧,也流露出无尽的辛酸。古人懂得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情感,一百多个字就能概括人的一生。那蕴藉优美的四言诗句,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是思乡,是厌战,是忧虑,是希望。那一声声嗟叹咏歌,一字字敲打着我的心。三千年前,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人,唱着被时光封存了的悲歌;三千年后,也有一个我,踏着纸张铺成的道路和他一起手舞足蹈。杨柳依依,一片沉郁的青色再次在我眼前铺开。
流经千年、泛着三百多朵浪花的河流被繁茂的蒹葭、依依的杨柳、参差的荇菜染成了青色。我开始认为属于《诗经》的颜色是青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也许只有这沉郁、沧桑而又蕴藏着生命力的颜色才属于《诗经》。既清且青的河流承载着多少故事,渔人的歌谣、弃妇的哭诉、官吏的牢骚、文人骚客的咏叹、少男少女的誓言、劳作时的号子,以及故去的人、中断的事件、枯朽的草木、升起又落下的星辰……只有青色才受得住这样的文化积淀,只有青色才能既简单又复杂若此。青色,是大自然的颜色,与《诗经》稚拙古朴、带着泥土和青草以及鱼腥的味道的文字相得益彰。
风雅颂,赋比兴。我们的祖先早已习惯了歌唱生活,从新帝登基到采集野菜,从战乱徭役到谈情说爱,他们无不咏叹歌唱。生活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的艺术宝库,而他们要做的,不过就是满怀感恩地用生动朴实的语言捕捉住灵感罢了。沿着河岸漫溯,我们渐渐被感染,不由得也揣着一颗不染尘埃的心,寻找着先民们的足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诗经》,这条哺育并承载了婴儿时期的人类思想的河流,用它的清澈水流洗涤了今人的头脑和心灵。
且让我们在繁华浮躁中暂歇脚步,回到我们的母亲河身边,站在蒹葭丛中,再看一眼那碧青沉郁的《诗经》之河。
(本文作者系天津市南开中学学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