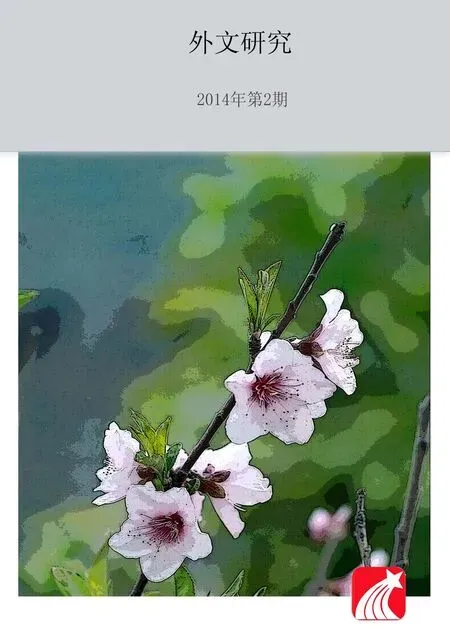论海明威的女性意识
厦门大学 杨仁敬
几乎从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年出版以来,批评界在解读女主人公布列特的言行时,就提出海明威女性人物的塑造问题。1929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问世后,批评界有人将女主人公凯瑟琳与男主人公亨利进行了比较,认为凯瑟琳的形象比较单薄、个性软弱,成了男主人公亨利的附属品。
随着海明威小说的陆续出版,批评家们更关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如玛丽·摩根(《有钱人和没钱人》中男主人公摩根的太太)、玛丽娅(《丧钟为谁而鸣》中男主人公乔登的女朋友)、雷娜塔(《过河入林》中男主人公坎特威尔上校的情妇)等。他们不断地批评海明威“缺乏女性意识”,认为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比男性形象差,而且很不真实,几乎成了漫画式的人物。
不仅如此,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成了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麦康伯、《乞力曼扎罗的雪》中的海伦、《第五纵队》中的达洛思·布里兹斯、《在密执安北部》中的李兹·柯特斯、《事情的结局》和《三天大风》中的玛约里、《医生和医生太太》中的亚当斯太太、《艾略特夫妇》中的艾略特太太、《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基格、《十个印第安人》中的普鲁登斯和《父与子》中的特鲁迪等。不少批评家认为这些女性形象具有上面提到的缺陷,是令人遗憾的败笔。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女权主义批评家进一步批评海明威的女性意识很差劲,嘲笑他小说中一些被动的女性形象,认为她们成了男主人公的“性工具”或“陪衬”。有的人认为这与海明威现实生活中歧视、甚至憎恨女性是分不开的。
有的学者从海明威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原因,认为这源自海明威对他母亲的憎恨,使他对女性形成了抹不掉的偏见。据海明威的朋友、退休美军上将查尔斯·兰哈姆回忆,海明威千百次告诉他:他恨他母亲,并骂她“那个淫妇”。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也证实,海明威的确恨他母亲。为什么呢?据说,他母亲很好强,在家里支配一切,不会理财,造成他父亲自杀,令海明威气愤不已。因此,有人说,海明威一生强调男性的魅力是出于他对母亲支配父亲的痛苦的回忆。他对女性刻画的思想障碍和他笔下顺从的女主人公都反映了他不愿意像他父亲那样屈从于他母亲脚下的决心。海明威在尼克·亚当斯的故事里写了尼克的母亲。她身上影射了海明威母亲的性格缺陷,表露了海明威的不满。(Kert 1983: 21)
诚如克特所指出,尽管小说反映了海明威对他母亲的不满,但对他的个人评论和小说本身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作为对他母亲格拉斯的全面描述,这些证据应该被谨慎对待。
然而,有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罗格·维特洛在《卡桑德拉的女儿们》*卡桑德拉 (Cassandra):希腊女神、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的凶事预言者。中指出,“四十年前,艾德蒙·威尔逊最早指出的负面的‘党的路线’的批评,已经被两代的海明威批评家所接受和重复说下去,包括最近的一些博士论文都提到海明威的女人们。应该消除有关海明威的女人们的许多思想定式。这不仅因为上十年重新考虑‘女性作用’成了时髦,而且因为海明威小说的逻辑和语言本身也需要这样”。(Whitlow 1983: xii)
因此,海明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成了学术界久争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两种对立的批评意见
有些批评家对海明威小说的女性形象提出了种种批评的意见。菲力普·扬指出: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往往像麦康伯太太,是恶毒的、有破坏性的妻子,或像凯瑟琳、玛丽娅、雷娜塔那样的白日梦。杰克逊·班逊说在海明威小说里可以发现姑娘喜欢性活动,而且真诚地能够奉献自己,但“全是淫妇”,具有攻击性的、不像女人的女性。约翰·基林格则认为海明威按照她们卷入一个男人生活的程度,将他的女性分成好女人和坏女人两种。那些头脑简单、参与男主人公活动的、让他们尽可能自由的女性,如印第安姑娘们、玛丽·摩根、凯瑟琳、玛丽娅和雷娜塔,受到富有同情心的处理;那些对男主人公苛求的、限制他们自由、甚至企图占有他们的女性,如玛约里、玛格丽特·麦康伯和达洛思·布里兹斯,成了男人们离开她们就活不下去的女人。巴米拉·法雷则认为在海明威牧歌式的浪漫体裁里,“女人是个挂牌的奴隶,仅仅为增加男人的身份而存在”。(Whitlow 1983: 11)
著名批评家特里宁则从海明威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比较中宣称:海明威笔下的男人都是主导的、有知识的,而女主人公主要都是天真的、具有敏锐情感的。安德烈·毛洛伊认为,“对海明威,像对吉卜宁来说,女人既是一种障碍,又是一种诱惑”。(Whitlow 1983: 12)
李昂·林德洛思将海明威的女性形象分为六类:(一)没有思想的印第安姑娘们。她们对男人没有要求,只是奉献她们的肉体。(二)情人受世界伤害的女性,如凯瑟琳、玛丽娅、雷娜塔、李兹、玛约里、基格等。(三)相对处女型的女性,如海伦、达洛思等,她们并不主动使一个男人堕落,仅伤害其生活。这些女人可能变成麦康伯太太一类的淫妇。(四)偶然的淫妇型女性,如布列特、玛格丽特·麦康伯等。海明威常常对她们的行为做些解释,既不加以指责,又让人们了解造成她们困惑的社会势力。(五)纯粹淫妇型的女性,如艾略特太太、亚当斯太太和《有钱人和没钱人》中的海伦。她们往往使与她们生活的男人完全堕落。(六)“地球之母”型的女性,如彼拉、摩根太太等。她们与生活中的自然因素或突发因素密切相连。(Whitlow 1983: 12-13)虽然这种分类比较琐碎,不太方便操作,但比好女人与坏女人的两分法有了较大的改进,具有借鉴作用。
著名学者菲德勒(Fiedler 1959)坦率地指出海明威的书中没有女人。他认为在海明威早期的小说里,关于性变的描述是有意的残忍,而在他后期的小说里则是无意的喜剧性。
上述观点大体反映了持批评意见的一方。
另一些批评家不同意上述观点,如罗格·维特洛。他认为上述批评家们忽略了大部分海明威女性形象的优点。他们常常只采用男性人物对待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女性的姿态来看待女性,不切实际地将凯瑟琳和玛丽娅当成“被动的玩物”。事实上,她们在两部小说中都参与了严肃的战争,经历了痛苦的磨炼,以顽强的意志从发疯的边缘走回来。玛丽·摩根的丈夫是个暴徒,她以自己炽热的爱给予他力量,两人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批评家盲目赞扬摩根的行为,对她视而不见。至于雷娜塔,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情妇”,而是一个有见地的年轻女子。她用简单的心理分析法,让思想混乱、临近死亡的坎特威尔上校有机会在她面前大发牢骚,宣泄不满,得到心灵上的平静。
那些被贴上“海明威的淫妇”的女性形象也是不幸的。事实上,布列特和海伦都不是淫妇。像凯瑟琳和玛丽娅一样,她们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跟她们两人不一样,布列特和海伦无法从真诚的爱情中获得恢复。跟亨利和乔登不同,杰克自己生理上残疾,没法给她精神和肉体上的满足。而真诚又可爱的海伦却撞上一个自私软弱的丈夫。他不但不懂得珍惜她,而且责怪她的优点使他变坏。
玛格丽特·麦康伯有时候爱争吵,却不是许多人所谴责的“凶手”。她是个比她丈夫和向导威尔逊更诚实的人。她的形象20多年来被歪曲了。《第五纵队》里的达洛思可以说有点给宠坏了,她感觉迟钝,但与评论她的男人菲力普·罗宁斯(那个中央情报局特工似的杀手)相比,她显得比较高尚。
至于海明威短篇小说中一些次要的女性形象,如李兹·柯特斯和尼克的玛约里,也常常受到误读,因为她们的男人和批评家很大程度上看不到她们早期恋爱和性经验的心理创伤。艾略特太太和亚当斯太太被斥为“纯粹的淫妇”,其实很少将她们和她们的丈夫艾略特和亚当斯进行比较。这两个男人不再比他们的妻子受到更多的赞扬,但他们逃过了他们妻子所受到的不间断的指责。连《越野滑雪》中看不见的海伦,也往往被认为她自己故意怀孕,给尼克带来不便,而评论家们不谈尼克在这件事中的作用,更不提怀孕给海伦自己造成更大的不便。
海明威曾说过,他的工作是“用我能说的最好又最简单的方法记下我看到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东西” (Whitlow 1983: 13-15)。在塑造他的女性形象和描述每个形象活动的复杂环境中,实际上他记下了他所知道的和比许多批评家所发现的更多的东西。
威特洛认为海明威作品中的女人们,特别是那些重要的人物,如凯瑟琳、玛丽娅、雷娜塔和摩根太太,往往反对跟她们每人息息相关的男主人公追求死亡的心态。海明威给她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关注人们的愿景和她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肯定。像卡桑德拉一样,她们显然缺乏成功的希望,但她们跟她们的男人们分享愿景,催促他们清除他们生活中的“垃圾”。“她们无望的预言所留下的东西成了‘主要的东西’,即爱情和个人水准上的奉献。在我看来,它像是给予思想上有使命感的文明的成员们的一种神圣的礼物”。(Whitlow 1983: 47)
这些观点大体反映了一些批评家对海明威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肯定,同时为海明威辩解,批评某些人指责海明威女性形象是“淫妇”的论点。
二、对上述批评之批评
尽管海明威发表过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他的著名长短篇小说里都有女性形象。这是不可避免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大千世界由无数男女组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列特、《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娅、《过河入林》中的雷娜塔、《有钱人和没钱人》中的玛丽·摩根以及短篇小说中的麦康伯太太、海伦等,引起批评家的热议是很自然的。
在笔者看来,海明威的女性形象,可分为四类:(一)顺从而真诚的女性,如凯瑟琳和玛丽娅;(二)失落、任性、追求自由的女性,如布列特;(三)善良而刚强的女性,如彼拉;(四)想控制男人的女性,如《伊甸园》中的凯瑟琳(限于篇幅,暂不包括他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这些不同类型的女性反映了海明威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女性意识的变化。
在现实生活中,海明威接触了许多女性。谁影响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在家里,他有母亲格拉斯·海明威、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成人后,他先后与四个女人结婚,即哈德莱·理查逊、葆琳·帕菲弗、玛莎·盖尔虹、玛丽·威尔斯;他的女性朋友和初恋情人,如阿格尼丝·蒙·库罗斯基,后来成了《永别了,武器》女主人公凯瑟琳的原型;达夫·退斯登成了《太阳照常升起》里布列特的原型;简·梅森很像《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里的麦康伯太太;意大利姑娘安德里亚娜·伊凡茨奇则是《过河入林》里雷娜塔的原型。他的母亲常常被指责造成了海明威对女性的偏见和不满。果真如此吗?除了一些例外,海明威似乎不愿意探讨有血有肉的女人们的需要、期望和冲突。他作品中的男人们往往是真实的,获得读者的认可和称赞。他作品中的女人们则常常成了他想象和预测的老一套。(Whitlow 1983: 9-10)
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种类型的凯瑟琳和玛丽娅都是受过战争创伤的女性。两人都对男友忠诚和真挚,但各自的经历和性格是不同的。凯瑟琳是个英国女护士,一次大战中到意大利米兰战地医院服务,亨利受伤后到那个医院疗伤认识了她。她原先的男朋友在战场上牺牲了。这给她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当她和亨利一见钟情时,她心里仍对他半信半疑。亨利认识凯瑟琳时,只感到她年轻美丽,第二次约会时强行拥抱和亲吻她。凯瑟琳并不顺从,而是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记耳光终于让亨利清醒了许多,使他明白对待爱情要真诚,而不是逢场作戏,图自己快活。开篇不久,她与亨利的一段对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噢,亲爱的,”她说,“你会对我好,不是吗?”
我的天呀!我想。我摸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膀。她哭了。
“你会的,不是吗?”她抬头望望我,“因为我们将开始新生活。”
(Hemingway 1929: 27)*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只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
她看着我:“你真的爱我吗?”
“是。”
“你的确说过你爱我,不是吗?”
“是,”我撒谎,“我爱你。”我以前没这么说过。(31)
后来,她对亨利提出要求:两人要以诚相待,不要欺骗对方。
“咱们都别撒谎,不应该撒谎。我有过一点可笑,现在我很好。”(32)
当亨利在米兰医院康复后,凯瑟琳对他说:“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开心。见到你后,我几乎快疯了。也许我疯了。”(120)亨利要返回前线时说:“我以为你是个发疯的姑娘。”凯瑟琳回答说:“我是有点疯。”(160)小说末了,凯瑟琳生小孩前又说:“我刚醒过来,想起第一次见到你时,我是多么快疯了。”(311)
由此可见,凯瑟琳不仅了解她自己脆弱的心理,而且懂得怎样恢复自己的心态。前男友的死给她留下终生的遗憾。身处战争环境也使她害怕死亡。她曾预感到“在雨中死去”。这是很自然的。后来,她从亨利身上找到了爱情和安慰。她是个有思想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她就问亨利:“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为什么到意大利打仗?”亨利说:“我不知道……并不是每件事总有个解释。”(18)第二天,她又问他为什么加入意大利人的战争?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在意大利,我讲意大利语。”(18)不久,亨利考虑是否会被打死的问题。他想,“好啦,我知道我不会被杀死,不会死在这次战争中”(38)。这说明亨利对到意大利参战的目的是迷迷糊糊的,根本没有好好想过。凯瑟琳的提问触动了他,为他往后与战争“单独媾和”打下了基础。
卡波雷托大溃败中,亨利差点被意大利警察杀死。他急中生智,跳河逃生,连夜赶往米兰找凯瑟琳。凯瑟琳同意他与战争“单独媾和”,与他一起乘小船逃亡中立国瑞士。她与亨利同心同德,历尽艰辛,胜利逃脱意大利警方的追捕,获得了可贵的自由。两人在瑞士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凯瑟琳最后不幸死于难产,但她不是一个淫妇或顺从的女人,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女性。
由此可见,亨利的爱情抚平了凯瑟琳的心理创伤,激起了她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她给亨利的真诚的爱情和启导,使他对非正义战争的认识逐渐清楚,最后与战争“单独媾和”,回到温馨的爱情生活,但纯真的凯瑟琳没有能逃过死亡的命运。她的死摧毁了亨利的梦想,也成了对一场非正义战争的控诉。
玛丽娅的身世与凯瑟琳不一样。她是个活泼可爱的西班牙姑娘。她的父母在西班牙内战中惨遭法西斯叛军杀害。她遭到蹂躏,并被剃光了头发,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后来,她被游击队所救,随他们回到山区驻地,得到游击队长巴布洛的太太彼拉的关照。她曾想死,后来精神渐渐恢复正常。彼拉告诉她,要是爱上一个人,就能把过去的全抹掉。男主人公、美国大学讲师乔登到达山区游击队驻地后,玛丽娅与他一见钟情,相亲相爱,后来同居。玛丽娅抚平了创伤,燃起生活的勇气,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她全心全意地爱上乔登,想永远做他的女人。她对他说,“如果我做你的女人,我一定用所有的方法让你开心。”又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完全成了一个人”,“可我们现在要变成一个人,永远不会再分开了……你不在身边时,我也就是你。啊,我多么爱你,我一定要好好疼你。”(海明威 1997: 328)(作者注:个别词略有改动) 她对乔登的“顺从”实际上是一种爱情上的真诚。当彼拉问乔登是否关照玛丽娅时,他说是的。乔登接受了国际纵队高尔兹将军的命令,负责组织山区游击队炸毁一座桥,以配合对叛军的打击。他认真执行这个使命,曾与老猎手安索尔莫到现场视察地形。后来,他发现敌方似乎已知道政府军的进攻计划,一面派人到司令部送信,一面继续准备炸桥。玛丽娅支持他的工作。乔登同情她的遭遇,两人真心相爱。最后,炸桥后遭遇敌人反击,乔登受了伤,掩护游击队员撤退;玛丽娅痛哭流涕,被彼拉拉回去。乔登英勇牺牲,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生命。
有些评论指责乔登空谈爱情与婚姻,没有回报玛丽娅的爱情;有的则妄评乔登的使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因此,他们将玛丽娅贬为“变态人物”、“一种象征”、“没有思想的被动的女人”、“乏味而顺从的女性”等等。这些都是误导读者的谬论。
第二种类型的布列特·阿斯莱是个奇特的女性。批评家常常指责她是个“淫妇”、“妖女”、“没有女性的人”、“强制性冲动的淫妇”等。这些都是脱离文本的评论。
不错,小说中布列特离开西班牙斗牛士罗慕洛后曾对杰克说过,“你知道决定不当个淫妇,令人感到好些”(海明威 1995: 245)。批评家们经常引用这句话,断定布列特是个淫妇,似乎这是她自己承认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它仅从一般的道德观来判断,没有从历史语境来进行客观的评析。
事实上,布列特也是第一次大战的受害者。作为一个英国姑娘,战时她当过志愿救护队的护士。她的第一个未婚夫死在战火中。她的心灵创伤是不言而喻的。她的第二个夫君也不好,正在闹离婚。她的第三个未婚夫麦克·康贝尔对她没有感情,她也不爱他。她对杰克十分钟情,杰克战时在住院时认识了她。但杰克因战争造成生理上的缺陷,无法娶她。这使她痛苦万分,不能像凯瑟琳和玛丽娅那样,找到爱情的归宿,抚平心灵创伤。她成了20年代游荡在巴黎、马德里等地的“迷惘的一代”的一员。
“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战后,许多经历过大战的英美青年感到失落和迷惘,不知今后的路在何方。他们滞留在巴黎和马德里等地。欧洲社会受到战争的冲击,旧的传统观念处于瓦解状态,有点混乱。现代主义悄然而至。青年人追求新时尚。女青年理男发,穿超短裙,戴蛤蟆镜,随意进出咖啡厅、夜总会和酒吧。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比以往松散多了。“一夜情”的出现并不奇怪。有的女孩变得很放荡,追求个性解放。《太阳照常升起》对“迷惘的一代”的描述就是当时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
处于上述语境下的布列特的确思想有点乱。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想寻找真爱,医治她的心灵创伤。但周围的男人,除了杰克以外,她都不满意。她在美国青年柯恩的诱惑和追求下曾经跟了他几天。她一度看上了比她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罗慕洛,与他同住了几天,后来离开了他。最后,她无可奈何,想与未婚夫康贝尔重归于好。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布列特有些放荡。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分析,这又不是太奇怪的事。可以说这是女青年生活道路上的一个挫折。
布列特是个追求时尚的漂亮姑娘。从小说开篇,人们就发现她很有诱惑力。杰克说,“布列特太好看了。她穿着一件针织紧身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呢裙子,头发往后梳,像个男孩子。她开创这种打扮。她的身段的曲线,如同赛艇的外壳。那羊毛套衫使她的整个体型毕露无遗。”又说,“布列特是她自己的名字。她是个好姑娘。”柯恩回答说,“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他认为布列特有良好的教养,“绝对优雅又很正直”。比尔·戈登说她是个美女,“她太好了!”麦克·康贝尔说她是个“可爱的人儿!”(24-43)(作者注:个别词有所改动)总之,在那群人中,布列特魅力四射,和蔼可亲,处处受欢迎。她美丽、性感、聪明伶俐,又任性、大方、有主见。柯恩骂她“把男人变成猪”,其实她并不迁就男人,做男人的附庸。她反复告诉杰克她与别的男人的艳事,一点也不掩饰。她有时以酒浇愁,不能自制,难以排除内心的苦闷。这种苦闷带有战争创伤留下的烙印。
不仅如此,布列特有时成了那一群人的中心。诚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她还有母亲般的作用,这是她的另一方面。如麦克·康贝尔看到柯恩老跟着布列特转悠,有点吃醋,想揍柯恩,她就加以劝阻。她对麦克说,“闭嘴!麦克,要有点教养!”(156-157)柯恩是个自私傲慢的蠢驴,处处纠缠布列特。她不客气地告诉他,“看在上帝份上,走开吧!你没看到我和杰克要交谈吗?”(156-157)柯恩跟麦克一样,不得不听她指挥。那一群人谈论她与一些男人的关系,布列特批评他们,“谈这些事无聊透了”。(156-157)由此可见,布列特不愿受男人支配,也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她拥有与男人平等相处、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
有人说布列特是个女色情狂,千方百计折磨杰克,其实不然。小说开篇不久,他俩在出租车里亲吻,接着她转身伏在座位的一角,离他尽量远些。她说,“别碰我……请别碰我!”(28)后来在旅店里,杰克问她,“我们不能住一起吗?”她回答,“我看不行。我会见人就搞关系,对你不忠实。你会受不了的”。(62)不久,她在咖啡馆里对杰克说,“我太可怜了!”又说,“晚安,亲爱的,我不能跟你再见了”。(73)其实,她渐渐爱上杰克,信任杰克,将柯恩写给她的情书都交给杰克,但他不想看。末了,他俩又紧紧偎依着坐在一辆出租车里,布列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有这么多好时光该多好!”(270)由此可见,布列特与杰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布列特并非那么轻浮、下贱、庸俗,也不会一见个男人就扑进他的怀里。海明威这么写符合真实的生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布列特是一次大战后受冲击的欧洲社会的产物。她身上既留下战争的创伤,又接受了冲破旧传统的一些新思想。她要求保留自己的名字,在现实中占有女性的一席。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个爵士乐时代的新女性。
第三类是母亲型的女性。彼拉是个突出的代表。她是西班牙山区游击队长巴布洛的妻子,她会卜算凶善。她爱国爱家,痛恨法西斯叛军的暴行,多次勇敢参加了游击队的战斗,曾在一次袭击中拯救了双亲被杀的少女玛丽娅。她对她关怀备至,亲如手足,迅速温暖了玛丽娅的心。当美国青年乔登到山区游击队驻地时,她热情接待,鼎力支持,多次批评她丈夫巴布洛自私脱离游击队的行为。她以大局为重,说服丈夫回归游击队,参加炸桥行动。她关照每个游击队员,受到他们的尊重,成了实际上的游击队长。她支持乔登与玛丽娅的恋爱,叮嘱乔登要好好关照玛丽娅。她是个深明大义的西班牙劳动妇女的光辉形象,又是西班牙山区游击队员的母亲。她勤劳朴实,无私无畏,爱队如家,待所有游击队员如亲人,待乔登如亲兄弟,全力帮助他完成炸桥任务。乔登牺牲后,她又抚慰玛丽娅,期盼未来的新生活。她是海明威笔下最成功的一个妇女形象,也是当代美国文学中难得的一个完美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可惜,许多批评家对她视而不见,总是津津乐道那些“淫妇”、“魔女”和“驯服女郎”。也许这种情况也要改一改。
第四种类型是女性意识十足,一心想控制男人的女性。《伊甸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便是突出的代表。她追求时尚,改男名,理男发,俨然一副女权主义的派头。她要求丈夫戴维改用她的姓名,听她安排。戴维是个青年作家,一心想婚后继续写作。凯瑟琳只想及时行乐。后来,他们在一个旅游胜地认识了一位外国姑娘玛丽塔。凯瑟琳邀她与戴维一起去海边游泳,留她住在他们住的旅店隔壁房间,多次激励丈夫与玛丽塔上床,后来成了三人的性爱游戏。没料到,玛丽塔支持戴维将以前的非洲之行写下来,凯瑟琳顿生嫉妒,偷偷地将戴维的手稿烧掉,然后逃走。临逃时她留下一封信给戴维,她说她会回来的,不想了结此生,同时承认她一向唐突无礼,自行其是,近乎不近人情。但她仍爱他。
凯瑟琳走后,戴维正式与玛丽塔同居。在玛丽塔精心关照下,他将一个短篇小说完整地重写出来。他和玛丽塔过着温馨而甜蜜的伊甸园般的生活,顺利地继续写作。
据说,海明威于1946年和1947年写《伊甸园》,1958年进行修改。1961年他去世时来不及定稿出版。50年代末60年代初,女权主义逐渐兴起,海明威是否意识到这种社会变化,还不清楚。但他笔下的凯瑟琳的形象与他以前塑造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不同。她个性倔强、任性、古怪、支配欲很强,想当一家之主,让丈夫听她使唤。在现实生活中,她搞同性恋和多角恋爱,最后自食其果,背离了丈夫,走出了家庭。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海明威长篇小说里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单调的“老一套”。她们有很大变化。从第一类到第四类,她们大体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欧美女性形象的变化,揭示了海明威女性意识的发展。总的看来,海明威并没有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崇拜男性权威,片面地突出男子汉气概,恶意地轻视女性。相反地,尽管他是个富有男性刚强性格的硬汉子,但他能克服个人偏见和生活中的问题,用双性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塑造女性形象,揭示不同时期女性的感受和内心冲突。他不愧是个敏锐而机智的艺术家。
三、海明威的“秘密缪斯”:双性转化论
1981年和1983年,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林恩相继在《论坛》发表论文,对很有影响的菲力普·扬的“创伤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支配海明威小说的不是“创伤论”,而是男子女性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海明威一生内心不得安宁, 一直无法处理好男女主人公的优缺点,喜欢描写男性特征明显的人物,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则缺乏力度。1987年,林恩在《海明威传》里又贯穿了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热烈争论。Androgyny(男子女性化)一词一度成了报刊上海明威研究的关键词。
1990年,美国批评家马克·斯皮尔卡出版了《海明威与男子女性化的争论》,受到广泛的重视。作者支持林恩的意见,认为海明威一生都在进行男女情人或配偶性别转换的试验。“男女之间具有相同优点的问题是他从来无法回答自己的一个问题。”(Spilka 1990: 2)事实上,海明威对男子女性化问题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他一生钟爱表现男性的英雄主义和兴趣爱好,比如斗牛、深海捕鱼、当兵打仗、拳击、非洲狩猎等,但他在小说中还是流露出男子女性化问题。比如,《太阳照常升起》描写了男性化的布列特和非男性化的巴勒斯。两人因巴勒斯一次大战中性器官受伤而无法成婚。布列特理了男式短发,行为举止像个男孩,让她周围的男人不知所措。在《永别了,武器》里,海明威写了亨利和凯瑟琳的浪漫爱情,最后无果而终。凯瑟琳离他死去,亨利无法继续战后的温馨生活。他不得不面对眼前的一切,只好怪罪于命运和外在原因。在《伊甸园》里,女主人公凯瑟琳则理男发,改男性姓名,搞同性恋。她的丈夫、青年作家戴维逆来顺受,接受她的安排。海明威男子女性化的困境依然没有改变。此书写于1946年,完成于1958年夏秋,大体反映了海明威后期对女性看法的改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男子女性化问题则更加明显和突出。
马克·斯皮尔卡还分析了海明威男子女性化问题的原因:一是海明威小时候受到他母亲在家里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父亲倡导室外运动的教诲,他母亲不断地培养儿子基督教式的文雅。二是海明威在中学阶段读了许多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和20世纪初乔伊斯、伍尔夫和劳伦斯的作品,滋生了比较温和的感情。当时学校里主要讲授英国文学,而不是美国文学。英国作家勃朗特、吉卜宁和梅斯菲尔德以及马克·吐温对海明威的成年有较深的影响。海明威渐渐地养成温文尔雅的基督教男人气概,同时也逐渐隐入他想象中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世界。后来,他的姐姐和妹妹的温柔的女性感情又影响了他。三是海明威后来的经历,尤其是20年代在巴黎时葆琳介入他与哈德莱的家庭生活,形成了“三角恋情”。这有点像《伊甸园》里的三角恋。起先是葆琳的步步进逼,海明威被动接受,到最后放弃妻儿,与葆琳重组家庭。离婚后,海明威还痛骂自己背叛了初衷。其实,他与葆琳的结合揭示了他自己就是个男子女性化的人物。
马克·斯皮尔卡认为林恩的《海明威传》似乎对海明威的内心困惑的根源和重复出现做了良好的评述,并称这种内心困惑为“男子女性化之伤”。他认为林恩只将这种内心困惑当成海明威童年时代的心理怪象,而且过多地责难海明威的母亲,观点比较狭隘。应该从文化的广阔视角来公正地看待海明威与他的双亲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他们对海明威性格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影响。(Spilka 1990: 13)
有人指出,海明威的男子女性化问题主要与他母亲早年的关照有关。他母亲个性强,事事爱做主,他父亲往往忍让,听她的。尤其是海明威3岁前,他母亲一直让他穿连衣裙,与他姐姐成了一对“孪生姐妹”。“他留着与姐姐一样的发型,穿着一样颜色的衣服……母亲要求他俩心里要有‘孪生姐妹’的感觉,安排他俩晚上同睡一张床,白天玩一样的娃娃。”(杨仁敬 1996: 6)海明威从小脾气温顺,倒有点像女孩子。他平时从来不乱闹。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笔者在访问海明威橡树园故居时,一位讲解员对笔者说:给自己年幼的子女穿上同样的女装在当时橡树园是很普遍的。它不是海明威母亲的独创。既然如此,它为什么会成为海明威的心结而影响他毕生的生活和创作呢?显然,以此为论据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其实,男子女性化的问题和基督教有关。在《圣经·创世记》第一章中,一个男子女性化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另一个版本是在《创世记》里,两性的亚当从他身上产生了夏娃。Androgyny一词来自希腊文,它由Andro(男)和gyny(女)组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酒会》里创造了第三个版本。书中说人的性别原先与现在是不同的。性别现在分为男女两种,原先有3种,即男性、女性和双性,据说古代曾存在过双性,现在消失了。今天,Androgyny这个词带有侮辱的意思。不过,英国18世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在《桌边谈话》(1832)里提到Androgyny的概念。他认为伟大的思想必须是双性的。现代英国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则在长篇小说《奥兰多》里塑造了一个双性的人物形象。她在《一个人自己的房间》最后一章里又提到双性的概念。这说明她也喜欢这个概念。可见,Androgyny已有了正面的意义,人应该走出性别的牢笼,反映各种性别的形式,进入一个个人行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世界。
1989年,林恩在《海明威传》里运用心理分析法,以海明威的“男子女性化”和“性别混乱”为切入点,解读了海明威的生活和创作,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从根本上揭露了菲力普·扬“创伤论”的弊病,批评了艾德蒙·威尔逊和马尔科姆·考利关于《大二心河》里尼克从战争创伤中康复的论证。从此,称霸美国海明威研究舞台几十年的“创伤论”和“准则英雄论”宣告消失。“男子女性化理论”取而代之,影响日益兴盛。
虽然马克·斯皮尔卡的专著《海明威与男子女性化的争论》从文学文化的语境出发,以男子女性化为中心,多角度地解读了海明威的小说,颇有新意,而且,他的评析获得苏珊·比格等学者的称赞。但唐纳德·江肯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斯皮尔卡尽管在书中用了20多次androgynous这个形容词,但根本没有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他将海明威艺术创作的人物形象与海明威本人混为一谈,混淆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很难令人信服(Junkins 1994: 59)。笔者认为江肯斯的质疑是有道理的。马克·斯皮尔卡支持林恩的观点是好的,但在评释中往往从海明威的生活经历中考证他人物描写的证据,多处混淆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有些地方沿用了“创伤论”的老方法,虽然有的章节写得不错,颇有参考价值。1994年,罗伯特·斯科尔斯和南茜·R·康姆雷合著的《海明威的性别:重读海明威的文本》进一步探讨海明威小说文本中的性别差异和转换。两位作者在书中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以海明威作品的文本和生活经历为中心,联系海明威成长过程中其他文化因素,探讨了他作品文本中复杂的性别和性欲问题,指出海明威的性别意识早已有之。(Comley & Scholes 1994: 46-47)生活中流传他的“爸爸”神话,他早期作品的语境则没有“爸爸”的刚性。他的文本的重要部分具有强烈的感情,但在“爸爸”的面具下可以看出一个男孩对父亲的反抗。海明威写了一个男孩在没有父爱的情况下如何成熟。他不想成为他父亲一样的父亲,最后成了一个“反爸爸”。
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具有不同的类型。他塑造最成功的女性往往是他几类女性基本类型特点的综合或被称为男性代码的女性。他所刻画的3个女强人形象是布列特、彼拉和凯瑟琳·布尔纳。海明威在早期和后期作品中对同性恋、性别变化和种族通婚很感兴趣。在《伊甸园》手稿里,这达到了高峰。他还写了西班牙斗牛士中的同性恋和情欲。
两位作者认为性别差异体系有一部分是生物性的,一部分是文化性的。它以人类基本性别——男性和女性——为基础,逐渐扩展到文化方面多种因素。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两位作者高度重视《丧钟为谁而鸣》中彼拉形象的塑造。他们没有采用“雌雄同体”一词,却细致分析了彼拉形象具有女性和男性的双性特征。他们认为布列特、彼拉和凯瑟琳·布尔纳都具有双性特征,以彼拉最为突出。彼拉是以格特鲁德·斯坦因为原型塑造的。她是母亲型和培育型加上男性同性恋的混合物。她的魅力来自双性。(Comley & Scholes 1994: 46-47)她说过, “ 我会做个好男人,但我毕竟是个女人,丑得很。”(海明威 1997: 97)。她的外貌魁梧高大,像她丈夫巴布洛那么强壮,但比他勇敢,比他进步。她酷似斯坦因。两人都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和农妇般强壮的体魄。两人都被认为是性别模糊的人物。在她俩身上可以找到男性的强壮和女性温柔的混合。海明威将她们两个女性不仅当成不同性别的范例,而且作为这些性别差异的老师。
从以上不难看出:“双性转化论”日益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海明威的性别》一书从海明威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出发,结合他的家庭背景、他和母亲的关系、他和四任妻子的分分合合等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海明威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同类型及其特色,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它标志着这场关于“双性转化论”争论的新发展。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从美国学术界的争论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尽管海明威崇拜男子汉英雄气概,塑造了激励人们向上的硬汉子形象,但他仍然超越尘俗,用双性的视角去描述他所了解的人与事,客观地揭示女性的情感,刻画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双性转化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秘密缪斯”。
Comley, N. R. & R. Scholes. 1994.Hemingway’sGenders:RereadingtheHemingwayText[M].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edler, L. 1959.LoveandDeathintheAmericanNovels[M]. New York: Stein and Day.
Hemingway, E. 1929.AFarewelltoArms[M]. New York: Scribners.
Junkins, D. 1994. Mythmaking, androgyny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 answering Mark Apilka[A]. K. Rosen (ed. ).HemingwayRepossessed[M]. Westport: Praeger. 59-61.
Kert, B. 1983.TheHemingwayWomen[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Spilka, M. 1990.Hemingway’sQuarrelwithAndrogyny[M]. Lincoln/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Whitlow,R. 1983.Cassandra’sDaughters:TheWomeninHemingway[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海明威. 1995.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海明威. 1997. 丧钟为谁而鸣[M]. 程中瑞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杨仁敬. 1996. 海明威传[M]. 台北: 业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