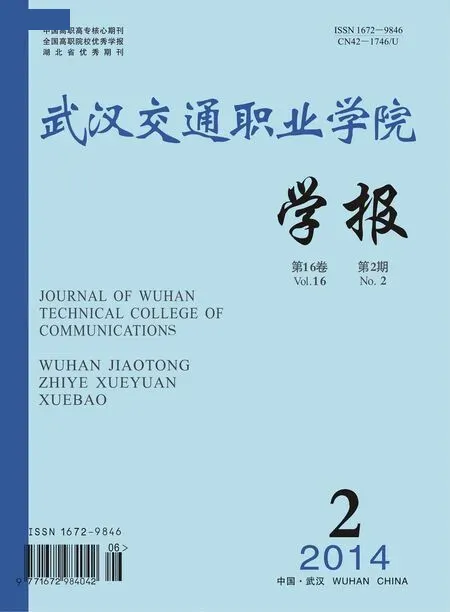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伦理观的批判*
潘峻岭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伦理学是研究人与人关系的学问,这门学问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评判人们行为的善恶是非,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追问人生意义和价值。费尔巴哈的伦理道德思想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其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受制于感性直观的方法论,最终导致唯心主义伦理观。马克思伦理道德观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曾经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和观念的影响,包括基督教神学伦理思想、康德与黑格尔等的伦理道德思想。尽管在恩格斯眼中,费尔巴哈的伦理思想极其贫乏,但不应据此将费尔巴哈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排除在马克思伦理学研究之外。
一、费尔巴哈伦理道德思想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人是基督教之上帝,人本学是基督教神学之秘密。”[1]他的一生都在探寻如何从神下降到人,如何抛弃彼世世界的虚幻期待而实现人在世俗世界的幸福生活。
(一)费尔巴哈伦理思想鲜明的反宗教特色
所有超自然主义的道德,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排斥人,排除幸福,排除“一般的利己主义”。这种超自然的神学伦理大都崇尚神性,否定人性。因为人奉献给神越多,留给自己的就越少。费尔巴哈认为旧宗教的核心是上帝,上帝是人崇拜和景仰的对象。旧宗教的目的就是指引人们以全知全能的上帝为榜样,向上帝学习,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上帝。这样,人逐渐脱离他的现实基础,世俗的人逐步发生异化,转变成一个“抽象的”“属天的”存在者。在这种情形下,宗教的本质只有通过道德才能反映和显现出来。只有道德才能判断一种宗教信仰的真伪。因为,对于超自然的上帝,只有“当他导致一种超乎人的、超乎自然的或不如说违背自然的道德时,才是一个真理。”[2]即人愈远离人,愈超越自然,人愈具有神性和真理性。对德国道德学家来说,亦是如此。道德学家们愈是夸大其词,愈是使用“夸张的”“超验的”“超自然的”的概念,愈能显示其高明与不凡。他们把“那种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利己主义或哪怕暗示一点点利己主义——纵然这种利己主义是健康的、与本性相协调的、必需的、与人生一致的、不可避免的利己主义——的道德,也看为是对于圣洁处女的玷辱、污辱和耻辱。”[3]而费尔巴哈的新宗教与此相反,“新教并没有超自然主义的道德,它只有属人的道德,这种道德,来自血肉,并且为了血肉;从而,新教的上帝,它的真正的、实在的上帝,至少不再是什么抽象的、超自然主义的存在者,而是由血和肉组成的存在者。”[4]新教的上帝是真正的、现实的、自然的人。可见,费尔巴哈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强调道德是属人的道德,人是道德的尺度,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即人的一种健康、快乐的生活状态。他认为基督教神学从道德中取消属人的幸福是伪善的,不人道的。没有人道的、幸福的道德实际上抹去了道德的实际内容,是虚无的道德。世间的恶德与罪过就是对人性扼制与扭曲。而世界上最大的恶德,就是假仁假义、伪善的教会道德。那种不灭的、永生的个性对人来说,是虚妄的、毫无价值的。因此,他的新宗教追求的不是不灭的个性,而是“能干的”“身心健康”的人。在他的伦理价值中,健康远比永生更有价值。为了表明自己反对伪善的神学伦理学家的态度,费尔巴哈特别使用“利己主义”这一名词代替中性词“自爱”,明确指出只有“利己主义”的道德才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才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真正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在反禁欲主义的宗教伦理的斗争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伦理思想有历史进步意义。
(二)费尔巴哈伦理道德的自然基础
感性直观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方法。通过感性直观的中介和纽带,费尔巴哈将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勾连起来,初步地贯彻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费尔巴哈哲学感性直观的方法以人的感觉为基础,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的伦理思想中。
首先,费尔巴哈伦理思想以人的感觉为基础。“如果没有感觉,那就不会有苦恼、痛苦、疾病、不安乐,不会有贫困和悲哀,不会有不足和需要,不会有饥饿和口渴,简而言之,不会有不幸福,不会有祸害。”[5]离开了感觉,人就无法体验喜乐苦痛,亦无所谓幸福与否。他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只欢迎对他有利、有益、有好处的东西。外在事物要与他的感觉相适应而不与之相抵触,这样才能促进和发展他的生命力。“没有快乐感和不快乐感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善与恶的区别。感觉的呼声是第一重要的绝对命令……对于脱离一切感觉的纯粹理性说来,既不存在神与恶魔,也不存在善与恶;只有立足于感觉并为感觉服务的理性,才能做这种区别,并遵守这种区别。”[6]人的幸福与否、善恶区别以是否快乐的感官体验为标准。费尔巴哈将这种快乐的感觉称为最重要的“绝对命令”,它是道德的基础,是第一重要的东西。没有快乐的感觉便没有善恶的区别。
其次,费尔巴哈伦理学以满足和维持人的生存为前提。人的生命存在是人生幸福的首要和基本条件,费尔巴哈伦理思想紧紧抓住了与人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健康的关系。“幸福不只以我个人为转移,幸福的到来不能不有我的参加和我的独立行为,同样地,遵守道德不只是以我的随意的活动为转移,而且也依外界的物质、自然界和身体的状况为转移。”[7]对于神学道德学家们提出的“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的观点,费尔巴哈针锋相对,提出“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道德规范和行为需要经济和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条件取得幸福,那就缺乏条件维持德行。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8]在论证这一观点时,费尔巴哈甚至还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论据予以证明。他明确指出生活的基础同时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如果连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都无法保障,道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一切有生命和爱的生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一切呼吸着的和不以‘绝对漠不关心的态度’吸进碳气和氮气而不吸进氧气、吸进致死空气而不吸进新鲜空气的生物的基本的和原始的追求。”[9]对幸福的追求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存在物的一种天生的、本能的和原始的追求。
再次,费尔巴哈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费尔巴哈特别强调人的身心健康对人生幸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身心健康是实现人的幸福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对于人,乃至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来说,“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某一生物的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它的十分强健的或安乐的状态;在这一种状态下,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和实际上满足为它本身所特别具有的、并关系到它的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10]他认为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就有爱,即使是只爱自己和自己生命的自私自利的爱。一切生命都希望活着、希望生活、希望存在,而活着、生活、存在的目标是健康和幸福。因此,对于一切有生命、有感觉、有愿望的生物来说,只有幸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此外,身心的健康不仅是生物追求快乐的基础,而且具有生物学上的重要意义,即身心健康的生命状态是保存和延续自己种群的基础和保障。“人自然只想到自己的快乐,只想满足自己的追求,但自然界所追求的目的只是在于保存和延续类或种。”[11]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对费尔巴哈“合理利己主义”观点讨论得较多,并引证了很多论据,如费尔巴哈提出要开诚布公地承认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不仅是伦理道德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道德的基本构成中处于“极尊贵”的地位。认为人性对幸福的追求不是“单方的”“排他的”,而是“双方的”“相互的”对幸福的共同追求。评价好人的标准是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只有对别人像“待自己一样好”的人才是好人。
但若进一步分析,无论是费尔巴哈合理利己主义、富于同情心的利己主义,还是善的利己主义,其实质都是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伦理思想。费尔巴哈合理利己主义强调个人在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要兼顾他人的利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利己主义、完全的自私自利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实现的。即使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生活中亦是如此,家庭成员的自私自利无法维持家庭的团结与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弟兄们的拳头和他的姊妹们的撕扭将教训他应该遵守怎样的风俗习惯,教训他别人对于幸福的追求也和他自己的一样是有其充分权利的,加之他们还可使他确信,他自己的幸福是与他的亲人们的幸福最密切地相互交错在一起的”,[12]绝对利己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自身现实利益的丧失。这也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观察的生活经验。只有节制自己的利益,兼顾他人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中,侵犯或剥夺别人的幸福权利,妨碍或阻止别人享受快乐都是不道德的行为,包括对他人追求幸福权利的否定、对他人不幸的无动于衷,甚至他人的不幸给我们自身幸福造成的损害,都是不道德的。只有对他人幸福的关心、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并与他们同甘共苦才是真正的道德。
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伦理道德思想的批判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13]但仔细分析,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除了在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上一致外,无论前进还是后退,两者都有根本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伦理观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
(一)对费尔巴哈感性伦理道德的批判
伦理道德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而费尔巴哈哲学感性直观的方法对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常常束手无策。因此,只要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唯心主义尾巴就露出来了。费尔巴哈认为一切和感性相矛盾的哲学、宗教和制度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如果想要改善人们的生活,就必须使他们幸福,而一切幸福和欢乐的源泉都在感官那里。宗教神学否定感官,是造成人类一切堕落、仇恨和病态生活的根源。人类无论是生理的、精神的健康都源于对感官的肯定。对感官享受的剥夺,总和那些消极否定的特质结合在一起,比如困苦、克己、否定、忧郁、阴沉、龌龊、淫荡、畏缩、吝啬、嫉妒、奸诈、凶残等等,而感官的满足则和快活、勇敢、豪侠、坦率、直爽、富于同情心、自由、善良这些积极肯定的特质相联系。费尔巴哈伦理道德的自然主义倾向以人的感觉和自然属性为基础,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感性,相对于神学伦理的虚幻性和精神性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亦不能否认,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伦理道德的社会性,如他认为道德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只有把人对人的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我对你的关系加以考察时,才谈得上道德;只有把对自己的义务认为是对他人的直接义务,只有承认我对于自己有义务只因为我对他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乡村、对我的民族、对我的祖国)有义务时,对自己的义务才具有道德的意义和价值。”[14]如果不涉及社会关系,就无所谓道德了,“被思考为自身独立存在的个人的道德是毫无内容的虚构。在我之外没有任何你,亦即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是谈不上什么道德的;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15]但是,其伦理思想基本的直观自然主义性质是确定的、不可否认的。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和动物一样,都有男女雌雄的性别差异,但人的性别差异更“人性化”“高尚化”“精神化”。性的关系直接决定着人类种群的延续。没有男人和女人,人类就无法繁衍下去。因此,他把性关系看作是基本的道德关系。“也和为了人的肉体的来源必须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一样……为了精神上的来源、为了道德的发生至少也必须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加之,性关系可以直接地看为是基本的道德关系,看为是道德的基础。”[16]按照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方法,层层剥去人与人的表面联系,人类社会剩下的就只是男人和女人。可见,费尔巴哈伦理学实质上就是从具有人的生物特征的实在的人出发的。这种人只是理论中的抽象的人,不是现实的、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的人。离开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人要么只剩下自然属性,要么便羽化为神,空有一副人的躯壳。这就是费尔巴哈为什么特别注重和强调性的关系,为什么在他的宗教哲学里,反复强调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和关系问题,根源就在于其伦理道德思想的直观性。
恩格斯曾将费尔巴哈伦理学与黑格尔伦理学作过比较,认为黑格尔伦理学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现出了实在论的内容,道德、法、经济和政治等都被囊括在内了。费尔巴哈伦理学则相反,形式是唯物主义的实在论,内容却是唯心主义的。恩格斯将费尔巴哈伦理道德基本原则概括为两点,一是“自我节制”,二是“对人以爱”。这种抽象的伦理思想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倾向和感性直观的方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不仅仅是众多具有相同类属性的人的共同生活,最根本性的特征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劳动,并在这种共同活动中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共同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因此,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单个人的个体活动,如劳动、饮食、交往等,背后都表征和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总是社会的人,“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费尔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17]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从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提出了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重属性。人的两重性决定了人的伦理道德的两重性。和将幸福要么理解为快乐,要么理解为德性的传统观点不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从人的两重性出发理解幸福。按这一思路,有学者提出幸福就是“人由生存需要得到适度的满足、发展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不断追求进一步满足所产生的对人生总体上感到满意的愉悦状态。”[18]这里所说的生存需要是维持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主要涉及到人的自然属性;发展需要是在生存需要基础上不断追求进一步满足的需要,涉及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而实现幸福的环境和条件包括社会、家庭、职业和素质四个方面,主要涉及人的社会属性。可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属性,是科学的、现实的伦理观。它将幸福看作是历史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
(二)对费尔巴哈抽象伦理道德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伦理学的肤浅还表现在对善恶范畴的理解上。黑格尔将恶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但费尔巴哈伦理学没有涉及到恶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领域。他只把恶当做纯粹的利己主义,认为只有爱才是善。“爱吧,但是要真正地爱!——这样,一切其他的德行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归于你了。”[19]在费尔巴哈那里,爱就是神,就是上帝,它随时随地都可以创造奇迹,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这种永恒不变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爱深刻反映出了费尔巴哈伦理道德的抽象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看起来具有无限的适用性,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阶级,但在现实世界里,爱无论何时何地都毫不适用,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道德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范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级,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其道德。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在这个相互分裂的、利益对立的阶级社会里,则表现在战争、冲突、纠纷,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中。
客观评价,应该说,费尔巴哈伦理学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阶级问题,意识到了不同阶级的存在。“遵守德行的人受饥饿,而无赖汉则过度地享受物质上的幸福。”[20]自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两次引用到费尔巴哈所说的“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这句话便成了名言。国内学界也常常将这句话引作费尔巴哈哲学阶级对立思想的证据,认为住在皇宫里的人代表统治阶级,住在茅屋里的人代表被统治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两个阶级的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对这句话的理解应结合费尔巴哈整个思想体系以及说这句话的上下文语境,不能主观臆断、人为拔高。费尔巴哈原文中是这样表述的:
人脑和猿脑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人与猿的头盖和颜面该有多么不同!猿所缺乏的根本不是思维的内部诸条件,不是脑;它所缺乏的只是思维的适当的外部关系。只归咎于颜面角偏斜,位置配置不利,所以它的脑没发展为思维器官。皇宫中的人所想的,与茅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茅屋的低矮的天棚好像在压迫着我们的脑。我们在户外和在室内判若两人;狭窄的地方压迫着心和头,宽阔的地方舒展它们。哪里没有表现才能机会的地方,哪里便没有才能;哪里没有活动的广阔空间,哪里便没有对活动的渴望,至少没有真正对活动的渴望。空间是生命和精神的基本条件。[21]
由以上文字可见,费尔巴哈是从对人脑与猿脑的差别比较,延伸到了住在皇宫中的人与只在茅屋中的人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直观的、肤浅的空间上的区别。皇宫高大宏伟,住在里面的人舒展开放,茅屋面积狭小、顶棚低矮,压抑人的心灵和头脑,两者根本没有上升到阶级差别的高度。而且恩格斯讲得亦很清楚,费尔巴哈这些话看起来意蕴深远,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些命题的深刻意义,亦不知道用这些命题去干什么。费尔巴哈哲学中间或出现的类似命题,还有“如果由于饥饿由于贫穷你腹内空空,那末不问在你的头脑中、在你的心中或在你的感觉中就不会有道德的基础和资料。”[22]等等。但是,不管他主观意愿如何,费尔巴哈实际地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对此,恩格斯进行了深刻剖析。费尔巴哈所谓的“绝对幸福”“平等权利”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从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到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从来只有奴隶主和领主的幸福,没有奴隶和农奴的权利。统治阶级的幸福从来都是建立在被压迫阶级被压迫、被统治、被奴役的痛苦之上,而且是依法合规的。只不过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在古代和中世纪,被统治阶级连这种幸福权利的名分都没有。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和迷惑性就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被表面上承认一切人的平等权利掩盖着。“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23]现实却是,工人阶级被盘剥后所得到的物质生活资料远比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少,以至于并不比奴隶制或农奴制下奴隶和农奴所得到的多一些。
至于资本主义的证券交易所,按照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的道德论原则,简直就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殿堂了。人们为了追逐幸福而经营证券投机,而且又正确估量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人们既感到愉快又不引起任何损失,亦未妨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人们达成投机交易时,皆是按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的。赔了钱的人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只要“爱不纯粹是温情的空话,交易所也是由爱统治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做的事情,爱也在这里得到实现。”[24]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伦理道德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费尔巴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的。“爱还非常幽默地把我们的高贵的贵族同布衣小民同一起来。”[25]他竭力以抽象的、超阶级的、善于创造奇迹的“爱”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费尔巴哈找不到从抽象王国通往现实世界道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他被迫脱离当时德国社会的孤寂的乡村生活,而在于他哲学的出发点。他不理解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不懂得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更不用说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其伦理道德思想对人只能抽象的、孤立的、直观的考察,局限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生活实践,最终重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总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道德,它是历史的、具体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每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没有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抽象道德。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一定的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必然会产生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解决过程,亦是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观念意识的形成过程,这就是道德的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道德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可见,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逐步形成,归根到底,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点发端而来的,以物质生产活动的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6]人们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从他们自己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而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道德起源的揭示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出发点,认为伦理道德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它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由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所维系,伴随人类社会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并反映和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从而从根本上超越费尔巴哈伦理道德观。
[1][2][4][2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15,416,416,76.
[3][5][6][7][8][9][10][11][12][14][15][16][19][20][21][2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60,536,589,569,569,536,536,553,573,572,571,572,233,569,205-206,569.
[13][17][23][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1,292,293,293-294.
[18]江畅.幸福与和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