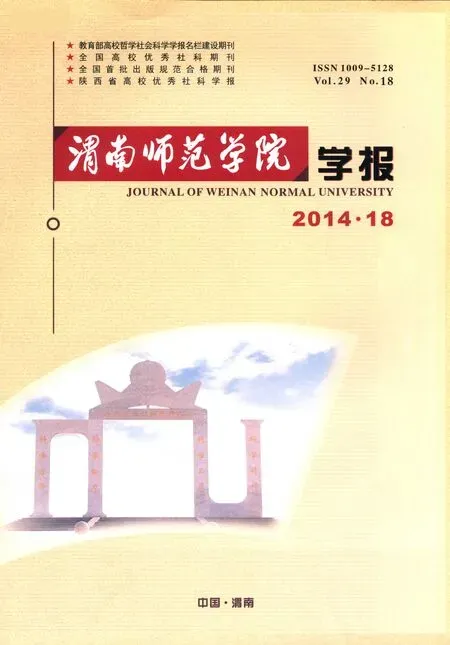对传统审美形式的创造性化用
——贾平凹小说艺术技巧论
程 华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对传统审美形式的创造性化用
——贾平凹小说艺术技巧论
程 华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贾平凹具有自觉的艺术意识,除了在艺术审美观念上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具有为实现此种审美认知所使用的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艺术技巧。贾平凹小说的艺术技巧观集中体现在他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创造性化用中。贾平凹对传统文学理论中虚与实的理解,小说与说话关系的理解,以及从民间和古语中寻找好的语言等进行创造性改造和发展,就是从文学表现的技巧上对中国传统审美元素的创新和突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
贾平凹;意象;结构;语言
文学是具有一定规则和方法的技艺,写作过程不是自然表现的过程,而是精心构思的过程,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成熟,意味着文学创作风格自成一派。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能够独步文坛,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形式的探索是分不开的。贾平凹注重借助中国传统的审美表现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绪。贾平凹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指出,“西方文学的境界可借鉴,因为追求境界是大多数作家共通的,但是形式不能借鉴,像水墨画和油画,京剧和话剧,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形式是借鉴来的就雷同于翻译式的语言,丧失了民族性,虽说穿过云层都是阳光,但云层各有不同。”[1]231在贾平凹的意识里,要改变和发展传统的文学表现形式,创造出具有中国作派的小说形式。贾平凹对传统文学中虚与实的理解,小说与说话的关系,以及从民间和古语中寻找好的语言等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
一、对传统意象的创造性使用
1.将意象从传统的感发功能升华到具有普遍的象征功能
“时下的文学作品中,时髦着潜意识的描绘,方法多是意识流,以一种虚的东西写实的东西,《太白山记》反其道而行,它是以实写虚,将人的意识用实体写出,它的好处不但变化诡秘,更产生一种人之复杂的真实。”[2]272在这里,贾平凹提出“以实写虚”的新观念。所谓“以实写虚”就是以象写意,而以往的“以虚写实”则是以意写意;以意写意通过心理或意识的真实揭示生活的真实;而贾平凹企图借助生活中的客观物象解释他对生活的理解。这个象就是我们在意象论中论述的“象”。言不能尽意,而“圣人立象”却可以尽意。立象的目的是为了见意。从艺术思维的角度而言,承接的是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传统的意象论从观物取象到立象见意,强调的是作者的感悟能力。中国是诗词大国,王国维评价好的诗词是有境界的,有境界就是要情景交融,情为意,是虚的,景为象,是实的。好的诗歌就是要虚实相融,要借象生意,强调作者的兴发感动能力。贾平凹钟情于意象论,不仅强调作者的感悟能力,而且要使意象具有象征和隐喻的功能。黑格尔认为,“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3]11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题名,作为意象,就具有丰富深刻的象征意义。“浮躁”是20世纪80年代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废都”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没落者的精神映像,“秦腔”是传统农耕文化衰落的象征[4],“高兴”则是对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追求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精神想象。如果说,传统意象重在兴发感动,那么,贾平凹熟练使用意象,使得意象具有普遍的象征功能。
2.扩大意象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功能
贾平凹对传统的意象论有创造性的超越,这种超越还体现在如何将意象思维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诗歌中的意象主要是物象,在贾平凹早期作品中,细节意象只具有点化作用,而无情节贯通作用。小说讲究的是结构上的整体贯通。贾平凹想要寻找一种与小说文体一致的意象,《土门》的写作在“虚实相间”中,明显看出作者在意象营构中的刻意追求,实的部分没能写得更精彩,而“虚”的部分又显现不足。《怀念狼》在“以实写虚”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作者在写作之前已有了明确的写作宗旨:“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如果说,以前小说企图在一棵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2]272。因此,我们能看到,作者圆满的用“具体的物事”,即在寻找狼——捕杀狼——怀念狼的过程中,将意象直接变成情节,这是依小说文体而对意象的创造性化用。
3.对意象的超越,还表现在对虚与实的处理上
贾平凹一再强调,他所创造的意象世界、虚构世界是要通过原生态的生活流来表达的。贾平凹的关键点是要达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在对两者的结合上,贾平凹是有哲学依据的:“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顺利或困难都要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的兴趣。”[2]272在这里,贾平凹理论上完成了他的整体意象论,那就是通过生活流的实存之象来传达他对生活的形上之思。现在新写实强调生活的原生态,整体上消解了作品本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力求通过生活流达到对生活的平面化的再现。而在贾平凹这里,他要通过原生态生活的流动,凸现作家的某种精神指向。就如同贾平凹所言:“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5]494现实的形而下的生活世界是他的象的层面,生活之上的形上之思则是他极力表现的意。这样,意象不仅是表现手法,也是结构手法。不论在《废都》《秦腔》,还是《古炉》《带灯》中,我们在这种密实的流年似的生活流叙述中,找不到绝对的意念,独立的意义,而是在似生活的、混沌的,多元的话语结构的背后,看到了小说多层次的、流动的意识形态,那是超越于形下生活的形上之思。谢友顺认为,当代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要么极端的写精神抽象,要么极端的写生活现实,匮乏的是将写物质和写抽象相平衡相综合的能力。而贾平凹在写实中,恰恰兼顾了物质与抽象的平衡,这就是贾平凹“以实写虚”的魅力,而这正是贾平凹对传统意象论的现代性突破。
二、“说话体”的小说结构
贾平凹将“小说”与“说话”联系起来,明确表明自己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超越与反拨。贾平凹在《白夜》后记中阐明了他的说话理念,传统说书人的说话方式重在“哗众取宠、插科打浑、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善于煽情”[6]317,全视角的讲述又类似领导干部式的“慢条斯理、拿腔捏调”[6]317。这两种说话方式都存在叙述者横亘在故事与故事接受者之间,都强调叙事者的态度对叙事文本的硬性切入。改变说话的方式,就是创造新的文体结构,如何拉近叙述者、接受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做到叙述的自然、随意,是贾平凹孜孜以求的。
在不断进行小说结构的尝试中,贾平凹认为,如何达到在叙述生活故事的时候,如同生活本身在展示,这就要求在写作中寓“技巧”于“故事”和“生活”之中。“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而在这平平常常只是真的说话的晚上,我们可以说得很久,开始的时候或许在说米面,天亮之前说话该结束了,或许已说到了二爷的那个毡帽。过后一想,怎么从米面就说到了二爷的毡帽?这其中是怎样过渡和转换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过来的呀!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禅了。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6]318贾平凹在这里阐明的是“说话”体的文体观念,其实是从“怎样说”和“说什么”两方面完成他的叙事结构。“怎样说”,贾平凹强调聊天式结构,力戒叙述者观念的硬性切入,追求叙述技巧的非表演性,达到让人“看不出在做”的痕迹。“说什么”是指小说的叙述内容,贾平凹小说中的事不是传统的有完整情节的故事。他强调的是那些生活中的“细微之事”,他认为:“如果看到了获得了生活中那些能表现某人某物某景的形象而细微的东西,这也就是抓住了细节,文学靠的是细节,而素材的积累,说到底是细节的积累。”[5]447
贾平凹对小说世界的营造是出于一种重建小说世界的完整性的考虑。贾平凹在“说”的方式上要求与生活尽可能的靠近,使小说像生活本身一样让读者看不到做的痕迹,在“说”的内容上又要求小说尽可能细微地袒露生活的真相,十分看重生活的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如果我们回到我们民族小说传统的审美艺术领域,我们又会发现这种审美追求恰恰是我们民族的东西。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颠覆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汉语体系,小说家学西方的文论观念,注重以刻画典型人物,强化叙事结构的完整性为特点的焦点叙事,忽视的恰恰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贾平凹的写作,放大了日常生活的内容,这种更接近生活本质的叙述其实联结的是中国文学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代表的生活叙事传统。但同时又是在古典小说叙事基础上文体探索的成果。
三、现代背景下语言功能的转变
1.好的语言是冶炼出来的
贾平凹自开始创作小说,就非常注重语言的运用,而且有非常自觉的语言观。在早期他就强调“语言是作品的眉眼”[5]442,贾平凹认为:“金在沙中,浪淘尽,方显金的本色;点石如果能成金,那也仅仅只是钻进了河蚌体内,久年摩擦、浸蚀而成的一颗珍珠,如果以为是现实里发生过的,就从此有了生活气息,以为是有人曾说过的,就有了地方色彩,那流氓泼妇就该是语言大师了?艺术,首先是美好;美好是冶炼出来的。”[5]444关于语言是怎样“冶炼”的,他谈了三点看法:首先,好的语言要充分的表现情趣,“月有情而怜爱,竹蓄气而清爽”,语言中有情操的内涵。在之后的创作中,他致力于追求有情趣的语言。王一川曾经评价贾平凹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是白描化语言,白描是中国画技之一,鲁迅对白描有总结: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贾平凹在语言的白描化追求上,与鲁迅先生如出一辙,他同样反对浮华雕饰的语言,强调语言的单纯朴素。“骗子靠装腔作势混事,花里胡哨是浪子的形象。文学是真情实感的艺术,这里没有做作,没有扭捏:是酒,就表现它的醇香;是茶,就表现它的清爽;即便是水吧,也只能去表现它的无色无味。”[5]443这种语言观,从他最初的成名小说《满月儿》到近期的《高兴》,白描化的语言一直是为批评者们所称道的。早期白描化语言清丽隽永,至后来,其语言愈加富有质感且生动鲜活。其次,他认为要和谐的搭配虚词,其实是讲语言的节奏感。他说:“为着情绪,选择自己的旋律,旋律的形成,而达到表现情绪的目的,正是朱自清散文情长意美,正是孙犁小说神清韵远的缘由。”[5]443作家的语言风格其实就体现在语言的节奏感上。和谐的搭配虚词,使语感铿锵有致。笔者认为,虚词的使用,会使运笔有疾徐,声调有抑扬,节奏有张弛感,语感自然充满韧劲和质感。第三,他认为要多用新鲜准确的动词。“生动,生动,活的才能动,动了方能活”,动词能使句子充满动感,状物记人犹在眼前一般,给人栩栩如生之感。他认为古今中外,“锤句锻字,都在动词”[5]444,好的动词,不仅能够状物逼真,形象凸显,而且可引发读者产生文学性想象。动词运用得好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特征。
2.恢复和起用语言的本意
文学语言要具有诗意,如何从现在的日常语言中寻找诗意,有的作家提出从古诗词语中寻找,有的作家提出从翻译语中寻找。贾平凹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还得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母语是与生命直接相关联的东西,每种语言的产生,都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哲学、文学有关系,语言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汉语文学原来是古汉语,时代发展变化,文学语言也要发展。白话文的写作从五四到现在有百年时间,白话文没有古汉语凝练,但用古汉语写作又有一种迂腐感和陈旧感,这就需要对旧的语言进行超越,给予古语以新意。
贾平凹非常看重语言的本意。汉语本身就具有诗性,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能够直接传达文化的感性与智性内容。“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汉字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幅抽象画,它比现实简单,经过提炼,但仍保持现实对象的感性质地,与其所处的境况,及它与它物的关系。因此,当汉字传递知识信息时,它所传达的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如拼音文字那样。它所传达的是关于认知对象的感性、智性的全面信息”[7]。对于中国汉语的这种诗性特征,贾平凹也有认识,“现在许多名词,追究原意是十分丰富的,但在人们的意识里它却失去了原意,就得还原本来面目,使用它,赋予新意,语言也就活了。……运用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新意就出来了。”[8]他非常看重汉语语言的本意,正因此,从一开始创作,他就十分注重从民间学,从古语中学,“向古人学,学习他们遣词造句的精巧处,向民间学,留神老百姓口中的生动的口语”[8]。贾平凹认为,陕西民间土语相当多,语言是上古语言遗落下来的,十分传神,笔录下来,充满古雅之气,他早期作品非常注重古语在作品中的运用,其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就是古拙、质朴,这在《废都》之前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而且引起了批评家的高度认可。
3.提倡在现代背景下小说语言功能的转变
贾平凹认为随着西方文学的全面介绍,西方文学中语言的各种表现手法也为中国的作家们推崇效法和学习。传统小说多写人生、命运,现代小说多写的是人性、生命,语言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小说中的语言更多是描述性的,现代小说的语言则更多在于叙述;传统小说的语言要求描述得生动逼真,现代语言却要求直达精神。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中国戏曲上,唱段是抒发心理感情的,即言之不尽而咏之,对白则是叙述的,承上启下交待故事。中国戏曲上的这种办法被中国传统小说采用,对话在小说中的功能当然也能起到塑造人物之效,但更多的还是情节过渡转化,或营造氛围。一般作品中的对话仅是交待,优秀作品则多营造渲染气氛,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现代小说则改变了,将对话完全地变为营造渲染气氛和书写心理活动……对话成了现代小说展示作家水平高低的舞台。可以看出,现代小说中的对话就是对话,直抵精神。如一座水泥建筑上的窗户,在这里,潜意识得到显露。”[8]贾平凹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对话中充分地把潜意识显示出来,从而扩张、丰富着人的精神世界。现代小说中对话功能的改变可能只是现代小说语言表现的一种探索,一种为了使语言更好地传达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式。不仅是贾平凹,余华和王安忆等一批现代作家,都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丰富着现代文学语言,语言的功能的改变是文学创造性的表现。
[1]孙见喜.制造地震,贾平凹前传:第二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贾平凹.怀念狼·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3][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程华,李荣博.秦腔声里知兴衰——论贾平凹作品中秦腔和文化的映照关系[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1):44-48.
[5]贾平凹.平凹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6]贾平凹.白夜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7]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J].文学评论,1996,(4):72-80.
[8]贾平凹.关于语言——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2,(6):4-8.
【责任编辑马 俊】
The Application of Creativity in TraditionalWay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Jia Pingwa’s Novels
CHENG Hua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China)
Jia Pingwa possesses consciously artistic awareness,besides his unique cognition in the art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e author has the only art expressing ways and art skills to realize this cognition of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while he is writing. The viewpoints of art skills in Jia Pingwa’s novels embody his application of creativity in traditionalway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His understanding to the virtuality and reality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ies,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and speaking,and even searching forwonderful languages in order to creatively reconstructand develop from folk languages and old languages.That is to say,he innovates andmakes breakthrough to China’s traditionalelements ofaesthetic appreciation from the literary expressing skills.His purpose of doing so is to better expressmodern people’s thought and feelings.
Jia Pingwa;images;structure;language
I206
A
1009-5128(2014)18-0072-04
2014-07-15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贾平凹莫言创作风格比较论(13JK0288)
程华(1975—),女,陕西韩城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