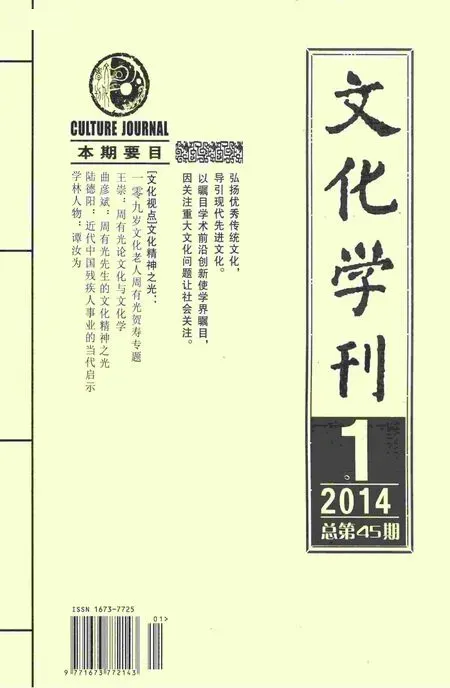被命名的“后期浪漫派”
乔世华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有的评论家喜欢对作家发出类似的忠告: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兢兢业业,才能写出能载入文学史的传世之作。这话好像有那么些道理,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拿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两部爱情小说在国统区文坛闻名的作家无名氏来说,他的这两部小说的写作就都挺随意的:《北极风情画》总计14万字用了20天完成,每天平均写作7000多字;10万字的《塔里的女人》也只历时一个来月即完成。《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故事虽然曲折有趣,但粗制滥造。因为小说主人公韩国人林上校(《北极风情画》)和小提琴家兼医生罗圣提(《塔里的女人》)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就是无名氏的好友李范奭与周善同,受着男性沙文主义思想影响至深的无名氏既欣赏朋友的艳遇,也要表现朋友的种种美德、为这两位负心郎在爱情上的不负责任开脱罪责,遂在塑造人物编织故事时总要想着突出男主人公们品行的高大、完美、正派、清白、专情和无辜,奈何真实生活中的两位主人公又不那么争气,所以无名氏就免不了要对他们涂脂抹粉,结果就“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弄得叙述上前后矛盾。无名氏在晚年对这两本小说都煞费苦心做过程度不同的多次修改,意图是让小说凤凰涅槃华丽转身,怎奈小说的整体框架已经成型,他也只能做局部修补,有时甚至还会欲盖弥彰地衬出林上校、罗圣提的无比虚伪来。
就是这两本叙事上破绽百出、连无名氏自己都视作“习作”的小说却让他享誉一生。大众读者提到无名氏时就不自觉地会联想到他的这两部作品,一如由徐志摩想到《再别康桥》、由戴望舒想到《雨巷》、由余光中想到《乡愁》、由郑愁予想到《错误》。上述这些作家都不是“一诗”或“一本书”作家,这“一诗”“一书”并非他们创作的全部,但他们又都很容易被这“一诗” “一书”之名所累,叫人觉得这就是他的招牌菜似的。无名氏2002年去世时,海峡两岸的媒体在报道该消息时就不忘给无名氏贴上这样的标签—— “以《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而闻名的作家”,而《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是远不足以代表他的整体创作的。无名氏是有很多更重要的作品的,比如《无名书》,这部270万言的六卷本小说耗去了无名氏十五六年心血,无名氏在后来还一再对这部作品进行修改完善,可造化弄人,《无名书》在普通读者那里就不大被人所知了。
无名氏写作《无名书》的意图很明白:“我主要野心是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其夙愿是“调和儒、释、耶三教,建立一个新信仰”[1]。听上去口气大得很,但《无名书》又的确具有着大制作大手笔的种种气象:贯穿小说始终的主人公印蒂虽九死其犹不悔地寻求生命的“圆全”,倾其力去寻找比生命本身还重要的东西——解决人类种种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无名氏借着印蒂的足迹相继对人类文化进行了一番大巡礼,参透革命(《野兽、野兽、野兽》)、爱情或曰人性美(《海艳》)、“地狱”或曰人性恶(《金色的蛇夜》)、中西宗教(《死的岩层》),而后“悟道”(《开花在星云以外》),最终提出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创世纪大菩提》)。在六卷《无名书》中,无名氏努力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优长以求创造出能解决人类各种矛盾、问题的新文化,并推出自己的“星球哲学”——简言之,他是要让人类拥有更宏观的地球感觉,以此代替过去人类生活中狭隘的一镇一城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国家的感觉,地球人从此利益完全一致并息事宁人,若是有纷争有矛盾,那也一定应该是和外星球生灵间发生的。《无名书》末一卷《创世纪大菩提》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最终设计和解决方案可能让人觉着有些一厢情愿有些不切实际;而且按照司马长风的说法,这么宏大繁复的文化主题要以小说的方式、“要集中在某一人物、某些人事片断上表现出来,那等于把宇宙浓缩为一粒原子”,是难上加难的,但无名氏在表现印蒂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文化的巡礼上,的确“作得相当辉煌绚烂,显示了睥睨百代的才华与气魄”[2]。因此,司马长风在才看到《无名书》的前两部半时就曾激赏:“我毫不迟疑的说,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无名书初稿》(即《无名书》,笔者注)是最伟大的小说作品。”[3]可就是在认识这位“打破了传统文学品种的疆界,蹂躏了小说的故垒残阙”[4]“在艺术天地里简直有我无人”[5]的无名氏上,文学史的编撰者们,有时也免不了庸俗趣味作怪和眼界所限 (六卷《无名书》至今也未能在大陆出全),对无名氏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和代表作《无名书》的论说遂不偏不倚等量齐观。即以此单独文学个案来看,文学史可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保持着某种神圣姿态,印染着人观念的诸种文学史肯定不会像那些个亦步亦趋的书评所说的那样“客观”“公正”,难以避免知识盲点、难以摆脱现实桎梏的文学史家,也在所难免地会令自己书写的文学史笔走偏锋、出现偏差和无知的情形,所以,进入到文学史中的作品未必都是最佳,真正好的作品未必就会得到文学史家的垂青,反倒有可能被遮蔽与埋没。哪座庙都有冤死的鬼。文学史尽管是白纸黑字写着,但学习者和阅读者也不必完全当真。尽信书不如无书。
有的研究者将无名氏定性为“通俗小说作家”,就仿佛《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是他创作的全部似的,而且也正是基于对这两个作品的认识,有的研究者把无名氏和早于其几年即已成名的徐编排成了同一个流派,名号有“后期浪漫派” “后期现代派” 或者“新浪漫派”“后期海派”等不一而足。这两位作家确实有点渊源,当无名氏在1943年底以连载小说《北极风情画》 (初名叫《北极艳遇》)风靡一时之际,当时就有读者拿他和早几年即以小说《鬼恋》成名、现如今又以一本言情特工与哲理三合一的小说《风萧萧》而大红大紫的作家徐相提并论。这一面可能是就无名氏这位后起之秀的名气直追徐而言的,因为1943年被人称为是“徐年”,无名氏恰在这时异军突起;再一面则可能是觉得无名氏《北极风情画》与徐此前的《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等小说有些相像。不过,要把这二人总结成为一个流派,总让人感觉着势单力薄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毕竟,这是一个总计由二人组成、代表作家自然也只有这两个人的文学流派,多少让人感觉着这样的文学组合有点“悬”。
谈到文学流派,不得不饶舌几句。文学流派的形成有两种:一种是自觉形成的作家集合体,他们惺惺相惜志同道合,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以及共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在文学创作上你我呼应互相唱和;再一种则是不自觉形成的作家集合体,是后人依照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某些作家在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上的相近度、在作品风格上的类似度而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出来的,这后一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就会存在两种情形:一种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再一种就可能不那么符合事实而是更符合研究者的主观意志了。徐和无名氏虽然生活年代相同,彼此应该互相知道,但没有任何人生上的交集,他们并不相识更不心灵相通,无名氏自己都认为和徐创作风格有根本不同,他们并非文学写作上的“同志”,所以他们肯定不属于前一种。若是把他们两个人看成一个流派,还就得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式了。一旦研究者一着不慎乱点了鸳鸯谱,让两个根本不搭界的对象发生着奇妙的联系,要在“被流派”的两个人之间找出共同点来似乎也不应该是什么难事。你能说桌子和椅子、癞蛤蟆和天鹅没有可比性?还是说吴荪甫(《子夜》)与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王熙凤(《红楼梦》)与斯佳丽(《飘》)不存在共同的精神禀赋?这应该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文学研究上的一个表现。更直接一些来说,文学史的研究者或曰刀笔吏是具有一种权力的,这种权力使用不当,就能以讹传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本全国诸多高校通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多年来就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舛误,譬如把许地山小说《命命鸟》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弄串了,再如一直在延续着“南玲 (张爱玲)北梅 (梅娘)”这个子虚乌有的说法……使用者如果不察,那头脑就难免会被这错误的书写格式化,一种背离事实真相远矣的文化记忆就此深深植入头脑中,新的历史由此形成。
人们得承认,出现这样一个文学流派有很多好处,比如,它可以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天空中从此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显得流派多姿多彩,壮大了小说“流派史”的声威,为流派史的撰写添砖加瓦,至少研究者们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类的文学史时不愁没米下锅,至少在形成研究成果时,学术专著能够有足够的厚度。还有,出现这么一个流派可以把那些原本不太好把握的“点”串连成一条有序的“线”,和许多其他的流派、思潮一样让本来可能不太好把握与叙说、不存在什么关联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变得相互贯通、变得脉络清晰,更容易为人掌握与总结,似乎文学史是有着一个铁定的历史进程似的,一切都在一种有条不紊中进行。至于事实真相如何,徐和无名氏被组合在一起是否属于关公战秦琼,研究者们倒不大在意了。
归根结底,同样是由人来书写的文学史和一切其他历史一样都是“当代”史,都尽可以由着写史者的意志和心情任意涂抹打扮。可以肯定的是,在从前文学创作现场的作家们可能会因为单打独斗闷头搞自己的写作,诸多作品的产生、文学现象很有可能是零散的、碎片式的,很可能与他人与时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当然也不必否认,这期间作家们也会有组织有派别有策划有风潮,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吵吵嚷嚷热闹无比。但到了文学史家那里,在他们描述文学史场景时,一切就都变得有条理有秩序有规律有章法可循了;无论在历史的坐标上有多少个“点”,这些个“点”又是怎样无规律的存在着排列着,文学史家们都会按照自己的观念画出一条自己所期待的曲线来。“阶级论”流行时,革命作家左翼文学遂占据了文学史的大半江山,那时像无名氏所写的爱情小说怎么可能进入到文学史家的法眼中!待到“人性论”家喻户晓时,歌舞升平成为了主旋律,阶级的文学又黯然退场,无名氏的谈情说爱自然就会浮出水面。而这样的在某种观念统摄下写作的文学史究竟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或者还原了历史,太值得我们追问了。其实,各种既往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就一直那样静静地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等待着文学史家的打捞。文学史家们的观念更新了、认识不同了,便会按照某种需要对一切进行取舍、再把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揉和成各种样式的面团。文学史的学习者阅读者很容易会以为这被不断揉和的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全部真相。而其实呢,真相一定远不止于此,甚至真相有可能已经被文学史家的叙说掩盖了、弄拧了,某一时期的文学史只是呈现出了这一时期文学史家们所期望呈现的那个样子。
说到这里,似乎给人一种挺悲观的感觉:文学史以及历史真的就是这样变得不可知了吗?文学史上的一切是不是就此都令人难以置信了呢?我从不这样认为。认识到文学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着的种种问题与局限,意识到文学史家在书写文学史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霸权”行为,并对此保持必要的警惕,这是接受者在面对各种文学史时应该保有的态度。如何反抗这种“霸权”?一个最好的途径可能恰恰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不断的有人来继续书写文学史。只有不定于一尊的文学史书写,只有在罗生门似的众口评说中,我们才可能更好地掌握那些个被有意无意遗漏的、说错了的“点”,才可能更加清楚地接近真相、才可能更好地返回文学史现场。
[1]卜少夫.无名氏的生死下落[EB/OL].http://bbs.openow.net/showthread.php?t=39726。
[2][4][5][9]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108.105.106.100.
[3]编者.无名氏最后遗言[J].展望,2002,(11):48.
[6]无名氏.我心荡漾[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235.
[7]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95.
[8]周锦.中国新文学史[M].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