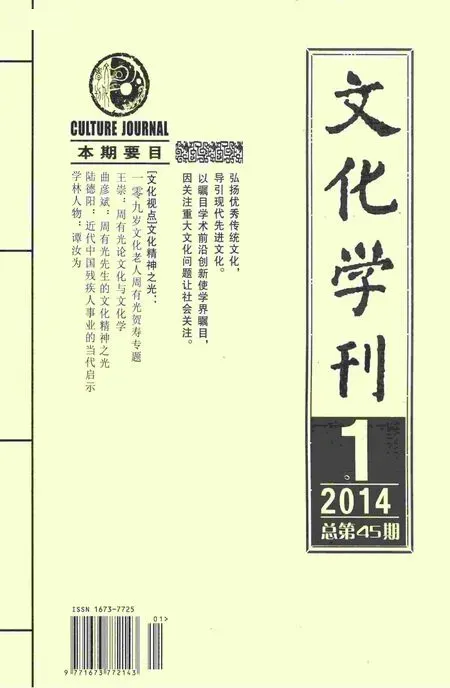周有光的眼光
杨继绳
(《炎黄春秋》杂志社,北京 100045)
周有光生于1906年,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他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了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工作过,还游历了很多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了无数世界级名人,他曾同爱因斯坦多次交谈。他至今思维清晰而敏捷,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每天用电脑写作,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他出版的著作有30多种,涉及经济、语言、文化多个领域。百岁以后,他还是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反思。他说:“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温故而知新’。” (《“百岁新稿”自序》)
现在,对中国、对世界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相信谁呢?当然相信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 (个人正反面的经历),从学识中来,从不断地反思中来。就这三个方面综合优势,中国当代有几个人能和周有光比肩?另外,他没有当过高官,又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不是利益中人,能够客观地看中国、看世界,所以,对他的看法我虽然不能说深信不疑,但信任度超过了对当今的一些高官显贵和硕学鸿儒。
我是在他百岁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有几次他给我寄来稿件并附亲笔信。信的字迹如竹根,如枯草,但清秀、有力,没有一点抖颤,不像百岁老人的手笔。最近几年,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他也参加。记得是在2010年的春节联谊会上,他坐在轮椅上发言,声音高吭,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挤到前面举起了照相机。那次他发言的内容是,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持续好久。
在他108岁的时候,北京知识界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聚会,与会者谈论周有光的道德文章、评点周有光的学术成就。发言者按主持人的点名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自由发言。当主持者点到我发言时,我交了白卷。我说,我还没有想好,以后再写点东西吧。我的确没有想好。周有光老人又像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没有读懂,哪敢妄加评论?
后来我算是读了几本周有光的书,不敢说读懂了什么,但受到很大的启发。徐继畬写了《瀛寰志略》,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被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周有光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给人们展现了更高更远的风景,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就以“周有光的眼光”为题。
他站在星际空间看世界
周有光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 (《周有光年谱》第163页)“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还要添上一句: ‘登月球而小地球。’地球的确太小了,不能再说‘大地’,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地球村’。” (《周有光年谱》第210页)
“在21世纪,人与人、国与国,正在重新定位。世界各国,原来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现在大家都挤进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成为朝夕相见的近邻。今后早上见面可以说一声‘嗨!’当然仍旧有敌对,但敌对的方式和过去不同了。”
(周有光:《走进世界》,载《群言》2002年第12期)
“地球变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变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天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周有光: 《漫说太平洋》载《群言》2001年第9期)
然而,现实和周有光的期待差距甚远。大家都成了“地球村”的村民,却还是“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进入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不知道哪一天会因自己制造的科技成果而毁灭人类自身。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可以登上月球,可以向火星发射飞行器,但也越来越愚蠢,不知道如何在地球上和平相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说过,人类僭取了上帝和自然的权力,但没有上帝那种智慧。处于这种境地的人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儿童拿着子弹上了膛的枪一样。
请看看当下世界:因弹丸之地引发的领土纷争,相互拔枪怒对;因宗教、民族的差别引发武装冲突,殃及妇女儿童;因对地球资源的争夺引发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面对朝鲜这样一个“玩火”的“顽劣儿童”,全球慌作一团,毫无办法……凡此种种,都是周有光说的,地球变小了,而人类的胸襟没有开阔起来,人类还没有在“地球村”和睦相处的智慧。也正如他说的,现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没有树立起全球化的世界观。
他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朝闻道集》第28页)
周老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即人类对天体构造的理解。二是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政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科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政治制度的逐步演进。(《拾贝集》第88页)
在当今的“地球村”,各国经济已经联成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人们的认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改变。周老说:“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人民‘入世’就变成了‘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也没有公民证,但是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周老说的扩大视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改为从世界看世界。”(《拾贝集》第48页)
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什么叫“信息时代”?周老用一个通俗的回答:“不能一刻离开手机,这就是‘信息时代’”。他说:“我国传统说法:‘食衣住’是人生三大需求,孙中山加了一个‘行’字 (交通),‘食衣住行’成了人生四大需求。现在要加上一个‘信’字,‘食衣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 (《拾贝集》第119页)有了信息的即时交流,各种误解就容易消除,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交流中逐步取得共识。这是成为“世界公民”的最重要条件。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了。
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周老说,美国有很多民族,大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民族固定一个地区。人跟土地没有固定联系,迁徙自由,没有形成“民族州”,没有形成“州语言”。这叫民族的“掺合结构”,稳定性比较强。前苏联不同民族都有固定的地方,人跟土地固定联系,有各自民族的语言,这叫民族的“拼和结构”。这种结构不稳定。
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史。民族融合既是趋势,也是和谐相处的必要。前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却违反了这个常识。本来某个民族已经和别的民族融合了,还要再造它的特点,还要帮它创造文字。这是不是自讨烦恼、自造祸端?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周老写道:“二战后经验,与其掠夺别人的疆土,还不如发展自己的经济,掠夺不如创造,创造90%的成功,掠夺50%的失败。德国和日本就是榜样。财产在美国已从‘土地’,变为‘资本’为主,又变为‘知识’为主了;这就是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知识时代’”。 (《拾贝集》第20页)“一战之后,法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采取‘惩罚’原则:废除军备,限制经济,还要支付巨额赔款。结果狗急跳墙,跳出个希特勒。二战之后,美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 (即联邦德国)改变策略,采取‘援助’原则,限制军备,以GDP的1%为度;发展经济,协助资金和技术。德国生产迅速恢复,德法化敌为友。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极化变为一体化。这是美国宽大吗?非也!经过两次大战,美国变聪明了,懂得‘援助’敌人就是‘援助’自己。日本购买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日美贸易迅猛发达,‘援助’比‘惩罚’更有利。” (《拾贝集》第23—24页)
在周老看来,昔日攻城略地的战争,今天应当被经济竞争所代替。经济互补,贸易互惠,对各国人民都有好处。一旦发生战争,贸易中断,经济停顿,对各国人民都有损害。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但是,请看看近来有些媒体,宣传军备,宣传战争。满屏幕都是这个国家的战机如何先进,那个国家的航母如何强大;这里搞演习,那里搞战备。好像世界进入了临战状态!这种鼓动扩军备战的舆论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呢?这是令人深思的!政客为了拉选票,为了将自己打造成强者,常常迎合民族情绪甚至不惜打一场战争,“地球村”的人们可要警惕啊!
在“地球村“里,邻居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左邻右舍该不该管呢?当然要管。不是帮助老婆打丈夫,而是调解。不过,如果丈夫过于凶狠,要置老婆于死地,调解无效,也得对凶狠的丈夫加一点压力。按过去的说法,这样做就是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涉及到国家主权。
在“地球村”里,人权应当高于主权。政府通常是主权的代表,但从根本上还是主权在民。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权,所以人权应当高于代表主权的政府。主权不是绝对的,欧洲各国由于对国家主权作适当的让渡,就形成了欧洲共同体。对领土也不要看得那么神圣,考察各国边界,哪有永恒不变的国界线?在“地球村”,邻居间边界矛盾可以通过商讨解决,有争议的领土上的资源可以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何必大打出手?
“地球村”的文化是现代国际文化
周老认为,“地球村”的文化就是现代国际文化。他反对前几年一种流行的说法:“21世纪是中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手里。”这种说法的确满足了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周老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周老认为,人类文化是随着人类的聚合运动中前进的。部落文化聚合成城邦文化,城邦文化聚合成国家文化,国家文化聚合成多国区域文化,多国区域文化聚合成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什么是现代国际文化呢?那就是“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是一元化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庞旸:《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载《群言》2008年第12期)数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数学、唯心数学。逻辑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逻辑学、唯心逻辑学。同样,辩证法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辩证法,唯心辩证法。(《拾贝集》第106页)周老强调人类共同的东西,肯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就存在于国际现代文化之中。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从专政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按这个观点回首历史,周老说: “帝国主义是一种科技文化的冲击波。现在我们面对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击波:现代文化的冲击波。清末老一代人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拾贝集》第66—67页)今天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人,就是不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所以排斥现代文化。
周老强调国际现代文化,但不否认各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他说:“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朝闻道集》第9页)关于重建“现代儒学”,他说:“第一件事应当恢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跟先秦的学术自由接轨,在竞争中确立儒学的权威,不是用垄断来强制改造别人的思想。上接先秦学术自由,下接‘五四’的民主科学。‘现代儒学’就能贯通古今中外。”谈到“三纲五常”,周老说:这是董仲舒“把原有孔孟学说和原有社会制度归纳起来,写成公式化的说法,便于称说,便于传播。如果改一下内容,这个公式还是可用的。例如,‘君为臣纲’改为‘官为民仆’就适合现代的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三纲。”(《朝闻道集》第13页)
“地球村”的政治应当是民主政治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主流。(《拾贝集》第37页)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制度。……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 (《拾贝集》第86—87页)
周老认为,马克思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没有看到初级阶段的后期,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拾贝集》第106页)马克思说: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生产要素 (资本、技术、管理)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的结果,可是,西方国家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早已达到60%—80%;相对而言,活劳动所起的作用明显下降。周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学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了?(《拾贝集》第108页)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我们比周老晚一代的人 (70岁左右)的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马克思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情怀,这是它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主张建立计划经济。在他设想的这个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必须仰承政府分配,权力控制了每一个人的食品和衣着,人生而有之的个人权利也就被政府收缴了。搞计划经济,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格式化”,所以,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写过,马克思的人道精神只是停留在理念上,而他的“革命精神”却落实在制度上:一旦建立了国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制度就吞噬了人道精神。
前苏联就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终于消失了。前苏联解体的那一天,一位名叫闻一的中国学者正在莫斯科。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七十年的帝国倾刻垮台,一定会有强烈的社会影响,但是,他写道: “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人们说前苏联轰然倒塌,不是,没有“轰然”,是无声无息地冰消瓦解。这是一个奇迹。为了解释这个奇迹,周有光老人读了大量的有关前苏联的书,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苏联结束,档案公开,历史学者恍然大悟:苏联走进了历史误区。消灭了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都违反历史常规,结果发生大饥荒和大清洗,自相残杀,自行消亡。”“苏联创造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真科学’,后来全都自己否定。俄国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瓦解的原因是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苏联创造‘共产主义特权阶级’,有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掌握全部党政军、企业和农庄。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发出调查问卷:‘苏共究竟代表谁?’答案: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官僚的85%。”(《拾贝集》第90页)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抛弃了这个专制制度。
周老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发展越快,流弊越大。波浪起伏,周期往复。上次 (1929—1933)发生经济大恐慌,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已临末日。罗斯福新政后又见青天。今天(2008)又一次出现金融大海啸,资本主义能再度自行调节,走出没顶之灾吗?(《朝闻道集》第37页)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资本主义渡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地球村”的公民就是“世界公民”
周有光引用了军队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他认为,这句话十分剌耳,但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爱祖国爱美国》,《拾贝集》第21页)
我认为,刘亚洲这句话不准确,那些身居美国的华人,虽然国籍变了,热爱美国,但还是非常爱祖国的。祖国是他们魂牵梦绕之地。我有不少朋友、不少同学成了美国公民,但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他们思乡之情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强烈,他们回乡祭祖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勤。他们侨居美国,是因为那里更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我想到周老说的“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不太在乎国界。“国”字外面的方框既不能框住老百姓的身体,更不能框住老百姓的大脑。人们可以在国内生存,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存。世界公民的主权观念和领土观念已经淡漠。主权在民,主权不是政府手中的神器,居民有权选择政府。领土的主人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不是政府,有争议的领土可以通过协议共同开发。在世界公民眼里,祖国就是祖国,政府就是政府,二者不是一回事。政府是匆匆过客,而祖国永恒;政府有优劣之分,而祖国永远是美丽的。爱国和爱政府不能划等号。党和政府也不能划等号,党更不能和国家划等号。为了整体利益,老百姓应当和好的政府合作,要遵纪守法,维护稳定;老百姓要帮助不好的政府,促使它改进,推动它变革。中国人不管生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不管持什么护照 (护照是政府给予的标识,不是祖国给予的标识),多数中国人都保持有大体相同的特性。这个特性不能用美与丑、良与莠来评价,它是历史和传统铸就的客观存在。周老说的“双方化”不仅体现在国内的人身上,也体现在华侨身上。而在华侨身上有“三文化”:现代国际文化、祖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只要保留了中国人这个不可磨灭的特性,不管是多少代的华侨,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