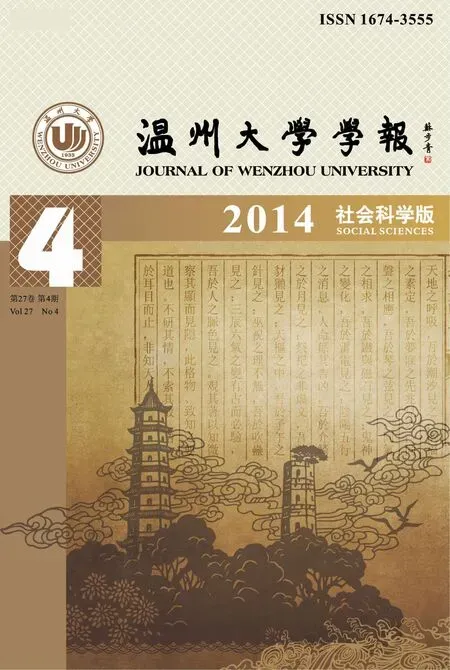唯形式主义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
吴家荣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唯形式主义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
吴家荣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新时期文学创作由朦胧诗、寻根文学到先锋小说,形式技巧的变革越来越显得突出,但始终没有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而一部分新生代、新人类作家,受后现代理论蛊惑,使文体革命逐步走向唯形式主义乃至反形式主义的死胡同,作品弥漫着颓废主义的精神气息。由此,文坛呼唤新的理性精神也就势在必行。
形式主义;颓废主义;文学思潮
颓废主义与唯形式主义是一对相辅共生的孪兄弟。无可否认,新时期文体革命的兴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但由文体革命走到唯形式、反形式的不归路,却不能低估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所派生的形式主义理论乃至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新时期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正是从西方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那儿获得足够的理论养份而日渐做大做强,反过来它又为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蔓延提供了丰腴的土壤。
一、新时期文体革命对形式美的价值肯定
(一)朦胧诗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
新时期文体革命意识导源于朦胧诗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北岛就公开说道:“诗歌面临着形式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觉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注意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1]建国以来作家对形式的传统认识在朦胧诗这里有了质的突破。传统文艺观点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表达内容服务。”这种视内容为文学作品第一要素、支配力量的看法,导致艺术表现手法的陈旧与俗套,作家们重视的是写什么,批评家们看重的也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这与当时普遍强调政治标准作为第一的批评准则,以及重视作品的教化功能是一致的。随着文艺从主流政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随着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标准被搁置,文学的审美品性日益受到作家与读者的青睐。以内容暴露的大胆成为轰动效应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波过去,日益偏重于审美感受的读者逐渐离文学远去。正是这样的时刻,朦胧诗人们以其一反传统的新颖手法以及表现的奇特、意象的朦胧,再一次把读者关注的目光拉回了文坛。形式的别致以及与之相伴的异样的内容,令接受者耳目一新。如顾城的诗《凝视》:“世界在喧闹中逝去/你凝视着什么/在那睫眼的掩盖下/我发现了我/一个笨拙的身影/在星空下不知所措/星星渐渐聚成了泪水/从你的心头滑过/我不会问/你也没有说。”[2]隐喻在跳跃的诗句中给人意味深长的茫然。这就是诗,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诗。这些诗确实比那些一览无余、毫无诗味的“革命”诗更有审美品味,更耐人咀嚼。朦胧诗人们就是这样大胆地移植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使新时期的新诗另辟了一条路径。当然,有些朦胧诗过份堆砌零乱的直觉、破碎的意想、玄奥的隐喻,影响了与广大读者的情感交流,以致受到拒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朦胧诗的消沉,并不意味着新时期对作品形式美的追求落下帷幕。相反,追求作品形式美的努力在寻根文学、先锋小说中又获得了新的成就。
(二)寻根文学使作品形式的变革具有了突破性进展
寻根文学在纵情于仿古返荒的同时又借鉴外来手法而使作品形式的变革具有了突破性进展。不少寻根作家自觉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种种长处,运用象征、隐喻、意识流、梦幻、变形、荒诞等手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思考,振聋发聩。冯骥才的《神鞭》,把荒诞、象征、写实与幻想融为一炉,有力地鞭笞了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抱残守缺的心理,说明保守僵化必遭挨打受辱的道理。作品新颖的表现手法让广大读者为之倾倒。韩少功的《爸爸爸》引入荒诞意识,运用象征手法,意蕴隽永地揭示了封闭社会中人的思维观念停滞与衰落的可怕,针砭了旧传统的劣根性。在《死河的奇迹》中,废弃多年的死河瞬间复活;在《古里——鼓里》中,时间突然停止运行。这种浪漫激情与神话意识的复苏,显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迪。而在《隐性伴侣》、《河东寨》、《伏羲伏羲》中,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心灵潜藏的民族文化的心理机制,从一个侧面破译出汉民族独特文化心态的遗传密码。这些在当代文学中未曾出现过的艺术形式与技巧获得了新异的效果,使长期不变的创作模式受到致命的冲击,为后来者更积极地探寻艺术形式美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尽管这类作品注重形式的新颖、技巧的别致,给人审美的意蕴,但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削弱。精巧的形式后面,仍然是令人咀嚼而难以释怀的思想容量。
(三)先锋小说家力求使小说新颖的形式突出对意义的承担,以陌生化的效果来引起读者对内容的关注
寻根文学作家对艺术技巧的探索、运用,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陈旧传统观念的劣根性、顽固性,从而唤醒人们起而扫荡历史因袭的重负。因而,他们对艺术手法的探索,对固有创作模式的突破,对艺术观念的更新、艺术手法的丰富,乃至新的艺术原则的确定,无疑有着积极意义。到了先锋小说家手里,情况有了变化。他们开始把“怎么写”看作远比“写什么”重要。追逐艺术形式的新颖别致成了文学创作的时尚。这显然是受到西方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理论思潮的冲击而引发的小说从内到外的“爆炸式变革”。小说本身作为艺术故事文本的特征愈来愈被确认。当然,先锋小说虽轻视内容但不否定内容,更不拒绝意义。相反,在不少先锋小说家那里,他们都力求使小说新颖的形式突出对意义的承担,以陌生化的效果来引起读者对内容的关注。王蒙是早期先锋思潮中开风气的人物之一。他的一批“集束手榴弹”小说,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对时空进行重新组接,最大容量地表现作品中人物对历史跨度的心理感受,完整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情绪,给人耳目一新的震惊,使传统小说注意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准则受到挑战。到了残雪、马原、余华、苏童手里,先锋小说的形式获得全新变化。马原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叙事变革令人瞩目的实验者。他以叙述语言为切入点,从小说叙事视角、叙事时间诸方面对传统小说进行了大胆的叛逆。在他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虚构》中,情节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某一视点讲述“事件”的手法。他在作品中,以不断的提示告知读者,你不要相信小说中叙述的一切,因为这是马原在“虚构”,并设想种种讲法,将故事频频肢解后重新拼装组合,让读者参与到其拼装情节的游戏中去,进而“遗忘”现实,在对事件发展的任意推测中感受到小说叙述形式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而余华的做法突出在叙事语言的革命。他善于运用冷静的叙述语调,不动声色地揭示历史的随意性、理性的荒谬性,以“虚伪的形式”,抒写自己对社会、人性的理解。特别是他的“叙述的和声”的精彩运用,造成语言美与事实残酷的极大反差,给人痛苦的咀嚼。在小说《一九八六年》①参见: 余华. 一九八六年[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3.中,余华将疯子自残的行为当作一场令人咋舌的“艺术表演”,由此反衬出群众对于“启蒙者”行为的不理解,以及“启蒙者”对牛弹琴的悲哀。在《在细雨中呼喊》②参见: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中,余华写道:“我离去以后,父亲孙广才越加卖力地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成为无赖,还需“卖力的培养”,这种“叙述和声”的运用,突出了讽刺的力度。还是这篇小说,余华写道:“半个月以后,父亲从拘留所出来,像是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一样的白白净净的。”虽有着事实的根据,但以这种大不敬的语言,描写自己的父亲,反衬着“他”对父亲的鄙弃之情。在《活着》③参见: 余华. 活着[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中,余华写道:“最后一把,我压上了平生最大的赌注,用唾沫洗洗手,心想千秋功业,全在此一掷了。”赌钱的侥幸心理、无赖形象简直在“千秋功业”四个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余华以“叙述的和声”为特征构筑的“虚伪的形式”,收到了强烈的反讽效果。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④参见: 香港《明报月刊》于2009年刊载的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也进行了大胆的先锋语体实验。在这篇小说中,苏童将“当下状态”的感受碎片连缀成不连贯的文本,突出强烈的语感形式以及叙述中的诗性感受,而将故事“退居二线”。
在先锋小说家眼中,无论叙事方式、叙事语言还是故事结构在文学作品中多么举足轻重而需时时着意匠心营造,但充其量都是小说载体意义上的变革,先锋小说家从来没有把这一切看作小说本身。他们的“叙述圈套”、“叙事迷宫”和话语反讽,只不过切合着他们关于世界的不可把握性和虚幻性的观念,传达出颓废的形而上迷惘。就是说,他们只是以新异的形式、陌生化的手法承载他们颓废的社会、人生情怀,并希望在这种意趣中求得生命的,同时也是文学的出路。
二、新生代作家对形式美的变味追求及其理论探源
(一)新生代作家对形式美的变味追求
然而到新生代新人类作家手里,形式美的追求就变了味。从朦胧诗开始,经由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形式技巧的变革越来越显得突出,却始终没有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这类作家的文本实验的价值还是大于其消极影响,他们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创作命题的颠覆,仅是给新艺术形式的涌现打开了闸门。然而,这一开放的势头却在一部分新生代和新人类作家手中断送了最后的生机。一部分新生代和新人类作家作品中弥漫着颓废的精神气息,混同着唯美主义的形式雕凿,完全摒除了内容的积极意义,使文体变革违背了形式探索的初衷,走向了唯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唯形式乃至反形式,以丑为美遂成为世纪末文坛的一大景观。
一部分新生代和新人类作家,缺少严肃的人生态度和扎实的生活根基,思想空虚,性情浮荡,由此对颓废主义情有独钟,他们妄图以对形式的张扬,来为作品生存打开市场。于是颓废与唯美也就成了他们手中的双刃剑。他们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作为理论武库,兜售陈旧过时、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纲领;一方面又以醉生梦死的心态嘲弄道德,反叛文化,宣扬刹那享受主义,鼓吹极端个人私欲,编织起怪异、眩目的颓废情怀。他们有意淡化乃至完全抹煞文学社会功能,极力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注意语言、结构、叙述方式上。他们在标榜语言形式与叙述策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同时,也就逐渐滑向唯形式主义泥坑,文学终于在他们手中完成了由文以载道到道术不分再到重术轻道、有术无道的蜕变,唯形式主义的高调也就唱到了极致。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形式主义理论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浪作用。
(二)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推波助浪
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肇始于康德。康德认为,美感不以概念为依据,不涉及事物的存在,也不包含具体的目的,只关乎对象的形式。他指出:“去发现某一对象的善,我必须时时知道,这个对象是怎样一个东西,这就是说,从它获得一个概念。去发现它的美,我就不需要这样做。花,自由的素描,无任何意图地相互缠绕着的,被人称做簇叶饰的纹线,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依据任何一定的概念,但却令人愉快满意。”[3]康德的“纯粹美”与“审美无利害说”的理论刺激了法国唯美主义的迅猛崛起。法国的唯美主义旗手泰奥菲尔·戈蒂叶首先亮出了“艺术无功利”的旗帜。他认为,艺术与道德、政治无关,它完全无用,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这本身便是唯美是求。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继戈蒂叶后,领导了欧洲唯美主义新潮流,他将唯美主义推向了形式主义的层面。王尔德坦称:“‘形式是生命的奥秘’,从崇拜形式入手,艺术中就没有秘密不向你显露。”①转引自: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90.这就是说,艺术的生命就是形式,形式也就是艺术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形式主义正是唯美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一切唯美主义无不看重形式,而形式主义正是唯美主义的理论核心。
应该说追求艺术形式美、强调艺术形式的价值地位,本身并无大错。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就是以其不同凡响的独具一格的形式技巧,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缺少艺术性的作品不是好作品,缺少形式美追求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然而颓废主义思潮中的一批作家却由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走到了玩弄技巧与形式并完全排斥内容的唯美主义顶峰,再由这顶峰走向“反向诗学”的下坡路,即对艺术自身的否定。由追求形式美到否定形式美,否定艺术具有永恒、不变的美学原则,夸大审美的相对性,进而否定一切审美判断与价值标准,不但颠覆了好与坏、美与丑、精致与粗糙的客观标准,更强调所谓“生命迷失”、“盲目书写”、“无意识写作”;由对生命本质的混乱理解,以及对无意识心理的支离破碎的认识,进而要求一切艺术形式也要与人的生理现象对应,鼓吹艺术形式的无形式,艺术技巧的无技巧,强调拼贴、时尚,以及作品内容的转瞬即逝,造成快餐式粗制滥造作品的批量生产。由此,那种重复单调的艺术品的制作也就代替了创作,艺术本身也就同时消失,我们从新时期一批作家的创作演变过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发展颓势的不可逆转。
(三)后现代理论对艺术形式的鼓吹与破坏,远比现代派理论更为强烈
造成一批作家在创作中由唯形式到反形式这一发展趋势的推动力是后现代理论的催化。后现代理论对艺术形式的鼓吹与破坏,远比现代派理论更为强烈。
后现代产生的土壤是后工业信息社会的存在。“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发明权无疑属于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社会革新和政策形成的根源。”[4]由此,后工业社会,就经济而言,标志着社会经济由产品型经济变成服务型经济;就职业而言,专业和技术阶级处于优先地位,科技型人员成为主体劳动者,以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型机器体系成为最重要的劳动工具;而在决策方面,则是创造新的知识技术,即信息技术,成为社会发展活力的基本途径;再次,后工业社会发展方向,是控制型技术的发展,通过“控制技术”的大量运用,社会管理者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最后,在产品制造和经济管理方面后工业社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贝尔所概括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与中国目前正在迈进的社会形态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中国的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其社会形态一步步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似乎难以置疑。因而,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长驱直入也就顺理成章而难以阻遏。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脚步逼近神州,人们也就必然对旧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嘲笑乃至厌倦。一些人开始放弃对社会的责任,热衷于将个人生活置于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状态中,从而使中心变成多元,永恒成为瞬间,绝对变成相对,整体成了碎片。面对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奔涌之势,文学创作与理论也就发生着断裂与颠覆。诚如美国作家莱斯利·菲德勒所言:“今天,几乎所有的读者和作家——从1955年起——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经历着文学现代派的垂死挣扎和后现代主义分娩的阵痛。那种自封为‘现代’(声称它在感觉和形式上代表了最先进的倾向,除它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创新’),其胜利的进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文学形态已经死亡。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历史而不再属于现实。就小说而言,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曼的时代结束了,对于诗歌来说,T·S·艾略特和保尔·瓦雷里同样已成为过去。”①转引自: 道格拉斯·凱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M]. 张志斌,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304-305.那么,后现代艺术与现代派艺术在总体精神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德国文学批评家弗利德里希·基特勒认为:“现代艺术是工业化社会属于少数受教育者的精华艺术,它强调艺术媒体的高雅和纯粹,仍然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的要求,因而与当今的时代格格不入。后现代艺术与此不同,作为后工业大众社会的艺术,它摧毁了现代艺术的形而上常规,打破了它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②转引自: 道格拉斯·凱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M]. 张志斌,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25.
(四)后现代的艺术主张与现代派的区别
首先,现代派作家虽在形式探索上做过大胆而有益的试验,然而,他们并没颠覆小说之为小说的类的概念,他们从没有否定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根本特点:写社会中人的思想与行为,怪诞的心理与无可名状的意绪。而后现代作家根本不承认小说这一样式的存在,完全混淆小说与非小说的区别,他们提出了所谓“反小说”、“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这样一些不着边际的概念,对传统小说的形式与“叙述”本身进行彻底的不留情面的解体。这些所谓的“反小说”、“元小说”,诚如萨特所说,它虽然“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向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为我们叙述他们的故事,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失望。作者旨在用小说来否定小说,在它产生之时,便在我们眼前将它毁掉。”①转引自由蒋孔阳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后现代作家否定小说的再现生活功能,他们声称,现实是语言造就的,虚假的语言造就了虚假的现实,小说的使命不是要用虚假的故事去反映虚假的现实,而是把现实的虚假与故事的虚构展现在读者面前,促使他们去思考人生。而且,小说不仅失去了类的特征,其与其它体裁的界限也被完全突破。其它文学体裁乃至新闻体裁、评论体裁的技巧、手法统统融于小说技巧之中,使人分不清也没有必要分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样式。德国评论家伯恩哈德·格莱纳就说过:“对于后现代写作来说,‘类’的概念已经消失……过去关于体载、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等种种流行的规范仅仅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强加在作者身上的枷锁。而现在,这种禁忌已被打破,枷锁已经腐烂,再也不存在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了。从根本上说,一切仅仅是单纯的刺激材料而已。”②转引自: 埃金根. 后现代先锋派的终结新的开端[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42.后现代注重对立面的消失,不仅否定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还否定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甚至否定文学与哲学的对立。他们认为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哲学、叙事类作品与非叙事类作品,正好通过互参性和差异性来互释其意义。因而,它告诫人们要以一种平和的心境看待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精神历史的发展是延伸与回溯、结构与解构的统一,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界限和框框来限定事物与现实。
其次是后现代作品深度的消失。现代派作家不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与表现终结真理为主题,就是以揭露现实黑暗、引起疗效注意、体现人文关怀为旨归。萨特的《可敬的妓女》是这样,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这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也是这样,《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同样如此。而后现代作家则放弃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如果说现代派艺术对形式的追求与翻新还着眼于吸引读者对思想内容的关注与兴趣,从而使深邃的思想借助形式的别致而深入人心,那么,后现代则放弃对作品内容意义的承担,走进了为形式而写作,唯形式而形式的泥淖中。他们不再追求作品历史性的深度,而将历史性转换为空间性的、多元并置的、共时性的存在状态。打破叙事的完整性和话语的统一感,强调非完整性,强调表述生命、历史和时间的零散化。后现代作家都认为小说文本没有统一的意义核心,他们拒绝承担作品意义的许诺,而把小说的写作仅仅视为“能指的延续”。作家在写作时可感受到能指的巨大力量,他们不是以能指来精细地表白所指,而是通过能指本身的变化建构成不同的所指。因而读者要从作品中认识某种特定的意义是徒劳的,即使他认为他读出了作品潜藏的深意,那也是他自己一厢情愿赋予作品的产物,而非作品本身所固有。作家创作的兴趣就是做文字游戏,而任由读者自己去发明无穷多的意义。由此,造成后现代作品平面化的语言堆砌。有人甚至公然宣称:写作就是运用符号这副牌来创造意义。这就造成后现代拼贴手法的反复使用。1962年,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尔达,进行了一场“请读者参与创作”的实验。他将一些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零乱故事分别写在52张卡片的正反面,每面的字数约50到100字不等。然后将这52张卡片象扑克牌一样洗牌后再排列。除了开头和结尾部分,任何读者可以从任何一张卡片阅读,可以读到任何一张卡片结束。读者不断的洗牌、阅读,也就欣赏了不同的小说,感受到不同的文本意义。这种洗牌的任意组合情节,就成了后现代拼贴手法的肇始。许多后现代作家将古今中外的不同小说情节储存在电脑中,任意点击,重新组合,再稍加润饰,就创造出一篇篇出人意表而令人惊叹的作品,由此造成快餐式、平面化的文学作品批量生产。
最后则是后现代作品中距离的消失。这里的距离既指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也指创作主体与客体的距离,还指作家与读者的距离。距离的消失意味着二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填平,界限的不复存在。在现代派作家看来,距离既是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而在后现代派作家眼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价值的颠复,作品失去了深度和历史感,仅仅成了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物,作品只强调欲望本身,也就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一切归于语言的游戏,游戏本身也就是游戏目的。如此一来,单一、平面化、欲望化的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由于一切意义的不复存在,后现代派作家的创作也就醉心于反讽、拼贴与蒙太奇的运用。他们在小说中,对所谓的历史事件进行随心所欲的“戏说”,使历史成为作家借题发挥的当下史,让真实性在嘲弄的戏说中被粉碎。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同时,他们也对富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与正面人物进行扭曲的夸张,让传统的正面影响在形式的变革中成为辛辣的反讽。当《南泥湾》这首歌颂陕北军民自力更生、奋斗自救的歌,被摇滚乐疯狂的节奏摇滚成欲望的发泄时,《南泥湾》还有什么革命的教育意义呢?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没有崇高,也没有价值,甚至连意义都是读者赋予它的外在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为所欲为地运用拼贴手段,将其它文本的片段、生活中的偶发事件,乃至新闻报导、报刊文摘拼接组合从而形成妙文,以此来嘲弄传统作家的精心构思是怎样的无意义,作品虚构的价值又是怎样的无聊。他们以任意拼接的作品打破传统小说凝固的形式结构,给读者强烈的陌生化震撼,同时也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得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将处于不同时空层面的场景任意衔接,根本不考虑内容形式的统一与完整,任由读者自己在故事的中断、叠化、对比、特写中发明无穷多的“意义”;用预设、追叙、插入等手法,增强对读者的感官刺激,取得强烈的冲击效果。总之,后现代将创作视为无规则、无意义的游戏,最终使文学创作走上了由唯形式到反形式,由唯技巧到反技巧,最后否定文学创作、否定文学作品的不归路。谁都是作家,谁都是读者,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艺术,都是创作。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消解,原本泾渭分明的范式都被打破,文学与非文学、读者与作家的鸿沟被填平,连意义与价值都不复存在。
(五)中国现实社会中颓废主义思潮使唯形式主义走向不归路
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旨的强调,国家调控能力没有完全丧失,这块土地上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也不典型。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毕竟降临,竟争激烈、一夜暴富、股市飚升、企业兼并破产、个体户纷起、农民工潮水般外流,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都从头开始。由此导致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人文精神危机”、乃至“生存危机”,席卷一代又一代人。这一切,对于涉世不深而又极度敏感的青年人的冲击更甚。尽管中国的后现代式颓废只在一部分人那里很火热,作品也不占文坛的主流,但后现代思潮激起的兴奋、引起的震荡,却是毋庸回避的事实。
1986年5月9日,在北京纪念“国际和平年”的歌星演唱会上,一个身披大襟,背一把破吉他的青年崔健,以一副沙哑粗放的嗓子,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顿时震撼了全场。那粗犷、猛烈、山崩海啸般的摇滚乐从此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它唱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无所有》唤醒了青年们压抑的“生命意识”,表达了他们深沉的失落、迷惘与颠狂。摇滚乐,使跃上文坛的新生代诗人更加疯狂、更加大胆地唱出心底的悲凉,发泄着心里的不满与愤慨。如崔健的歌词: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不是我不明白》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假行僧》
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
我说得多/也想得多/可越来越没有主意
我明白抛弃/也明白逃避/可就是无法分离
——《不再掩饰》
崔健的歌典型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后现代式颓废情绪。由迷惘到玩世不恭,由玩世不恭到借“艺术”发泄不满。于是行为艺术、网络色情文学、戏说历史影视、撒娇派、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妓女”作家都匆匆跃上文坛,显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随着这股颓废思潮的日甚一日,艺术上的粗制滥造、快餐文学的批量生产,也将创作上的唯艺术逐渐推向无艺术、反艺术的尴尬境地。不少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追求定格于“流动的语感,诗感,节奏感,哪怕是大白话。”他们宣称:“我们宁愿做平民诗人,也不要成为贵族作家”[5],由是,一种新的反艺术的美学观便油然产生。他们由认为“诗歌本身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产生美感”[6]47到鼓吹“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活计’,艺术家应该算作手工劳动者。”[6]81将艺术等同于工匠,也就否定了艺术美的创造意义。由此,他们坦言“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6]91,而且,“拿定主义要超越‘是’与‘非’的两极价值评价”[6]130,完全否定美丑标准,这也就为反艺术,以丑为美的艺术张目。“鲁西南群体”就公开放言,“我们拒绝那些所谓‘文化’,我们喜欢土地,悍气,我们歌颂生命,我们不会创造,只会随着自己的性子。”①参见: 《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39期.随着自己的性子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地冲击着文坛的圣洁,沾污着艺术的崇高,破坏着形式的完美。请看这样的诗句:“经一个女人介绍/出现两个男人//一个个儿高/一个个儿矮//个儿矮的白又胖/个儿高的黑且瘦//第一句话是胖子说的/第二句话是瘦子说的//胖子话少/瘦子话多//瘦子奚落胖子/观众哄堂大笑//……。”②参见: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之《相声专场》.在这里,诗失去了提炼,涂鸦式的自然主义耍贫嘴,没有一点深度,没有一点匠心。再看一首:“在风中点烟不容易/一根三根九根……/剩下最后一根火柴/我在犹豫/划还是不划/这是一个问题/划点不着/不划没法吸/结局与我想象的一样/它只燃烧了一下就熄了/我长出一口气/叼着完好无损的烟卷/在风中居然乐了/仿佛完成了什么。”③参见: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之《在风中点烟》.此诗苍白、平庸,既没有丰厚深遽的思想意蕴,也没有精巧的艺术构思。平面化叙述,造作的语言,大白话的排列,这样的“诗”,一天写一千首也不觉得累。有的评论者激愤地指出:“当前在中国诗坛上,一些诗人无视诗歌艺术最基本的创作原则,沉溺于对日常生活中无聊场景毫无诗意、流水账式的分行记录。把这种诗歌写作现象称为‘撒尿主义’颇为确切。因为这类诗歌表现或排泄出的正是一堆非诗意的东西。”[7]中国的这类后现代诗歌消解了诗歌,也消解了艺术。他们终于从唯形式走向了诗歌创作的“胡涂乱抹”,走向了反形式、反艺术的极端。正如《诗歌之死》的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后现代作家们“艺术上则恶意消解诗歌秘密,以一种平面化的结构,单向度的叙述,快餐式的语义,睥睨文化。……人们担心新的恶劣的传统正在形成,如若真是,那‘诗歌死了’是无疑的。”[8]诗歌经后现代诗人的折腾竟如此糟糕,这对拥有“唐诗、宋词”,自诩为诗的国度的中国,这对于拥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东坡、辛弃疾、郭沫若、徐志摩、藏克家、艾青、贺敬之、郭小川等一批杰出诗人的中国,无疑是悲哀而又可怕的事实!
诗歌创作是这样,小说创作也存在这种情况。
马原、洪峰是用离奇的形式,让读者“遗忘”现实,突出小说形式的“博尔赫斯化”,使故事转向了叙事行为,使文本成了一个新的形式。这个独立构造的陌生化形式,让人们认识到语言的意指功能仅仅针对语言形式,“文学是从语言这种特殊的能指体系中派生出来的”[9],从而精心于语言的运用,形式的营造,以期形式本身产生较好的审美效果。而在一些后先锋作家手中,形式的追求逐渐走向了反面。叶曙明的《环食·空城》,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北村的《谐振》,乐陵的《板网》,杨争光的《土声》等作品,就以一种“反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对传统小说的挑战,他们有意抛弃故事与情节,淡化人物与个性,强调叙述语言的“话语”化、叙述行为的个人化,让小说着意整合个人感觉的碎片,罗列涌上心头的各种意识,造成了一种“拼盘式”小说文本的出现,由此再发展到木子李等人,形式与内容都不再刻意提炼,一切都似有实无,那种存心挑战传统小说的心态已不复存在,连什么是小说也都不再考虑。只是平面化地记录自己难以见人的隐私,告诉别人欲念满足的甜蜜与烦恼。《遗情书》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木子李从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创作。然而,这部点击率极高的网络作品却风靡了一批青年。《遗情书》完全消解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不考虑布局、悬念、结构、叙事角度、陌生化、反讽等手法的运用,任由拉杂的语言抖落自己难以启齿的隐私。文学还原于非文学,技巧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作者叙述自己与各种男人鬼混、上床的过程与感受。颓废主义思潮终于使文学在后现代颓废者手中变成了什么也不是的文字垃圾,拒绝了作品的责任,也否定了作品的形式追求。以致快餐式、平面化、非小说的作品批量生产,在局部范围内泛滥成灾。由此文学似乎就走到了它寿终正寝的尽头,呼唤新的理性力量使之复苏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形式主义的极至就是反形式,艺术性的“顶峯”就是无艺术性。这种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无法置疑的结局当然不是文坛的主流,但也该让文坛的探索者深长思之。
[1] 北岛. 谈诗[C] // 《上海文学》编辑部. 百家诗会选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42.
[2] 顾城. 凝视[C] // 《上海文学》编辑部. 百家诗会选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134.
[3] 康德. 判断力批判: 上卷[M]. 宗白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78.
[4]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M]. 高铦,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235.
[5] 程蔚东. 别了, 舒婷、北岛[N]. 文汇报, 1987-01-29(02).
[6] 徐敬亚, 孟浪, 吕贵品.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
[7] 宋辉珍. 撒尿主义: 对当前一种诗歌写作现象批评[N]. 太原日报, 2000-05-29(03).
[8] 马策. 诗歌之死[C] // 杨克.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1: 135.
[9] 罗兰·巴尔特. 文学与今天[J]. 张小鲁, 译. 上海文论, 1987, (6): 47-48.
Study on Literary Trend of Unique Formalism and Decadent Literature
WU Jiar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China 230039)
Developing through the Obscure Poetry, th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ill the Pioneer Novels, new-era literature has changed prominently in formal skills, but has never risen to the ontological status. Instead, a part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new human writers, bewitched by postmodern theory, has made the revolution of styles gradually walk into the dead end of unique formalism or anti-formalism, and as a result, the works ar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of decadent atmosphere. Thus, the call for a new literary rational spirit is imperative.
Formalism; Decadent Literature; Literary Trend
I206
A
1674-3555(2014)04-0001-10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4.00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3-11-14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BZW015)
吴家荣(1949-),男,安徽无为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