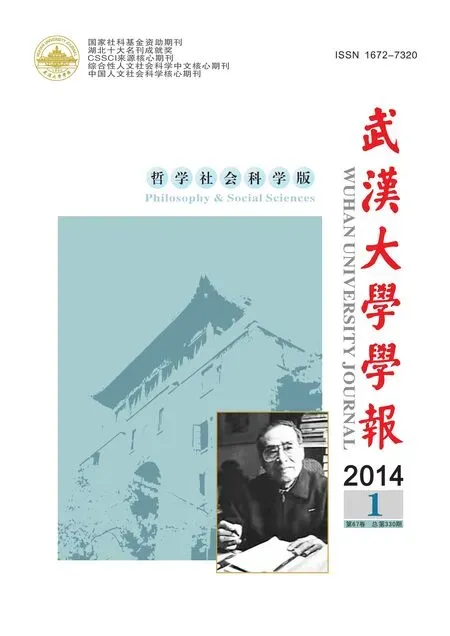从宋代妇女名字看社会性别文化建构
——以宋人笔记为中心
杨 果
一、前 言
姓名是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除了用以指代人群中的个体外,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如信仰、习俗、审美观、民族心理等。当代学者对姓名及其意义的研究比较关注,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有贯通性地考察中国人名的论著,如李学勤(1991)《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张孟伦(1988)《汉魏人名考》、萧遥天(1987)《中国人名的研究》、郑宝倩(1993)《华夏人名与中国文化》等,对中国古代人名的发展演变和命名形式、特点等进行了梳理、介绍。有对先秦至汉魏六朝女子名字特点及意义的分析,如田恒金(1998)《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刘增贵(2005)《汉代妇女的名字》、王子今(2004)《走马楼竹简女子名字分析》等。也有学者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探讨女性名字的变迁,如焦杰(2006)《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但是,有关唐宋以后女名的研究相当薄弱,迄今尚无专文,而唐宋恰是中国古代社会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女名的变迁有可能成为对“唐宋变革论”进行逼近的、细密的研究,使其免于“模糊影响之说”①台湾中研院研究员陈弱水语,参见其“唐宋连带研究”意见稿。《“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讨会简述》,2004年7月19日。的一个例证。
从资料上看,宋代私人撰述繁荣,现存的宋人笔记多达四五百种,因体裁自由、记述灵活,笔记保存了丰富的宋史研究的宝贵资料,类似女性名字这种相对边缘的记载在宋人笔记中有大量留存。有鉴于此,本文遂以宋人笔记为史料基础,兼及记载女名较集中的南宋法律判词和官府公文的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以及部分宋人文集等相关资料,对其中的女性名字进行统计、归纳,进而分析女性名字所蕴涵的性别文化意义。
二、宋代女性名字的统计与分类
据笔者初步统计,在《东轩笔录》、《青琐高议》、《能改斋漫录》、《墨庄漫录》、《梦粱录》、《碧鸡漫志》、《老学庵笔记》、《癸辛杂识》、《齐东野语》、《鹤林玉露》、《夷坚志》等50多种重要的宋人笔记,以及《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曾巩集》、《忠肃集》、《苏轼集》等宋人资料中,记载了当时女性名字、称呼共680余例①限于篇幅与刊物规定的新作注格式,相关统计表略去,文中出现的女名实例也不一一注明出处。资料来源请参见文末《参考文献》。,其中约150例属于“娘”、“婆”、“姑”、“姐”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特指作用的称谓,如(元)三娘、(李)二婆、(解)七姑、(翟)八姐。其余明确为女名者,约20例是有名并有字或号的,如名姬孙枢,字于仪;娼女曹文姬,号书仙;另外,大多数是有名无字号的。还有约20例属于虚构的鬼仙精怪类女子名字与称谓,在《夷坚志》一书里最为集中,如英华、道华、玉真道人、次心(字筝娘)、喜奴、进奴、千一姐。
从命名主体看,680余例女性名字、称谓中,自字自号者不过寥寥数例,其中为人熟知的如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脱脱,1985:13122),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况周颐,2009:110);另如金溪女子何师韫“号云韫道人”(洪迈,1981:1479),尚书黄子由妻胡氏“号惠齐居士”(周密,1983:183)。此外的绝大部分女名属于他命名,多数是由其出生家庭命名,或由其出嫁家庭(丈夫)命名,贱籍女子往往由其人身所有者命名。
从所属阶层看,身分可明确者570例,包括皇室女眷、宫廷女官如马兰秀、看经刘娘子等293例,仕宦家妻女如晁德仪(字文柔)、吴嗣真(字道卿)等52例,普通民妇民女如鲍娘、姜添福等100例,侍妾如怜怜、惠柔、婢女朝云、采苹等57例,公私妓女如宫花、陶心等58例。另有多种民妇,如商妇甘百十,当垆女侑觞,浣濯妇赵婆,乳母任采莲,乳医赵十五嫂,女巫圣七娘,女侩施三嫂,女使进喜等10例。
三、女性名字反映的社会性别文化建构
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宋代妇女的名字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女性气质”的名字是当时妇女命名的主流。尽管对于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的界定,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的主流文化中大同小异。比如,一般认为男性的特点是阳刚、独立,女性的气质是阴柔、顺从。人们通过有意识地区别和建立身分边界,来强调不同性别之间的“共性”尤其是“异质性”。表现在女名上,则是命名者根据自身与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期待,给女子选取具有女性特征的名字,赋予其特有的性别角色含义。在宋人女名上,它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对女性生理性别的突显,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对女性内在品德的规定和对女性外在姿容的期待。
(一)对女性生理性别的突显
女性人名的外在形式和结构都与男性人名有明显区别,强调女性的生理性别。
在字形的选择上,带女字偏旁部首的字词,如娘、娥、姬、媛、妙、媚、娇、妍、奴等是宋代妇女命名的常用字,有金姑、月姊、真姬、月娥、妙婉、淑媛、巧姝、花媚、娇奴等。选用这些字,能直接表明个体的性别身份。宋人喜称年轻女子为“娘”,因此命名为“(某)娘”的为数众多,有数字加“娘”者,从一娘、二娘到五十娘至百二娘,多种数字不等;有形容词或名词加“娘”者,如媚娘、瑞娘、真娘、秀娘;有动词或名词加“娘”者,如意娘、睡娘、插娘、息娘,其主要用途都只在于表明被命名者的女性身分。
在字音的选择上,宋人喜用叠音,如师师、田田、惜惜、莺莺、珠珠、巧巧、袅袅之类,不仅意在婉转入耳,更在彰显女性的娇柔和乖巧。宋人女名也隐含了性别身分。语言学研究者(纳日碧力戈,2002:165)指出,一般情况下,汉语音韵十三辙中的一七、姑苏等音色细弱,而阴平声调听觉清脆,如玉、媛、娇、花、云、娴等。这些字也正是宋人女名的多用字。
在字义的选择上,宋代女名更突出地强调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将女性的生理、性格等规定为“阴柔”的特质,女名的选用也因而多用表示阴柔的字词,如柔、静、娇、婉等,有娇奴、顺淑、静珠、文婉之类。以花草云月字命名,如秋月、香云、弱兰、樱桃等,也主要是强调阴柔、甜美的特性。
女性的名字与社会文化所认定的女性生理特征相一致,不仅用来指代女性的生理性别,更成为女性的社会性别符号。
(二)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
首先表现为大量的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本身就是社会性别分工的反映,因为名字“产生于社会交际的需要”(纳日碧力戈,2002:1),“定位乎内”的女子自然不必有名。女性从基本符号上就被社会边缘化了。多数女性仅以“某某女”或“某某妻”等代称行世,这是“由于古代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无独立地位”;女子出嫁后称姓不称名,不过“是避免同姓婚媾的一个措施。”(纳日碧力戈,2002:143)
其次,为数众多的指代性称谓婆、姥、媪、嫂、姑、姐等,也表明了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这类称谓使用的范围上自帝王嫔妃,下至普通民女,十分普遍,前者如兰姑、和姑、柳姊,后者如(李)媪、(徐)十八婆、(邓)八嫂等。这些是用性别、年龄和家庭角色来指代妇女,结果是使得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形象被湮没无闻。
再次,留存下来的女性名字,往往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联系在一起。例如,贵族女子常以闺阁物命名,如玉屏、檀香、璎珞、串珠等。职业民妇的名字多带有性别分工的色彩:酒肆当垆女名侑觞;女使名进喜;乳医与巫婆、洗衣妇同类,通常没有正式名字,只被称作老娘、四娘、十五嫂、婆之类。伴随着宋代声伎业的繁荣,娼妓的名字琳琅满目,那些用以取悦嫖客并多半出自于嫖客的妓女名号,字义读音堪称女名中最美妙动听而又充斥情色意味的一类,或名慧、美、柔、盼、惜惜、赛赛、盈盈、韵可人、白牡丹,或字才姬、仙才,或呼书仙、娇娘。娼妓的名字对妓女自身而言,是她们谋得生存的一个辅助工具;对男性命名者来说,则是他们各种欲望的载体,他们借由为娼妓命名,把自己对女性容颜、姿态、才情等诸般欲望尽情地挥洒到妓女的身上。
复次,在宋代女名中,“奴”字的使用频率很高,涉及到各个阶层,在嫔妃、婢妾中尤为集中。如徽宗的嫔妃有近20人以“奴”为名,三宝奴、红奴、月奴,金奴、阿奴、星奴、富奴、娇奴、元奴、香奴、小奴等等;而在57例婢妾名中,称“奴”的就超过了10例,如馨奴、柔奴、均奴、庆奴、宜奴等。“奴”属贱称,张舜徽先生(2009:3040)指出:“古者奴隶易逃,奴字从又,所以拘执之也。此与奚字同意。大徐以持事解从又之义,非也。古文从人从女,女旁有人,即所以监守之也。”“奴”字代表着地位卑下,受人役使。女子以“奴”为名,无疑是用来表明其在主人面前的卑微。即使贵为嫔妃也不例外,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男性君王的享乐需要。可见,尽管有着贵贱、贫富等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女性比之于男性是身分地位卑下的。
(三)对女性内在品德的规定
综观宋代男女人名,不难看到,宋人命名注重从道德上对两性加以区分。主流文化认为男性的美德在于刚强、果敢,女性的美德则是贤惠、柔顺。因而,在女名中,“淑”“静”“柔”“惠”“巧”等标识妇德的字样占有很大比例,如皇帝嫔妃名顺淑、温和、蕙卿、灵好、心香,宗室女子名懿、善、惠仪、淑媛、巧姝,士家女子名琬、淑、德静、德仪,侍女婢妾名惠柔、惠英、意真、柔奴,妓女歌姬取名婉卿、弱兰、慧、媛等。女子的字号也常见柔、淑等,如晁德仪,字文柔;曾德耀,字淑明;曾德操,字淑文。以妇德字作为女名,寄托的是家庭期望女子恪守妇道的心愿,遵循的是社会要求女性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等妇道规范。宋人正是通过美化妇女内在品性的方式来强化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依附、顺从的特质。
叠音字的使用也蕴涵着对女德的规定。两宋时期这类女名多数使用在嫔妃、侍妾以及妓女身上,仅徽宗嫔妃就有袅袅、拂拂、巧巧、珠珠、癸癸;侍妾则如莺莺、怜怜、安安、端端、酥酥儿;妓女则有惜惜、赛赛、师师等。以叠音字命名前两类女子,体现的是宋人对充当特殊角色的妇女所应具备的娇嗔、狎昵这类特殊“妇德”的期待;用叠音字称呼妓女,则反映出这类女子作为商品,必须满足购买者的玩赏欲,这是一种特殊市场交换中的“道德”,骨子里也寄托着一种对“妇德”的原始性期待。这类被赤裸裸物化的“妇德”,与主流文化所张扬的贤妻、良母、孝女、顺妇之类妇德一道,共同构成宋人对不同类型的妇女所应具备的不同内在品德的规定。
(四)对女性外在姿容的期待
主流文化要求女子外形庄重、洁净,因而女名或称仪真、观音,或称淑静、道清。但是,在留存下来的实例中,更多的是形容女性娇艳的名字。有关这一点,在徽宗对其嫔妃的命名上表现得最为突出。680余例宋代女名中,徽宗嫔妃名近130例,其中柳腰、蜂腰、月媚、花媚、香奴、娇奴、袅袅、拂拂之类的香艳名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还有猫儿、弄玉、醉仙桃、小娇奴等带有玩亵意味的名字,以及月里嫦娥、赛莲花、一翦红之类不乏轻佻色彩的名字。其他各类女名也都少不了对女性姿容的描摹,如宗室女子名艳、细眉、芳姿、舞蝶,家姬侍妾名酥酥儿、怜怜、莺莺、眄眄,娼妓名美、柔、妙、秀、韵可人、白牡丹等,仕宦家女子则有名“花不如”者。这些名字都刻意表现女性具有妖美冶艳的特性,这在骨子里还是视女性为观赏物,用来满足命名者对女性的幻想,正像周煇(1994:390)所说:“士大夫昵裙裾之乐,顾侍巾栉辈得之惟艰,或得一焉,不问色艺如何,虽资至凡下,必极美称,名浮于实,类有可笑者。岂故矜衒,特偿平日妄想,不足则夸尔。”夸饰溢美女性的容颜,不过是用来满足男性心目中对所谓“美女”的“平日妄想”。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宋代妇女名字主要是按照社会性别文化有关妇女的规范来命名的,其主要功能是标示所谓的“女性气质”,甚至是将女性物化,女名因而成为妇女社会性别的符号。
四、结 语
名字这一语言符号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宋代女名从总体上看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气质,所标示的不仅是女性作为女人而存在的自然属性,也标示着女性作为女人而存在的社会属性。这种“女性气质”是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是宋代社会按照其主流文化要求而设定的女性标准形象,反映的是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男性精英群体的要求。
宋代妇女命名的形式和结构大体继承前朝的基本趋势,又有自己的特殊发展历程。尽管从总体上看,宋代女名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气质,但仍有一些女性的命名规律与男子有相似之处。譬如:寓意倾向于中性或男性化,如女名好郎、金男、仲贤、三福、德耀、希孟等,不仅体现了家庭对男性后裔的期盼,更是将像男子一样成就功名的梦想寄托于女子之上;再如,用字排行与家中男子相同,如关景华,与其兄弟景棻、景元、景仁等皆共享“景”字,女子与男子一样进入家族排行,共同体现着显亲敬祖、昌大后裔的宗族观念;另如,名字与个人信仰、特长等相连,如佛迷、神佑、铁笛、咏絮等。这反映出尽管社会性别文化在宋代已经成为主流,但仍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变通性,性别刻板印象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以性别气质为主要特色的女名与当时的女性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及其变迁相伴相随,呈现出宋代两性关系胶着、博弈的特征,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性别秩序逐渐固化的历史基本走向。
宋代女性的命名方式体现了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社会性别文化正是通过命名,对男女性别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强化对男女角色模式的认同,实现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清理这种“性别气质”建构,有必要反省社会制度与结构秩序,清除性别气质相互对立的观念。
[1] 焦 杰(2006).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6.
[2] 李学勤(1991).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5.
[3] 刘增贵(2005).汉代妇女的名字;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 纳日碧力戈(2002).姓名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5] 田恒金(1998).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河北师大学报(哲社版),3.
[6] 王子今(2004).走马楼竹简女子名字分析.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7] 萧遥天(1987).中国人名的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8] 张孟伦(1988).汉魏人名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9] 张舜徽(2009).说文解字约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0]郑宝倩(1993).华夏人名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蔡 绦(1983).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2]陈师道(2007).后山谈丛.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3]范成大(2002).范成大笔记六种.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4]范仲淹(1985).范文正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5]方 勺(1983).泊宅编.许沛藻、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6]费 衮(1985).梁溪漫志.金圆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洪 迈(1981).夷坚志.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8]洪 迈(2005).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况周颐(2009).蕙风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刘 斧(1983).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1]刘昌诗(1986).芦浦笔记.张荣铮、秦呈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2]刘克庄(2008).后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3]陆 游(1979).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4]罗大经(1983).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5]孟元老(1982).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中华书局.
[26]欧阳修(1981).归田录.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7]確 庵、耐 庵(1988).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北京:中华书局.
[28]司马光(1989).涑水记闻.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9]邵伯温(1983).邵氏闻见录.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0]宋敏求(1980).春明退朝录.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1]苏 轼(1986).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2]脱脱等(1985).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33]王 栐(1981).燕翼诒谋录.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4]王辟之(1981).渑水燕谈录.吕友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5]魏 泰(1983).东轩笔录.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6]吴处厚(1985).青箱杂记.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7]吴自牧(1980).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38]叶梦得(1984).石林燕语.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39]佚 名(1987).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40]曾 巩(1984).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41]周 密(1983).齐东野语.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42]周 密(1988).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43]周煇著(1994).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44]朱 彧(2007).萍洲可谈.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