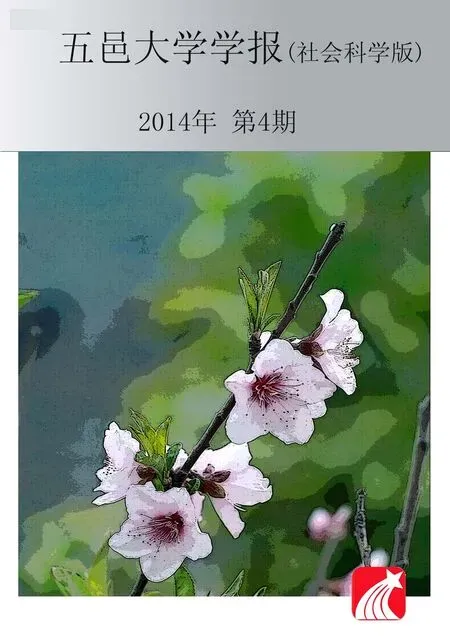罗瘿公诗歌的精神世界
冯珊珊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罗瘿公(1872-1927),名惇曧,号瘿公、瘿庵、掞东等,以“瘿公”号行于世,广东顺德大良人,庚子事变后旅居京师。瘿公雅擅诗歌,其传世作品有《瘿庵诗集》(卷后附《瘿庵诗外集》)、《赤雅吟》等诗集,另有集外诗近百首,散见于近代报刊中。他与诗人梁鼎芬、曾习经、黄节并称“岭南近代四家”,与其堂弟、著名诗人罗惇并称“顺德二罗”。以上诸人又与晚清民国著名诗人王闿运、陈宝琛、樊增祥、林纾、陈三立、陈衍、易顺鼎、郑孝胥、赵熙、黄濬等人同为庚戌、辛亥诗社等京都雅集的主要成员,也是1913年梁启超在京举办的万牲园修禊活动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见罗瘿公诗歌的卓越水平。
当前学界对罗瘿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其京剧创作状况和他与程砚秋的关系,相关成果有朱文相《罗瘿公生平及剧作资料辑录》、《罗瘿公与程砚秋》,姜德明《罗瘿公与程砚秋》,董昕《罗瘿公对程派艺术形成的作用与价值》,韩洁《程派私家剧本研究》,颜全毅《文人京剧创作与“角儿”演剧风格创建的合力与难题——以齐如山、罗瘿公为例》、《罗瘿公京剧创作叙论》等。而罗氏之生平,及其诗文创作、学术成就和政治实践,均有待进一步探究。尤其是其早年诗作的散佚,导致今天几乎不可能对他的前半生详细考述。幸运的是,现存诗作寄托遥深,反映了他穷困潦倒的人生境况,关心国运民生、愤世嫉俗、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和寄迹梨园的隐幽情怀。诗人旅居京华时期的生活、交游、思想状况,亦可从《瘿庵诗集》与其集外诗中窥豹一斑。
一、嬉笑怒骂人间世,兴废荣枯笔下知
通都大邑,正是一国政治中心,旅居京华的罗瘿公目睹了诸方势力在这里一番又一番的粉墨登场。其《兵后问樊山翁起居,翌日翁过访投诗,次韵敬和》云:“同居石火流丸地,是我槐荫午睡时。举国未成三日酺,长安又了一枰棋。吾生四海能无事,共和尧夫击壤诗。”该诗讽张勋复辟①,起笔直叙争战情景,令人惊忧之情顿生;续以“槐荫午睡”,情境陡转,仿佛“石火流丸”只是梦中景象,实则不然。梦中争战是假,人间涂炭是真。诗人有意用典,在他看来,张勋等人汲汲追求的“复辟”之举,不过是《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的黄粱美梦,转瞬即逝。乱世人生,如梦似弈,波澜叠起,而这名利的争攘、权势的代谢,虽然作者举重若轻,结尾未尝不透露出诗人对海清河晏的殷切期待。
不唯国家权势令人觊觎,一官一职之名利亦令人智昏,如《长沙张文达公灵輀南下志哀三首》其二:
忆昔辛壬间,筹学集众谤。忧危耿不寐,委曲跂一当。积诚恃信主,卓绝赖冥剙。于(式枚)黄(绍箕)文章宗,吴(汝纶)严(复)天下望。汪(诒书)王(仪通)号博物,张(鹤龄)李(希圣)实宗匠。五百识聚贤,时流孰堪抗。屹立镇骇流,百川此东障。侁侁生徒会,天门开詄荡。群材待陶甄,皇风日敷鬯。志未竟十一,孤怀冀谁谅。万方悲一概,山颓吾安仰。[1]2
是诗所述,即1901(辛丑)年至1902(壬寅)年间,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之事。当时国债累累,疮夷满目,百废待兴。罗瘿公《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云:“回銮后,筹大学经费。中国先与俄国合办东清铁路,岁给中国利息银○○(原稿如此)万两,积存华俄道胜银行,共○○万两,百熙奏请拨充大学经费……庚子后一大新政,只有学务,乃以属百熙。有用人之柄,复掌财权;既杂用外吏,又薪俸厚,羡妒者多。诸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蜚语浸盛。荣禄、鹿传霖、瞿鸿禨在枢府,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谤谄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百熙直南斋久,宫廷信其谨厚,无他肠,惟召对时恒训诫之而已。忌者必欲摧锄大学,目为革命之府,人争为大学危。百熙苦心支拄,力任群谤,大学赖以存。”[2]罗瘿公咏时事诗,多隐晦冷峻,不直叙本事始末。是文所述,恰是对本诗自作郑笺。权要之辈祸国殃民尚且不以为耻,教育之兴废又从何谈起!
国事如此,人情亦如此。其《长沙张文达公灵輀南下志哀三首》回忆恩师生前情形:“去年寿觞举,冠盖倾一国”,何其壮阔!及至恩师谢世,“今年素车来,杳不盈什一。”[1]2生死喧寂、世态炎凉,变换之急速,不言自彰。他洞达人世的纷争,参悟了盛衰之变。辛亥革命欲取消帝制,曾习经(字刚甫)为明善始善终之志,于宣统帝退位前一日辞官归隐。罗瘿公赋《晨起偶成示刚甫、翙高、毅夫》云:“暖旭觚棱散积阴,花前负手费沉吟。经过忧患供谈笑,吟望溪山变古今。春鸟丁宁思早计,故人慷慨谢朝簪。东门帐饮知无绪,揽结河桥柳十寻。”[1]9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只有寄情于诗,嬉笑怒骂罢了。因而钱仲联先生说:“罗瘿公诗歌的重要特点是反映了这位才丰遇啬的知识分子的客观境界和内心世界,颓放的诗笔描绘了‘新儒林外史’的一些景象”[3]。
二、宣南雅集驱车毂,江湖况味驰笔书
京城人物盛集,罗瘿公日与文人雅士相过从,或结社赋诗,或煮酒论史,如其诗所述:“春明诗社盛宣南,日叩招提啜茗谈。一老贞元知旧事(陈弢庵),几人弥勒证同龛。看花走遍城中寺,画卷林逋吸翠山(林畏庐)。”[4]崇效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法源寺的丁香、花之寺的枣花……宣南花事、京都名园、林间古刹、画中山馆,和着对世态人生的品味,无一不入于诗。黄节云:“瘿庵之为人,若无所用其心者,然亦时有忧生之嗟。”[1]序登览游赏、结社赋诗虽是骚人墨客的雅趣,在忧时伤世的罗瘿公心中,更是一种消减郁结,暂求解脱的方式。
本文所设计的机械臂是基于弹簧连杆机构的静平衡原理,如图3所示。机械臂整体结构由2个弹簧连杆机构串联而成[17]。在弹簧弹性范围内,通过机械臂,工人可以毫无负重感地支撑重型工具。
生于乱世,眼见“旧日江山付霸才”[4],他常有劫里逃生、朝不保夕之感,正如《天宁寺赋呈石遗叟》借风后牡丹喻乱世云:“人世哪可料,风起红妆退。”[5]乱后游览旧日园林,使他不禁生发“重来已觉千林改,逃劫能添一噱资”[6]的喟叹。闲暇时候,他曾与王闿运、陈宝琛、杨宗稷、李希圣等人谈论晚清历史,更每每于诗中记述他所目睹的社会治乱。正是得益于此,罗瘿公才书成《宾退随笔》、《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等掌故史书。他曾言“胸罗国故关兴废,莫作寻常野史看”[1]22,抒发了他借乱世之史垂戒后世的希望。
罗瘿公有诗云:“接坐花光荣四照,停杯茗话散千忧。”[7]其诗常借乐景写悲情,如《尧公招集法源寺》云:“小坐春风啜茗谭,长安花事数精蓝。眼前景物丁香占,劫后风光老衲谙。似水年华过浴佛,故乡桑柘正眠蚕。时危哪更知来日,且可勤来共一龛。”[8]即使居身锦簇花团之中,盛衰之变、流离之感、朝不保夕之忧仍难释怀。无怪乎其《吊寄禅和尚》云:“酸辛我岂免,亦曰有情故”[1]10。
时局动荡使人心忧自怜,生老病死更令人伤怀。罗瘿公除了与友人唱和赠答之作,还有许多悼念故友的诗篇。其《春尽日蛰庵招同崇效寺牡丹花下饯春因呈病山京兆》云:“昨夜东风取春去,荒庵留得一分花。寂喧车马从僧说,迟暮园林况日斜。孤艳风前宜自惜,故人地下足长嗟(罗瘿公注:客岁丁叔雅同游今宿草矣)。使君莫靳深杯醉,尚有楸英殿物华。”[9]夕阳虽好,终近黄昏。罗瘿公只能婉言宽慰友人,“漫劳书札劝加餐”[4]。
除此之外,为自己无力改善现状而无奈、惭愧,也是罗瘿公诗歌精神的一脉琴弦。他屡屡于诗文中感念恩师张百熙,事实上,也只能感念罢了。面对前来投奔的恩师遗孤,罗瘿公泫然泣下:“握手相看泪不收,北来知汝困粱谋。一尘无地容孤托,广厦当年庇万流。玉垒浮云伤北极,石桥斜日怆西州。负薪未敢呼优孟,惭愧年时旧辈俦。”[10]文人自愧不如优孟,其悲哀可想而知了。其《追悼顾印伯即题其遗诗》云“八表同荒悲路阻”[1]12,又如其《晏起》云:“富贵原关命,奔腾空尔劳。殉名终近祸,耽懒误成高”[1]20,又何尝不是一种怀才不遇、无路可走的无奈与悲哀?正是因为无力改善现状,他只能自我安慰,期待海清河晏的到来。其外甥麦孟华卒,罗瘿公挽诗云:“期君忍须臾,天地或清澈。”[1]16一个“或”字,亦表明了诗人心中的希望似有还无,只不过聊以自欺罢了。
罗瘿公之诗,虽于时弊多用隐晦之笔,然沉郁顿挫之外,亦有崭露锋芒、愤世嫉俗之时,故为权势者所不容。其《伯芗自黔驰书吾所,亲言得都中书,谓余已得狂疾,寄此慰之》云:“久已世人皆欲杀,竟能容我醒而狂。学书倘到杨风子,浪迹便随元漫郎。官里捉将终幸免,面皮受打定何妨?(罗瘿公注:高爽题延陵县阁下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三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见《南史·卞彬传》)黔山万里劳相问,颠草还应报数行。”[1]15融性情于浓墨,诉真情于笔端,这也许就是罗瘿公嘱托陈三立以“诗人罗瘿公之墓”为其题写墓碑的缘由吧。
三、庙堂山林两难计,驰情鞠部岂是痴
罗瘿公遗嘱云:“不喜科名,官职前清已取消,述之无谓也。民国未入仕,未受过荣典,但为民而已。如公府秘书、国务院参议上行走,及顾问、咨议之类,但为拿钱机关,提之汗颜,不可陈及。”[11]事实上,他并非无意出仕。不仅仅因为他原指望靠“鹤奉”养家糊口,还因为罗氏家族原本世代簪缨,罗瘿公从以“经世致用”为育人之旨的广雅书院走来,他的心灵深处也希望能够为国所用,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不仅官位卑微,而且多难长久。
罗瘿公之所以多次于诗中对张百熙深表感激与怀念,不仅仅因为张百熙佳言懿行、求贤若渴,更因为张百熙对他有知遇之恩。其《长沙张文达公灵輀南下志哀三首》对探讨罗瘿公的仕与隐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三云:
汪汪千顷波,日月互吐纳。公存士气申,公殁正气灭。王路失清夷,履蹈莽荆棘。文采致为灾,直节终自贼。嗟哉受恩人,渺若非素识。悠悠天地间,念此心魂折。吾生绝知己,谁更念薄劣。还当慰公灵,益励岁寒节。[1]2
罗瘿公入京未久,即遇京师大学堂筹办之事,正是张百熙提携他做了编书局编纂。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官场的名争利攘,恩师的管学大臣职务最终被追求名利者荣庆取代。荣庆排挤张百熙所用人员,使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又陷入困顿。故罗瘿公于《志哀三首》其二中感叹:“志未竟十一,孤怀冀谁谅?万方悲一概,山颓吾安仰?”[1]2这充分说明了罗瘿公与众多怀才之士原本寄希望于得遇知人善任之人以施展抱负,可惜晚清朝臣大多唯名利是瞻。张百熙的逝世使他痛失伯乐,怀才不遇,这是他在仕途上遭受的打击之一。
14年后,他作诗《赠韩力畬》,回忆同仁及京师大学堂筹办往事。诗云:
接席回思十四年,荒寒事业不殊前。虎坊桥屋今谁主,雁影斋诗赖尔传(罗瘿公注:“大学堂编书局初设于虎坊桥,余与力畬同任编纂,李亦元希圣亡后,力畬辑其遗诗,叙而刊之。”笔者按:罗瘿公《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载:“李希圣为编局总纂”,“百熙深倚沈兆祉、李希圣”,及至荣庆为管学大臣,“深恶希圣,希圣旋病殁”)。同局几人夸九列,长沙一老痛重泉。袖中不敢陈封禅,耐守黄齑也自贤。[1]18
首联即奠定了沉痛、忧愤的基调。14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令人心伤,国家毫无起色的“荒寒事业”更令人扼腕。曾为众多有志之士所仰仗的张百熙,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也已与世长辞。留在世间的人又能如何呢?“袖中不敢陈封禅,耐守黄齑也自贤。”这是作者“浮云阅尽长安变”[1]11之后,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也是作者不汲汲于阿谀奉承、有心归隐的一条佐证。
罗瘿公的诗中看不到他对革命的热情,如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为杨宗稷(时百)题《琴粹》时说:“今年真笑立锥无”,“山河破碎从公等,门巷荒寒称老夫”。[1]11在他看来,“革命”只是王公大臣等权势之流以名利为目的的争持罢了,于国家、平民并无利益。袁世凯的阴谋残暴,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潘若海等师友为变革、“倒袁”而奔波逃亡,无一不加重他对时代的失望。
这种认识与失望,自然使他更无意于入世为官。国家兴亡之因由,江湖况味之变幻,使他早已参透了功名利禄,更看透了才华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他喜用《庄子》典故入诗。他给桂埴(东原)寄诗云:“欲以佉庐穷道窍,未能槁木丧今吾。当年漆室忧天坠,留命桑田看海枯。”[1]11又于《题潘若海麦孺博遗墨》中愤愤地写道:“移山岂有神能助,衔石应无海可填。始信魁材非世用,诚知社栎以天全。吾生宇内成孤寄,头白歌场只放颠。”[1]51这是时代给予他的生存法则,孤独、不遇使他残缺的归属感化作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逸抉择,化作了“头白歌场只放颠”,即“戏隐”的人生道路。
戏曲首先为他朝不保夕的忧患生活带来了几多欢愉。其《扰扰》云:“扰扰名利趋苦恼,纷纷蛮触自争持。终年听曲行吟处,尽是先生快活时。”[1]30又如《丁巳除夕》云:“差幸听歌无间阻,不知来岁定何如。”[1]28同时,戏曲也给予了他施展才华的空间。他结识了诸多梨园名伶与票友,遂有“日夕歌台逐年少,憎爱强分评甲乙”[1]21等记载他与伶人交游的诗句,以及记载了大量梨园掌故的《鞠部丛谭》一书。不仅如此,从1915年认识程砚秋起,他开始倾心栽培程砚秋,不仅为其延师授艺,还亲自教程砚秋作诗和书法,甚至为程砚秋编写了十余个剧本,在当时颇有影响,故黄节评罗瘿公云:“放怀自有平生志,听曲看花亦绝伦”[12]。但这些剧本题材多非作者原创,是罗瘿公为了扶植程砚秋,结合程砚秋的气质与唱腔、观众的嗜好与趣味,就古传奇、杂剧改编而成的。所以,剧本中体现的思想,更多的源于原著作者。研究者不宜忽略罗瘿公改编者的身份,忽略原创者的思想,武断地为罗瘿公的思想贴上批判封建制度、争取妇女思想解放等标签。但不可否认,罗瘿公之戏瘾,异于清末民初文人士夫之狎妓。他非沉湎于声色之欢愉,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罗瘿公《焕廷示樊山听曲诗,笏卿、惺樵、治芗并有和作,依韵呈一首》云:“听曲自编为日课,隽谈时足补阳秋。晓风残月歌三变,淡饭粗茶学四休。”[1]50“四休”即“四休居士”,系黄庭坚邻居,性格豁达,淡泊名利,曾云:“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两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13]无论是自比柳永,还是自比“四休居士”,均说明罗瘿公晚岁自甘清贫平淡,已做了梨园隐士。
四、安贫乐道丰于义,穷而后工兴于诗
罗瘿公摆脱了名利的羁绊,以卖文鬻字为生;寄迹梨园,以听曲编剧为乐。他的诗呈现出了安贫乐道的精神风貌,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集法源寺为陈后山逝日设祭》云:
工诗固多穷,人自穷非诗(原注:后山句)。力与文字远,未必富贵随。后山奇穷者,风义照一时。平生尊坡谷,坐此迫寒饥。沦谪百不悔,冻死天下知。落落二三子,遐躅勤摹追。相携就兰若,酹以酒盈卮。寒风迫除岁,蔬果僧为治。欲招千载魂,同慰平生思。霜竹摇暝阴,贞松挺寒姿。似参曹洞禅,试语参寥师。[1]15
他在盛赞陈师道之余,可谓赋诗明志。此时的生活亦令他欣慰有加,其《夜坐》云:“平生不负听歌耳,渐老能雄作诗胆。……筋骸作健天所骄,眠食自足吾何欠。”[1]42又如《逭热》云:“此心清静为真乐,说与朝官恐未知。”[1]49早期的忧愤疏狂与沉郁冷峻皆已淡然,一如诗歌经历唐诗的绚丽秀拔后归于宋诗的平淡超脱。最能代表他此际心境与人生感悟的是《答客问》:
有客叩门屡不值,每向吾友三叹息。谓我昏然废百事,苦伴歌郎忘日夕。吾友来致词:“君已鬓成丝。立名苦不早,乃逐少年为。黄金未足惜,毋乃心神疲。”我言何者为事?何者谓之名?簿书非吾责,米盐非吾营。既不求官不求富,廓落乃以全吾生。海宇奚为不清宁,尽坐名利相搆争。得时作公卿,失志煽戎兵。长此大宙何由平,既不爱博进,亦不游狭邪。关门著书太自苦,终覆酱瓿何为耶?积金将以贻子孙,能知子孙贤不贤。作书觅句吾不废,聊遣兴耳安用传。吾釜不生鱼,何为计锱铢。本无组绶缚,何必礼法拘。清歌日日吾耳娱,玉郎丽色绝世无。但知坐对忘昏晡,安问今吾与故吾?世人但学子罗子,知鱼兴耳忘江湖。[1]31
这首诗呈现了洗尽铅华之后的质朴与纯真,历经忧患之后的通达与恬淡。诗中言语平常如话,率性而为。观其气貌,文思流畅,自然圆融,看似不思而得,却又言简意赅,抒发了作者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于诗文戏曲中俯仰自乐的心境。
罗瘿公关心国计民谟,其诗作更表现出独到的眼光与敏锐的感触。清末民初的外忧内乱、国朝更替、名利扰攘、人事纷争,乃至于风云雨雪的代谢、草木鸟兽的变化,在他的笔下都牵动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重重思索。仕途与家居的穷困潦倒对于不汲汲于名利的人而言,未必是沉重的打击;然而国运民生的疲病与灾难对于目光犀利、思想深邃的人而言,却是一种无法消释的精神枷锁。他生于忧患,富于才情,却又仕途偃蹇,无力于乱世之中挽狂澜、扭乾坤。他兼具诗人、史笔、编剧之才,却只能于史料笔记、梨园掌故中直笔存史,于听曲编剧中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只有诗才是他慷慨抒怀、驰骋神思的精神园地,只有诗才是其精神最直接、最精深的体现。读其诗,方知其爱憎与忧乐;读其诗,方见其痴狂与超脱。
近人王赓《今传是楼诗话》云:“老友罗瘿公,负诗名三十年。其《香山雨香岩杂诗》云:‘清晨自课踏清峦,小住能令腰脚顽。莫笑老夫忘世事,爱将朝局当云看。’余最喜诵之。”[14]由此评论不难推想,瘿公于随意吟哦之间,引发了时人的共鸣,为今人了解清末民初的士人心态打开了一扇窗口。
注释:
①黄濬云:“瘿公丁巳有《兵后问樊山翁起居》诗,中云:‘同居石火流丸地,是我槐荫午睡时。举国未成三日圃,长安又了一枰棋。’即咏复辟”。参见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69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参考文献:
[1]罗惇曧.瘿庵诗集[M].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1928.
[2]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J].庸言,1912,1(13).
[3]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536.
[4]罗惇曧.送温毅夫南归[J].庸言,1912,1(11).
[5]罗惇曧.天宁寺赋呈石遗叟[J].国风报,1910(15).
[6]罗惇曧.雪后自岳云楼至江亭同尧琴书衡仲骞[J].庸言,1912,1(9).
[7]罗惇曧.春郊[J].国风报,1910(8).
[8]罗惇曧.尧公招集法源寺[J].国风报,1911(14).
[9]罗惇曧.春尽日蛰庵招同崇效寺牡丹花下饯春因呈病山京兆[J].国风报,1910(13).
[10]罗惇曧.张稚野释服入都相对凄泫次日书来宛然先师手迹怆然为赋[J].国风报.1910(22).
[11]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225.
[12]马以君.黄节诗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37.
[13]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238.
[14]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