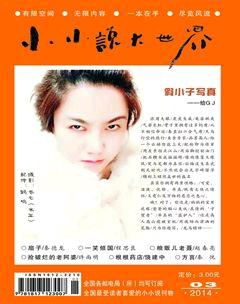粮贩儿老聂
赵春亮
老聂大名聂圪针,但这个名字除了在户口本上显示,几乎没人使用,侯兆川上至耄耋老人下到黄口小儿,一律喊他老聂,聂圪针这个名字连老聂自己都快要忘记了。有一次老聂去县医院看病,挂罢号,坐在长椅上等。医生喊号:“聂圪针。”连喊三遍没人应,只好叫下一位。老聂等半天没人理他,才一拍脑袋焕然大悟,娘的,我就是聂圪针啊!
在侯兆川这块地界上,老聂大小算个名人。侯兆川辖四个乡镇近百村庄,方圆三十平方公里的老少爷们大都认识他,你说算不算。
说他是个名人,老聂不承认,说:“我算哪门子名人呀,就是一人名,一个粮贩儿。”
老聂贩粮食贩了十多年,从拉着板车走街串巷,到开着“奔马”沿村收购,走遍了侯兆川大大小小每一个村庄,也几乎与所有的农户做过交易。
老聂收粮从不吆喝。早晨出门,选好一个村子,“突突突”就去了。到村子里把车停在大街上,找个平地儿盘腿坐下,摊开随身携带的棋盘,“啪啪啪”把双方的棋子儿全摆好,然后摸出一包香烟放在棋盘边,便开始招呼过往的村民:“来来来,杀一盘!”好像他来这儿不是为了收购粮食,而是专门找人下棋来了。
“又来了老聂?”然后就有人一边打招呼,一边撂下农具或手中的活儿,也盘腿坐在老聂的对面,跳马,架炮,攻卒,吆三喝六杀将开来。杀到酣处,不时从棋盘边儿的烟盒里摸出一支烟,点上,眼神却始终不离开棋盘。
围观的人也陆陆续续多了起来,聚拢在俩人周围,自觉分成两派,啦啦队兼智囊团,各为其主,支招呐喊,唇枪舌战,不可开交。
这时候若是有人过来问老聂今天粮食收购价钱,不用老聂开口,有人就大着嗓门吼开了:“老聂出的价钱还用问?车帮上有牌子,自己去看!”吼完扭头再看棋盘,发现俩人已经移动了几步,便摇头顿足:“我说跳马你偏出车……”
老聂的车帮上固定着一块铁皮牌子,黑底白字写得清楚:今日粮价,小麦多少钱,玉米多少钱。刚才问价的要么不是当地人,要么就是刚刚嫁来不久的小媳妇。老聂的粮价公示牌从板车到“奔马”,跟了老聂十几年,侯兆川人都知道。
对手不断更换,老聂自是来者不拒,稳如磐石。期间有人来问:“老聂,中午吃啥饭?”
老聂头都不抬:“随便!”
再有人来问,老聂还是“随便”。
一盘一盘杀将下来,不觉已是中午。附近的人就端着饭碗出来了,一手一碗,一碗是自己的,一碗是给老聂的。老聂便嬉笑着将棋局散了,站起身来,拍拍手,也不客气,接过饭碗,还不忘调侃几句,“咋没去割肉呢?”或者“和面洗手了吗?一股脚臭味!”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一碗没吃完,便又有人端饭出来给老聂了。老聂吃饭自然是免费的,村民吃啥他吃啥,不客气,不俗套。
饭后才是交易时间。老聂贩粮食跟其他人不同。其他的粮贩都会仔细查看粮食等级,讨好地帮主家背粮食,然后亲自过秤,沾着唾沫星子数钱。老聂不。老聂不识秤,也不看粮食等级,充分相信卖家。车上有杆大秤,谁粜粮食谁过秤,秤完找老聂报数,付钱。老聂也从不主动帮主家背粮食,老聂干啥?侃大山。老聂走街串巷,搜集了一肚子花边新闻和趣闻轶事。老聂讲起故事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除了四处抛烟,基本稳坐不动。
等故事讲了差不多,车就装满了,老聂的钱袋子也瘪了,老聂站起身来跟大伙打个招呼,上车,“突突突”回去了。
没办法,侯兆川的乡亲们都信赖他,粜给老聂的粮食从不以次充好,也不虚报斤数。老聂收粮食一天一村,一村一车,从未放空车回去过。
相比之下,其他的粮贩子就没有老聂这般滋润了,出力不讨好,中午还得自带干粮,有时候转悠几个村子也不见得能收满车。
有粮贩子就到处揭老聂的短,说老聂的秤不准,每一秤都会少一斤。这样一说,听得人就笑了,说:“瞎编!老聂秤都不识得,斤数全由我们报,还会缺斤短两?”还有人说:“就算是真的,老聂也不知道,谁敢说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虚报点?这一斤权当大伙填补他了。”
改天老聂再来,依旧只管埋头下棋,有人抢着管饭,饭后有人称重、装车,老聂“突突突”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