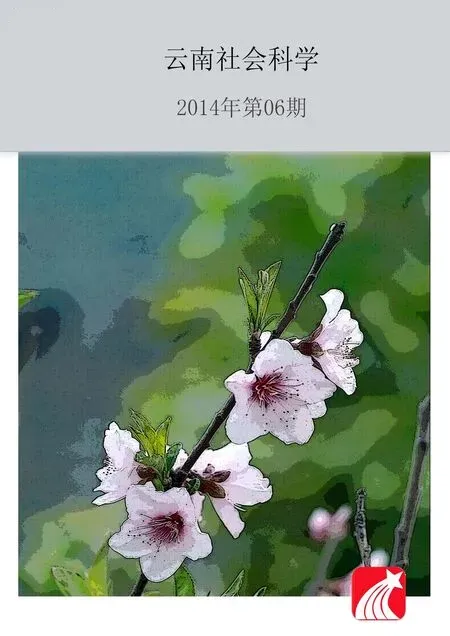国际法语境中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构建
刘学文
2013年8月14日开始,埃及政府出动警察,对首都开罗的两处穆尔西支持者示威聚集地实施清场行动。清场行动开始后,埃及全国多地爆发冲突,死伤无数。埃及的国家暴力造成的埃及人权危机以及人道主义灾难再次让世人警醒。时至今日,国家的力量已然强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在此情形下,国家的武装力量或暴力工具如若失去法律约束,被非文明国家的少数极权主义者或政客所滥用,主权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可能成为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屠杀民众、危害人权、破坏法治的“恶魔”,进而可能演变成恐怖的人间灾难。作为主要规范国家主权行为的国际法来说,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反思与回应,以禁止国家人格权的滥用。因此,国家人格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国家违法行为以及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的犯罪行为如何在国际犯罪体系中进行界定和惩处已成为现代国际法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国际司法实践的现实是,自二战以来的各种临时性、常设性或者国内特别刑事法庭的诸多审判或一系列刑事控诉行为都将这一制度不断引向深入,国际法实际上已悄然确立了国家人格否认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无人对此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而本文在学界提出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并为其清晰地界定了适用情形和实现方式。该制度的明确提出势必为人们重新认识国家行为,反思新时期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以及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等问题开拓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一、国家法律人格及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问题
1.国家法律人格的内涵与定义
国家具有一种“集合人格”的性质,这已被古今中外诸多思想家所论证。人格之概念被认为是法律中最为抽象的概念之一,关于人格的学术定义,最早可溯源至罗马法。在罗马法中,表示人的概念有homo、caput和persona,“其中Homo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权利义务主体。Caput原意是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在罗马法中被转借指权利义务主体,标示具有主体资格的人,只有当homo具有caput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1](P2~3)。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如此阐述国家人格的有关问题:“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2](P21)。英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将国家比喻为一个“自动机”(automata)或“利维坦”(leviathan)*“利维坦”,是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描述的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常比作“集权主义国家”。见《新英汉字典(增补本)》(第2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30页。,他认为,艺术模仿理性的大自然,创造出最精美的艺术品——“人”;通过艺术创造的号称“国民整体”(Commonwealth)或者“国家”(State)的这种庞然大物,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拟制的人”(artificial man);在利维坦中,“主权”构成整个人造机器获得生命和动力的“拟制的灵魂”,行政官员和其他的司法工作人员是人造的关节(artificial joints)……最后,通过“条约”(pacts)和“盟约”(covenants)将该人造机器的诸部位建立、连接和组织起来,就如同上帝造人一样,人也能够创造一个拟制的“人”(国家)[3](P7)。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国家就是为人所创造和拟制的法律人格者,国家的存在有构成它的基本要素,其中,主权则是它赖以存在的“拟制的灵魂”。在国家豁免论中,“限制豁免主义”对非国家主权行为免于豁免也是主权作为国家灵魂的佐证。路易斯·亨金教授也认为,“‘主权’这个词最常见的用途可能是主权豁免——来自于法律的豁免权,免于审查、免于司法”[4]。国家的主权行为之所以能够在其他国家享有司法豁免权,乃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使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秉持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对他国所为之商业行为则不予此种豁免,因认为其缺乏主权内容。
“国家人格”是“国家的国际人格”的简称,它是“国际法人格”(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的子概念,所谓“国际法人格”是指在国际法上所具有的“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换言之,即享有为国际法所确定之权利、义务或权力者[5](P59),而国家是“国际法人格”中的主要类型。根据《奥本海国际法》之界定,国家人格其实是诸多特性结合起来的结果,因此它“可以说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平等、尊严、独立、属地与属人最高权和责任被每一个其他国家所承认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是从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本身产生出来的”[6](P199~200)。正是在此意义上讲,国家人格的存在构成国家间一切权利与义务的基础。
2.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内涵与理论缘起
在各国公司法中,“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特指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阻止公司独立人格之滥用,公司法“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7](P124)。其最大功能在于克制法律拟制的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僵硬性。当出现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独立地位、恶意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时,法律揭开公司虚拟法律人格独立责任之“面纱”,代之以公司股东连带承担对外责任的制度,这实质上是对传统公司法归责原则的一种突破,其目的在于保障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具体的国际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公司法人颇为相似,在一国之严重国际不法行为导致国际损害的情势下,国际法试图揭开国家身上所笼罩着的主权“面纱”,对隐藏在国家背后的个人追究责任,故在国家责任之外出现新的责任承担形式。因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资借鉴。笔者认为,所谓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即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因滥用统治权力突破必要限度*此处“突破必要的限度”应当理解为违背了“禁止性规范”,而禁止性规范主要指强行法、国际条约、习惯法或一般法律原则,此类禁止性规范均是由国际法创设或推动的,已演化为国际犯罪,受国际刑法的调整。,对他国主权或国际共同利益造成损害进而构成国际犯罪*关于“国际犯罪”的界定笔者比较赞同卢有学教授的观点,即“国际犯罪是指由国际法创设推动而被国际社会普遍予以犯罪化并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它具有国际法创设性、国际禁止性和国际危害性三个基本特征”。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很好地概括了国际犯罪的特性,这一定义将一些本不属于国际犯罪的罪行排除在外,更加彰显国际犯罪的特定性。参见卢有学:《国际犯罪概念的重新界定》,《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39页。,国际法责令该个人行为者对其行为连带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以实现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制度。
至此,有论者可能会批评笔者将国内公司法中的制度“生搬硬套”到国际法中。笔者认为:(1)前文已述,“法人”是国内民商法拟制的抽象人格,其独立享有民事权利、负担民事义务;同样,“国家”在国际法中也是一个拟制的法律人格,国家独立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既然一个‘人格者’仅存在于‘他的’义务和权利中,那么,就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具有与私人的义务和权利一样内容这一程度而论,国家的法律人格也就和私人的人格并无不同”[8](P227~228)。(2)国际法对内国法特别是内国民商法的借鉴古已有之,而且很多制度就是从罗马法(本质上属于内国法的“万民法”)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譬如,国际法领土取得中的时效、先占、添附、国际地役制度皆来源于国内民法;再比如,国际法中的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也是来源于传统民法中的有约必守原则;至于国家主权的概念,最早也是国内法上的制度,最后被学者引入国际法,成为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一借鉴正好为这一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优越的制度渊源。
3.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合理性
与公司法上的公司独立人格非常类似,国家作为国际法上的拟制人格,通常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事,故一般而言,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其行为应由其自身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即国家责任)。但在特定情形下,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很可能会滥用国家主权,法西斯运动就是典型例子,其特点就是大规模、疯狂的国家犯罪,以国家机器进行犯罪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犯罪更为严重和可怕。在那个年代,“担任过国家要职的、处于决策层的高官”,利用国家机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广泛存在的群众情绪,或在国内发动惨绝人寰的政治迫害,或在国外进行骇人听闻的侵略战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种国家人格性犯罪造成的历史惨剧有:“对土著居民的屠杀和掠夺,丧尽天良的贩奴和蓄奴;遍及三大洲的血海战火,惨死在毒气室、焚尸炉的六百万犹太人;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成百万正直无辜的苏维埃人遭到枪决、监禁和流放的大清洗……”[9](P401~403)。
总之,此类“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动辄滥用国家主权,以国家名义实施国际犯罪,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或危及国际共同利益的行为比比皆是。在此情况下若只追究国家之责任,一方面影响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实现,另一方面对谴责和预防国家犯罪难以奏效,且使得国家背后的个人逍遥法外。因此,战后涌现的各类国际法庭审判活动开辟了追诉此类个人或团体的刑事责任之路。尽管此类行为是以国家名义做出的,本可归因于国家而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因“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是由个人而非抽象的法律实体所实施的”,故国际习惯或国际条约等已经通过创设或者推动,将一些国家行为界定为国际犯罪,国际法除了要求国家承担相应责任之外,对此类个人亦同时进行谴责和惩罚。这种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其合理性具体表现在:第一,正确区分了各主体之权责,使其罚当其罪和不罚及无辜;第二,进一步完善国家责任制度,有效防止大规模国家犯罪的死灰复燃;第三,深入释明了国际条约以实体法形式确立个人的国际罪行和大量国际刑事司法审判次第出现之原因。
二、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界定及实施方式
随着近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早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实,只是缺乏学术理论上的梳理。任何制度的实现一定有其起始,国家人格否认制度亦是如此,可以说,国家人格否认制度是与现代国际法中的人权保障、国际犯罪、国际人道法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1.国家人格否认制度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实现方式
《纽伦堡宪章》第六条创设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被称为“纽伦堡原则”(Nuremberg Principles);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颁布的“纽伦堡原则声明”则进一步确认了国际法可以不考虑国家法的规定,直接适用于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10](P58)。此处所谓“个人”应包括两类:(1)享有特定职权的自然人,包括国家元首及其近亲属、亲信(如希特勒秘书马丁·鲍曼、苏丹总统巴希尔、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及其近亲属)、政府首脑(如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普鲁士总理赫尔曼·威廉·戈林)、外交部长(如德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第二任外交部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最高军事首领(如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党派掌权者(如纳粹党立法领袖威廉·弗利克、司法领袖汉斯·弗兰克)等具有特定身份的个人。(2)“非国家行为者”,主要包括武装部队、警察、准军事团体、武装民兵团体以及其他民办机构等团体。如准军事团体和武装民兵团体在前南斯拉夫冲突中,实施了很多国际犯罪行为;此类主体所涉足的最为典型的国际犯罪是“危害人类罪”;“非国家行为者”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成为“解决个人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10](P60~62)。当然,由于国际刑事责任是个人刑事责任,故而非国家行为者并非国际刑法主体的新种类。
纽伦堡审判的法庭判决指出,“正像对国家一样,国际法对个人也施加义务和责任,这是早已被承认的……本宪章的精髓就是,个人也有国际义务,这种国际义务高于各个国家所施加的国内服从义务。违反战争法规的个人虽然是根据国家的授权行事,但如果国家在授权时超出了它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限,那么,上述个人就不能得到豁免”,《纽伦堡宪章》以及法庭判决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上得到肯定[11](P496~497)。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同样规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国际罪行,犯罪者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1998年订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五条更是明文规定了“个人刑事责任问题”。总之,一系列临时性或常设性的国际法庭宪章或规约都规定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具体落实自然要借助于法庭的刑事司法审判。
综上所述,随着战后诸多国际刑事法庭对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国际法已牢固确立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这也标志着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真正确立。该制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的确立与发展伴随着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法律实现。
2.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国际法创设与个案实现
国际法的创设不同于国内法,其更多地体现在国家间意志的协调,通常表现为缔结条约,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当然,国际习惯法的司法确定也是国际法创设的一种重要情形*关于国际习惯法的司法确定之进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国际法上的理论问题,详见姜世波:《习惯国际法的司法确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342页。,如“以私人身份行事的个人”实施国际犯罪,最早为国际习惯法确定下来的有海盗和贩卖奴隶两种行为[12](P80)。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国际法创设集中在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法领域,具体指国际法创设和调整国际犯罪。
根据实施身份之不同,个人国际犯罪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私人身份实施的国际犯罪”,如海盗罪、贩卖毒品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人质罪等;第二类是“个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实施的国际犯罪”,如战争罪、反人道罪、灭绝种族罪等[12](P80)。对于前者,因各国国内刑法均无例外地将此类行为规定为犯罪,且管辖权上大多数国家采取普遍管辖原则,故通常在内国法院进行管辖和审判;而对于后者,通常由临时性或者常设的国际刑事法庭实施。此外,由专门的法庭审判一些特定的国际犯罪案件成为近年来国际刑事法治的新趋势,譬如判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绞刑的“伊拉克高等法庭”(Iraqi High Criminal Court),其前身是根据2003年12月10日生效的《伊拉克特别法庭规约》成立的“伊拉克危害人类罪特别法庭”;又如判处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核心人物穆罕默德·穆贾希德死刑的“国际战争罪法庭”(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由执政的孟加拉人民联盟政府于2010年建立并行使职权。
在处罚措施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演进,国际法对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实施的国际犯罪采取“二元责任原则”予以惩处已成为国际法学界的共识,但传统概念并未解决如下问题:(1)既然个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身份实施,这种职务行为是否为国家这一主权实体所吸收?此种情形下个人的行为能否得到豁免?(2)如果认为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应当对其做出的国际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理由又是什么?(3)如果认为个人须承担相应国际法责任,那么主权国家是否也应同时承担责任?如果实行“二元责任原则”*“二元责任原则”类似于国内刑法中的“双罚制”,指的是“国际社会在认定行为国家犯有战争罪、侵略罪等国际罪行并给予处罚的同时,还应当追究主要决策者、执行者和实际实施者等行为人的个人责任,即在国家实施的国际犯罪中确立二元责任原则”。参见马进保:《论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责任》,《杭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41页。,其理由又为何?笔者提出的国际法人格否认制度,显然对我们清晰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当然,与国家人格否认制度有关的国际犯罪行为与国家本身的犯罪行为胶合在一起,对外常表现为国家主权行为,故国际法须通过人格否认制度将二者进行剥离,惩处方式实行“二元责任原则”。如1945年11月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戈林等前纳粹罪魁共20多人进行了审判;1946年1月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犯进行审判,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在法西斯战犯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法西斯国家也承担了“最严重的一种国际责任形式”,同盟国通过订立《伦敦国际协定》,对德日实行临时性的军事占领和军事管制,并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行此项最高权力[13](P105~106)。此外,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还有判处罚金和损害赔偿、经济制裁、剥夺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以及道义谴责等。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创制和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实现是两回事,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只适用于个案,即在国际法庭上通过国际司法诉讼将此类规范适用于个案以实现之。
三、国家人格否认制度与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理论
1.国际刑法的发展扩大了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
通常认为,某一法律关系的主体者,即为某一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故要成为国际法的主体,通过考证其有无参加国际法律关系,即可明了。“当国际法学者称特定实体为法人,或是称该实体为‘法律主体’时,即意谓该实体有能力建立法律关系,并享有权利与负担义务”。因循该思路我们会发现,传统国际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就如同内国法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此观念显然已不合时宜,而关于国际人格的范围中是否包含个人、公司等问题早已是众说纷纭了[14](P325)。随着国际法律关系的纵深发展,国际法上的人格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国际法主体,从当前个人积极参加国际法律关系、成为国际法直接调整对象这一现象观之,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已然成为事实。但是,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形下国际义务都应由国家或国家间组织这种拟制的法律人格者承担,但在特殊情形下,由于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触犯了国际强行法,而对国家的惩戒不足以弥补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严重后果(或罪刑相一致)时,通过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国际法着力以个人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谴责隐藏在国家之后的个人行为者几成趋势。二战以后,联合国安理会指定成立的临时法庭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最为典型。对国际犯罪行为,因其违背了国际法规定的“禁止性规范”,国际法允许其法律效力刺穿国家主权的屏障,结果正如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言,“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是由个人而非抽象的法律实体所实施的,因此国际法的规定只有通过处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得到执行”[10](P57~58)。
可以说,现代国际法对国际犯罪的惩治便是典型的国家人格否认制度。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学界一般公认的是,“国际法可以对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可以由经合法授权的国际法庭或国内法院以及军事法庭给予惩处。这些国际法庭根据适用的法律以及法庭的宪章行使国际管辖权,国内法院则根据适用的法律以及管辖权的性质——这种管辖权的行使为国际法所肯定——行使国际管辖权”[11](P496)。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此种表面上看起来属于国内法上管辖的个人刑事犯罪通常不在一国国内审判,而由常设的或临时性的国际刑事法庭来审判的原因了,而且对其审判在法律适用上也主要以国际法为依据。此类国际刑事公约均有犯罪的实体性规范,譬如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公约“适用的法律”。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个人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在国际法上早已确定无疑。当然,此处最为合理的解释是个人对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的特殊性,国际法通过法律创设和推动刺破国家虚拟人格之屏障,进而将国际法律责任直接施加于个人行为者。
2.国家人格否认制度深刻映证了“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论
关于个人是否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的讨论众说纷纭。有学者独辟蹊径,提出将“国际法的主体”与“国际犯罪的主体”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看待,并认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是指犯国际罪行,应负刑事责任并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个人),因为犯罪是有意识的活动,特别是犯国际罪行,必须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心理要件,所以只有有意识的自然人(个人)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15](P75)。笔者并不赞同该说法,这是因为:(1)国家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尽管这一观点存在争论,但一系列的国际法文件也支持这一立场,如国际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将国际不法行为(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分为国际侵权行为(International Delicts)和国际罪行(International Crimes);2001年11月,国际法委员会又通过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将国际犯罪改称为“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被认为是对“国际罪行”概念的进一步扩大适用。(2)从国际刑法的视角界定“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无不当,但并不意味着个人就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这是因为假定“国际犯罪的主体”成为国际法的一类新型主体,则更加支持了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说法。对此,笔者有四点理由:其一,萌芽时期的国际法主体就是个人。根据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缔结的条约,“国际法主体不是国家本身,而是法老、国王以及各城邦国家的独立统治者或附属统治者”,当时为数众多的通婚条约也证实了这一点[16](P9)。其二,“国际犯罪的主体”的提法是从国际犯罪学的视角考察的,而如前所述,国际犯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法律渊源也是基于国际法,也就是说,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进行的国际犯罪行为本身是国际法直接施加给个人行为者的责任承担形式,故提出这一概念并不能使其从逻辑上绕开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其三,从国际犯罪的流变来看,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亦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历程,二战以后的国际法更加明确地惩治个人的刑事犯罪,如“把战争罪作为一种国际罪行,并对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由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和审判,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事”[17](P28)。其四,正是由于传统国际法中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已无法防止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实施的国际犯罪,导致严重危害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情势,所以国际法要通过人格否认制度,穿越国家主权的屏障,进入国际刑法层面来惩治国际犯罪,使个人承担基于国际法创设和推动的国际刑事责任。
因此,正如意大利国际法学家帕里埃里(B.Pallieri)所认为的,在纽伦堡和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中个人直接被审判,“就是把个人同国际法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成为国际法的主体”[15](P75)。故笔者提出“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理论,所谓“有限主体”,乃是因为个人行为仅在国际刑法等特定领域承担个人国际法责任与享受权利情形下,方能成为国际法之主体,即使是持批评论的林欣教授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国际法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那就是在特定的场合下,个人在国际上具有一些有限的行为能力”[15](P75)。个人在国际法上具有“行为能力”,当然是国际法的主体无疑了,这不正佐证了笔者的“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的观点?换言之,在国际法上,国家、个人都可能承担责任,而且国际犯罪等特定领域,对于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做出的国家行为,因为超过必要的限度,国际法通过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实行“双罚制”,直接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正是由于国家人格否认制度,无论是个人承担国际犯罪之责任,抑或是国家承担国际不法行为之责任,均是国际法主体之责任承担形式,只是个人的国际法责任较为有限,但其国际法主体资格并不能否认。所以,学界不应再拘泥于个人是否国际法主体的讨论。
四、结 语
国家作为国际法最主要的主体,是国际法律关系的主要参加者,享有依国际法而起之权利,亦承担依国际法而起之义务,乃国家的法律人格使然。国家与国内法中的公司法人一样在国际法上具有拟制的身份与独立的人格,而主权则成为国家法律人格赖以存在的“拟制的灵魂”,也因此,以国家做出的法律行为一般均被视为主权行为,均由国家承担法律后果。但二战以来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国际法开始追究那些滥用统治权力、以国家的名义肆意发动战争、侵害人权、屠杀民众等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的刑事责任,《纽伦堡宪章》第六条创设的“纽伦堡原则”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法实质上已悄然创立了国家人格否认制度。而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别适用也决定了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势必在极其特殊情况下存在,一般认为应限于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与享受国际权利等方面,笔者继而提出了“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理论,它很好地回应了当前学界关于个人是否国际法主体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