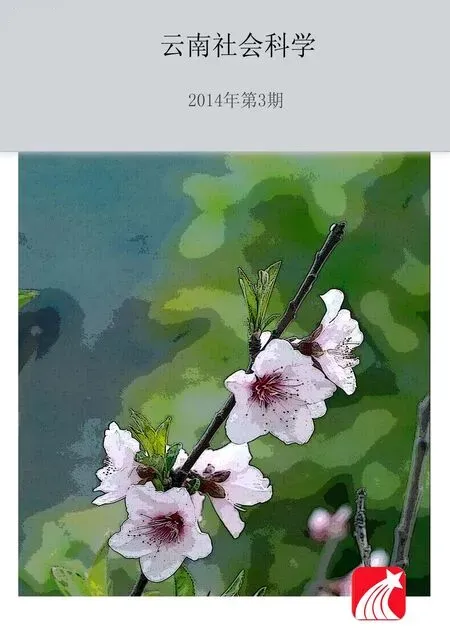社区视域下西双版纳传统社会宗教生态平衡研究
李守雷
宗教关系是当今与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并列为“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必须妥善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之一。为建构和谐的宗教关系,宗教管理部门和宗教研究学者积极探索和反思,形成一些宗教管理思路和理论,包括一直盛行的宗教引导论,还有新兴的宗教市场论、宗教生态平衡论、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等。在反思基督教自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的原因时,有学者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分析宗教文化现象,又提出了宗教生态学理论,主张各种宗教“彼此间应该是互相制约达到一个平衡状态”。[1]这一理论对我国多宗教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概括,同时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前宗教发展失衡的原因,重建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下辖景洪市、勐海和勐腊两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该地区立体的地理地貌造就了立体的民族分布和宗教文化。[2]民族群体以规模不等的村寨形式,分层次生活在这种立体生态环境中,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宗教信仰。以坝区傣族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为中心基点,扩展到周围半山区域哈尼族、布朗族、彝族等民族的宗教分布,再到山区苗族、瑶族等民族的信仰空间,呈现出栉比鳞次的“条块式”排列格局。自然环境与社会形态共同铸就了西双版纳“天人合一”的地理人文和各类宗教平衡发展的宗教生态景象。
一、村社组织成为民族和谐共处的支撑
传统社会,西双版纳实行封建领主经济。傣族“召片领”和各勐土司在名义上拥有西双版纳所有土地。傣族倾向于以村寨为单位占有和耕种土地,并集体承担相应的赋税义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体。山区民族多数是以村寨和氏族的形式占有土地,以“氏族”或“大房子”为单位将土地分配给家庭。土地以村寨为范围,某户外迁就要把土地归还给村寨或氏族,不能私自出卖。村民的结合以地缘为基础,并保存着浓厚的血缘联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若干氏族组成一个地缘性村寨。[3](P154)村寨成为维护土地集体财产的主要力量。所以,村寨集体成为西双版纳各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主要依托。
傣族、壮族占据河谷坝区,土地肥沃,以水稻种植为主,适于定居生活,所以人口比较集中,村寨规模相对较大。山地相对贫瘠,以刀耕火种为主,单位面积产出低。刀耕火种分为定耕和游耕两种形式。定耕刀耕火种的土地和村寨都是固定的,但随着人口增长,周围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就要进行分寨。部分村民搬迁到较远的土地上,建立新寨。一个村寨分成几个,每个村寨的人口都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实行游耕刀耕火种的民族为寻找更适合耕种的土地经常迁移,“连收三四熟,地瘦则弃置之,另择他所”。在频繁的迁徙中,为保证流动的灵活性,方便找到适量的土地,村寨规模必定受到限制。传统社会,各民族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形成相互依赖的民族生态关系,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口平衡点,从坝区规模较大、相对集中的定居村寨,到半山区规模较小、不断分散的定居村寨,再到山顶规模更小的流动性村寨。规模较大的定居村寨固守基地,无意主动侵占规模小的流动性村寨;流动性村寨也回避与定居村寨发生冲突,达成一种动态平衡。民族是群体划分的一个参数,但真正具有实际意义和影响的是村寨组织。村寨成为民族生产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成为宗教信仰的基本单元。
二、村寨生活中神圣与世俗的相互建构
在传统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结合成“群”,才能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下求得安身立命。村寨作为一定区域内的群体组织,便于成员间彼此依赖与合作,形成村寨意识,并凝聚成宗教信仰。个人只有在村寨内才能求得衣食之需、人身安全、种的延续和身份认同。“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是得不到村寨的合作协助,其生活便立刻会发生问题的。”[4](P50)在西双版纳地区,各少数民族村寨都是团结互助的集体。不论是婚丧嫁娶、搬迁建房时亲戚邻里的相互扶持,还是劳役贡赋的共同承担、公共财富的平均分配都普遍存在于民族村寨。宗教“起源于社区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的道德价值体系和‘终极参照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功能性的。这就衍生出了对超自然实体的集体信仰及其对外在表现形式”[5](P36)。各少数民族通过宗教信仰维护着村寨的凝聚力和权威,不断强化村民的村寨认同力和归属感。
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为村社制度服务,保证村寨的团结和凝聚力,维护村寨利益统一体。西双版纳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存在寨神信仰和相关的祭祀活动,如傣族、基诺族、布朗族和拉祜族等都有寨神信仰,哈尼族有祭寨门的传统。寨神是建寨氏族的氏族神。当氏族公社演变为封建领主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神也变成了区域性的社神,成为全寨成员共同崇拜、祭祀的对象。傣族的寨神“丢瓦拉曼”在寨子的中心,又称为寨心神,是寨子生命和灵魂的象征,保佑着村寨平安兴旺。布朗族的寨神是由男女氏族神“代袜么”、“代袜那”演化来的。村寨里有婚丧、建房、生病或迁入新户都要由召曼(头人)祭祀祷告。当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和布朗族地区后,佛寺又成为全寨成员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哈尼族建寨都要在进出村寨的路口立寨门(哈尼语称“竜巴门”),一般有一道正门、两道侧门,作为人鬼分界线。哈尼族认为住在寨门内,可以得到寨神的庇护和寨内群众的帮助,走出寨门也就离开了神和集体。瑶族的原始宗教融合了道教信仰,丰富了本民族的神灵体系。每年举行打斋,祈求“盘王”、“玉皇”诸神保佑村寨平安兴旺;同时进行“扫寨”,驱除妖魔鬼怪。瑶族村寨保留着古老的“寨老制”,以解决村寨内部事务,对抗外部的骚扰和攻击。基诺族尊称寨神为“左米思巴”,并有盛大的“洛嫫洛”祭祖节。期间,村民巡查村寨的土地边界,子寨拜望父寨,子女拜父母,弟弟拜哥哥,村民拜寨父寨母(即卓生卓巴,是寨神的代表)等礼仪。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中,基诺族再现了村寨界限,加强了村寨间的联系,融洽了村民关系,强化了村寨的凝聚力。
三、村寨边界巩固了宗教生态平衡
不论是在“地理隔绝”或“社会隔绝”的民族关系下,还是发生“社会互动”或“社会接纳”的情景下,每个民族群体的延续都依赖于民族“边界和界限的维持”。[6]村寨是构筑西双版纳宗教生态平衡的推动力。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投射在村寨社区上,具体化为村寨边界。农业生产的村寨组织形式和村寨生活的人神共建,铸就了村寨的集体凝聚力和信仰文化的同一性,进而形成村寨边界的维持力。同质性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同质性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文化相映照。宗教文化通过合理性论证、神圣性监督、集体性惩罚维护了维系了村寨生活秩序。“宗教社会化不仅通过一代代的人进行传递,还在空间上通过不断强化居住在某个地点的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得以实现。”[5](P92)传统村寨社区通过持续的“信任评价结构”强化机制,维持了社区成员的宗教参与热情和忠诚度。
村寨边界不仅保证了村寨内宗教文化的同质性,也维持了不同民族村寨间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清朝时期,壮族和回族迁入西双版纳,与傣族保持通婚,深受傣族文化的影响。村民住傣族式的干栏式建筑,穿傣族服装,用傣语交流,在日常生活和某些观念中流露出傣族文化的痕迹。勐海县曼短村委会曼赛、曼峦是两个回族村寨(被称为“回傣”),秉承伊斯兰教信仰,同时受到傣族宗教观念的影响,比如鬼魂思想的存在。村民相信意外受伤、病痛和家庭不顺是因有鬼作祟,要请人打卦,将糯米饭、香蕉、盐等用芭蕉叶包成小包,放到村寨外的路边“赕鬼”。穆斯林传统丧葬,用清真寺的共用“经匣”抬“默伊特”(死者),然后抬回“经匣”。而“回傣”由丧家自制“木盒”送葬,下葬后将“木盒子拆开倒扣在坟堆上”,并“把亡人用过的东西,弃在坟边,怕把死人的东西带回寨子,会有鬼魂跟随而来,作祟于人”[7]。勐腊县勐伴镇勐伴村委会曼里村的壮族保持浓厚的祖先崇拜;把迁移中的英雄奉为神,建庙供奉;吸收傣族的祭“寨心”仪式;借用傣族节日,在关门节祭天,求风调雨顺,在开门节吃新米,祭祀祖先。宗教文化具有扩展性和共享性。信徒可以借鉴几种宗教文化元素,融会贯通,成为“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儿”。这种深层次的交往带来宗教适应和文化融合,并没有抹平村寨之间宗教文化的差异。宗教文化将不同的民族村寨区别开来,既有民族认同又有宗教认同的成分。在民族村寨间“社会互动”与“社会接纳”的过程中,出现了宗教文化的碰撞、交融、整合和创新,保持了宗教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同时维持了群体文化的独特性。
一方面,西双版纳地区以包容性的立体生态为不同民族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立体生态边界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赢得了生存空间,保护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具体到微观层面,村寨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依托,也成为宗教文化生存的基本单元。村寨边界的维持力来源于村寨归属感和集体排他力,保护了村寨内部宗教文化同一,维持了村寨间宗教文化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宗教既可以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组成要素体现在社区生活之中,也可以作为社区的组织和构建的主导发挥作用”[8]。维持民族村寨的边界,就是维持民族群体的主体性。宗教文化以“对内”团结和“对外”排斥的机制维持村寨边界,并由点扩展到面,由村寨扩展到整个民族,将宗教文化的村寨边界升华为民族边界。从宏观到微观,宗教与民族互为主体,互为对象,通过村寨社区的凝聚衔接,共同构筑了西双版纳传统社会“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