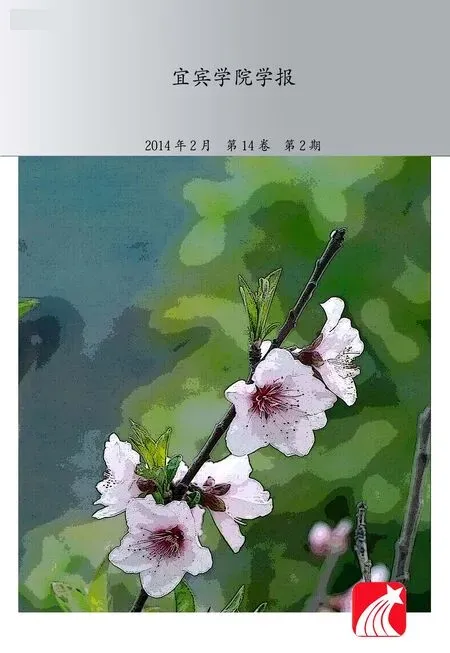雁翼作品中几个有新文学史料价值的问题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是作者雁翼生前亲自校订的作品选集,实际上是作者雁翼之作品的最后文字定本,是雁翼研究的重要的基本文本。即雁翼初次发表的原始文本如果有错误,在这次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中应该修改,也就是说四卷本《雁翼选集》的文献可靠性应该超越雁翼之作品初次发表的原始文本或版本的文献可靠性。
现雁翼已去世,四卷本《雁翼选集》作为作者雁翼生前亲自校订的版本是雁翼研究的基本文献,若此基本文献存在硬伤,则直接影响雁翼研究的开展和进行。此基本文献本身的问题或硬伤是任何一个认真的雁翼研究者都不得不首先面对并想方设法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此基本文献本身之问题或硬伤,若作者雁翼还活着,尚可与之从考证,现作者雁翼已去世,这些问题或硬伤已无从考证,这就为弄清楚这些问题增加了难度,本文拟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文论卷存在的问题或硬伤加以研究。
一 关于雁翼从喜爱文学起就开始读艾青的诗的问题
雁翼《创作前的准备》云:“人与文学发生关系,大约都是在他识字之前,还不会看书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就是说,在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时候,就与文学交朋友了,我指的是口头文学。”[1]124
雁翼《创作前的准备》云:“上面讲的是‘听文学’,下面再说说‘看’……参加革命后,经过一定的文化学习,从看戏发展到看书,开始看不很懂,生字多,但书里的故事吸引我,就边问字、边猜字的读下去。我记得读的第一部小说是线装本的《西游记》,读了半年多才读完,学习了不少生字。从那以后,就更爱看书了。”[1]125-126
雁翼与文学发生关系之后就更爱看书了,书自然是文学书,更爱之前是爱,爱文学自然就是喜爱文学,但此时雁翼并未读艾青的诗。
雁翼《艾青是榜样》云:“艾青的诗与诗论,对于我个人来说,既是课本,又是榜样。从我喜爱文学起就开始读,读了一辈子,好像是吃饭,总是想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长得更壮更健康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活得更勇敢一些。”[1]184雁翼说他自己从喜爱文学起就开始读艾青的诗,这是谎言。雁翼说与文学发生关系应当是从与口头文学发生关系开始的,此时是否喜爱文学尚很难确定,但到主动阅读文学作品阶段可以算是喜爱文学,而此时雁翼阅读的文学作品是《西游记》,根本不是从喜爱文学起就开始读艾青的诗。
雁翼《艾青是榜样》又云:“在诗里说真话,故然(笔者按:应当是固然)。有一个知识的和思想的高度问题,但起支配作用的是做人的勇气,可以这样说,艾青诗创作的一生,是他为人民说真话的一生,他的有幸和不幸,都是因为人民为民族说真话而造成,这是对为我非常有启迪有鼓舞作用的,也是我非常珍惜的,要研究和学习艾青的诗美学,首先要研究和学习这一条。”[1]185雁翼声嘶力竭地讲要研究和学习艾青说真话的品质,而雁翼本人与此同时却在说着假话。
二 关于对艾青的评价问题
雁翼《艾青是榜样》云:“而艾青,是一座时代的诗的高山,需要我们学习,研究,理解一辈子、两辈子、五辈子、十辈子。”[1]186雁翼认为艾青是一座时代的诗的高山,时代就是艾青所处的时代,即在艾青所处的时代里艾青的诗是一座高山,这个评价基本上是恰当的。但是,雁翼接着认为艾青需要我们学习,研究,理解一辈子、两辈子、五辈子、十辈子。十辈子就是一千年,这实际上是认为艾青不仅是一座时代的诗的高山,而且在一千年后仍然是一座诗的高山。一个诗人是否能够传之后世,不是依靠是否有另一个诗人的吹捧,而是依靠其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看其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能够打动后世的读者。唐代诗人罗隐《黄河》云:“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平安。”[2]20一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话高山。清代诗人赵翼《论诗》第二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3]1252艾青的诗是不可以与李杜相提并论的,所以,雁翼所谓艾青需要我们学习、研究、理解十辈子即一千年显然言过其实了。
雁翼《艾青是榜样》云:“一座纪念碑耸立在多风多雨的二十世纪之初,和之尾。”[1]186雁翼把艾青及艾青的诗比作一座纪念碑,这并无不可,但是,这座纪念碑耸立在多风多雨的二十世纪之初和之尾就有问题。朱栋霖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云:“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笔名有莪伽等,艾青是他1933年发表《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开始使用的笔名。”[4]582该书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于1933年,实误,《大堰河——我的保姆》实际上发表于1934年《春光》杂志第1卷第3期上[5]。艾青生于1910年,似乎可以勉强说艾青这座纪念碑耸立在多风多雨的二十世纪之初,但是,艾青不是一生下来就已成为一座纪念碑耸立在多风多雨的二十世纪之初,艾青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是发表于1934年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也是说在1934年发表《大堰河——我的保姆》时作者才第一次使用艾青这一笔名,所以,如果艾青可以被称为一座纪念碑的话,那么这座纪念碑也只能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耸立起来的。因此,这样的评价严重失实。
三 关于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问题
雁翼《学诗初记》云:“但学文学究竟需要读哪些书呢?我给不少作家写信询问。严文井老师寄给我一张书单子,是粉连纸铅印的,共有五百多部书,幸好泸州川南图书馆藏书比较多,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那五百多部书我基本上读完了,而且,还陆续的学写了一些作品。”[1]162既然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在雁翼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此书单是何来历、到底有多少书、到底是何书就应弄清楚,这对于研究雁翼的知识结构和创作道路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雁翼《紫燕传再版小记》云:“应当说,这部长诗的写作从开始就和严文井老师有关系,我是从战争生活走出来的人,想从事写作就是想记下战争生活中那些人和事。但对于文学苦于不知怎样学起,就给许多作家写信求救。这是一九五〇年,失望之中接到文井老师从北京寄来的几张书目单,是粉莲纸印的,大约二百多部,有文学有历史有文学理论,花了两年时间我读完了书目单上的书,从此开始了正式写作,而且,写作计划中着重构思的作品也是《紫燕传》。令我永生难忘记的是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拜望严文井老师,提起二十八年前他寄给我的书目单,他竟然忘得一点影子也没有了。”[1]348-349严文井不记得有给雁翼寄书目单之事。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全国胜利以后,我的读书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搞文学写作,读书有了计划性。中国的书,基本上是按照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史》和刘绶松先生的《现代文学史》的排列次序来读的。而对于外国的书,则侧重于人,就是尽量地把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传记)都找来读(对于中国某些作家的作品也是这样读的)。”[1]330
首先,雁翼《我的读书生活》未记录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既然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在雁翼学习写作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雁翼《我的读书生活》就应该记录下来,现雁翼《我的读书生活》未记此书单,则是否真有此书单都成问题。其次,关于书单的内容存在矛盾,雁翼《学诗初记》说书单共有五百多部书,而雁翼《紫燕传再版小记》说书单大约有二百多部书,五百多部书与二百多部书相差甚远。既然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在雁翼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雁翼对此书单所开列书籍的数量就不应该记错。再次,读完此书单上之书的时间存在矛盾,雁翼《学诗初记》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基本上读完了那五百多部书,用时三年,而雁翼《紫燕传再版小记》说花了两年时间读完了书目单上的书,读完此书单上之书的时间明显存在矛盾。既然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在雁翼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雁翼对读完此书单所开列书籍所花的时间就不应该记错。又次,严文井不记得有此书单,实际上是委婉地否定了此书单的存在,也是委婉地否定了有严文井本人曾经给雁翼寄过书单之事。另假设有此书单,而雁翼《我的读书生活》记载其读书自有计划,则此书单之作用等于零,雁翼《学诗初记》和《紫燕传再版小记》关于此书单在雁翼学习写作过程中所发挥过之重要作用之记载就有可能失实。鉴于以上情况,该书单根本就不存在。
四 关于雁翼第一次负伤的细节问题
雁翼《我与儿童文学》云:“一九四三年麦子要割的时候,我们从单县韩庄突围,跑到村外,不见了政委的马和饲养员老曹,我又冲进村里找,马被打死了。马夫牺牲了。牺牲了还紧紧地抱着政委的皮包——显然,他是从死马身上摘皮包时被打死的。我从他怀里夺过皮包,又冲了出去,但是我也负伤了。伤好后,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我才十六岁。”[1]132雁翼说他第一次负伤的细节是雁翼从马夫怀里夺过皮包,又冲了出去,自身也负伤了。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说老实话,我第一次负伤,就是和书有关。那是一九四三年仲夏,我和刘政委正合看线装的《岳飞全传》,他看的那几册书装在他的皮包里。有一天夜里被敌人包围了,突围的时候他的马夫没有跟上来,而他的皮包还挂在马鞍上,我心里惦记着那几册书(当然,皮包里还有文件和军事地图),就转身冲进了村子,才知道马夫和马都牺牲了,待我把皮包从马鞍上摘下来,重新冲出去赶上部队,把皮包交给刘政委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也负了伤。”[1]328雁翼说第一次负伤的细节是待他把皮包从马鞍上摘下来,重新冲出去赶上部队,把皮包交给刘政委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负了伤。
如上两次说的内容不一致。显然,二者存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军人对自己第一次负伤的记忆非常清晰准确,而如今,军人出身的雁翼叙述自己第一次负伤的细节却前后矛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说老实话,我第一次负伤,就是和书有关”[1]328。雁翼的一句说老实话,却有问题。首先,雁翼这里的一句说老实话实际上是在说以前他关于自己第一次负伤的细节的叙述都是谎言,而在这里却特别强调这一次讲的是老实话、是真的。其次,雁翼这里的一句说老实话实际上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意,使读者对雁翼所谓的老实话也产生了怀疑。再次,人说谎具有连续性或曰惯性,即当一个人说了第一个谎言,这个人必然要说第二个谎言,而且要一直说下去。为了圆自己说的第一个谎言,这个人就必然要说第二个谎言,这个人为了圆自己说的第二个谎言,这个人就必然要说第三个谎言,依此类推。既然谎言具有连续性或曰惯性,那么,雁翼的说老实话也可能是谎言。
五 关于雁翼读书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好书的问题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一些社会言情小说,政委就拣了去烧掉了或藏起来不让我看。也有一些好书,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艾青的《大堰河》、郭沫若的《瓶》,还有俄国的一册诗集《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抄本,就是这时候看的。”[1]329鲁迅的《阿Q正传》收在《呐喊》之中,《呐喊》有单行本,可以算作书,而《阿Q正传》只是一篇中篇小说,不能算作书,好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接着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我们打开了济宁城。”[1]329如此则雁翼读手抄本《为真理而斗争》的时间当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实际上,济宁城不是一天打下来的,雁翼读手抄本《为真理而斗争》的时间当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如此则雁翼读手抄本《为真理而斗争》的时间就与雁翼《创作前的准备》所述雁翼读手抄本《为真理而斗争》的时间相矛盾。雁翼《创作前的准备》云:“一九五七年,我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叙一九四六年一册血染的诗集的事……一九四六年初,在山东距野(笔者按:当为巨野)城下的战场上,连长把一册手抄的、血染的诗集交给了我,使我激动的不仅仅是烈士的血染的遗物,还有那诗集的内容。那册手抄的诗,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写的全是贫苦农民的生活,读了令人心酸。”[1]126-127
另外,打开了济宁城后部队整训两个多月,雁翼所谓一九四六年初打巨野只能是在打济宁城之前,但巨野距离济宁城的直线距离有一百多里,一天或两天之内不可能既打巨野又打济宁城。
又:陈士芬《解放济宁城》:“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下午,我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在杨勇司令员指挥下,挥师济宁,直捣城下……”①陈士芬《解放济宁城》:“于一月九日上午,为我一举攻克。”②田平《首次解放济宁和撤离见闻》:“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我晋冀鲁豫大军区的第七纵队奉命解放济宁城……九日胜利解放了该城”。③显然,雁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打开了济宁城之说是错误的,应于再版时加以修改。
(二)关于德国教堂及其藏书的问题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我们打开了济宁城,住在北关代庄一座大教堂里——据说,这是德国天主教驻山东的总部——里面藏有许多书,我们在这里整训了两个多月,学‘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我乘机读了一些我过去没有读过的书,才知道德国有一些大诗人——歌德、席勒和海涅,而且还偷偷读了一本《圣经》(是团长劝我看的)。”[1]329济宁之戴庄,因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戴鉴生活于此而得名,雁翼写作代庄是错误的,应于再版时加以修改。教堂是有藏书的,但教堂所藏之书一般与宗教信仰和传教有关,一般不会收藏与宗教信仰和传教无关之书,绝对不会收藏反对或妨碍宗教信仰之书。歌德、席勒、海涅力主理性、崇尚自由,基督教堂一般不会收藏歌德、席勒、海涅之著作,一般也不会收藏关于歌德、席勒、海涅之著作。
即使德国基督教堂收藏有歌德、席勒、海涅的著作及与之相关的著作,根据北京西什库天主教教堂的藏书情况,基本上全是外文图书,德国天主教戴庄教堂的藏书也应该基本上全是外文图书。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我不懂外语。”[1]331不要说教堂里还没有有关歌德、席勒、海涅的书,就算有,雁翼不懂外语,他又焉能读之?
另外,雁翼说还偷偷读了一本《圣经》,《圣经》就是《圣经》,一本《圣经》不知为何意?
(三)关于雁翼把中国所有古典小说都读完了的问题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读过了全部古典小说之后,我觉得文学性最高的是《红楼梦》、《老残游记》和《聊斋志异》。”[1]331
有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现在只有抄本,还未刊行。还有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由于种种原因就是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没有看过。著名学者吴晓铃《〈金瓶梅〉的艺术特点》云:“我们在六十年代写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但当时的一代,即使研究小说的,也没有看到过这部作品。”[6]413
雁翼一句读过了全部古典小说,口气太大,雁翼是不可能读完了中国全部的古典小说,笔者认为这是雁翼没有注意及时使用限定词的一个小小的语言失误,“读过了全部古典小说之后”这句话在《雁翼选集·文论卷》再版时应当修改为“读过了全部常见的古典小说之后”。
六 关于刘绶松著作的名称及雁翼创作准备阶段结束的时间问题
雁翼《我的读书生活》云:“全国胜利以后,我的读书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搞文学写作,读书有了计划性。中国的书,基本上是按照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史》和刘绶松先生的《现代文学史》的排列次序来读的。而对于外国的书,则侧重于人,就是尽量地把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传记)都找来读(对于中国某些作家的作品也是这样读的)。”[1]330雁翼提到刘绶松的《现代文学史》,刘绶松是没有写有《现代文学史》这部书的,刘绶松的关于新文学史的著作叫《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本书若要简称,应该简称为《新文学史》,而不应该简称为《现代文学史》。雁翼是否读过该书,值得怀疑,若雁翼真读过一本影响过自己读书计划的重要指导书,不可能连书名都记不清楚。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于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7],作为大学教材,印数有限,主要针对高校发行,1956年9月以后才发行到高校,有些高校还是没有拿到该教材,就不得不用油印翻印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作为教材。因此,雁翼于1956年当年拿到该书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雁翼于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的1956年当年就拿到该书,开始按照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排列次序来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但是,1956年3月雁翼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议,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创作前的知识积累,雁翼自称此时才开始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这绝对不真实。
雁翼《学诗初记》云:“一九五六年三月,参加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回来之后,我决定辞去行政工作,去作协搞专业创作。”[1]164雁翼自述此时确已结束文化积累阶段,开始专业创作。
雁翼《我与儿童文学》云:“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参加了北京的中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议,同年七月,被吸收为全国作协会员,同年底调作协四川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133雁翼自述此时确已结束文化积累阶段,开始专业创作。
其实,雁翼文化积累阶段结束的时间还应该在一九五六年之前,笔者认为雁翼文化积累阶段结束的时间应该在一九五四年《大巴山的早晨》出版之时。雁翼《我的第一本诗集》云:“我和出版社都没有料到,《大巴山早晨》出版后是那样轰动,洪钟等连连写文章在报刊上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连续配乐朗诵,苏联的报刊也翻译刊载,北京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来函邀我参加,公木老师也在报告中表扬我的诗。”[1]345可见,一九五四年《大巴山的早晨》的出版直接让雁翼一举成名,直接让作者雁翼被邀请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可以说一九五四年《大巴山的早晨》的出版标志着雁翼创作准备阶段的结束。即雁翼在一九五四年《大巴山的早晨》出版之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创作的文化积累或知识积累,若说雁翼到一九五六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之时才开始按照《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排列次序来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这是绝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也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
另外,雁翼所言《大巴山早晨》有误,经查雁翼的第一本诗集题名为《大巴山的早晨》[8],重庆人民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第1版。雁翼将其第一本诗集《大巴山的早晨》多次说成是《大巴山早晨》,误脱书名中的“的”字,这不是误记,而是一种基于方言影响的习惯性的省略“的”字的语言习惯或现象。
七 关于雁翼原名、家乡的村名及任分队长的时间问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每一卷卷首都有一篇《出版前言》,《雁翼选集·文论卷》之《出版前言》云:“雁翼原名颜洪林。”[1]1但是,雁翼《我与儿童文学》云:“我是老二,原名颜鸿林。”[1]130一个人的原名只有一个,一个人总有一个最早的正式之名,这个最早的正式之名是原名。颜洪林、颜鸿林在使用时总有一个先后。
《雁翼选集·文论卷》封面内折上又说:“雁翼,原名颜鸿林。”[1]这与雁翼《我与儿童文学》所载相合而与《雁翼选集·文论卷》之《出版前言》又不合。
雁翼《囚徒手记》云:“‘找的就是你这个黑雁翼’他把枪掏了出来。我也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对不起,我不是雁,我叫颜洪林。’他夺过工作证看了一眼,气馁了:‘你不是雁翼?’我说:‘工作证上写着哩。’”[1]398雁翼工作证上的姓名是颜洪林,可见,颜洪林是雁翼工作后所用之名,是曾用名,而非原名。雁翼原名当以雁翼自述其原名颜鸿林为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每一卷卷首都有的那篇《出版前言》中之“雁翼原名颜洪林”在再版时应更正为“雁翼原名颜鸿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每一卷卷首都有一篇《出版前言》,主要内容基本一样,《雁翼选集·文论卷》之《出版前言》云:“(雁翼)一九二七年农历五月十一日生于河北省馆陶县颜窝头村一农民家中。”[1]1但是,雁翼《我与儿童文学》云:“我于一九二七年旧历五月十一日午时,诞生在卫河(老名叫运粮河)西岸一个下中农家里,这地方原属山东,‘文化大革命’前夕划入河北——馆陶县颜家窝头村。”[1]130根据河北、山东村名的一般情况,即村名中有“家”字,当以雁翼自述其其家乡之村名“颜家窝头村”为准。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每一卷卷首都有的那篇《出版前言》中之“颜窝头村”在再版时应更正为“颜家窝头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每一卷卷首都有一篇《出版前言》,主要内容基本一样,《雁翼选集·文论卷》之《出版前言》云:“(雁翼)于一九四六年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文工团任分队长。”[1]1一九四六年尚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这一名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云:“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军在平津、淮海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于2月至4月先后进行了整编……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9]317既然一九四六年尚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雁翼也就不可能于一九四六年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文工团任分队长。雁翼《我与儿童文学》云:“一九四七年三月,我正式到野战总医院宣传队报到,任分队长,这是我搞文艺工作的开始。”[1]133当以雁翼自述其一九四七年三月正式到野战总医院宣传队报到、任分队长为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每一卷卷首都有的那篇《出版前言》中之“于一九四六年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文工团任分队长”在再版时应更正为“一九四七年三月正式到野战总医院宣传队报到,任分队长”。
注释:
①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6页。
②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8页。
③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2页。
参考文献:
[1] 雁翼.雁翼选集·文论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2] 罗隐.罗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季镇淮,等.历代诗歌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4] 朱栋霖,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5] 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J].春光,1934,1(3).
[6]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7]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8] 雁翼.大巴山的早晨[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4.
[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五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