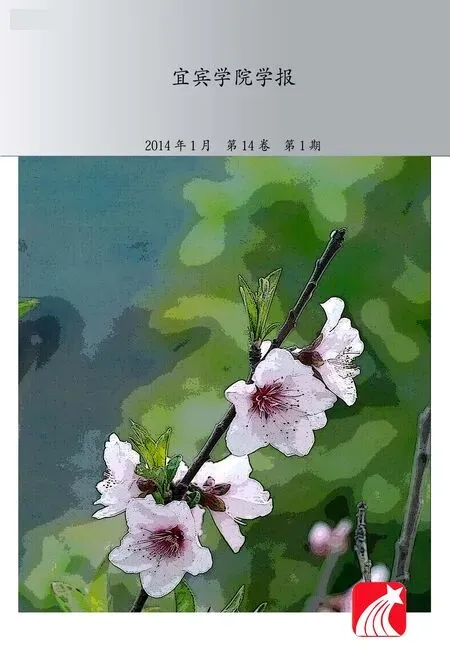《中庸》的修身思想
张 轩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为数不多的注重形而上理论之探讨的典籍,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然而,反观学术界对《中庸》的探讨, 对“中庸”大多以“不落两端”的思维方式或者“致中和”的终极诉求为集中论证与考究的核心,而其中关于“修身成己以成人”的教化理论却鲜为人所关注。毋庸置疑,注重天命、人性等理论的探源固然对于儒家自身的逻辑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一向注重礼乐教化、倡导成人成圣的儒家自然也把对人本身道德人格境界的修持放在一个极高的地位,这种劝导与规勉也自然而然地在众多典籍中成为了落脚点与必然归宿。
这种情况在《中庸》里面亦是如此。开篇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9,其实已经在总体上对修身之教化作了说明,也即依循本初之性、竭力尽性地修持人道。而所谓慎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20则是强调自律以及对性情关系的合理调试。“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既是孔子对“中庸之道”不得实行的慨叹,也是对后来之人能通过自我修持去切实贴近“中庸之德”的期盼。《中庸》里包含了这种关于人格修养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中庸》或许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儒家整体的教化与修养思想提供某些有益的思考。
一 “修身”的显现 ——贯穿于《中庸》始终的核心话题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把子思作《中庸》的原因归结为“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这是一种基于儒家道统传承的观点,代表了宋明理学家为复兴儒学而作的努力。关于这个道统,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将其明确为“允执厥中”,具体说来就是“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16。而关于“中”本身的内容,朱熹训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1]19他还引用了子程子的话,“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19这种对《中庸》主旨核心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切要的,因为“中”在先秦儒家本就是一个受推崇的理念,其内涵具有一种恰到好处和公正的性质。相传尧在禅位于舜时曾勉励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2]289。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就已经作为一个类似于“正义”亦或“公正”的宏观性原则被确定为政治运行的关键。因此,统治者对“中”的重视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王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3]261。这里政治原则的保障在于君主的道德状况,“中”具有了道德层面的意义,而这种伦理之“中”经过发展终于在《中庸》里有了比较明显的表现。
《中庸》开篇讲“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处“道”即是指“人道”。对“人道”进行修持就是教化的所在,而“人道”本身就是一个践行的过程,是实践之学,只有在不断修身的过程中才可以实现“人道”的彰显,实现对天命人性的复归。在这里,朱熹注解为:“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1]19朱熹认为,人之本性都“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人之差异、道德之沦丧在于气的缘故,因而教化就是用礼乐行政来对人“品节”,以期重新回到“无过不及”。尽管朱熹的注解大多是基于他本身理学的立场,以至于一句一个“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就这里对“中庸”之修身的教化指向而言确有依据。因此,整本书的重点在开始就已经说明了是对教化修养的一种探讨。“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20儒家强调常存有敬畏之心,无时无刻不循礼而动,而且特别把基于内在道德自律的“慎独”摆在一个尤为突出的地位,这种强调自我的节制、符合于礼,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诚”,与后文讲求“不诚无物”相呼应。无论是在《中庸》前一部分慎独的具体要求,还是后半部分对“诚”之本体层面、人性层面的论述,“真实无妄”一直都是“诚”的核心含义,也是对人涤除私心杂念,重返天道本心的一种导引。实现了自己内心的“诚”也就是对天命之性的复归,因而就可以说是“人道”的彰显。这样,《中庸》的道德教化意义就比较明显了。
“君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包含有很多德性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中庸之德”。“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1]20。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能够做到中庸,而且还是随时处中,这是因为君子明白“人道”“本心”之所在,朱熹解释为“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1]21。能够做到“中庸”就自然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为“中庸”作为一种根本的道德修持包含着对仁和义的一种合理践行。由此可见,“中庸”除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含义之外还有道德境界的属性,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甚至是区别君子和贤愚的一个标准。
然而,具体如何能达到“中庸之德”呢?《中庸》基于对孔子道德修身理想的一种理解,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身路径,这些理论贯穿整部《中庸》,从而使得“中庸”不仅是方法论的倡导,更多的还是人格的修炼和提升。比如“道不远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等。《中庸》所提出的这些人格完善的理论涵盖了孔子“仁爱”、“崇礼”、“重义”等众多的人格培育思想,体现出了儒家对道德境界本身的追求,也从理论上对道德修养、人道践行之意义作了充分的论证。与《论语》格言式的分散说明不同,《中庸》在具体人格修持的思想主张上有着一套极为严密的逻辑结构,主次分明,秩序规整,具有很强的体系性。
二 修身视域下的“中庸”义解
(一)修身之总纲——“诚”与“中庸”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1]21。“中庸”本身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和境界层次是至高无上的,它本身就是一切修身的终极指向,作为总纲对人们如何修身进行着导引,所有具体的道德条目和要求都服从于“中庸之德”这一根本性目的。“中庸”之为总纲就在于它“恰到好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这里体现的是一个“权”,因时制宜,不拘泥固执,具体到道德修身方面是对各种道德要求和道德实践的合理把握,使之分毫不差、灵活得当。而要做到这点则必须建立在对天道和人道的充分理解之上,所以孔子认为要真正做到中庸是十分困难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1]23。但如果真的所有人都无望达到,那这种理论又未免过于消极,对于人们道德的自我改善也是用处颇少。所以《中庸》又肯定了人通过努力还是可以达致的。对于实现修身成己以至于中庸的途径,《中庸》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32朱熹把“诚”训作“真实无妄”,这种理解在后代得到了继承,如宋代大儒陈淳就在《北溪字义》中说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至诚乃是真实极致而无一毫之不尽,惟圣人乃可当之”[4]33。“至诚”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天,一为圣人。就天而言,儒家认为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完全按照他的本性去生化万物因而天具有了“至诚”“至公”的属性。关于这一点,陈淳论述得最为清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秋杀了便冬藏,元亨利贞,始终循环,万古常如此,皆是真实道理为之主宰”[4]33。就圣人而言,儒家理论系统下的圣人作为道德的绝对理想,具有“生而知之”、完全依照人性之本初去视听言动而不为私欲私意所掩蔽的品质,这种不被外在欲望杂念所诱惑而始终在人性的中正轨道上运行之圣人便是“至诚”,是对“性”的诚,因而是与天合一的。正是因为圣人具有不偏离人性轨道的天生素养,所以圣人的教化才有了自身的根据,自己的状态便是人们修身的楷模和终极目标。“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33作为天所命的“性”是和天一样“至公”的,所以只要能返回到“诚”也即实现了人道的复归。在儒家看来,圣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圣人生而不会违背本性。与之相反,作为被后天物欲遮蔽的常人,其为学用功处则就应该是努力通过学习人伦之常德去体认不变之常道,从而后天逐渐地实现复归。这样,由“中庸”到“诚”又到了具体德目的学习和践行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所学的便是义理之学,贯穿于其中的是“诚”。一方面,通过仁智勇去逐渐修持人道,而修持的结果就是达到“诚”;另一方面,“仁智勇”本身的实现又只有在做到了“诚”时才有可能。“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1]30这里的“行之者一”就是以“诚”为核心,无论是培养自身的三达德还是去处理无论关系都应该不离“诚”这个主线,否则只会偏离人道之常。这样,《中庸》的修身与教化就是以“中立而不倚”为至高标的,以“诚”为实现“中庸之德”统摄的具体路径,而又具体化为“仁智勇”等德目的塑造。
(二)修身之关键——以礼制中,以和为用
儒家讲求“仁礼”并行,把“仁”看作内在表现而把“礼”看作“仁”的外在表现,因此就作为具体外在实践的道德修身而言,“礼”自然而然被更多地提及,以此作为人们由外在之“礼”巩固、发散内心之“仁”的保障。在《中庸》里,对“礼”的强调也是十分繁多的,“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1]29,在这里,“礼”实现了从家庭祭祀到国家运行的一贯作用,自然地成为人们应该遵循的原则。其实,“礼”和“中”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礼夫礼, 夫礼, 所以制中也”就在强调礼本身的规范性和具体操作性对于实现“中”的意义。而“礼”之所以能够“制中”不仅是因为它有具体的规范性质,更主要的还是二者之间具有深层次的统一性,礼之所以得到肯定就是因为它是和“中”一样都有一种“正”:“中者, 行之无过不及, 正者, 立之不偏不倚, 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 故得其序而无邪僻, 此礼之本质也”[5]。礼强调的秩序等级,亲亲、尊贤、长幼都是一种合乎天理人心的“正道”所在,代表的是合理适度的原则,所以礼的规范性必然就会帮助人们实现“正”,依靠秩序的遵循、礼仪的典章制度来保持一种合理不偏。
“中”强调一种中立不倚、不偏斜,因此“中”体现在不同行为的关系处理上。在这一点上,“礼”同样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因为儒家的“礼”历来强调一种秩序性,《春秋说题辞》曰:“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天下咸得其宜,便是一种不过分、不偏执一端。《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6]这种得体就是一种不落两端,表现在对人道德行为的作用上就是防止人们走极端,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111,就是在强调过分的谦恭、谨慎、勇猛和正直都不是合于儒家理想的标准,都会走向与初衷相悖的反面,只有把这些道德要求置于礼的调节指导之下才会有合理的结果。
这种“礼”的秩序性、调节性在《中庸》里被作为修身的关键所在,很多道德品质的修养就依赖于遵循礼。“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1]29,礼和位是紧密相关的,循礼而动也包括着爱亲、尊贤,“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1]37,礼乐之所以能导人以正,就在于它是圣人在其位而作。其中,周礼最为孔子称颂,被视为安身立命乃至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1]37所以,《中庸》反复强调了礼之于修身的重要性,“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切德行还得要礼来规约。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20《中庸》除了强调礼作为具体德行的一种指导原则,还提出了“和”的目标。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也,万物育也”,“和”在这里是以一个目的性的标准来对修身进行方向的指导。二者相比,“礼”更多是从修身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规范角度进行调节,而“和”是从行为最终之结果的期望上进行指导。《说文解字》:“和,相应也,从口禾声”[7],这说明“和”的本义在于众多事物关系上的共生共荣,是一种积极性的“共在”。这样,“和”就与“中”有了相同之处,唯有恰到好处的适度不偏,才有所谓的“和”。回到《中庸》本身, “中和”在开篇就有很明确的指向,喜怒哀乐作为情,人性之先天状态是“未发”,但一旦生发出来则是“发而中节”。这种中节的状态就是“和”,朱熹把这解释为“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用道心去指导人心。可以看出,“中和”首先的一层含义就是对性情关系的一种调试,是让情不至于动荡不安、泛滥无边。性和情的关系永远都不能让情遮蔽性。这种“中和”的理解,对于修身自然有着比较明确的意义,也因此在后世为宋明理学所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
(三)具体德目的塑造
《中庸》十分重视从具体的道德品质方面为人们的修身提供指导和要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1]25孔子以谦虚的口吻说自己未能尽到仁义孝道、忠信之义,其实是说明这些道德品质对于人修身的重要性。这种对道德品质的强调可以见到很多,“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其中,《中庸》比较推崇的应当还是人们对三达德的自我培养,通过仁智勇这些儒家历来重视的核心道德品质去处理好“五达道”的关系,这样才会有人道德品质的提升,“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1]30。
当然,因为儒家历来强调天子与庶民的不同位格,因此在道德修养的具体条目上也有专门针对君主自我修养的要求,这集中体现在治国九经之上。“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1]32这些要求就其根本来说由“诚”统摄,其关键点应该以礼为标准,以和为标的,同时它们又都显示为众多的具体条目,从而表现出《中庸》在修身方面的体系性。
三 《中庸》修身思想的特点
切中伦常,随时随地在生活中修身。“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20人道所以为常道就在于它是“成人”的标准,丧失了人道也就只能是行尸走肉而没有了人的本质性内涵。所以,《中庸》强调自我的道德修持并不是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暂时性修炼,而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努力修为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才有了“君子之道费而隐……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1]24,这样人们就应该
从生活中,在日用伦常里去体会人道,修身养性,调和性情,复归于天命之初的状态。
反观内省,突出自我的能动性,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1]26。在《中庸》看来,自我的道德提升只有在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中才有可能,怨天尤人只会让人心生不满,从而情欲动荡难以有自身境界的提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是内省和反观的功夫。与之相应,既然内省则必然就要求能够自律、慎独。内省而不改正则毫无意义可言,所以慎独和自律强调了人自身对于道德改善的意义。外在的监督只是一时的强制,既不能从内心的根本上提高道德境界,也不能从长久的时间性上给人以保障。
结语
总而言之,《中庸》的价值不仅在于从理论上对“不落两端”、“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操作进行了论证,更重要的是它对儒家的修身进行了很好的说明。儒家思想历来以“成人”、“成圣”为核心指向,《中庸》便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从根本之“诚”与礼、和、仁、智、勇等不同的层面进行了详细的诠释说明,从而对于儒者理想人格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中庸》的落脚点在于实践性,尤其是道德的实践性,这体现了儒家历来追求的“知行合一”,也是当今道德滑坡情境下应该深入挖掘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陈澔.礼记集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6] 刘熙.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