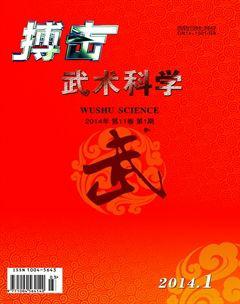导致古代中西方体育差异性因素分析
崔怀猛
(徐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徐州 江苏 221116)
1 中西体育竞争意识的差异性
1.1 古希腊人的体育竞争意识
体育运动有多种方式,竞技性比赛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人类自产生以来,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与自然展开了长期斗争,斗争的结果使得人类逐渐地认识到竞争的作用与价值,竞争是动物的天性,人类的这种天性表现在体育活动中便是竞赛取胜。古希腊是商业贸易兴盛地区,城邦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不断发生争战,民风习俗崇尚竞争,喜好体育竞赛,以体育竞技为聚会欢乐,这便是顺应了人类天性中的好胜心理以逞强取胜为满足,并且把这种满足的欢乐奉献给奥林匹亚诸神,创造了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是强者大显身手的地方,在体育场上万众瞩目的地方,能够战胜对手取得优胜,既是满足个人争强好胜的心愿,更能够增强雄视一切的自信心,有更多的优越感,更加激励起个人的奋斗精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出的“更高、更快、更强”口号,就是对古代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提炼,希望通过体育竞技赛会创造更高、更快、更强的成绩,发挥人体生理极限能力。竞赛是“奥林匹克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古代希腊人从政治需要、民俗发展、人民喜爱,这几个方面要求表现出来的“强者文化”,是肉体与力量崇拜的心理反映。古希腊人把胜利当做衡量人生成败唯一标准,对于成功与失败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次,体育竞赛之所以受到希腊人的推崇,还因为在体育竞赛中制定了平等、公正的规则,凡是在体育场上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取得优胜,戴上冠军的桂冠,受到城邦的重视。裁判员对于场上比赛的运动员是一视同仁,只要你是希腊血统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凡是参加比赛的都按同一规则来对待,是绝对的平等。体育场上公平的比赛,平等的法规,公正的执法精神,给予了社会一种美好的期望,期望社会也能像体育赛场上一样的平等、公平、公正。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的“公平竞争”原则得到了希腊各城邦的一致认可,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名诗人提摩克雷翁,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社会名流索福克勒斯、欧里兹德斯,都积极参加各种体育竞技赛会的比赛。柏拉图还曾获得摔跤的桂冠,毕达哥拉斯获得拳击的冠军。
1.2 古代中国对体育本质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也有以竞技方式开展的体育活动,早在周朝初年就有射箭、摔跤、驭车等体育比赛,到了汉代,还创造了集体的蹴鞠竞赛方式;但是,这些体育竞赛都是以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为目的,参加者必须遵守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抑制人们争强好胜、不服输的天性。“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1]这种竞争是君子之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只要在竞赛中用尽自己技术,就达到了参加的目的,至于能不能取得好成绩,这是不必计较的,重要的是在比赛过程中礼仪规范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现。所谓:“胜亦可喜,败亦无忧”,成功与失败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这样的竞争意识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成为教化民众的重要工具。
中国古代个人的修养是以“温、良、恭、俭、让”为最高标准,温和、谦让都是和竞争相对立的[2]。竞争意识虽然能有鼓舞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优点,但是,也有纵容贪慾无厌、恃强凶狠的缺陷。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更是不能有争强好胜的贪心,贪心一起,战争随之而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而一般人民有了竞争的贪心就会犯上作乱,“勇而无礼则乱”。“好勇疾贫,乱也。”一旦竞争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人人都从为个人谋私利出发而进行竞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一个国家会在竞争中兴起,也会在竞争中衰亡。中国古代不主张与人竞争,对人要温和、谦让,但是却提倡自我超越,在讲自我修养的《礼记·大学》中就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所谓“吾日三省吾生”,就是要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每天才会有新的收获[3]。
古代的中国由于等级制度森严,体育竞争自然也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环境,于此同时,古代的统治者还会以各种方式抑制人们的竞争观念。辽国大臣马得臣曾上书皇帝,建议皇帝不要提倡打马球,因为马球竞赛是“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辽史·马得臣传》)马球竞赛没有等级制度的约束,君臣同在一个马球场上竞赛,会助长臣下竞争思想的滋生,破坏礼制规定。乾隆皇帝在北京福海举行龙舟竞渡时就下令取消竞赛的方式,“有例怀忠粽,无争竞渡船。对老百姓的教育就是要安居乐业,不要有竞争之心;龙舟竞渡奖励胜利者,就是提倡了竞争,这就破坏了对人民的教育成果。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就是以抑制竞争观念来教化人民。
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对于体育竞技有不同的观念;古希腊赞扬竞争,认为公正的法规可以保证竞赛公平的进行;中国古代认为,竞争应该从内心克制,以道德来约束竞争心理的发展。两种对竞争不同的观念导致了开展体育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体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就有很大的差异。
1.3 竞争意识对体育的影响
竞争意识是一把双刃剑,社会上竞争观念过于浓烈,超出了礼制约束的范围,就会造成社会上秩序混乱。体育竞赛场也是如此,如果强烈的竞争欲望超出了竞赛规则和道德的框架,就会发生出轨行为,后患无穷。古代奥林匹肯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感性竞争的欲望压倒了理性的立法。虽然,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者虽然也采取了许多补救措施,对舞弊者处以罚金,把姓名刻在耻辱柱上,但是,竞赛成败关乎个人一生的利益,损人利己的舞弊行为并未能得到制止,就是因为这些舞弊行为和个人利益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源也就在利益的竞争上面,竞争的基本动力是建筑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竞争能够调动个人的积级性,鼓舞人的奋斗精神,做出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前进的事;但也能够利令智昏,做出违反体育竞赛规程、法令、道德,不利于体育竞赛发展的事情来。
2 对“休战”态度的不同理解
2.1 古希腊对于“休战”的认识
“神圣休战”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希腊分裂动乱的年代,城邦各自独立,称霸一方,没有“神圣休战”的措施,就不可能召开全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也就没有了“奥林匹克文化”。古代希腊虽然分裂成为一二百个城邦,但是,他们是同属于一个民族,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祭祀同一个天神宙斯;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就是在祭祀天神宙斯的名义下召开的,如果谁阻碍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的召开,就是亵渎了天神,背叛天神的意志,必然会遭受到天神的惩罚。“神圣休战”就是在全希腊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民族情感之下达成的共识,得到各城邦一致同意下签订的条约。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的倾向,竞技赛会成为大会的主要形式,“神圣休战”就成为“奥林匹克文化”的一个部分,连外来的侵略者,马其顿王国、罗马共和国也都承认、遵守“神圣休战”的条款,也就是说,是体育竞技赛会给希腊半岛带来了战争局部休战,带来了一时的和平,商旅通行,人民安居,能够过上一段安稳幸福的生活。应该说,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能够顺利的召开,并延续了一千余年,“神圣休战”是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神圣休战”虽然并非完全是因为体育竞技而产生,但它是伴随着奥林匹克竞技赛会而共生共存。奥林匹克运动场外各个城邦的战争停止了,奥林匹克运动场内各城邦文化才能亲密交流,给全希腊民族带来一次团聚的机会,体现了和平友谊的情义。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景象,几个月的休战时间,但是,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希腊人民来说,这已经是可以满足的了。
“神圣休战”毕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希腊半岛上为利益争夺而发生的各种军事战争,举其大者而言,在公元前500年,发生了“波希战争”;公元前431年,开始了“伯罗奔尼撒”的城邦内战;公元前356年,希腊本土为马其顿王国所占领;公元前146年,罗马共和国代替了马其顿王国侵吞了希腊。“神圣休战”并未能给希腊人民带来永久性的和平幸福,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大部分时间是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包围之中。“神圣休战”只是全希腊民族共同宗教信仰的临时措施,政治和商业贸易的需要,并非是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文化必然的结果。
2.2 古代中国对于“休战”的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神圣休战”的方式是赞成的,但是,临时休战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真正解决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达到永久的和平。要社会真正的永久和平,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实行王道的大同社会,王道的大同社会虽然只是儒家的一个理想国家,两千多年来还没有国家能够实现过,但是,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大同社会虽不可及,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却是能够实现的。《孟子》书中记载了他同梁惠王有一段对话:“(梁惠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这段对话反映了战国分裂动乱的局面,诸侯王和普通人民都不满意,他们希望天下早日统一,过安定的生活。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几经分裂都终归统一,各民族文化不断的融合在一起,合的时间占大多数,统一是大众人民的愿望。国家统一了,社会随之可以安定,没有了内战,就减少了许多战争。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动乱的年代只延续了几百年,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便併吞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4]。中国古代与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的时代对比,是统一多于分裂,国家统一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少了许多。
3 古代中西方教育思想方面的差异性
3.1 古希腊的教育特点
古代希腊在创造奥林匹克竞技赛会之时已经有了明确的教育思想;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是全面发展教育,培养有文化、有教养、身强力壮、能够战斗、经商、政治管理的人才。以斯巴达城邦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是纯军事教育,培养能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身体强壮的武士。虽然,古希腊的两种教育思想有所差别,但是,其共同点是:都特别重视身体训练,培养青少年一代身强力壮,可以胜任保卫城邦的任务。斯巴达城邦对品德教育看得是较为简单,只要能服从军事首长的命令,进行战斗,就是一个好的战士。雅典城邦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是,他们把身体训练与思想培养分裂开来,身心二元化,身体强壮是由体操训练来完成,品德培养是由文艺修养来进行薰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次提到这种二元化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5]”虽然,雅典的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方计,但是,把品德培养和身体训练完全分离开来,人的身体强壮是由体育训练来完成,人的品德修养则由文化艺术来塑造,“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情操”,这种分离式的培养不可能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统一,体育训练中的思想和文艺培养的思想发生严重的不和谐,其最明显的冲突是在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章程与比赛规则方面的矛盾;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的章程规定,“竞技者必须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法律上,被认为没有污点的人。”也就是说参加竞技的人在道德上是没有污点,没有残害过别人的前科,但是,参加拳击、摔跤、混斗比赛的运动员则可以在比赛中使用最残酷的手段。无数的英俊青年就是这样在奥林匹克竞技赛会上遭遇到残害或者死亡,甚至获得冠军的本人也会是遍体鳞伤。这就使得参加体操训练的运动员在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成为铁石心肠,心狠手辣,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就和品德要求相去甚远,和教育方针中有文化教养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
雅典城邦是古代最早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人们享有极大个人自由;但雅典又是一个对于英雄、力量极度崇拜的城邦,自由与英雄崇拜两者相结合,在“奥林匹克文化”的教育思想中就产生了个人英雄主义。奥林匹克竞技赛会上是非常崇拜冠军的,冠军所享有的荣誉完全是个人的,冠军在城邦的各种事务中都享有特权,如免除个人税金、赠予别墅、获得养老金、终生得到赠予的食物,遇有战事发生,冠军可以晋级为带兵的军官。这种种措施都表现了一种教育观念,就是对个人英雄的崇拜。
古代希腊由于忽视了体育的其他教育功能,只注意体育的健身作用,过分地推崇竞技,崇拜竞技的胜利者,竞赛的结果对于参赛者来说至关重要;对于结果的无比重视导致了一些运动员出现道德败坏,发生了腐败舞弊行为,反而阻碍了体育竞技的正常发展。
3.2 古代中国对教育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教育方针早在周朝初年就已经确立了下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国子”学校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教育作用更深入的了解,教育思想不断的补充完善,春秋时代,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品德的培养。孔子是当时的大教育家,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勇力、勇气的人,特别要求要加强品德修养;他说:“勇而无礼则乱”,“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6]只注意身体锻炼而不重视品德修养,其结果,是会走向危害社会道路上去的。对于那些凭借个人勇力而逞强好胜的人,孔子是不予赞许的,对于那些逞强好胜、徒慕虚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眩耀个人勇力的人,中国古代社会是不予赞同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认为人的身心是一体的,身心一致,身心并重,练身体必须要先练心。《礼记·射义》中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内心端正,身体站直,才能够平心静气的瞄准,才有可能射中靶子,身体能力和心理品质是相辅相成的。古代射箭名教师飞卫在教弟子学习射箭时,先教练习静心,注意观察目标,躺在织布机下看布机的梭子来回穿过,待到眼睛看梭子穿过而不眨动时,心理素质稳定了,再去练习瞄准射箭,就可以百发百中了。驭车名教师泰豆氏教学生学驭车,首先是要行走在“梅花桩”上,待到不用眼看而能够熟练的行走时再去学驾车,这样,就可以不专注马匹而熟练驾车,做到得心应手。中国古代的体育是主张身心一体,要练好身,先练好心,心理素质在体育训练中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之,“身心一体”的教育观念是把身体锻炼纳入于教育之中,体育是教育的一个环节,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部分。身心分离的教育观念则是把身体锻炼与心灵培养分离开来,身体锻炼只注意体能训练,心灵培养则是从另外的途径进行,其结果是南辕北辙,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古代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的衰落早在它兴起“奥林匹克文化”时的教育因素中就已经埋下了。
4 结论
古希腊所创造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是超越城邦的体育大会,其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体育原有的功能,“奥林匹克文化”,“奥林匹克精神“,对当时及其以后的欧洲文明发展起到了原始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体育受政治、经济及民风习俗的影响,没有集合多个诸侯国家开过体育竞赛大会,甚至对体育的竞技形式也很少开展,社会上推广较多的是军事、娱乐、养生性质的各种身体活动,并从实践中认识到身心一体,无论是从培养人的教育角度,还是增强人体的健康角度,都要身体与心灵一体化,形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特色,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1]潭 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1994.
[4]钱 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