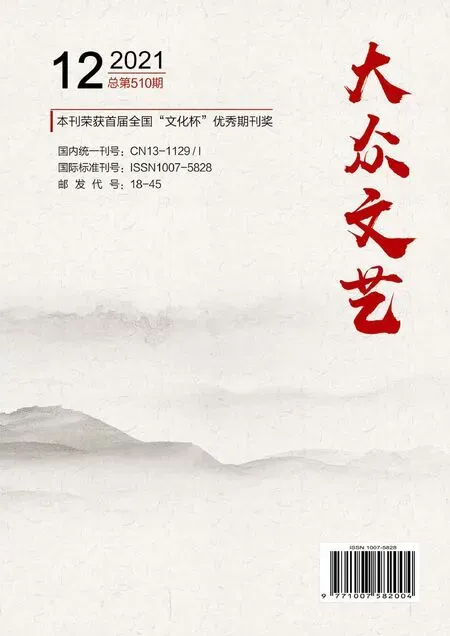论《罪与罚》中的三种独特存在
商雪晴 (首都师范大学 100089)
论《罪与罚》中的三种独特存在
商雪晴 (首都师范大学 100089)
拉斯科尔尼科夫、丽莎维塔、斯维理加洛夫在《罪与罚》中构成三种独特的存在,承载着作者的深度思考。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地下室人的代表,他的杀人行为源于对深层自由的实践,最终走上了人神之路。丽莎维塔是众声喧哗中的休止符,在小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斯维理加洛夫在人性罪恶和恐惧的重压下以自杀终结,虽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重身但他的选择是一种与之区别的超人信仰的殉道,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体内超人意识的提纯与汇聚。以上三者承担着作家尤为别致的思考,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丽莎维塔;斯维理加洛夫;独特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塑造了多个极具个人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丽莎维塔、斯维理加洛夫较之他人更为复杂,最值得深度分析。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地下室人的代表,是对“深层自由”的实践者;丽莎维塔如同复调中的休止符,大音希声;斯维理加洛夫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重身,他的自杀也具有极大的象征性和必然性。这三者构成了《罪与罚》中的三种独特的存在。
一、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深层自由”实践的“地下室人”
作为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对他的研究层出不穷。纵观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视域。其一,看重他的“二重人格”。一方面,他善良、真诚,在拮据之时依旧帮助马美拉多夫,但另一方面,他却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成为杀人犯。他想要怀着人道主义精神解救被剥削的如同他一样的小人物,但他却用杀人的非人道主义的方式去实施,于此就必定陷入到悖论的漩涡。其二,侧重对他“超人思想”的阐述。他作为“超人”的原型提出了关于“平凡人”和“不平凡人”的理论,怀着一种超人的思想认为可以如拿破仑一样用极端的方式去拯救受苦的人,但又仇恨剥削的魔鬼,认为他们就是“虱子”,一定要被推翻,这样又具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于是研究者就从他的“超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中看重他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不可否认,以上两种视域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也会发现,这其中潜藏着二元对立的倾向。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来审视他、探究他的杀人动机并以此来深层了解这一人物。我们不妨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对“深层自由”实践的“地下室人”。
(一)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地下室人”的代表
《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一个“畸形的和悲剧性的”地下室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作品延续了这一形象并形成了地下室人系列,拉斯科尔尼科夫就是其中一员。他具有地下室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是一个虚荣和自卑的矛盾体。而这种矛盾的心理逐步演变成病态的人格。怀着因“过多的意识”而带来的“野蛮人的孤独感”只能“从裂缝中观察和倾听”,而观察和倾听到的黑暗就造就了他的批判意识,这重重可见可闻的黑暗让他感到屈辱和压抑,终于促成了他对自由的寻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室人揭示出了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在不为人知的“地下室”中贮藏和囤积着的丧失理性的自我意识。
(二)其杀人源于对自由的实践
地下室人看似极端化,但实则在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只不过将一般人的内心隐蔽的世界得以发现、放大和实践。正如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就把人们心中的侧影变成现实。每个人都有对自由的寻求,这种自由是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的,“一种无法消除的需要的和永恒的梦想”1。在小说中曾写到小饭馆里的学生和军官的谈话,在谈话中学生说到:“我真想把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杀死……我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2但是他们的谈话只是想法,最终以“下不了这个决定”“再打一盘台球”3而告终。拉斯科尔尼科夫听到之后不觉感到某种定数,于是他就成这场杀人案的实践者。他完成了一般人心中渴望做却不能做的事情,实现了一种“自由”。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杀人动机是一次对自由的追寻。尼•别尔嘉耶夫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思想,即没有罪和恶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体验,就不可能取得世界的和谐。”4为了取得世界的和谐,他就承担起了对自由的一种尝试,即使这是罪和恶的自由也在所不惜。在马美拉多夫所谓的“人无路可走”的社会中,这种对自由的追寻和实践就成为了一种反抗的形式。
(三)实践的自由是一种“深层自由”
拉斯科尔尼科夫追寻的自由是“深层自由”。这是地下室人自由观的一种延续。徐凤林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谈到了地下室人不同于地上人的三种规则,即意志不服从理性,向往对自己有害的东西,反抗必然性的自由。这也成为了对“深层自由”的三个证明。
从第一个证明来看,他在“地下室”中一切理性规则都被消解了。他在谋划杀人之前经历过多次挣扎,充分展现内心深处自由与理性的交锋,但是最终他思想中的理性因素都被意志替代了。从第二个证明来看,地下室人坚决反对利益的原则及其普遍性,他们向往深层自由,甚至向往对自己有害的痛苦的东西。正如同尼•别尔嘉耶夫所说:“人不是必然的趋向于益处。在自我意志中人常常是宁愿受苦,他不与理性的生活秩序讲和”5从他反复的挣扎就能看出,他必定知道他的行为会为自己带来害处,但是他依旧去实施了。此时,他把愿望自由看成最重要的追求,这也是促成他杀人的一个动机。于是“他就在自我意志的自由之路上痛苦地徘徊、流浪”。6从第三个证明来看,他的“杀人”行为是公认的罪恶,但这种必然性也不能扼杀自由的愿望。在理性面前他没有妥协而是在反复的挣扎中勇敢地反抗必然性,打破“石墙”,甚至是“以头撞墙”。综上三个证明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他的杀人是一次追求“深层自由”的尝试,这种自由就如同他的信仰。他就是对“深层自由”实践的“地下室人”。
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被流放的结局看似显示出他的这场“深层自由”实践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其的否定。这一人物承载的不是褒贬亦或决判而是深切的思考。小说的最后,拉斯科尔尼科夫都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过,“要是命运能让他忏悔那该多好啊……但是他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改之意。”7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他“认识到错误并且走上善途”的认识就有失偏颇。他的流放不是一个弃恶向善的转折点,而是踏上对“人”之自由的追寻与实践的新旅程。
二、丽莎维塔:复调中的休止符
丽莎维塔这一人物的设置有着很深广的价值。为了构成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作者完全可以只设置阿廖沙这一个“被害者”,但是此处他却设置了丽莎维塔,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她的存在有着独特的意义。从复调层面来说,她就像是休止符,大音希声,是复调众声喧哗中不可忽视的“声音”。
首先,丽莎维塔的存在加深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恶,提升了整部小说的悲剧感。在行文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阿廖沙和丽莎维塔外在和内在的截然不同。她们就构成了一组“丑与美”,“恶与善”的二元对立。但这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都命丧于拉斯科尔尼科夫之手,她们的结局确是相同的。如此,就展现了小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的戕害。小人物不仅得不到所谓“大人物”的保护,还要在彼此之间开展杀戮,他们都是可怜之人,但却不能有相惜之处,从中我们就可以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剧感。同时,拉斯科尔尼科夫怀着一种拯救苦难之中的小人物的心理却最终杀死了曾为他缝补过衣服的小人物丽莎维塔,这大大加深了他的罪恶,使得小说中的“罪”有了更深切的内容。
其次,加深“罪”的同时也同步加深“罚”的内涵。她被杀死之后却仍旧出现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生命中,化作拉斯科尔尼科夫内心潜藏的厚重的罪恶感。他一心想要杀死虱子一样的阿廖沙,但是却杀死了丽莎维塔,他曾说:“我现在多么恨那个老太婆啊!……可怜的丽莎维塔!……丽莎维塔!索尼娅!……她们献出了一切……”。8拉斯科尔尼科夫重现当时的情景,认为阿廖沙活过来他也会再次把她杀死,可见他并没有为杀死阿廖沙而自责,他痛苦的源头是因为杀死了丽莎维塔,这个善良的如同索尼娅一样的女人。可以说,丽莎维塔促成了他的自我惩罚。丽莎维塔越美好,这种“罚”的内涵就越深广。
最后,当这种“罚”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发生了转化,促使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走上“新生”的道路。虽然丽莎维塔没有如同索尼娅一样的显性的规劝,但她隐形地贯穿在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秉持着“超人思想”杀死了虱子一样的阿廖沙,但是同时也殃及了本无罪过的丽莎维塔。他就在一次次的自我惩罚中促成了对“超人哲学”的摒弃。由此可见,她的“沉默”并不是一种话语权的丧失,而是在众声喧哗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贯穿在整部小说当中,加深了“罪”和“罚”的含义,也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生命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这种无声胜有声,带给人们更多的震撼和思考。
三、斯维理加洛夫:以自杀终结的二重身
(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重身
“二重身”源于德语,是哥特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哥特文学中的“二重身”常常以自我的变体、自我的镜像等方式出现。斯维理加洛夫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重身”,作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一种变体存在。
他们同为超人的代表,存在一种“镜像”关系。超人哲学是19世纪的产物,尼采所宣称的“超人”是在他宣称“上帝死了,要对一切传统道德文化进行重估”的基础之上,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取缔旧世界的一切事物。他们就是如此,以自己为标准来构建自己的超人的价值体系。如此,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应”。但是小说发展到最后非常值得玩味。二者同为超人思想的产物,但是结局迥然不同。在他们背负着“罪恶”的同时,拉斯科尔尼科夫选择了人神之路,而斯维理加洛夫选择了自杀之路。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同为超人的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这两种人物对归宿的选择其实也是对两种信仰的选择。前者选择了人生命中神圣性的复归,而后者选择了超人哲学。
“神性是人性的内在精神,神对于人来说不是完全外在的东西,而正是努力的目标,路程的终点”9。从这一意义上说,拉斯科尔尼科夫走上的向往神性之路是一种现实与信仰某种程度的和解,他正在努力地发掘曾经被自己背弃的自身的神性来开始进行对自我的改造。而斯维理加洛夫选择了自杀,这无疑不是一种向超人思想的殉道。“神的存在与其说是人的生命的前提,莫不如说是生命历程的结果”10,对他这个怀疑论者来说,神性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历程中,因此他最终的选择仍旧是对超人思想的坚守。他作为“二重身”就如同拉斯科尔尼科夫分裂出的变体,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超人意识的提纯。在他自杀的同时,拉斯科尔尼科夫就选择了自首,这种死向生的转化也象征着他所代表的超人哲学在拉斯科尔尼科夫那里真正的完结。由此,斯维理加洛夫就构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重身,他也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灵魂中的一部分。
(二)不能承受人性之重的自杀者
区别于德国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深处仍然保存着人的形象。他曾说,“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它……我想做一个人。”11他的作品展现了如此多的人物,承载着他对“人”无尽的思考。自杀者又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是展现人性的极端化表征。斯维理加洛夫作为小说中正面出现的唯一的自杀者形象,更加承载着作者对人性之重丰富的思考。
斯维理加洛夫承担着人性的“罪”。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列举出各种恶行的表现: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斯维理加洛夫就具有以上的“七宗罪”。他不仅为人傲慢、善妒、贪图食欲酗酒和放纵享乐,他还承认曾因为贪婪在赌纸牌时当骗子手,因为欠了很多债而被关入监狱。他的家奴菲利普的上吊自杀也与他暴怒下无止境的处罚有关联。他在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对话中曾明确表露过,“的确,我是个淫荡好色和游手好闲的人”。由此可见,这七宗罪在斯维理加洛夫身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除了人性中罪恶的重量,“恐惧”也构成了人性之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人物承载了人在茫茫宇宙间的恐惧意识。他展现了人在毫无边际的宇宙面前,无可依附的自身恐惧。在失去了自己的依赖以及上天的存在这两种因素之后,也就要必然导致失去自身存在的根基。首先,杜尼娅对他而言并不是简单的色欲的对象,而是一种必要的依赖。他曾有过表露,“是杜尼娅挽救了他”。当失去了杜尼娅之后他就失去了在人世的依附,失去了在宇宙间的安全感。他对杜妮亚的纠缠和留恋就如同是抓紧最后一根稻草,抓住与这世界的最后一点关联。其次,他又是一个纯粹的怀疑论者,坚决否定上帝。上天是不会在他的意识中存在的。从以上两点看,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依赖,也失去了上天的存在这两种因素,这就导致他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自杀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必然的。人性的罪恶和人性中的恐惧一起被赋予在了斯维理加洛夫这个人物上,它们一起构成了人性的重量。这重量使得斯维理加洛夫想要逃离,最终用自杀成就了“到美国去”的梦想。
在《罪与罚》的世界里,他们三者都承载着作者别样的思考,由此构成三种独特的存在,在整部小说中意义尤其深广。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地下室人的典型,他在黑暗中洞悉着“无路可走”的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反抗,不惜伤害自己的利益去实践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却又不敢实现的“深层自由”。从这意义上会更好地理解他最终不忏悔的姿态,他踏上的“新生”实则是对深层自由的延续,是走上人神之路寻求“人”之自由的探索;丽莎维塔的出现虽然短暂,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存在,与阿廖沙对比,她就是美好的化身,但这种美好加深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也同时加重了对他的“罚”。她大音希声更成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超人思想摒弃的催化剂,她的死亡余味之力量也显得更加震撼;斯维理加洛夫作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重身,他难以承担人性的罪恶和失去杜妮亚这关乎世间唯一依附后的巨大恐惧,由此走上自杀的极端道路。从另一个层面说,他的自杀也是对超人思想的一场殉道的仪式,象征着拉斯科尔尼科夫体内超人思想的彻底完结。这三者在《罪与罚》中都极具深远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他们所承载的意蕴和内涵甚广,值得不断考寻。
注释:
1.徐凤林.理性自由与神性自由——论舍斯托夫的自由思想[J]. 浙江学刊.2004(02).
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朱海观,王汶译. 罪与罚[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3.
3.同上第64页。
4.(俄)尼•别尔嘉耶夫,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6.
5.同上第28页
6.同上
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朱海观,王汶译.罪与罚[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534.
8.同上第273页.
9.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
10.同上。
1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冯增义,徐振亚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