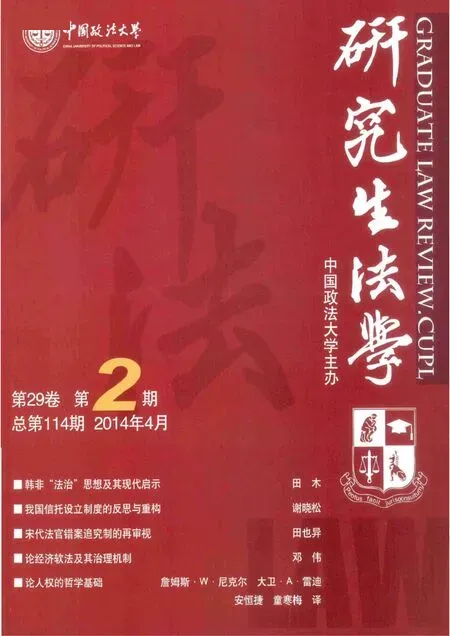中国传统法中的罪刑法定省思
王熠珏
语言给思想穿上衣服……从这种衣服的外边形式人们不能推断出它所遮盖的思想的形式;因为这件衣服的外表形式是按照完全不同的目的制作的,而不是为了让人们看清楚这个身体的形式。达至日常语言理解的那些隐而未宣的约定是极其复杂的。
——维特根斯坦〔1〕维特根斯坦语,转引自韩林合:《〈逻辑哲学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2页。
纵观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史,它的思想源初于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条,在理论上,贝卡利亚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对罪刑法定的内容作了系统界说,随后被誉为近代刑法之父的费尔巴哈第一次用拉丁文对罪刑法定原则给予明确而经典的表述;在立法上,该原则首先被纳入奥地利1787年刑法典〔2〕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2、251页。,并为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吸纳,此后在《人权宣言》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对其予以规定。经过不断地试错与进化,罪刑法定原则被视为保障人权的铁则、刑事法治的同义语,作为刑事领域的自由技术沟通着刑法与自由之间的桥梁,凭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整个世界,甚至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的内容而被多次重申和确认。对于向法治道路蹒跚迈进的中国而言,罪刑法定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它的旨趣关涉着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如何实现等宏大叙事。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前人及时贤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大致分为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3〕介于肯定说与否定说之间的观点中,举其要者,主要包括自相矛盾说、矛盾统一说、和合说、分层说以及主义与原则区别说。,为我们认识古代的罪刑关系提供了多维视角。持肯定说者大都从中国古代成文法入手,在各种律令典章、史书古籍中寻找罪行法定的痕迹,引经据典地论证其在中国古代的千年沉浮。持否定说者则以中国古代法中的比附援引和皇权擅断等现象为论据,指出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与西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形似神异的本质区别。通过爬梳,肯定说与否定说都能在中国古代存在罪刑法定规定上达成共识,双方立场的分野在于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是否承载了限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精神内涵。我们认同否定说的结论,但对其中批判比附援引和皇权专制的观点持保留意见。
一、传统寻踪:厘清中国古代罪刑法定变迁中的困惑
学术的“前见”是思想的基础,学术“偏见”是思想的毒素。〔4〕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我们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罪刑法定”的追问,厘清其中的困惑不能单纯以西方的概念范畴为质料,以现代价值观为导向,以我们受过的学术训练为方法打磨而成的“棱镜”去研究,否则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易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
(一)困惑一:被冷遇与误读的比附援引
吸纳西方罪刑法定主义,删除比附可谓是彰显清末修律的重大变革之一,修律大臣沈家本更是撰《断罪无正条》长文以论证中国古代本有罪刑法定的传统,抨击比附之弊来为改革声张。在沈氏影响下,比附与罪刑法定从此几乎成为绝缘的概念,传统中国的司法性质也陷入了法定与非法定的争论窠臼之中。比附是否与罪刑法定相悖?尔后学者们在讨论时都陷入了“轻重相举/比附援引=类推适用=罪刑擅断=违反罪刑法定”的简单的单线模式之中。易言之,仍未“超越沈家本的时代约束”。〔5〕参见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否定论者纷纷将比附援引作为中国古代法的诟病之处,视为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形成的客观障碍,从学理和实践方面对其进行抨击。近来一些学者开始理性地探索比附援引的价值意义,出现一些为比附正名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确犹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震动遐迩。
第一,比附援引是一种传统的方法论。实际上,中国的传统逻辑,主导的推理类型乃推类,中国人喜欢从一个事象向次一事象因果关系或理由归结之关系去追究的思维方法。〔6〕参见[日]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徐复观译,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43页。正如李贤中指出“在中国哲学的推理思维方式中,有相当多的部分藉着‘体证’而非‘论证’,‘论证’重在分析思辨,以及藉由推理形式规则保证推论的正确性。而‘体证’重在身体力行的实践,是在活动,变化中感应着同一主体的彼端……其推理的方式也就以‘推类’为主”〔7〕李贤中:“中国哲学中‘推理’思维的特性”,《哲学与文化》2003年第355期,第156页。,胡适亦认为中国逻辑“有学理的基础,确没有形式的累赘”〔8〕胡适:《胡适文集》(卷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是故中国传统逻辑的特点没有形式上的具体要求,更加强调的是实践上的经验,这与比附有异曲同工之妙,比附可视为中国传统逻辑思维的体现。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比附易成为罪刑擅断的工具,例如文字狱中,比附或许有助纣为虐之嫌,但究其本源,传统法律作为君主之命令,即使不借助比附,仍得以其他形式追究思想犯。〔9〕参见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所以,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思腹乃是学术上的不智。
第二,比附援引是一种量刑的司法技艺。如果立法者自己偶然遇到法律织物上的这种皱折,他们会怎样把它弄平呢?很简单,法官必须像立法者们那样去做。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10〕参见[英]丹宁:《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有学者主张“超越沈家本时代的约束”,认为比附乃缓和绝对确定法定刑的僵硬性,其更接近于西方法官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所进行的量刑,但对其有所制约,以“上请”的程序来防止法官的擅断,是很合理的法律制度。只是在从绝对确定法定刑向相对确定法定刑的转变中,比附才与罪刑法定产生矛盾。〔11〕[德]陶安(Arnd Helmut Hafner):“‘比附’与‘类推’:超越沈家本的时代约束”,载《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浙江,2013年10月),第462页。转引自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第三,中国传统立法采取客观具体主义和绝对法定刑主义是比附存在的客观原因。比附为何是传统法中的一项通行性规则?平允而论,是源于传统立法特征与传统观念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我国传统立法的客观具体的罪状〔12〕以杀人罪为例(见《大清律例》),就有故杀、谋杀、误杀、过失杀、斗(殴)杀、戏杀六种基本形式。难以包罗世间万象,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更使法律后果毫无弹性可言,可传统观念又要求司法断案应当“引断允协”“情罪相符”,即追求个案公允,致使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南辕北辙可见一斑。“当年,语词的精确是至高无上的法宝,每一次失足都可能丧命……”〔13〕[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1页。,然而人类深谋远虑的程度和文字论理的能力不足以替一个广大社会的错综复杂情况作详尽的规定。〔14〕参见[美]伯尔曼:《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页。法律的具体性与其所涵摄的范围恰成反比,法律越细化,其运用的范围就越小,司法者在“断罪引律”时既要面对“律例有限,情伪无穷”的具体问题,又要面临绝对法定刑与实质正义间的吊诡,此时需要比附援引来指引司法者寻找恰当的规则,惟其如此,才能调和当时的司法困境。
第四,比附不同于一般的类推(寻求最相似的规则),它更是一种发现、论证罚则的手段,有很强的创造性。它以“事理相同”与“情罪一致”作为相似性的基准,在传统立法技术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得以去发现、论证法条与罚则。是故,我们不能武断地将比附贴上“罪刑擅断”的标签,比附的应用也是一种依法裁判的表现,它基于司法者的经验,有其自身的适用准则。“许多学者都认为清代司法中的比附是任意比附、任情擅断,其实不然。清代司法中的比附有着严谨且严格的法理,必须按法理比附,否则到上级审转复核时会被驳案。之所以会出现任情轻重的情况,那只不过是比附的流弊而已。”〔15〕黄延廷:“清代比附的法理探讨”,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47页。
卒之,比附援引遭受了长久以来的冷遇与误读,它不是传统法制中客观的必要存在,而是放纵坏人的遮羞布,不是实质正义的试金石,而是魑魅魍魉的避难所。诚如考夫曼所言,法是当为与存在的对应(Kaufmann),法律发现实际上是在规则与事实间“目光往返流盼”的“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Engisch)。〔16〕参见[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41、103 页。而比附的价值就在于为规则与事实之间提供耦合的路径。比附援引最终奏响的往往不是迈进罪刑擅断的丧钟,而有可能是调和当时司法困境的变奏曲。
(二)困惑二:被歧视与曲解的皇权专制
人们一直“将权威和规则看得不是极美,便是极丑。其实美的是人们向往理想而产生的幻觉,丑的是他们揣摩现实而获得的浮象,二者都太极端,不合事实。事实可能处于两极之间,但是中庸的事物都不易造成鲜明深刻的印象”〔17〕张伟仁:“传统观念与现行法制——‘为什么要学中国法制史’——解”,载台湾大学法律学院主编:《台大法学论丛》第17卷(1),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1987年版,第3页。。皇权专制常被作为法制阙如时代中的内在痼疾而饱受学者们质疑和诘难,我们总将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视为挥之不去的精神幽灵,认为皇权专制窒息了罪刑法定司法化的生长。虽然从法治的视角看去,中国古代的刑事司法远非一副赏心悦目的山水画,但是将皇权专制=皇权擅断=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推理岂非过于简单?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进化过程并非遵循某种线性的因果链条,问题或许可以转化成为:传统中国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皇帝如何擅权?皇帝罪刑擅断的几率是否很高?被擅断的案件的范围、数量?皇帝擅断的程度是什么,是否存在其制约因素?皇帝擅权就一定没有罪刑法定?
首先,绝对君权只是专制者昔日梦呓和古老畅想。在中国的帝制社会中,与皇权统治相制衡的是朝野朋党与地方官权。一方面,朋党现象在帝制社会屡禁不止,是皇权统治的离心力。无论是皇室之内,还是君臣之间都相互提防着,皇权总是面临着祸起萧墙、变生肘腋、神器易主的威胁。另一方面,封建与专制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状态,“封建”更侧重表达的是地方的分权割据而不是中央的集权专制,易言之,封建表达的是地方自治,专制表达的才是中央的统治。封建的前提是天子不理俗务,君主是通过吏来治理国家的,而对吏权的控制就成为了帝国统治成败的关键,君主专制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源于地方的封建自治。所以,君主专制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封建”与“专制”是一对相互制衡的存在。皇帝与其说是具体的人,不如说是一种制度,一种既受朝野朋党制约,又受地方自治牵制的制度。
其次,皇权专制不是中国传统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缺位的主要原因。西方最初祭出罪刑法定的法宝是为了平衡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力,自由大宪章是起义和反叛的结果,遭受过度压榨的贵族们并没有改变历史、创制新制的宏愿,他们的反叛意识不过是对失去利益、财富、社会地位的条件反射、本能反应罢了。他们出于私利的行为却在客观上成就了历史的丰碑。〔18〕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39页。所以,自由大宪章并非一开始就是自由的圭臬,重要的是后来的历史。自由大宪章不是经历一条单一的从确立到实施的演进路线,而是历经无数次的确认、援引、论争、解释后才已然打磨成罪刑法定原则自由精神的依归。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可以发现中西罪刑法定萌芽时都存在权力制衡的背景,区别在于之后是否向罪刑法定这个术语中赋予自由、人权等的精神内涵。中国自清末以来的罪刑法定历程也是经过了历史风雨的润泽和政治之火的试炼,罪刑法定原则在中西方的命运是相似的,只是发展的时间维度相异而已。
再次,皇帝擅权不是常态且并非不受限制。在传统帝制时期,君主之命即有法律之效力,历朝历代中君主干预司法裁判之例并不鲜见。但这并非一种常态,更多的是,即使君主位于传统审转制度的最高点,其更多的也仅仅是种形式上的责任。〔19〕参见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页。皇帝在审转制度中更多时候履行的是一种行政审批的职能,并非总是以一个破坏者的身份改变司法官已严格按律裁判了的案件。有学者甚至认为“皇帝的一个功能在于自由地改变官吏们严格依照成文法做成的判决原案,以超越凌驾一切法律之上的方法来求得实质上的衡平……制度本身一开始就期待着皇帝发挥弥补成文法缺欠的积极作用”。〔20〕[日]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载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将皇帝擅权予以积极肯定的观点虽有偏激,但从另一角度也预示着皇帝擅权的结果并非全是使无辜者身陷囹圄。此外,从《大明律》起,增加了君主对个案的裁判不得作为以后裁判法源的规定。〔21〕参见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传统法具有“命令”之性质,君主的意志当然不乏法律的效力,但对个案的裁断有临时性和特殊性,与法的安定性可能存在冲突,于此情况下,排除其作为将来法源的可能性,具有合理性。〔22〕参见(清)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5册),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77页。
申言之,我国学者在界定罪刑法定的含义时,曾经把罪刑法定区分为观念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制度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与司法运作上的罪刑法定。〔23〕参见宗建文:“罪刑法定含义溯源”,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3期,第42页。这一区分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值得肯定。“观念意义上的罪刑法定是罪刑法定之形而上,指蕴含在罪刑法定之中的价值内容,可以称之为‘道’。原则、制度与司法运作上的罪刑法定是罪刑法定之形而下,指罪刑法定的制度保证,可以称之为‘器’。”〔24〕陈兴良:“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42页。皇权专制是当时存在的历史必然,且皇权同样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皇帝擅权更非一种常态,因而它影响或制约的仅是作为“器”意义上的罪刑法定,我国传统法中轻“道”而重“器”,真正缺失的恰是观念意义上的罪刑法定。
二、探幽分微:省思中国古代不存在罪刑法定的原因
古今的意义场域有所区别,同一语词所指代的意思也不尽相同。法学研究需要对整个历史的观念性与社会性材料进行整合,从中挖掘且遵循法制进化的规律。〔25〕参见于浩:“多维视角下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面临的三重矛盾”,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66页。不可否认,如果撇开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语词上的罪刑法定是存在的,以“断罪引律令”为代表的传统法的确是罪刑法定化的倾向,不过由于它强调的是君主对司法的控制,“故传统的罪刑法定化关注的是‘此罪∕罚’与‘彼罪∕罚’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基石,并发展出系统的犯罪成立要素理论,侧重“有罪”与“无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26〕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可见,语词上的“罪刑法定”并非真正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领域“自由”技术的罪刑法定,其旨趣必须承载着一定的精神内涵,价值冲突才是真正破解中国传统法不存在罪行法定原则的迷思之所在。
(一)刑事契约观念的缺位
如今,虽然民事契约观念已被广为接受,刑事契约的观念却缺乏认知。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刑罚权是公民与国家基于社会契约的让与,这份自由的让与只要足以够国家保护自己就行,故刑罚越公正,君主为臣民所保留的安全就越神圣不可侵犯,留给臣民的自由就越多。刑法作为公法的一个分支,相当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契约”,用于表明什么应当作为犯罪受到处罚和通过怎样的程序加以认定。刑法的主要作用是衡量和确认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契约”是否被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正好体现了国家对合理实施刑罚权向人们做出的庄严承诺,契约化的刑法可以有效地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膨胀,避免弥散化的惩罚,使人们不必生活在害怕遭受突如其来的刑事打击的忧虑中,由此而与法治的可预期性与连续性的要求相吻合,为个体自由的实现提供基本的法安定性保障。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研究“国家—个体”关系的两种进路:一是着眼于个人权利的市民社会进路,二是强调国家权威和社会控制的民族国家进路。〔27〕劳东燕:《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西方有较为发达的市民社会传统,刑事契约的观念有其萌芽的社会土壤。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民众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的和谐生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安逸舒适的诗文社会。人们希望看到的、得到的是皇恩浩荡、父母官的体恤爱民,而不是君臣平等和官民平等,〔28〕彭凤莲:《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百年变迁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在公法领域,个体只作为国家的臣民存在而不具有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主体性地位。并且民族国家的构建是支配与主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主流意识形态,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法制变革模式在客观上约束了个体自由的实现。在一个国家话语为主导的干预型国家内,国家权力对社会长驱直入,“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操纵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的行动但不断妨碍人的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终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任劳任怨的小动物,而政府则是牧人。”〔29〕See Alex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Vol.Ⅱ,(Vintage Books 1976)319.正是刑事契约观念的缺位,使得弥散化惩罚有时如幽灵般缠绕着中国社会,阻碍观念意义上的罪刑法定的萌芽。
(二)理性主义的膨胀
英国学者哈耶克把自由区分为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英式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认为社会的自发扩展秩序是经由不断试错和进化生成的,他们崇尚法治之下的自由;另一种是欧陆的以建构理性论为基础,它认为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都是人主观设计的产物,并相信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建构一个美丽新世界。〔30〕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1~62页。前者类似于一种不受他人干涉的消极自由,而后者主要是指个人自我做主的积极自由。作为刑事领域彰显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其强调和关注的应是一种免强制的消极自由,因为主张“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的政治理论往往认为,国家可基于某些大众自己无法看到的“好处”的缘故而对某些领域施以强制力,因为这种“仁心善意”的强制因基于公意而不被认为是自由的反面。〔31〕参见劳东燕:《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但公意与个体利益不总是相一致的,还有与个人意志所代表的自由相冲突的时候,若个体利益(权利)的实现需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而非消极的不作为时,则个体利益(权利)因处于国家权力的笼罩下而得不到实质的保障。中国的传统思维使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欧陆的建构理性自由观,在《孟子·尽心上》中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天下事也。”在这,孟子认为“心”是人的一种本能,若能发挥到极致,就可以洞悉人性,继而理解天意。在荀子看来,理智是导人向上的内在源泉。人之所以可以从善弃恶完全是因为“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到了宋明程朱理学更是强调心智的作用。〔32〕参见罗翔:《冲出困境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此外,相传严复当年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对于“Liberity”找不到对应的中文词汇,后来偶然想起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33〕《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于是禁不住感叹:所谓自由,正此意也。但需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舒心畅快的感受,相当于积极自由,但不是体现国家权力限制的那种消极自由。〔34〕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7页。故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选择的理性主义自由观,与罪刑法定所强调的经验主义自由观有本质的不同。
近代法律变革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英国模式,他们珍视传统而不抱守残缺,循序渐进而不急于求成,以温和的政治改革为过渡,以继承传统法为己任;另一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国模式,他们以流血的政治革命为先导,以理性构建法律为依归。英国模式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架一座桥梁,而法国模式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划一道界限。清末中国的法制改革无疑走上的是法国模式,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中国,成为维新志士们反传统的利器,它在清末长期的礼法之争中画上了标志性的符号,将中国传统评定为竞争中的劣者、败者,“西上中下”观由此形成,这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态度到了五四运动时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这一认识上的转换,也许是由那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子所引发的,但是这种转换本身却并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在顷刻之间实现的,因为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在各种不同的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方案中经由反复讨论而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35〕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中国百余年来的法治改革代表的是单纯走向理性化治理的努力,这种改革思路蕴含着“复制型法治”仅注重法治象征性效果的危机,理性主义的过度膨胀极易趋向权威主义,势必会导致社会陷入混乱。虽然理性化治理本身并不会影响个体自由的实现,关键在于这种理性化治理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体自由还是维护某种政治势力的统治秩序,〔36〕参见于浩、陈肇新:“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6~77页。但对于以“救亡图存”与“富民强国”的现代化情结作为主题的近代中国而言,在民族国家的理性化治理道路上选择维护统治秩序而压制个体自由无疑是当时国家主义话语甚嚣尘上的逻辑结果。
(三)人性至善的坚守
西方的主流观念是主张人性本恶,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即人自出生之日起就负有原罪,成长生活中的修行是一种自我赎罪,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对世俗中的一切人都不信任的观念,只有上帝才是至善的完人。洛克认为人类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除自然法外,不受任何约束。然而人与人基于利益冲突使社会陷入了战争状态,为了结束这样朝不保夕的危险状态,人们自愿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社会,让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公共权威来调和争端。但权力具有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就像霍布斯所言的利维坦具有吞噬一切的功能,因而这样的权威形成之后往往会出现异化,这就是人性趋恶的结果,所以洛克认为政府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诗人约翰·米尔顿有言:“国王和行政首长,他们既然是人,就可能犯罪过,因此他们必须受制于人民所制定的法律管制之下。”〔3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中国古代曾存在过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争论,不过在政治伦理学中人们基本都倾向于对人性至善的坚守。如孟子所言“人之趋善,如水之就下”,所以只要假以时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人们对于至善至美圣贤的推崇,让圣贤们用其智慧和美德来领导我们,相信这些至善至美的统治者不会犯错,即使偶尔犯错他们也能及时发现并改正,以致人们不可能要求限制皇权。〔38〕参见罗翔:《冲出困境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皇室之中充斥着篡窃相仁、残杀凌夺、史不绝书,明君圣主更是极少,正如荷尔德林那句至理名言——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带向了人间地狱。社会的建构实是一种非设计的结果,个人理性往往也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即使是圣贤之人也必须尊重那些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并且理性建构方式本身就存在意图削足适履地让生活适应逻辑,而非让逻辑适应生活的根本缺陷。因此,人们幻想着通过尧舜般的统治者一劳永逸地规划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设计出包括法律在内的最完美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呓。法律乃是一种需要靠一个人经过长期的探究与实践才能获得认知的试错型技艺,〔39〕See James R.Stoner,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30.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并非主观设计的产物,而是经过不断的试错得以被各国采纳,其间虽不可避免地受到欧陆建构理性影响,如过于强调形式上的罪刑法定或过于迷信立法的神圣性,而忽视了司法的能动性,但总体上并未偏离限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本意。
(四)普通公众对秩序的渴望
自由与秩序之争是盘亘于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它表现在现代公法领域,就是如何维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然而自古以来,中国普通公众对秩序的渴望都超过了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关注的是司法是否会成为纵恶长奸的引路石亦或是奸人趋避惩治之保护伞,担心的是司法是否“刑不上大夫”而导致王子与庶民犯法不同罪,司法擅断是民众心中难以医治的沉疴。“中国的犯罪率在统计上远远低于西方,同时中国公众的安全感也远远低于西方,社会公众普遍有着或多或少的安全焦虑,这个安全焦虑不是源于公权力的侵犯,而是源于其他社会个体的潜在侵犯。”〔40〕于志刚:“罪刑法定原则认识发展中的博弈”,载《法学》2010第1期,第38页。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与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追求相冲突,客观阻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古代的萌芽。自由与秩序之间本非对立,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哪一个是二者叠加后达到的相对最大效应,至少目前普通公众对秩序的追求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变成史学家手中干涸的标本,仍是当今人们对刑法的期许。当法律人为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扼腕叹息时,普通公众却可能为类推规则拍手称快;当法学界在为1997年《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而热情讴歌时,普通公众却可能对罪刑法定原则心存疑虑,罪刑法定原则似乎成为一种强加的正义而难以完成对自由的拯救。法律人对罪刑法定的解读源于理性、逻辑性的知识,民众对罪刑法定的认识却赖以感性、经验性的生活经历,二者思维视角的差异势必造成认识论上的冲突和抵牾。现行《刑法》第3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其核心意涵究竟仅包括消极的意义,亦或是可同时包含消极和积极的意义取向?学界为此陷入了论争,部分学者认为该立法措辞的模糊性,决定了我国罪行法定原则“对于守护其宣称要服务的价值而言几乎仅构成一丝渺茫的希望”〔41〕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86.。但在此需注意的是,公众对秩序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我国《刑法》第3条是在经典罪刑法定原则上的锦上添花而非画蛇添足,毕竟法条的表述是对司法现实的折射,“体现了与司法现实的合拍性,也是公民心理和法制传统的体现,它抚慰了民众对‘刑不上大夫’的疑虑,维护了民众的法公平感,并且保证了从1979《刑法》到1997《刑法》的无缝连接和平稳过渡。”〔42〕于志刚:“罪刑法定原则认识发展中的博弈”,载《法学》2010第1期,第19页。
结 语
在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法治作为一种改革工具承载着推动社会转型等诸多现代性意义,它在中国的发展可归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就其自身内涵来看,由于纯粹的形式法治仅是“建国”方略而非“治国”的技术,纯粹的实质法治却又无法将自由落到实处,故需从形式法治逐渐转变为以形式性为导向、实质性为第二位要素的相对形式法治论。二是就其外延发展来看,从以西方政制架构为底版、借助国家强制力推进法制建设的普世主义法治观,逐步导向以中国本土国情为关照、回应社会本土需求的国情主义法治观。然而国情主义法治观的出现虽为法治认识上引入了中国视角,却又为研究带来了如何把握“国情”的时空坐标和尺度等复杂困境。〔43〕张志铭、于浩:“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14页。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种法治治理方式,同样可基于法治的以上发展视角来解读:其一,在内涵维度上,文本上的原则注定只能不幸成为法治橱窗中的摆设,但若给罪刑法定加诸过多的实质性因素又将导致概念的肥胖症,使其失去规范性而沦为政治理想的口号,故立足相对形式法治立场的罪刑法定原则无疑是最理想的。其二,在外延维度上,罪刑法定原则并非派生于中国的固有话语传统,由于古代刑事契约观念的缺位,使得中国传统法中的罪刑法定本质上并非是对“国家—个人”关系的重新界定;传统伦理对人性至善论的坚守,决定了人们推崇贤人之治而缺乏限权意识。此外,无论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选择的理性主义自由观,还是为法制变革所选择的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国模式,都意味着理性化治理的过度膨胀在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同时,导致个体自由被压制;再加上普通公众一直以来对秩序的渴望,致使我国自古在观念层面缺乏接纳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土壤。法律的全球化是法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罪刑法定原则自清末修律被引入中国时,仅是一种徒有表象而欠缺精神内核的赝品,为那个风雨激荡的年代提供浮华的装饰和虚幻的慰藉。如今,转型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以“本土化”语境关注具体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罪刑法定原则只有被真正践行才能成为推动个人自由在我国实现。毋庸讳言,罪刑法定的本土化存在观念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等诸多困境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习,在某种意义上,以罪刑法定的本土化困境为切面,也能帮助我们透视刑事法治乃至考察整个法治在中国社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