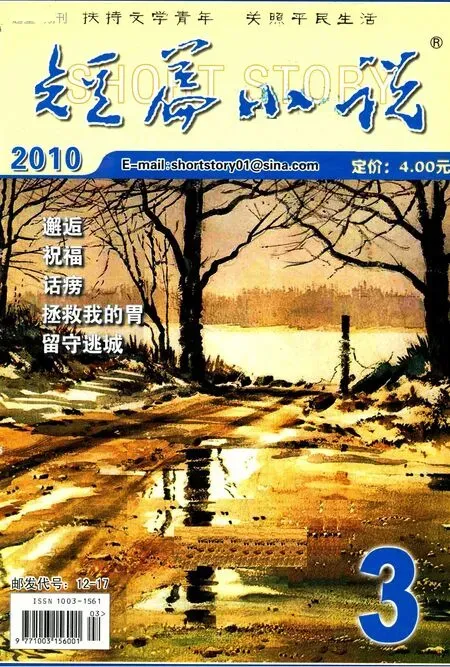从《驯悍记》看凯瑟琳娜“悍妇”形象
孟召军 沙丽华
从《驯悍记》看凯瑟琳娜“悍妇”形象
孟召军 沙丽华
一、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简介
作为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作品,《驯悍记》是一个情节极为滑稽有趣的故事。故事中聪明的男主人公迎娶了坏脾气的富家女凯瑟琳娜,在两人的生活中,由于凯瑟琳娜的任性,从新婚生活开始,对两个人而言就是一场灾难。凯瑟琳娜不把自己的新婚丈夫彼特鲁乔放在眼里,处处与他作对,聪明的丈夫为了改造自己的新婚妻子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计策,从而最终将这个骄横任性的富家女凯瑟琳娜改造成了一个温柔贤惠的贤内助。这个生活气息浓郁的戏剧故事中充满了众多吸引人的元素,莎士比亚用自己充满感情的笔触将凯瑟琳娜的刁蛮任性与彼特鲁乔的聪明风趣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故事中两个人充满个性的风趣对话打动了不少观众,使得这个喜剧故事受到了众多人的喜爱。《驯悍记》作为莎士比亚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喜剧,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情感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联系以及爱情与金钱价值观等,还通过凯瑟琳娜这个特殊 “悍妇”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当然,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带有浓厚男权主义色彩的剧作家,在自己的故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倾向,虽然给故事艺术性的展现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同时也以另一种角度展现了女性主义的特征与发展。[1]下面我们以《驯悍记》中凯瑟琳娜的 “悍妇”形象为例,解析一下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形象。
二、《驯悍记》中凯瑟琳娜形象解析
莎士比亚所处时期是欧洲女性主义启蒙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众多著名人物都试图从另外一种角度或另外一种方式上解析探索女性主义,舞台剧作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其生动、形象、直接的表现方式受到了青睐,很多人物都开始以舞台实践为基础,运用这种犀利而独特的方式去展现女性主义的表现与发展,莎士比亚作为其中较为典型的剧作家,也有表现这种思想的作品,那就是《驯悍记》,其中凯瑟琳娜的 “悍妇”形象更是一度成为经典。[2]凯瑟琳娜这个违背常规的 “悍妇”形象着实耐人寻味。
(一)“悍妇”的产生
所谓悍妇,是与传统男权社会期望相背离的一种女性形象,与传统文化中所寄望的 “家庭天使”形象不同,悍妇打破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主导地位,角色定位开始走出男性权威阴影,追求独立、自我,坚持贯彻自我的主张。在传统社会中,男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自身的独特诉求屈居于男权文化之下,多数人只能通过服从男性社会的规则、约束自己遵照刻板的既定规则走下去。父权社会文化机制中男性的权力与价值观是评价她们的唯一标尺,一旦女性出现与这些标尺不相符合或相背离的地方,就会被要求修正,以满足男性社会对她们的既定要求—— “家庭天使”或 “高尚淑女”,可以说,女性的幸福与追求全部都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无法真正表达出自己的自由意志,只能在男性的阴影下成为一个失声集团,尤其是敢于在生活中反抗男性、出言不逊、喋喋不休的女性被视为大逆不道,被称之为“悍妇”[3]。
戏剧中,女主人公凯瑟琳娜是富商巴普提斯塔的女儿,她暴躁任性的秉性吓走了众多的求婚者,以至于成为无人问津的姑娘,她的父亲十分着急,聪明绅士彼特鲁乔听说了这个姑娘的事迹之后,决定娶这个姑娘为妻,新婚期间,凯瑟琳娜的暴躁、任性困扰着两个人的生活,彼特鲁乔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装出一副更为粗暴、乖戾的样子,以爱护妻子为名折磨着凯瑟琳娜,让她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吃足了苦头,这种折磨最终让凯瑟琳娜觉悟,从而醒悟一个聪明的妻子不应该倨傲粗野,最终成为帕度亚城里最温柔顺从的妻子。但是,细细品味我们可以发现,莎士比亚所定义的 “悍妇”凯瑟琳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性格率真,敢于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虽然恶名远播,披上了 “悍妇”的虎皮,但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无奈之举也是因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和意识的压迫。[4]在这个社会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没有大声说话的权利,否则将会被视为粗野、无礼;不能直抒胸臆,面对一切都只能选择保持女性虚伪的矜持,否则就是粗暴、凶悍;婚姻方面只能遵从父兄的安排,作为商品为他们换取金钱,如同交易市场上的牲口一样被人买卖,完全没有自主意志和社会地位。凯瑟琳娜只是完全违背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认识的既定规则,就被冠以虚妄的 “悍妇”之名,由此,帕度亚城里的 “悍妇”凯瑟琳娜诞生。[5]这个女性只是希望能够释放自己的压抑,从社会给予她们的既定角色中逃开,想要以自己的声音去控诉这种压迫,但是结果事与愿违,她最终能够获得的只是在彼特鲁乔聪明的驯服中成为一个温柔的千篇一律的妻子。
(二)被 “驯悍”的命运
剧作中第二幕第一场是凯瑟琳娜与父亲激烈交锋的一幕戏,这场戏中凯瑟琳娜反抗自己的父亲,追打妹妹比恩卡,单纯来说好似又是悍妇的暴行,但是实则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凯瑟琳娜追打比恩卡只是她对于自己必须顺从的命运的反抗,是对家中重视宠爱比恩卡行为的一种发泄。作为家中符合当下审美的比恩卡,无疑是男权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她温柔顺从,逆来顺受,听命父亲,身上具备女性的矜持、内敛与温柔,可以说是与凯瑟琳娜截然不同的完美女性形象,正因为如此,与凯瑟琳娜无人问津不同,她受到了众多男人的追求,而反叛的凯瑟琳娜只能被男人们羞辱。面对这种羞辱,她反抗、捍卫自己的意志和尊严,结果却更加重了自己的悍妇之罪。后来,她被父亲像出售商品一样嫁给了彼特鲁乔,她的悲愤和无奈全都毫无用处,只能看着自己陷入一桩可怕的婚姻的陷阱与深渊,原本代表着女孩子幸福生活的婚姻,吹响了凯瑟琳娜被驯养命运的号角,她只能在这场战争中失去自己的骄傲、自尊与意志。[6]
在西方文化中,在教堂举行由牧师见证的婚礼是女孩子们向往的幸福,尤其是在清教徒的传统里,婚姻中妻子作为丈夫的精神伴侣而存在,为家庭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她们来说,婚姻不仅仅代表着经济利益,同时也意味着两个人互敬互爱生活的开始。但是,在凯瑟琳娜的婚礼上,穿着古怪的彼特鲁乔成为她的噩梦,在教堂里、牧师面前的无理取闹伤害了凯瑟琳娜的自尊心,践踏着她的梦想,试问,哪个少女愿意嫁给这样一个不尊重爱护自己、拿婚姻当儿戏的男人呢?所以,凯瑟琳娜不愿意和彼特鲁乔一起回家,这只是她理智、冷静的选择,但是却被视为大逆不道。原本应该充满甜蜜的新婚生活成为一场以新婚为名义的残酷折磨、调教,凯瑟琳娜在精神、肉体、尊严方面均遭受了彼特鲁乔的摧残。凯瑟琳娜在这样折磨中完全丧失了自我,在没有爱情与尊敬的生活中,只剩下了主人与宠物的支配和驯服,而且这个所谓的绅士迎娶凯瑟琳娜的目的只是出于钱财和男人的征服欲,这无疑是更为恶劣的初衷,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对于迎娶男人们避而远之的悍妇凯瑟琳娜毫不在意。可以说,彼特鲁乔的身上代表了残酷压迫女性的男权文化,无耻、无理得令人发指。凯瑟琳娜最终被驯服的结局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三)“悍妇”的反抗
《驯悍记》展现了以彼特鲁乔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男性的丑陋、卑劣与无耻,对凯瑟琳娜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命运作了注解,但是较为有趣的是,莎士比亚在其中匠心独运地加入了一个特殊的 “序幕”,虽然看似和后文没有太大的关联,也没有交代最终序幕的结局,实际上却隐晦地展现了 “悍妇”凯瑟琳娜的反抗。剧中斯莱被加冕为狂欢国王,这种梦境一般的历程让他沉湎其中,虽然最终并未在剧作中醒来,但是可以想象的是他最终必然要恢复到从前一文不名的情形。[7]同样的,彼特鲁乔对凯瑟琳娜的折磨和指鹿为马的行为也代表着他在家庭这个王国中的狂欢和独裁,凯瑟琳娜必须听从他的指挥,一旦违反他的意志,就会受到惩罚。教堂中那场混乱的结婚仪式可以看做是这位狂欢国王的加冕过程,从那一刻起,凯瑟琳娜就成为他麾下的私有财产,驯服开始。在凯瑟琳娜最终屈服于他的折磨,宣告自己的驯服宣言时,也意味着他的脱冕仪式。
“你的丈夫即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监护人,你的头脑,你的君主……把你们的手放在你们丈夫的脚底,为表示这种忠顺,如果他喜欢,我的手已准备好,让他享受一番。”凯瑟琳娜的这个宣言表面上看是对彼特鲁乔的顺从,但是结合前后剧目中她的性格与表现,这种过分谄媚的言词和谦卑的话语表明了这是她无奈妥协的假话,是对以彼特鲁乔为代表的男性们的讽刺,是对父权社会制度的反抗,可以说是在众人面前撕掉了彼特鲁乔的人格面具,从另一种层面深刻地反映了她追求意志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所安排的这个女性的最后的反抗。最终,凯瑟琳娜撕掉了彼特鲁乔求婚时所戴的爱护妻子的假面具,自己也在遭受了众多的折磨后带上了顺从、乖巧的假面具,将反抗隐藏到了更深的内心,这种悲剧与喜剧交织的思想与情感无疑让人在欢笑欷歔感叹的同时深刻反思凯瑟琳娜这个 “悍妇”命运背后的悲剧。
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 “悍妇”凯瑟琳娜被驯服的过程,以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方式反讽了男权社会的悲哀专制,将凯瑟琳娜这位 “悍妇”的悲惨命运展现在了观众面前,迫使人们去思考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深刻地剖析和展现了女性主义。
[1]孙萍.刍议《驯悍记》中的莎士比亚对凯瑟琳娜内心的描写[J].芒种,2012(02).
[2]饶一晨.回归经典文本,重拾思想明珠——对《驯悍记》的误读与重读[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1(Z5).
[3]段海霞.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地位分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4]王莎烈.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5]王玉凝.从女性形象塑造看莎士比亚剧作的男权视角[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02).
[6]杨莉馨.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2).
[7]王挺.西方文学中的女性意识[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5).
孟召军(1979— ),男,河北沧州人,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沙丽华(1979— ),女,河北沧州人,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本科,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