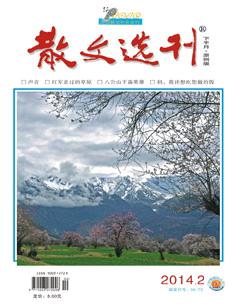多想让父亲站起来
郭志刚

每次回家看父母,父母都非常高兴,和我有说不完的话。不论我再忙,他们都希望我多待一会儿,都要留我在家吃饭。当我要走了,父亲想多看儿子一眼,想把儿子送到门外,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腿却像灌了铅一样一点都不听使唤,没办法,父亲只好又坐下,脸上全是痛苦、无奈和绝望。
走的时候,我从不敢回头,我不忍心看到父亲那痛苦的样子。但,车走了很远,我满脑子里还是父亲那花白的头发、伤心的表情和弯曲佝偻的身影,我的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此时,我知道父亲也在伤心地哭泣。
父亲年轻时,身体非常健壮。一米七八的个头,英俊潇洒的长相,使他成为全村最出众的青年。这还不算,父亲天性聪慧,干啥啥会,被乡亲称为“七十二行”。他上世纪50年代在洛阳当过建筑工人,盖过高楼大厦;60年代在工厂做过车工、木工、油漆工,生产过许多农业机械,打过很多漂亮的家具;70年代在人民公社参加文艺宣传队,会拉板胡、二胡、曲胡等乐器。在洛阳,他被从几千名工人中挑选出,推荐到干部学校进修,这是父亲平生最感自豪的一件事,当年的照片,至今还挂在老家的墙壁上。父亲年轻干农活,犁耧锄耙样样在行。收麦打场时,他可以扛起重重的麻袋,腰板直直的。记得挑水是农村比较重的活。父亲总是用扁担挑着两个大水桶去村庄老井里打水,打水时父亲用扁担轻巧地一摆就灌满了一大桶水,然后三下五除二就用扁担把水桶提了上来,一口气挑回了家。有时,左邻右舍没水了,父亲也热情地帮助他们挑水。
最高兴的是吃父亲做的“葱花面”。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一年吃不上几回肉,除了红薯汤、红薯馍,就是清汤寡水的素面条。但父亲做的面条却非常好吃。父亲比母亲有力气,和的面比较硬,擀出来的面条比较细、筋道。记得父亲先在热锅里放上一点大油(肥猪肉熬的油),油热后放入葱花和姜花,炸黄后再放入青菜,虽然是素汤面,却成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最美的佳肴。1981年,我上大学时,父亲去送我,下了车,离学校还有一段路,父亲硬是扛着一个大木箱子走了五六里路。那时,还不知道“伟岸”这个词,也许这个词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但在我心中,父亲真的称得上“伟岸”。
但正值健壮的父亲,1997年却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从此,疾病像恶魔一样不停地折磨着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的腰变弯了、头发变白了、目光也呆滞了、双腿僵硬得一点都不听使唤,我那个健壮能干的父亲再也见不到了。尤其是经过多处求医,两次手术之后,父亲知道这个病再也没有治好的希望时,父亲那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绝望,真是让人揪心的痛。父亲爱孩子,从不在孩子面前流泪,但他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疾病的痛苦。父亲希望孩子们常回家看看,但又怕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实在想得很了,就打电话给我,说别让我挂念,别常回去,其实他是希望我回去一趟,希望能天天看到我。明知这个病看不好,但从不服输的父亲还是四处打听医生,听说哪个地方有个偏方,就一定要试试,也不知吃了多少药,试了多少偏方。我经常在药店里给父亲买专治帕金森的“美多巴”药,好几次,出了药店门,我都想哭。现在生活好了,老人们不仅吃得好穿得好,还可以打打门球,练练太极拳。但我的父亲却出不了门,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吃好多的药,吃那一剂又一剂比黄连还苦的药。
儿时,父亲喜欢背着我,那是我最温暖的时刻;考上大学时,父亲欢快地拿着我的通知书跑回家,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刻;1993年和父亲游杭州西湖,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记忆了。许多事情,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还体会不到它的价值,当失去的时候才倍加感到它的珍贵。每当看到别人和父亲一起走着,有说有笑,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每当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父亲一起散步,我都痛彻心扉地难受。人,不管多大,在父母亲面前都是孩子,不管多坚强,也有脆弱的时候。尤其当工作和生活遇到困惑挫折之时,总想到父母身边,向父母说一说。这个时候,父母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使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力量。尤为向往的是拌上两个小菜、温上一壶老酒,和父亲喝上两杯,然后乘着酒意跟在父亲身后,把工作和学习的事情向父亲说个没完。
每年我都有个愿望,就是想和父亲登回山,因为对山的记忆最初是父亲带给我的。父亲当工人时,经常出差去外地维修他们工厂生产的榨油机。那一次,他去湖南、贵州,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来后,天天给我讲湘西大山里的故事。从此,大山就在我这个乡村孩子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时时吸引我去寻幽探秘。长大后,我也喜欢上了登山。上大学时,曾经和父亲登过一回山。参加工作后,多次想和父亲再去登山,但工作一忙,总想着今后有的是机会,一直没有抓紧,没想到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我做梦都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奇迹般站起来。我多想让父亲站起来啊!
美术插图:李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