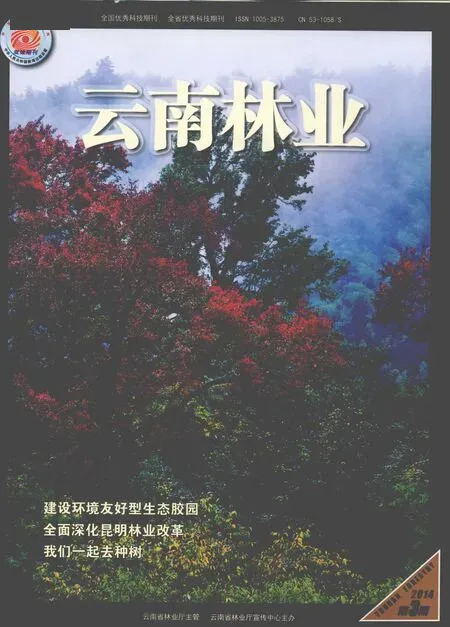植树节里忆亲人
□ 魏鹏
植树节里忆亲人
□ 魏鹏
让我对朱熹肃然起敬的,不是他的理学体系,而是他在祖母墓上栽了十九棵杉树,来怀念去世的祖母。受其影响,我也想为去世的母亲栽一棵树。
况且,母亲生前就爱栽树。春天一到,她都要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买回一些树苗,栽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在我的记忆里,全村谁都没有我家栽的树多。在瓦屋未建之前,母亲就在宅基上栽满了洋槐树。瓦屋建好后的那年春天,母亲还带我去县城买过树苗,我至今还记得那时一人高的槐树苗只卖一毛钱。母亲在宅基上栽的树有楝树、桑树、槐树、椿树、枣树、桃树、石榴树、泡桐树等,宅基下栽的多是柳树。
栽柳树不用树苗,而是栽下锨柄粗的“柳树栽子”。“柳树栽子”是从大柳树上锯下的,两端都是光秃秃的,就像是一支巨型铅笔,但栽下后十多天就发芽扎根了。诗人丁可说我们这里土地肥沃,连插下一支铅笔也会朴楞楞地长成一篇锦绣文章。这句诗的最初意象,我想是离不开“柳树栽子”的,见了丁可一问,果然如此,诗人说他也载过“柳树栽子”呢。
母亲在家西栽了5棵“柳树栽子”,几年过后全都长成了高大的柳树。柳树枝软根甜,易生知了,一到夏天,满树都是知了的歌声。我和姐姐们常把饭桌抬到柳树下,看书,写字,听知了唱歌。而父亲常拿着揎树的铲子,为柳树整枝美容。那些好舞文弄墨的叔叔,就戏称父亲为“五柳先生”。柳树成材后,母亲就用它为大姐二姐打做了漂漂亮亮的嫁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这里开始引进了意大利杨树,于是母亲又在房前屋后栽了二三十棵意杨。父亲天天说栽密了栽密了,让母亲去掉几棵,然而母亲她一棵都舍不得去掉。那些鱼竿粗的杨树苗,仿佛是她的一个个指头,去掉哪个都心疼。我曾看过母亲给玉米间苗,有时因错拔了一棵玉米她都要后悔小半天,她在田里犹犹豫豫的样子,就像是细吟一首唐诗。看着那一天一个样的意杨,她怎么也下不了去掉几棵的决心。不仅如此,她还在东大汪西头的废地上栽了一百多棵意杨,使我们家一跃成为全村的植树大户。
有一天,大姐来和母亲商量,要卖掉东大汪西头的意杨。原来那时户口政策已经开始松动,只要花六七千元就能买到一个非农业户口。听大姐说,有了非农业户口,在就业、提干、入伍、升学、孩子入托等等方面都有优惠待遇,仿佛高人一头似的。母亲左思右想之后,就把东大汪西头的意杨全卖了,一把交给大姐六千元。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非农业户口屁钱都不值。可当时母亲却感慨万千地对我说:“是意杨树换回了你大姐的非农业户口啊!”
刚要“跨世纪”时,母亲不幸患上了绝症。住院期间,我四处筹钱为母亲治病。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已拖欠我的工资款一万余元。我去讨要工资时,书记、镇长不但不发工资,还把脸板得像木锨似的,连句人话都没有,仿佛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房前屋后的杨树卖钱给母亲治病。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满眼含泪地看着那一个个树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母亲去世后,我就想学朱熹先生,想在母亲的坟地里栽上一棵树。因种种原因,我连栽了三年都没能栽活一棵松柏。后来栽活了几棵意杨,但村干部又说那里不能栽树,硬是给砍伐了。去年夏天,村干部把母亲的坟地卖给了一家客商,说我们这里已变成经济开发区了,要在母亲的坟地上建造厂房。他们给我送来了200元钱,强迫我把母亲的坟墓迁到外祖父的村子里去。
如今,母亲的坟墓已迁到南大河的河堰上了,但我仍想在母亲的坟前栽上一棵纪念树。可那河堰上,一个坟头挨着一个坟头,即便是栽上一棵“柳树栽子”,怕也没有扎根的地方了。
植树节又到了,我多想为母亲栽一棵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