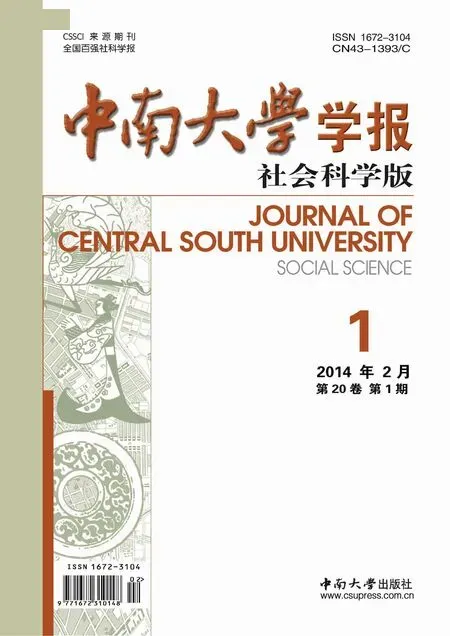塞尔言语行动和意义关系理论的批判
胡光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1100)
塞尔言语行动和意义关系理论的批判
胡光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1100)
塞尔的言语行动论对意义的说明引起一些误解,塞尔对这些误解的澄清基本是成立的,但是论据上存有谬误之处。塞尔在前期对意义的解释存在漏洞,但后期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意义的解释不但是成功的,而且解决了言语行动中的那些漏洞。
塞尔;意义;言语行动;交流;表征
塞尔在《言语行动,语言哲学论》中提出,对句子意义(meaning)的研究同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研究不是不同的研究[1](18),并认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基本原因是如下两个命题:
命题1:语言的语义(semantic)结构可被视为以约定的方式实现的一系列的构成性规则,言语行动本质就是按照这些构成性规则的集合通过说出话语执行的行动[1](37)。
命题2:可表达性原则:对于任何意义X和任何说话者S,当S意味X时(打算用话语表达,希望用话语交流),存在着一个表述E使得E准确表述了X[1](20)。
基于以上两个命题,塞尔得出:
命题3:(我们)可以把执行言语行动的规则看成表达某些语言成分的规则,因为,对于任何可能的言语行动,都存在一种可能的语言成分,它的意义(给定话语的背景)充分决定说出它完全执行了那种言语行动[1](20-21)。
但是,正是塞尔给出的这些原则,导致了人们对意义和言语行动相互关系的误解,本文从这种误解开始,考察塞尔是如何处理意义和言语行动的,并指出塞尔的工作哪些是成功的,哪些存在问题,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意义”这个古老又常新的哲学问题。
一、关于语词意义和言语行动
言语行动概念盛行以来,多人混淆了意义和言语行动。黑尔(R. M. Hare)在《道德语言》中说:“语词‘好’的主要功能是赞扬”,“好”有“赞扬的意义”,“好”有“评价的意义”,因此“好”与两类言语行动有关,即赞扬和评价。[2](127)类似地,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在使用“真”时,说“我们确认、赞同、承认、同意某人说的话”。认为语词“真”如何使用的问题和“哲学的真理问题”是同一个问题[3](83-97)。
塞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常常将意义等同言语行动,因为在讨论一个语词W时,常常认为:
(1) 语词W用于执行言语行动或者行动A。
(2) (1)说出了W的意义或者至少是部分意义。
因为(2)告诉我们,W的意义是(1),所以(2)很容易又被解释成:
(3) 如果W出现在话语S中,并且W在S中有它的字面意义,那么使用话语S,一个人做了行动A。塞尔认为这种看法很容易反驳,因为如果说话人说出了一句含有W的话、做了行动A,这种言语行动成为了W意义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要找出一个在说出含有W的语句时,没有做出任何言语行动,自然就反驳了这种观点[4](424)。例如,我们用“好”代替W,用“称赞”代替行动A。当我说“这是一辆好车”时,我确实是在称赞这辆车。但是,当我说“这是一辆好车吗?”时,却没有称赞任何东西。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辆好车吗”同样可以理解为“你是在称赞这辆车吗”,或者它也具有“你是在称赞这辆车吗”的话语力量,仍然没有构成对(3)的反对。但是,塞尔认为如此以来,(3)中的‘一个人做了行动A’就弱化成了‘会出现一个行动A’,(3)就变成了:
(4) 如果W出现在语句S中且具有字面意义,那么当一个人说出S时,本质上言语行动A会出现。如果S是简单的陈述句,行动A便被执行;如果S是疑问句,行动A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4](425)。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找出(4)的反例。例如:
(a) 如果这是好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
(b) 我想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好电热毯。
(c) 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一个好电热毯。
(d)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好电热毯。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以上四句话中的‘好’都有字面意义,但是,每一句中都没有做出‘在赞扬’的言语行动。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疑问句“这是一个好电热毯吗”与“你在称赞这个电热毯吗”具有相同的话语力量或作用,我们仍然不能得出上面四句话和以下四句对应的话具有相同的话语力量或作用:
(a′) 如果我称赞这个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
(b′) 我想知道我是否在称赞这个电热毯。
(c′)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称赞这个电热毯。
(d′) 我们希望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
我们从假设话语“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与“这是好电热毯”具有相似性出发,逐渐发现当语词的字面意义不变、改变它出现的语境时,这种相似性不复存在。条件句(a′)“如果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的确与“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有相同的言语行动(称赞),但是,(a)中的“如果这是好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却没有陈述句“这是好电热毯”中的(称赞)行动。概言之,只要我们把“好用于称赞”的言语行动看成是“好”的字面意义,我们就会遇到(a)~(d)的四个反例,即,存在有“好”的字面意义,却没执行称赞的言语行动。
用言语行动来确定语词的意义,问题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如果‘P是真的’”意味着“我肯定P”,但是,“如果P是真的,则Q也是真的”也不意指“如果我肯定P,则我也肯定Q”。很多哲学家把语词的意义看作是语词的使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W意味什么”转变为了“W是如何使用的”。在塞尔看来,把言语行动看成是语词意义的哲学家可能在思维上经历了如下步骤[4](428)
(1) 语词W的意义是什么? 等于
(2) 语词W是如何使用的?
语词是如何使用的又被默认为:
(3) 语词W在简单陈述句中是如何使用的? 进而又被认为等于:
(4) 包含语词W的句子是如何使用的? 最终表现为:
(5) 在说出这些句子时,说话者执行了什么样的言语行动?
但是,塞尔认为言语行动的最小单位是句子,具有意义的语词并不总能体现出说出句子时做出的言语行动,所以对于(5)的回答并不等于对(1)回答。
换个角度看,“什么是‘好’”的问题并不等于“什么被称为‘好’”的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相同是不充分的。‘好’用于称赞时,固然等于“说某物好”时执行的言语行动,但 “说某物好”也可能用于表达一种信念或希望。再者,尽管“说某物好”用在表达称赞上,也不能将“称某物好”的分析看成为对“好”的分析,因为任何对“好”的分析还要考虑“好”对于不同言语行动所做的相同贡献,所有使用“好”的言语行动并非都是在夸某物“好”。
笔者认为,一方面,塞尔的以上分析是成立的。的确像塞尔认为的那样,只要找出语词意义(不是虚词)的一个反例便可推翻意义和言语行动等值的误解,当然,施为动词(如“称赞”)的意义是否真的等于话语的言语行动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塞尔认为言语行动的最小单位是句子这点值得商榷。我们有时用借代手法称呼特定的某个或某些人,这时语词也属言语行动,实事上,塞尔在《言语行动:语言哲学论》的脚注中也承认,以言行事行动的F(P)中的P不一定是句子,也可以是单个的语词[1](31)。概言之,塞尔在论据中,把言语行动的最小单位放在语句上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用找反例的方法论证意义不等于言语行动的论证方式有效的,论证的结论也是成立的。语词的意义不等于言语行动。
二、关于语句意义和言语行动
顺便指出,尽管塞尔在诸多的著述中谈到意义和言语行动,但他从没有为言语行动和意义给出过任何确凿的定义。他只是在不同之处强调:意义离不开约定和规则,离不开‘网络’和‘背景能力’[5](141-144);言语行动离不开社会约定,更离不开人的意向,“我称为言语行动的举动(behavior),其必要条件是意向。”[1](17)
塞尔认为只要我们知道组成语句的规则和它的构成成分,我们就能够知道语句的意义[6](645),而说话者说出语句,却常常意味了不同于语句或比语句更多的意义。说话者意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语句意义。例如话语“窗户是开着的”,可能只是在表达语句的字面意义,即窗户是开着的,在具体的情境中,也可能不仅表达窗户是开着的,而且要求听话者把窗户关上。
格赖斯提出“非本质意义”(non natural meaning)概念,说明说话者S用X意指某事,就是打算凭借说出的话语,以让听者认出说话者意向的方式在听者身上产生某个效果[7](377-388)。塞尔并不完全赞同格赖斯的看法,认为他仅看到了意向在意义中的作用,忽视了规则和约定在意义中所起的作用,这将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说话者可以随便使用任意语句表达任何意义。塞尔认为,格赖斯对意义的说明没有给出说话人通过说出话语意指某事,和该话语本身意指某事之间的关系;而且按照意欲的效果(intended effect)定义意义,混淆了以言语行事行动和以言取效行动[1](43)。塞尔强调说某事并意指某事是以言行事行动不一定是以言取效行动。
说某事并意指某事为什么是以言行事行动?塞尔认为人类的交流具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我试图告诉某人一件事,那么只要他认出我正在试图告诉他的事就行了[1](47)。在以言行事行动中,我们成功实现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让听者认出我们正在告诉他的某事,至于在听者身上产生的进一步反应(以言取效效果),同以言行事和意义并没有直接关系。意义打算的本质效果就是理解,理解是以言行事的效果不是以言取效的效果。
不仅如此,理解的要点还在于,我们必须理解说话者的意向、约定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当话语的意义用于执行以言行事行动时,说话者是通过让听话者认出他产生效果的意向,从而产生特定的效果,并且打算通过所说话语的使用规则,将话语和产生的效果联系起来,最终完成以言行事的效果。就说话者而言,完成以言行事行动的手段是话语成分的组合,就听话者来说,理解说话者的意义就是认出说话者的意向。以言行事行动一方连接了说话者,一方连接着听话者,语句意义的实现就意味着以言行事行动的完成。理解的过程如下[1](48):
(1) 理解一个句子就是知道它的意义。
(2) 语句的意义由规则决定,这些规则指出了话语的条件和话语被当作的东西。
(3) 说出一句话并意指它就是(a)以言行事意向,打算让听者知道(认出或明白)由某些规则说明的事态成立,(b)打算以让听者认出以言行事意向的方式知道(认出或明白)这些事情,(c)打算凭借语句的规则让听者认出以言行事意向。
(4) 句子给出了在听者身上产生这个以言行事效果的约定手段。
说话者说出语句并意指它,要具有意向(a)(b)(c),听者理解话语就在于这些意向的实现。如果听者明白支配语句成分的规则,这些意向也就实现了,语句的意义便显现出来。
根据塞尔的以上分析,由语句意义决定的言语行动,一定存在一套规则,它不仅构成了具体的言语行动,而且构成了语言的语意。所以,对言语行动的分析集中在了行动的构成性规则和语言成分的语意规范,而且决定言语行动的构成性规则和语意规范必然是两个相关的主题。任何具体语言,只要我们知道了语句成分和它们决定的言语行动,我们就能通过表述那些言语行动的充分必要规则,给出完备的语言成分的意义规范。
但是,塞尔没有看到,对于具体的言语行动而言,如果存在着语言成分和言语行动的关联是偶然的,或者在说出这些言语时没有做出这种言语行动,比如当话语的背景给出了意义没有给出的东西,意义和言语行动的关系就会断裂。所以,语句意义和言语行动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符合塞尔的以上分析,因为既要考虑言语行动又要考虑其它因素,例如语境。尽管塞尔区分了语句意义和言语行动下的意义,但他终究没有厘清语句的意义规则和言语行动规则之间的区别。换言之,虽然对语句意义的研究和言语行动的研究可以视为不是两种不同的研究,但语句的意义规则并不等同于言语行动的规则。
塞尔以上分析的目的似乎是要告诉我们:(1)当语句的意义和以言行事的效果完全吻合时,以言行事的效果就解释了语句的意义;(2)当语句的意义和以言行事的效果不相吻合时,以言行事的效果则用来说明说话者的意义。塞尔的错误在于:当(1)不成立时,句子给出的约定手段和构成规则便不能用来确定以言行事的效果,所以无法再用以言行事的效果解释说话者意义,换言之,当(1)不成立时,(2)也不成立。实质上塞尔只完成了目的(1)。
三、关于语句意义与说话者意义
众所周知,塞尔以言语行动理论为基础,解释了语言中的反话、隐喻和间接言语行动的意义,区分了语句意义和说话者意义。他说,“只要我们知道构成语句的语词意义和他们的构成规则,我们就知道了语句的意义”,但是,“相对于说话者所说的语句,话语常常意味着多于或不同于该语句意味的东西”。[6](645)由此也可推断,尽管塞尔从没有为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给出过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他始终坚持并预设了语词和语句具有字面意义。但由于语词和语句意义牵涉到了人的知识“网络”和“背景能力”,致使我们无法为它们的意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例如,我们不能给出“肥”和“瘦”,“穷”和“富”,“民主”和“集权”之间具体的界线。
我们不能把语句意义看作是说话者意义。语句意义是语句的性质,说话者意义是话语或言语行动的性质[8](677-681)。但是也有学者与塞尔不同,认为:根本没有语句意义或语句的字面意义,只有说话者意义,例如,Knapp和Michaels[9](669-675)。我们认为,在有没有语词、语句意义问题上,塞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语句的意义,我们就无法解释说话者的意义,如反话或隐喻。语句的意义是约定的或者是受规则支配的,规则决定了句法和语意,说话者使用这些句法上有意义的对象执行具有意向的言语行动,于是有了说话者意义。
语句意义与说话者意义区别的关键是前者缺乏意向。塞尔指出,虽然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并且依赖于人的意向性,但句子只有在言语行动中才有意向,而不是句子意义本身具有意向[8](678)。意向是语句意义和说话者意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们也不能因为说话者的意义而取消语句意义,因为,只有说话者的意向没有语句的意义,我们就会对说话者意义束手无策。证明语句具有意义的最好例子也许是,计算机屏幕上现示“椅子是由木做的”语句,我们完全知道什么意思,也知道鹦鹉学舌时说出的“欢迎”是什么意思。
塞尔对言语行动的研究工作表明,理解说话者意义既重要又复杂。说话者意义依赖于说话者做出的言语行动,对言语行动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理解语句意义,还要求我们找出说话者意向;不仅要求我们理解说话者的话语内容,还要求我们理解话语的力量,因此,对说话者意义的研究就变成了对言语行动的研究。
四、关于说话者意义的晚期研究
塞尔对说话者意义的研究,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主要集中在对言语行动理论的技术处理上。他把以言行事行动的形式视为F(P),其中F代表以言行事的要旨,P代表关联世界的语词或语句(也称命题),F决定了P与世界的联系方式(包括了语词到世界↓、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和无适应方向∅),所有的以言行事模型都可以按照话语的成功条件加以分析。
与早期不同,晚期塞尔对说话者意义的研究集中在交流、表征同意义的关系上。塞尔说:“像大多数言语行动的理论家一样,我按照交流(communication)来分析意义,作为意义本质的意向就是在听者身上产生效果的意向。但是现在看来,出于文中我解释的理由,至少在‘意义’(meaning)的一种意义(sense)上,交流来自于意义而不是构成了意义。”塞尔认为说话者说某事并意指它不在于交流而在于表征[10](212)。
表征不同于交流。例如,当你在异国驾车旅游时发动机轴承坏了,你找到机师但没有任何互懂的语言同他沟通,也没法拿出发动机缸中的轴承给他看。幸好你身边带有纸和笔,又知道轴承是什么样子,于是画出一张带有发动机缸的损毁轴承,如果不出意外(画的图还过得去),你可以成功地把“车子的轴承坏了”意思传达给他。这种情形下的交流如下:
(1) 说话者在图画中表征了轴承坏的事态,一旦画完,这张图画也就表达了事态。
(2) 如果这种努力是成功的,说话者也就成功地向听者交流了事态,这张图画也被称为向听者交流了事实:车子的轴承坏了。
注意,(1)和(2)不同,前者是表征而后者是交流,表征的对象是事态(车子的轴承坏了),交流的对象不是事态,是表征(图纸)。图纸既用于表征也用于交流。交流的成功依赖于表征。使用言语行动论的术语,表征只相当于以言行事模型F(P)中的命题内容P,命题内容表征事态。

图1 表征、交流与意义的关系示意图
表征的事态“车子的轴承坏了”可以同交流的事实“车子的轴承坏了”分离开来。因为你可以不交流只表征,例如,在上例中,只画出这张图形而不打算给任何人看,或者用不带墨水的笔画出别人看不见的印迹,所以表征先于交流并独立于交流,而交流必须依赖于表征,人们不可能做出没有表征的交流。
一张图形怎么才能成为表征?塞尔认为相似性不是表征的本质,我的左靴子无论如何同其它东西相似,它都不表征任何东西,图形要成为事态的表征,说话者必须带有表征事态的意向[10](214)。但这样的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说明表征的根本特征时使用了表征意向的概念,出现了循环定义。但是,塞尔认为,“给出一个不使用这种概念的答案证明是不可能的”[10](215)。我们只能把表征需要表征意向作为一个预设,来说明表征意向可以完全独立于交流意向,交流意向需要表征。
回到上面图画的例子,只要技师认出我画的图是那种事态的表征,我就成功地向他交流了车子的轴承坏了。说话者的交流意向是,听者应当把图形视为表征事态的意向(意向2),而图画成为表征,在于说话者打算让它成为表征(意向1)。所以交流意向是,在听者身上产生认识意向1的意向,即让听者认出‘说者用图形表征事态意向’的意向。这和塞尔早期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说话者说出语句T并意指它等于:[1](29-50)
(a) 凭借话语T的规则,用话语T使听者认识事态的意向i-1,
(b) 打算以认出i-I(意向1)的方式让听者产生这种效果,
(c) 打算以听者知道的组织句子规则的方式,认出i-I。
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塞尔认为说话者的交流意向和意义意向是相同的,现在认为这是错的,因为以前他没有发现表征在意义中的优先作用。在后期,塞尔认为意义的主要意向是表征意向,它们独立并先于交流意向,交流意向是听者应当知道表征意向的意向。
在言语行动中,图纸例子所揭示的表征和交流之间的区别,由于话语既用于表征又用于交流而被掩盖,致使我们把交流的失败看作了言语行动的失败。但是图画表征事态的例子可以独立于交流,因此,意义也可以只用作表征不用作交流。
意义和言语行动的表征、交流解释是塞尔语言哲学理论的新发展,既是对言语行动视域下意义的一次修订,也是以意向为视角对言语行动研究的一次推进。如果抛开对表征意向的预设不论,笔者认为,交流表征理论将语句意义放回到它应有的位置——表征上,彰显了意向在说话者意义上的本质作用,不但解决了塞尔在言语行动理论中没有完成的目的2,也加深了我们对言行事F(P)的理解。但是,由于塞尔无法为表征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不免让人们质疑表征意向的合理性,特别是表征意向先于意义的预设。但是如果拿掉表征意向先于意义这个预设,塞尔对意义的所有建构都将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
[1] 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 R.M. Hare. The language of moral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52.
[3] P. F. Strawson. Truth [J]. Analysis, 1949, 9(6): 83-97.
[4] John R. Searle.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2, 71(4): 423-432.
[5] Searle, John R.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 John R. Searle.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4, 25(3): 637-667.
[7] H. P. Grice. Meaning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66(3): 377-388
[8] John R. Searle. Structure and intention in language: A reply to Knapp and Michaels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4, 25(3): 677-681.
[9] Steven Knapp, Walter Benn Michaels. Reply to John Searl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4, 25(3): 669-675.
[10] John R. Searle. Meaning, commun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C]// Richard E. Grandy, Richard Warner. Philosophical Grounds of Rationality.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2004.
Searle’s speech acts and meaning
HU Guangyuan
(Philosoph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Searle’s clarification about some misunderstanding that Seale’s speech acts theory interpreting meaning causes is available, but some errors can be found in his argument. There are defects in Searle’s earlier interpretation about meaning. Nevertheless, a new model of later interpretation is successful in solving those defects.
Searle; meaning; speech acts; communication; representation
B81-05
A
1672-3104(2014)01-0141-05
[编辑: 颜关明]
2013-05-25;
2013-12-04
胡光远(1975-),男,河南省鹿邑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逻辑哲学,科学技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