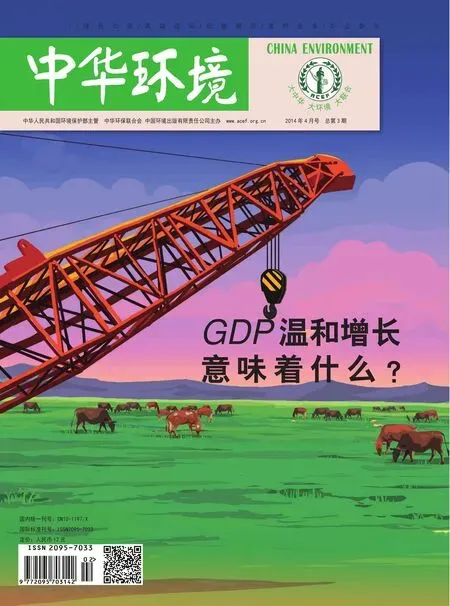马尔克斯的遗产
费米
马尔克斯的遗产
费米

马尔克斯过世了,有那么多文人写文章纪念他。我不是很会凑热闹的人,本没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但看过几篇纪念文章后,感觉有那么多文人误读了马尔克斯,并且还以自己的误读来误导读者,于是也就赶来凑这个热闹了。
最早读盗版的《百年孤独》,说实话我并没有读懂,后来分析起来,大概也是被一干文人误导了,他们告诉我马尔克斯的要点在于魔幻,并着重分析说全部精华在那个著名的开头上:“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十多年后再读,我发现要参透他的那个百年,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高兴的是我已经不把那个著名的开头当回事了,等我现在读那些纪念文章,感觉人何以会懒到如此程度,竟把十几年前的旧货假货再次搬出来卖弄一番。
要弄懂《百年孤独》,持续的阅读非常重要。我说的阅读,是一种文学传统的延续,或者是某种相互渗透与借鉴,比如拿奈保尔的《河湾》跟马尔克斯对照着读,就能发现一些共通之处。奈保尔在书里描述了河湾中的水葫芦,说这个外来的物种一路疯长,把当地居民死死困住。我当知青的时候水葫芦在江南被大量引种,除了做猪饲料外还能肥田,“许多年之后”也导致了生态灾难。奈保尔的水葫芦是在影射蒙博托治下的扎伊尔,看似美丽却危机四伏。而同样的内容在更早的马尔克斯那里已经出现,不同的是水葫芦换成了香蕉。
马尔克斯诞生在马格达雷纳省,从1904年到1910年拉斐尔·雷耶斯统治哥伦比亚时期,由于马格达雷纳河流域大规模种植香蕉,从而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地繁荣起来,并形成了令哥伦比亚人日后津津乐道的“香蕉热”。“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也在此时侵入到这个地区并扎下了根,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能为封建的大庄园里的农民提高工资,因此,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就能促使本地区实现进步和现代化了。其实,他们错了,这种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实际上是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他们沦为单纯的原料输出国这样一种畸型状况。
美国人彭慕兰和史蒂夫·托皮克在他们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这样说:三、四个世纪前,欧洲人喜欢吃糖,可欧洲大陆的气候不适宜种甘蔗,殖民主义者于是在东南亚、在中国台湾逼迫当地人种植了大量甘蔗。工业革命后,橡胶需求增大,巴西的雨林就被大肆砍伐,种上了大片的橡胶树,以及欧洲人喜欢的咖啡。结果是,东南亚的甘蔗和巴西的咖啡、橡胶种植是满足了殖民主义者的需求,却给当地带来了生态灾难。惟独台湾得以幸免:早些时候的郑成功,以及后来的清朝都强调种粮食,这就避免了单一物种种植给生态带来的危害。
因此,认清孤独何以长达百年,既不是多年前的看冰块和放大镜,也不是不停吃土和为自己织裹尸布,魔幻的只是其表皮,真正的内核是对政治经济和发展路径的深刻观察,这些都得益于马尔克斯多年的记者生涯,以及长期的独立思考。也许这样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康拉德那里:一个好的作家穷尽毕生功力所追寻的,就是认识人类的黑暗心脏地带,从而找出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层意思: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由此推演,一个作家如果仅仅执着于许多年以前的小家子货色,着迷于一些个小情调小技巧,缺乏对政治经济和生态层面的深刻观照,他或许不会孤独,得到的也只能是肤浅的欢乐。而这显然不是马尔克斯的遗产,他所留给我们的东西是:你若不找出孤独的根源,孤独将一直延续下去;香蕉固然好吃,你也不能拿它替换一日三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