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第一次和巴金见面
文/张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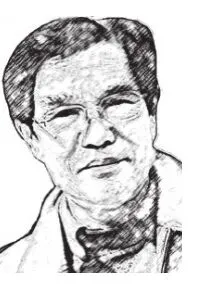
张斤夫中国作协会员,曾任《上海文学》社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小说组组长,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MFA创意写作校外导师

壹
我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78年2月15日。那时,我在东海舰队文工团任创作员。
1978年春节过后不久,舰队文化部在上海水电路舰队司令部小会议室召开创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舰队召开的第一次创作会议,部队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参加对象,除舰队文化部、文工团创作人员之外,还有舰队各基地、水警区的文化干部。
会议召开之前,传出消息,著名作家巴金将来给我们作报告。
一听说巴金要来,大家都非常激动,尽管天气很冷,纷纷表示要求参加。但或许正是因为巴金要来的原故吧,会议对参加的人数、时间、着装、气氛等要求很严格。通知书上特别注明:“二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时整开会,务必准时到达。”
文工团就在司令部大院旁边,通知书上要求九点整到达,为了找个离主席台较近的位子,看巴金看得更清楚一些,八点钟,我就来到司令部大院,先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本塑料封面烫金的笔记本,准备将巴金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我八点二十九分到了会场。没想到,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个位子坐下。
离开会时间还有半小时。主席台上,文化部长程景山和副部长李无言,正襟危坐在上面。他们的中间,留着一个空位,空位前面,摆放着一束鲜花。很显然,是留给巴金的。
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虽然大家心里都急切地等待着巴金的到来,不时看看自己的手表,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九点钟到了,两位部长站起来,走到会场门外的柏油小路上,准备迎接客人。全体与会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场外。
然而,巴金没有来。
一直等到九点半,九点五十分,还不见巴金先生的影子!
大家不禁纷纷议论起来,猜想巴金迟迟没来的原因。有的说,天这么冷,交通又不方便,晚来一会儿很正常;有的说,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见人影儿,说不定巴金不会来了。个别同志甚至小声发牢骚,大作家嘛,搭搭架子,情有可原……
正当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巴金乘坐的汽车突然出现在会场门口。两位部长热情地走上前去,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巴金身穿一件显得特别肥大的陆军棉大衣,他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用四川话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同志们久等了,请同志们原谅……”
巴金的身后,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等。
为什么来晚了?巴金没有说明;负责前去接巴金的那位海军同志站起来,想解释,巴金笑笑,制止了他说:“不要解释嘛,来晚了就是来晚了,我向同志们道歉。”说着,站起来,欠欠身:“对不起,让同志们等久了。”
巴金的报告,讲得很慢。与其说是“报告”,不如说是“谈心”。开始,我听得非常认真,记得很详细,恨不能把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记下来。但听着听着,握紧的笔,不仅停了下来。我发现,巴金很不善于讲话,又不注意条理,没有一句我所希望得到的高深理论或者创作经验。他翻来覆去强调的,我们听得最清楚的,几乎都是如何“讲真话”、如何“做人”、如何“把心交给读者”之类的大实话。而且,巴金一再强调:“我不是作家,我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等等。加之他瘦弱的身材、雪白的头发、突出的下颚、平缓而浓重的四川口音,一个朴实、平凡的巴金,取代了我想象中高大魁梧、出口成章、慷慨激昂的文豪、泰斗、大师形象!
贰
2010年,因参与上海作家手稿展的文字编辑工作,我有幸在展前接触了上海一百多位作家的手稿。从老一辈作家夏衍、巴金、茹志鹃、峻青、陈望道、柯蓝到中年作家王安忆、叶辛、赵丽宏、余秋雨、陈丹燕等等,他们写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环境的手稿,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这些手稿,或用钢笔,或用毛笔,有的甚至还用铅笔、圆珠笔;它们或是小说,或是诗歌、散文,有的是浩瀚长卷,有的仅用一叶便笺……无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手稿是无声的语言,手稿是历史的记录,虽然听不到他们的一句话语,但徜徉在作家手稿之林,却让我听到他们的心声。
在这些作家手稿中,最引人瞩目、最使我感动的,是巴金先生的日记。
解放后,巴金先生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写下去。洋洋几十万字,处处看出一个当代文坛泰斗的平易、谦虚;看出他与普通百姓、普通读者之间那种真诚、深厚的平等意识,字里行间闪烁着他高尚的人品人格。
当我将《巴金日记》翻阅到1978年2月15日(星期一,多云)时,眼睛不禁一亮:朴实的言语,真诚的文字,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二十年前难忘的一幕,同时,也解开了那次开会他迟到的原因。
巴金在日记中写道:
“因为要到东海舰队司令部给海军搞创作的同志做报告,七点钟不到就起了床,吃好了早饭,等着车子来接。直到八点整,XX才坐车来到我家。之后,又去接茹志鹃、赵自、孔罗荪和庄稼。等于在上海转了大半个圈子,九点三刻能赶到位于市区北郊水电路的海军大院已经很不容易了。”
已过古稀之年的巴金,由于职业原因,往往是晚睡晚起。但为了给我们作报告,这一天却很早就起了床,吃了饭,等待着出发。由于是星期一,又是早上,交通特别拥挤,加之,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茹志鹃等四五个人,都要一个一个去接,赶到海军司令部已近十点钟。我们这些等待开会的人心急如焚,巴金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叁
1978年,我从东海舰队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分到《上海文学》当小说编辑。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都很高兴,我激动得几夜没有睡好觉。巴金是《上海文学》主编,是我从小就无上崇拜的作家,到他手下工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据说,编辑部里,还有著名作家茹志鹃、工人作家费礼文、电影《大浪淘沙》作者于炳坤、《不死的王孝和》作者赵自、著名诗人肖刚等等。他们都是我从中学时代就崇拜的作家,与他们为伍共事,我既感到无上荣幸,又觉得空前的压力。到编辑部报到那天,我特地穿了一身刚刚摘去领章的军装,来到那座古希腊式大楼楼下。大厅里,迎面宽大的镜子里立刻显出我瘦削的身影;镜子的旁边,大自鸣钟正好敲响十点钟;随着“嘡——嘡——”的钟声,我踏上旋转的楼梯,阳光透过五彩的玻璃,照在我的身上,我感觉自己真正踏进了神圣的文学殿堂,仿佛又像走进了童话世界,不禁放慢脚步,耳边响起部队首长语重心长的嘱咐:
“你待人真诚,性格直率,不拘小节,这是好的,在部队里,同志们都了解你。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是人生的又一个起点,希望你顺利地走下去。可是,作家协会不同于部队,是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到了那里,一定要谦虚谨慎,虚心向巴金、茹志鹃他们学习,改一改自己的脾气。如果不改,恐怕你很难在那里呆下去。”
步履维艰。诚惶诚恐。我一面踏着楼梯,一面思考着怎样走好下一步人生之履……
肆
在我的想象中,巴金给部队作者做报告,当然会很谦虚。如果回到编辑部,作为主编,一定会是很威严的。然而,与我的想象相反,不论在任何时候,和我们任何一位编辑接触,巴金不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作家,更是一位亲切、平易的老一代编辑。平时,文联、作协有事,开会,需要巴金出面主持,他都是三言两语开个头,把更多的话让位于其他领导。相处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说,巴金曾对哪个人红过脸、发过脾气。因而,我对巴金的神秘之感打破,崇敬之情倍增,一个更加真实、亲切、平易、谦虚的老人,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巴金经常告诫我们,“把心交给读者。”来《上海文学》之前,我是一个作者,投过稿,亲身体验过老一代编辑交心的温馨。自己当了编辑后,我从“把心交给读者”,联想到把心交给“作者”;如果不把心交给作者,就发现不了新人,难以推出新的作品。“交心”,虽然只有两个字,简单、平凡,却是编辑人格的集中体现、繁荣创作的宝贵经验。她,犹如无价之宝,被以巴金为主编的《上海文学》《收获》编辑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发现一个又一个新人,推出一部又一部佳作,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作者的命运。至今,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仍有不少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每当接到他们的来稿,我都会下意识地想到“交心”两字,认真、仔细地阅读,尽最大努力,给作者提出修改参考建议。
与君见一面,听君一席谈,交心无保留,受用无期限——巴金,犹如一面旗帜,永远飘扬在我的心间。
- 上海采风月刊的其它文章
- 我和《援疆日记》
- 重建医患关系从细节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