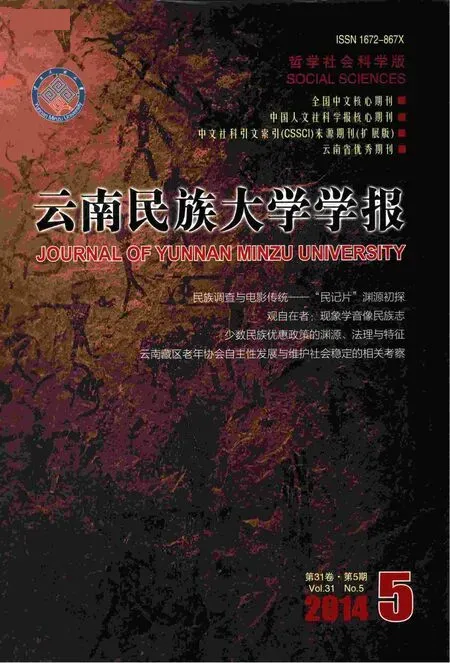民族调查与电影传统—— “民纪片”渊源初探
郭 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34)
从1957 年到1981 年,为配合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由一些有经验的民族学家提出动议,得到国家高层领导支持,①张江华等:《影视人类学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196 页。政府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实施了为中国大陆每个少数民族摄制一部民族志电影的计划,彼时官方文件对这批影片的称谓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这批影片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代表作。然而,这些影片并非无源之水,只有将其置于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它们的意义才能够彰显。
如果从1933 年凌纯声和勇士衡到湖南拍摄苗族考察的电影算起,中国的民族志电影已经走过80 年的历程。这段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3 ~1949 年,民国边疆考察电影时期;
1957 ~1981 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民纪片)时期;
20 世纪80 年代至今,新民族志电影或影视人类学时期。
这三个时期摄制的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承袭着若明若暗的学术脉络。而本文所探讨的“民纪片”,处在民国边疆考察电影和当代新民族志电影之间,既联系着前者,又启迪着后者。若详加分析,民纪片的产生既有近因,亦有远源。其近因便是1956 年发起的民族大调查;其远源,则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的电影和边疆考察传统。
一、民族大调查与影像手段的运用
民纪片并不是一个自发出现的纯学术现象,而首先是一个执政党主导的国家行为。它得以产生的前提,是20 世纪50 ~60 年代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解放初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广袤的西南、中南和西北地区建立了政治权威,却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是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 年5 月做出决定,从中央各部门抽调数百人组成中央访问团,在1950 ~1951 年间分赴西南、西北、中南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以“宣传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密切中央与各民族联系,了解民族情况与要求”②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1 页;王连芳:《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工作初步总结》,《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299 页。。其中,西南分团访问地区为川、滇、康、黔;西北分团访问地区为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中南分团访问地区为两广和湖南。这次访问,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调查资料,为中国的民族关系勾勒出了基本轮廓。
而在地方的层面,局部性的调查也在展开。以云南为例,早在1950 年,中共云南省委就在民族工作会议上把全省划分为“内地民族杂居区”和“有土司制度的边沿区”,并摸清了少数民族人口中有近400 万人分布于内地民族杂居区,有近200万人分布于有土司制度的边沿区。从1950 年到1952 年,在前一个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而后一个地区的局势则异常复杂。因此,全面深入地进行民族调查,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要求。1953 ~56 年,云南省边疆工委和省民委多次派出工作组,基本搞清了沿边各民族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状况,将这些民族按社会进化的形态分成几类。与之同时,又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民族语言和民族识别调查,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①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2 ~7 页。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设立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召集民委负责人开会,决定首先抓调查研究。当年,全国人大民委就派调查组分赴云南傣族、景颇族、四川彝族和新疆维吾尔族地区进行调查。这些由地方和中央党政机构发起的考察,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调查做了重要的铺垫。
1956 年6 月,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全国人大民委主持的少数民族大调查正式启动。这次民族大调查能持续地进行10 年,并取得重要成果,不仅有赖于国家领导层的远见和意志,也得益于中国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解放以后,社会学因受到政治的干预被取消,但原来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转变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20 世纪50~60 年代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实际上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由一批专业的社会学-民族学家带领着进行的,②据王建民等人研究,1950 年代民族大调查的总体设计、原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由一批民族学家具体完成的,参见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六章,第二节。如费孝通在1950 ~1951 年的访问团和1956 年的民族调查中都是负责人之一,他也是1956 年云南民族调查组的组长,③费孝通先生1957 年被召回京,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参见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 年2 期。副组长是云南大学著名的地方史专家方国瑜和具有长期边疆工作经验的侯方岳。④侯方岳(1915 -2006),四川广安人,早年参加中共,建国后曾任云南省边疆工委副书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等职。而另一位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早在1954 年就受国家民委委派,率领一个调查组到昆明,协助语言学家付懋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⑤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6 页。并在之后的民族大调查中起了组织者的作用。⑥潘守永、张海洋、石颖川:《林耀华与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民族报》,2010 年4 月16 日。北京派到云南的民族调查组成员有宋蜀华(中央民族学院)、朱家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仰松(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宋恩常(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黄宝璠(民族出版社)、田继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致藩(北京建筑艺术学院)等。⑦田继周:《西盟佤族地区调查回忆片段》,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81 页。这些人经过民族大调查的锻炼,后来都成了有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中有的人对民族学知之不多,但也有一些人继承了民国时期社会学、民族学的知识和传统,如佤族调查组的组长就是从法国毕业的人类学家杨堃,⑧杨堃(1901 ~1997),男,河北人,早年赴法国学习民族学、社会学,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就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1950 年代参与民族大调查,文革后调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其一生虽多处逆境,仍致力于中国民族学的建设,代表作有《民族学概论》、《原始社会发展史》等。组员中如徐志远等人则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徐志远回忆说:
费孝通教授是云南民族调查组的组长,他带领着20 多个全国人大的、中央民院的和很多研究单位的人来,这些人起码都是助教,大量的是讲师,只有我一个是应届毕业生,小毛头。这样就进行学习,学习了一个多月。⑨参见徐何珊:《徐志远访谈》,载徐何珊、谢春波、郭净、陈湘、王珍:《中国民族志电影口述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出。
……
当时全国人大民委制定了一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①这个提纲称为《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主要由中央民院的一些学者起草,参见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162 ~163 页。,很厚一本,有原始社会调查提纲、奴隶社会调查提纲、封建社会调查提纲,通过学习了解解放前我们国家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社会形态。
参与调查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专业训练的背景,如1956 年中央民院历史系的研究生,就听过林耀华教授的《原始社会史》,傅乐焕教授的《史料学》,徐宗元教授的《古文字学》,以及吴文藻和费孝通教授的民族学和民族调查报告。调查人员事先还参加了专门的培训。当时遵循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受到前苏联民族学的深刻影响,有些内容甚至由苏联专家亲自传授,广西学者陈衣回忆说,1956 年他在中央民院参加民族学研究生班学习:②陈衣:《黔省侗乡访古今》,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286 页。
这个班是学院第一期比较正规的研究生班,学院相当重视。从苏联请来民族学专家尼·切博克萨
罗夫教授讲授《民族学概论》,除我们班外,历史系56 级本科全体同学、系里一些青年教师和中科
院民族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也来听苏联专家的课。
整个调查不仅有理论的指导,在方法上亦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如调查组的很多人都学会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此次行动更采用了综合调查的方法,调查组包括历史、民族、语言、考古、艺术等学科的成员,③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165 页。而且从一开始,每个调查组就担负着三项任务:田野调查和文字整理、拍摄照片、收集文物,这是在收集“三重证据”(调查、文献、考古资料)思想指导下的全国统一部署。如云南佤族、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调查组在1958 年3 月的总结报告里,就写明了他们的工作成绩:“上述五族调查,原始资料164 万字……另搜集文物193 件,摄拍照片900 张”④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1956 年12 月至1957 年6 月云南西盟大马散卡瓦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1958 年3 月,前言。。徐志远提到,1956 年开始云南民族调查的时候,每个调查组配发了两台照相机,⑤徐志远:《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 -1957)》,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 页。他本人还负责照片的整理工作:
在民族研究所除了调查、编写调查资料、写调查报告之外,我还负责照片资料的整理工作。各个组领了胶卷领了相机下去,回来要交回胶卷,我就负责去冲印、放大、然后分类、编目、装册。现在你们社科院里面,紫色的七八个大纸盒子里面的底片袋上都印着云南民族调查组,还有若干本装贴好
的大相册,那些都是我当年整的。⑥参见徐何珊:《徐志远访谈》。
20 世纪50 ~60 年代的民族大调查,在影像收集方面成效显著,仅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档案中,就有专门的“云南民族调查照片资料”和“云南民族调查电影纪录片资料”两个系列,前者收藏了12000 多张底片和照片(少部分为1960 年以后拍摄),其中大部分已由调查者整理成了不同民族的专辑,如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佤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独龙族、苦聪人、崩龙族(今德昂族)、沧源岩画、民族印谱、民族考古等照片资料集,⑦杨福泉:《总论》,纳麒、汤汉清主编:《远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2 ~3 页。徐志远就是这批资料的整理人之一。由此可见,用影像帮助调查者收集资料,绝非一种偶然的策略。在中国民族学转型的这一时期,影像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已经被纳入整体战略的考虑。而这个变化,是有历史线索可寻的。
20 世纪50 ~60 年代这批影片最早使用的名称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有如下说法:
由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主任
夏辅仁和业务秘书张正明代表调查组和科研人员意见,到承拍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同厂长陈波商议
后,将这种片子命名为“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其后,根据这种影片的性质和特点,正式修订为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并一直沿用到
(19) 80 年代初期。⑧张江华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第六章(本章由陈景源撰写),第197 页。
根据以上叙述,民纪片最初曾叫做“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之后改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后一个确定的名称由三个关键词组成,每个词都有特定的含义:
其一为“少数民族”,这是1949 年以后,由新建立的国家政权确定的对汉族以外各民族群体的标准称谓,它被纳入“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政治概念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二为“科学纪录片”,这个词是用来给这批影片定性的。1961 年9 月,主持这批影片摄制的文化部和全国人大民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历时近一个月。①文中的“空了同志”为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萨空了。齐燕铭:《齐燕铭同志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 年。在9 月7 日的会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齐燕铭做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提出:
刚才听了同志们介绍,有科学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科学研究片好几个名称。各种不同的名称,各有不同的目的。现在已搞出了七部片子,通过对这七部片子的总结,我们首先要把这种片子的目的性明确起来。我看这种片子就是科学纪录片,对不对,请大家研究。②齐燕铭:《齐燕铭同志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 页。
11 月7 日的会议总结,确认了齐燕铭的观点,并指明了所谓“科学纪录片”的含义:
应该明确,这种影片就是科学纪录片,不同于科学教育片,新闻纪录片,更不同于故事片。过去由于对影片的目的性不够明确,在影片中既有科学纪录片的内容,也有新闻纪录片或者其他片种的内容,以致减弱了影片的科学作用。
摄制科学纪录片的目的是纪录少数民族原来的社会面貌,主要是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同时根据需要向有关人员进行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③《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摄制工作总结提要》,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第8 ~9 页。
据此可知,在1961 年以前,关于民纪片的目的和名称存在不同看法,而此次座谈会确定这批影片冠以“科学纪录片”的名称,旨在认定它们的“科学研究”性质,因而在中国电影中创立了一种区别于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的新片种。这种以“少数民族”为对象,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纪录片,尽管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却已具备“民族志电影”的基本特性,应当归属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早期形态,以区别于文革后在“影视人类学”观念指导下兴起的新民族志影像。上述座谈会纪要提到这次拍摄计划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云南民族研究所、北京科影厂的有关人士参加,由此可以推测, “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这一标准的提法,是经过讨论斟酌的,当有民族学者和电影专业人员的意见参与其中。
其三为“社会历史”,这个词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发展观点,而且包含着“抢救落后”的含义,它是对1956 ~1966 年民族大调查基本内容做出界定的词汇。据底润昆、张正明《彭真同志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词是彭真根据毛泽东主席1956 年春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的。④底润昆、张正明《彭真同志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民网》“彭真纪念馆-评论研究”,http://cpc. people. com. cn/GB/69112/99985/100001/9809365. html。当时在民族学领域,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中国的民族研究应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注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有见于记载的历史,甚至一些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故而此次大调查强调不仅要进行现状的调查,也要进行历史的调查。⑤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60 页。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便界定了民族大调查的基本内容。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与此次行动有关的调查活动一律被称之为“社会历史调查”,做调查的机构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与之相应,作为调查手段的电影拍摄也被冠之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影片的制作。
可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这一名称有着明确的政治寓意,也蕴含着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学术内容。可以说,它的表达非常准确而鲜明。今后,若能根据更多的资料对这一名称详加探讨,或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民纪片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二、民纪片与民国影像的渊源关系
民纪片不但与20 世纪50 ~60 年代的民族大调查相关,也与百年以来影像在中国的发展相关。倘若细细追踪,便可发现隐藏在历史中的两条线索,即民国照相和电影的历史,和边疆考察的影像纪录。
其一,民国照相和电影的历史
这条线索,是笔者在和杨光海先生①杨光海(1932 -),云南大理白族,是民纪片最主要的拍摄者之一。交谈时发现的。1947 年,他离开大理老家到昆明打工,考进“子雄摄影室”当学徒。这个照相馆的老板叫郭子雄,云南玉溪人,原来在国民党空军做事,退伍后在昆明市的晓东街开了个叫“维纳斯”的照相馆。晓东街在抗战期间到20 世纪40 年代末是昆明很热闹的地方,集中了剧院、电影院等许多娱乐场所。郭子雄赚了钱以后,又在抗战胜利堂旁边的云瑞西路开了第二家照相馆,叫“子雄摄影室”,其规模比维纳斯更大,有30 多位员工,一楼是收款和取照片的营业室,二楼是摄影室,三楼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卧室,四楼是员工的居室和工作室,做些修底片、着色的活儿,五楼是洗、放照片的暗室。②参见郭净《云南,藏地和纪录影像——杨光海访谈录》,《民族艺术》2014 年1 期。
云南因其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地理位置,在清代末年就受到了西方影像文化的熏染。照相和电影进入云南大约在20 世纪初期。法国人方舒雅(Auguste Francois)和马尔薄特(Pierre Marbotte)是目前所知最早到云南拍摄照片的西方人,他们肩负着修建滇越铁路的使命,却因为个人的兴趣带来了照相机。③参见方舒雅:《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皮埃尔·马尔薄特: 《滇越铁路——一个法国家庭在中国的经历》,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 年。而第一部关于云南的电影,也是这条铁路牵引来的。据考证,1903 年至1910 年滇越铁路修筑期间,法国滇越铁路总局拍摄了一部名叫《滇越铁路的修筑与通车》的影片,纪录了从云南昆明至河口沿线的修路过程。方舒雅在云南担任领事,操办滇越铁路谈判期间,也拍摄了一些影片。
电影在云南公映的年代也很早,1907 年,昆明“水月轩”照相馆的老板蒋楦将可容纳200 人的客厅改为临时放映场所,放映默片,此乃云南最早的电影院。他还在《滇南钞报》上刊登广告云:
本轩现放之奇巧活动电影,今又由西洋添办更奇数十场。其中火车、轮船、人物、鸟兽,生动活泼; 又有日俄战景,枪炮轰击,烟雾腾天,恍如身入战场,令人惊心动魄。本轩不惜重价,购运来滇,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 1907 年2 月13日) 起,在新盖的电影院场里放映,每位收银三角,凡欲赏识者,请先期至本轩购票入场”。④张亚南:《昆明电影宣传史话》,桂云剑主编:《五华文化史话》,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367 ~368 页。
蒋楦曾想建立自己的制片厂,但此愿望未能实现。1923 年,云南省长兼建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为纪念“护国讨袁”战争,请香港友谊电影公司来昆明拍摄了一部名叫《洪宪之战》的电影,并于当年7 月在昆明逸乐影戏院上映,这是云南人自己筹划的第一部故事片。1916 年,法国百代电影公司派人从昆明到上海拍摄了《蔡锷灵枢归国》,1918 年在昆明上映。1920 年,百代公司又拍摄了《云南大观楼风景》、《凯旋运动会》等纪录片,在昆明公映。1926 ~1929 年,法国驻云南领事馆拍《唐故总统出殡》、《东陆大学之内外观》,于1932年在昆明公映。1925 ~1932 年,云南省教育厅拍摄过《云南省运动会》、《金马号飞机》等纪录片,未公映。1939 ~1944 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场在云南摄制《抗战建国中之云南》、《建设中之新云南》等11 部纪录片,在国内外发行放映。⑤谢德明:《万千宠爱集一身:云南电影粉墨登场》,《民族艺术研究》2007 年1 期。从1930 ~1940 年间,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以及法国、瑞士和英国的传教士都在云南拍过照片和电影。在20 世纪40 年代中后期,援华美军中的摄影部队和个人更在云南拍摄了数量庞大的影像资料。⑥参见约瑟夫. 洛克(Joseph F. Rock):《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Jim Goodman,Joseph F.Rock and His Shangri-La,Caravan Press,2006;北京意大利文化处、意大利当代中国高级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博物馆主办:《他乡雪山——云南三江流域老照片展》,2011 年3 月;乐维思(R. Alison Lewis):《1900 -1950 年的云南影像文献:英国传教士和旅行家记录中的地方和人》,郭净主编:《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手册》,96 ~98 页;艾伦. 拉森、比尔·迪柏:《飞虎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 -1945)》,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 年;章东磐编:《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抗战时期,东部的大城市多为日军占领,大批文人、学校和文化机构西迁入滇,使昆明成了大后方的文化艺术重镇,照相和电影事业随之发达。子雄摄影室的美国照相机、电影摄影机、放映机和柯达胶卷从香港经滇越铁路转运到昆明,电影院放映的好莱坞影片拷贝则直接用飞机从印度运来。杨光海和学徒们不但时常到南屏电影院看故事片,他们的老板还拍起了电影。1944 ~1948 年,郭子雄购置了箱式摄影机,拍摄了《市运动会盛况》、 《一二一学生运动》、《双十运动会和童子军表演》等9部纪录片,均属于资料性的,未公开放映。1950年,他还拍过解放军进昆明的入城仪式,其影像资料被许多影片采用。①谢德明:《万千宠爱集一身:云南电影粉墨登场》,《民族艺术研究》2007 年1 期。
杨光海说他在子雄摄影室的二楼看过自己老板拍的纪录片:
我们放映就在摄影场,有个小型放映机,16毫米的,很小啊,我们有个小银幕,活动的,布一拉开,就在银幕上放。自己放给自己看,也有别人来看,老板经常组织跳舞晚会,来的人在那里玩,跳舞。没有音乐,就用留声机,放着唱片上的音乐。他也拍过昆明1945 年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游行。我是1947 年到子雄的,但我看过那个片子。在子雄二楼的摄影场,挂个银幕,很大的,面积不小呢,很多人可以坐,一两百人都没有问题。子雄是很阔气的。学生也来看过。在抗战胜利堂广场也拍过一个学生跳舞的,“美丽的小鸟,飞去不回来”。学生来看过,无声电影,没办法录音的。拍了印成拷贝,一段一段剪接起来。那是昆明最早的电影的开始了。②参见郭净:《云南,藏地和纪录影像——杨光海访谈录》,《民族艺术》2014 年1 期。
除了杨光海先生以外,担任民纪片《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渔猎生活》摄影师和导演的杨俊雄先生,早年也曾在湖南靖州县内一家照相馆当了3 年学徒,学会了照相技术。1950 年参军,在部队当了多年摄影记者,之后才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拍摄工作。③王珍:《杨俊雄访谈》,载徐何珊、谢春波、郭净、陈湘、王珍:《中国民族志电影口述史》。他们俩人,尤其是杨光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民国影像与民纪片之间的联系:
郭子雄很有野心,想在昆明建一个电影制片厂,但1950 年2 月昆明解放,他的梦想破灭。而在子雄工作室当学徒的杨光海被新生活吸引,报名参军,继而被命运引导着,于1952 年从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航测大队转行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这当然跟他在子雄摄影室学的手艺有关。结果,老板没圆的梦,最终由徒弟来完成了。杨光海先生于1957 年参加《佤族》的纪录片拍摄,之后成为中国民族志电影最重要的先行者之一。他个人的经历,在民国云南电影业( 子雄摄影室) 和解放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 简称“民纪片”) 之间,连起了一条细微却不可或缺的线条。没有在子雄摄影室培养起来的对影像的爱好以及精湛的摄影技巧,杨光海不可能加入民纪片的拍摄队伍; 而没有这样一位终生坚持民纪片拍摄的先行者,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命运则必然有所不同。个人和历史就是如此相互缠绕着,结下了缘分。④郭净、徐菡、徐何珊编著:《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438 页。
其二,边疆考察的影像纪录
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建立初期,就有学者开始运用影像工具辅助田野调查。1928 年杨成志到云南考察少数民族,1930 年发表《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 (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11 集)附有若干照片。⑤蔡家麒:《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记杨成志先生滇川调查之行》,蔡家麒:《田野拾遗——文化人类学随笔》,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232 页。1937 年杨成志率江应樑到海南岛考察黎族,还请来广州三星电影社的邝光林拍摄照片和电影资料。⑥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177 ~178 页。而供职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则是把影像民族志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加以运用的第一位中国民族学家。1933年,他和芮逸夫到湘西南做苗族和瑶族调查,带上了技术员勇士衡,让他专门负责照相、拍电影。当地民族代表怀疑他们的动机,上书蒙藏委员会指责其“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图”。凌纯声的辩解则称:⑦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80 页。
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显。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
凌纯声的所行所言,是中国民族学家完整运用影像手段的开始,也是他们关于影像民族志最早的表述。之后每次外出从事田野工作,凌纯声都要带上技术员勇士衡,如1934 年他和芮逸夫到浙江调查畲族时,勇士衡随行拍摄了一组畲民的照片,今天还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①周率:《畲民旧影寻踪》,《丽水日报》,2011 年11 月12 日“文史版”。1934 ~1936 年凌纯声、陶云逵到云南考察傣族、纳西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佤族,亦有赵至诚、勇士衡两位技术员带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同行。②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81 页。曾跟随杨成志调查的中山大学研究生江应樑,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影像的重要性,20 世纪30 年代他从事云南傣族的实地研究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③江应樑摄影,江晓林撰文:《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关于德宏地区20 世纪30 年代的老照片和老故事》,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 年。彼时,其他社会学、民族学家亦多借助影像辅助田野调查和人体测量,收集了许多图像资料,大多发表在学术刊物或作为资料收藏,少数发表在流行刊物上。
20 世纪30 ~40 年代,由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事业的感召,以及救亡图存这一理念的刺激,加上社会学-民族学的影响,边疆考察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在那个时期,民族学和社会学者拍摄照片已不是个别现象。据台湾学者王鹏惠对该专题所作的研究,当时有许多学者、记者、作家、探险爱好者乃至旅行团出发前往西南地区,拍回大量影像资料,在内地各种专业和非专业的报刊上发表,如褚民谊《湘桂边境苗女之服装》(《旅行杂志》1937年11 月)、《抗战中的苗民》(《申报》1939 年11月12 日)和《贵州苗民》(《申报图画特刊》1937年5 月);李霖灿《黔滇道上》 (香港《大公报》1939 年9 月)、《贵州的苗民》(《东方画刊》1939年2 期);萧乾、邝光林关于滇缅公路修筑的《从昆明到仰光》(《良友》1939 年)、《滇缅公路上之新动态》 (《良友》1940 年);朱契《倮罗群像——乐西公路途中见闻之—》(《旅行杂志》1946年)等。这一时期的《良友》、《中央日报》、《文汇报》、《申报》、《民俗》、《东方杂志》都刊登过此类照片,有的甚至整版登载,以吸引读者。④参见王鹏惠:《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影像:从三条公路上的民族影像谈起》,在“重现的边疆:2010 人类学社会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上的发言,2010 年4 月23 日。近年被摄影界和学者们重新发掘出土的庄学本和孙明经的作品及故事,是民国边疆影像考察的两个典型案例。⑤参见孙明经摄影,孙建三撰述:《定格西康——科考摄影家镜头里的抗战后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孙明经:《孙明经手记——抗战初期西南诸省民生写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1 年;马鼎辉等主编:《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 世纪30 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年;庄学本著/摄,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庄学本全集》,中华书局,2009 年。庄学本来自南京的照相行业,孙明经则是南京金陵大学的专职电影教师。他们分别从照相和科学研究两个方向进入西部民族考察的领域,和社会学-民族学的影像调查汇合成一股潮流。在此还必须提及一个重要的电影人郑君里,⑥郑君里(1911 -1969),男,著名电影演员和导演。他于1939年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委派,带着摄影和放映队到西北宣传抗日,并筹拍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1939 ~1941 年间,郑君里的团队在宁夏、内蒙、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用美国的埃姆牌摄影机拍摄了回族、蒙古族、藏族、土族的生活、宗教仪式、歌舞,并反映了西南彝族、苗族支援抗战的场景。⑦《民族万岁》的拍摄经过详见郑君里:《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 -1940》,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 年。电影研究者单万里认为,这部长达90 分钟的纪录片具有浓厚的人类学电影色彩。⑧参见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第三章,第五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年。该片抗战期间曾在重庆等地公映,之后便消失了踪迹。直到2005 年,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才从台湾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得到拷贝,并复制一份DVD,捐赠给了中国电影博物馆。⑨俞亮鑫:《民族万岁重见天日》,《新民晚报》,2005 年9 月1 日。
民国时期的西部边疆考察,在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已呈现出重视影像工具的趋势;而1950 ~1960 年的民族大调查,则对影像的运用有了全盘规划。这前后两种影像考察的理论基础虽然存在本质的差异,但其中延续的脉络依然有待我们去探寻。指导民族大调查的学者,有些在民国时期就接触过影像工具,如1935 年,费孝通和妻子在广西考察时,曾拍过瑶族的照片。1954 年和1956 ~1957 年,费孝通到内蒙草原和江村考察,都曾带上他的弟子、《新观察》的摄影记者张祖道同行,让他专门拍摄照片。①张祖道:《江村记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年,第9 页,114 页。1957 年民族大调查启动之际,费孝通是主要的指导者之一。他和其他参与策划的民族学家有可能推动了民纪片摄制的立项和实施。而林耀华则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且担任主要的审片人,杨光海拍摄的影片就曾接受过他的审查和指导。
三、中共革命电影传统对民族调查的影响
20 世纪50 年代民族大调查伊始,国家高层领导便支持和倡导在民族调查中运用电影的手段,这其实并非突发奇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革命文艺乃至电影的重视,是有悠久传统的。1931 ~1936 年,中共就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电影运动”。1938 年,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电影团,下辖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从1939 到1940 年,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延安第一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工业展览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 (《南泥湾》)等纪录片。1945 年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的先遣小组赴东北接管了长春伪“满映”制片厂,于次年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制作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1946 年,在华北军区政治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华北电影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将大部分器材藏在山洞里,而将必要的制作器材装备在一辆大骡车上,用手工业方式完成了一些新闻纪录片。②参见袁牧之:《解放区的电影工作》,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 年3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辑出版,转引自《新影集团网站》http://www. cndfilm. com/20101124/105112. shtm;晓何:《抗战时期的延安电影团》,《党史博览》,2010 年11 期;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边静:《赵伟访谈录》,陈墨:《龚涟访谈录》,陈墨、启之:《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影业春秋:事业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年,24、303 ~305 页。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共队伍中兼具电影和照片拍摄以及放映的摄影队已发展到30 多个分队。③袁牧之:《解放区的电影工作》,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这种做法,与二战中美军摄影部队的设置颇有相似之处。解放后,延安电影团的骨干如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等,都成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者。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在放映队的普及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939 年秋,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一部35 毫米移动式放映机和一些苏联故事片,由此成立了隶属于总政宣传部的电影放映队,后该放映队并入延安电影团。1943 年2 月4 日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王家坪军委礼堂举行首映式,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举行自拍纪录片的放映活动。④晓何:《抗战时期的延安电影团》,《党史博览》2010 年11 期。解放前后,电影摄制和放映逐渐成为军队文艺宣传的重要内容。杨光海在访谈时提到,他1952 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纪录片《战胜怒江天险》,该片完成后就拿到进藏部队中放映。1954 年,他又参与拍摄彩色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片子都涉及少数民族题材,而杨光海也以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拍摄过程。1954 年底,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杨光海随着修路部队到了拉萨。那时,各个部队的放映队都赶到拉萨参加庆典活动,他还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看了一场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建国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布局建立电影工业基地,其中就有为部队配备电影放映设备的考虑。
在战争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电影制作和放映传统,也延伸到了建国后的民族调查中。1950 年至1951 年,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到云南访问,该团配备了医疗队、文工队、展览组、放映队和摄影及电影组。⑤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第4 页。访问期间,在路南县圭山西山区,访问团拍摄了八百余尺新闻纪录片,一百多张照片;⑥夏康农、张冲、王连芳:《在圭山西山区的工作简报之一》,云南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第286 页。在丽江地区,访问团为四万观众举办展览四天,文艺演出五次,演电影六次,还拍照片三百张,电影胶片七百尺。①夏康农、张冲、王连芳:《丽江专区两周工作简报》,云南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第292 页。访问团在丽江举行民族代表会议,为300 多位代表举行了文艺晚会、放电影和办展览等活动。②夏康农、张冲、王连芳:《在丽江专区民族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云南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C,第294 页。1950 年8 月29 日,访问团在圭山的联欢会还出了一个有趣的意外:
这次到圭山访问,因为组织不够严密,刚一到就参加五万人大会,超过预计。群众对电影最感兴趣,有从二百里外来看电影,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由于我们没有带电影( 因为秘书处对放映队没有交涉好) 使他们感到不快,已决定将来设法放映。③夏康农、张冲、王连芳:《在圭山西山区的工作简报之一》,云南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第286 页。
可见,早在建国初期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电影就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和记录手段。据徐志远的日记,1956 年11 月他参加调查组到云南佤族聚居的西盟地区调查,当地的西盟工委有一个放映队,部队有两个放映队,他在工委驻地看过露天放映的《天仙配》,另一次放映《山间铃响马帮来》,他没有赶上。④徐志远:《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 -1957)》,第9、40 页。1957 年,中央领导部署在全国民族调查中加进纪录片摄制内容的时候,以中央电影局和几大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组成的国家层面的电影战略已然成型,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影片摄制就是这个战略布局中的一个棋子。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1954 年制定的规划中,就列有反映少数民族状况的摄制要求。这些制片厂后来大多承担过民纪片的摄制任务,如八一厂、科影厂、新影厂等,而一些地方的电影机构如云南、新疆等省区的电影制片厂也给予配合,新疆电影制片厂甚至在1960 年还单独拍摄了《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一片。
当我们把民纪片放到历史的河流中观察时,它就不再是一个横空出世,遗世独立的现象,它自有其前因和后果。往前,它与民国时期的电影以及社会学-民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后,它启迪了1980 年代以降蓬勃兴起的新民族志电影。本文仅对这一线索作了初步的梳理,而一些关键的部分,如民纪片为何人提出,老一辈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前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界对中国纪录片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尚有待考察。尤其是对民国以来边疆影像考察资料的整理,还需要取得新的突破。本文就民纪片几个来源的探讨,也只是对其整体研究的起步而已。文中浅陋错谬之处,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