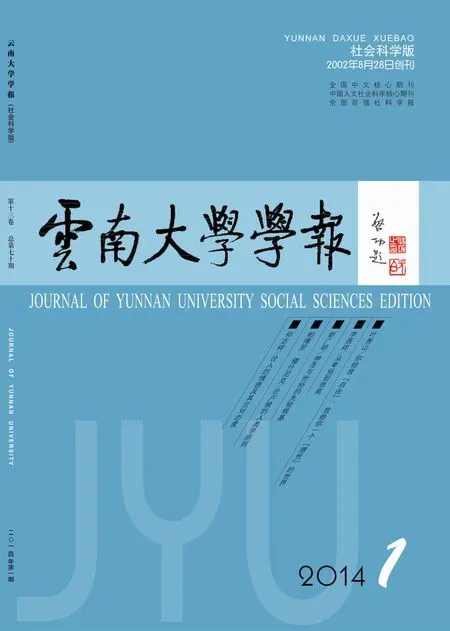斯宾诺莎与霍布斯自然法权学说之比较*
黄启祥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受到霍布斯的影响,这是许多学者都认同的。例如,以研究斯宾诺莎和霍布斯著称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曾说:“霍布斯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宾诺莎的老师”。[1](P273)罗素认为:“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基本上与霍布斯一脉相承”。[2](P570)他们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不仅因为斯宾诺莎的书架上就有霍布斯的著作,而且他们的政治哲学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都采用自然状态假说,都从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概念开始政治哲学的叙述,他们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也很类似,而且都主张社会契约论。难怪埃德温·柯利为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亲和性感到着迷。[3](P85)但是,他们在论述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之后,进而阐述国家政体时,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霍布斯认为,法律应是君主一人理性的体现,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而斯宾诺莎则认为法律应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理性的体现,他赞同共和政体。如何解释他们在自然法权学说上的观点分合,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在讨论他们观点分合交错的过程中呈现其各自学说的隐秘走向。笔者认为,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理性运用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这就使他们为超脱自然状态提出了不同的依据,从而使得他们在权利转让方面见解不同,在政体问题上立场迥异。
一、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含义
西方近代自然法权理论的建构往往从自然状态开始,而自然状态的含义是通过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来规定的。不同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与霍布斯赋予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自然法权理论的各自形态和特征。
关于“自然权利”,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一书中说,“即据以产生万物的自然法则或自然律,也就是自然力量本身”。[4](P683)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是:“自然的权利和法则,我只是指支配每一个体事物本性的律令,每一事物都天然地以一定方式为这些律令所决定而存在和行动”。[4](P526)简言之,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然权利即产生或支配每一事物的自然法则。
斯宾诺莎把自然权利等同于自然法则。而在霍布斯看来应当把它们区分开来,他说:“权利是做或者不做的自由,而法则决定并约束人们采取其中之一。所以法则与权利的区别就像义务与自由的区别一样,两者在同一事物中是不一致的”。[5](P86-87)霍布斯把自然权利定义为“每个人依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生命力即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而“自然法则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这种诫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并禁止人们不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5](P86)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在是否保全自己生命的问题上,人没有自由,无可选择,他必须尽力去做最有利于保全生命的事情,不能去做损害自己生命的事情或者剥夺维护自己生命的手段。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但是,对于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在如何服从自然法则方面,人是有自由的,人可以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保全生命。
霍布斯的这个区分反映了他与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权学说在起点上的不同。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人的权利,而自然法则是从外部所加于人的法则,人在自然法则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尽管斯宾诺莎也认为自然的最高法则是每一事物都因其本性而尽其所能地保持其存在,但是他所说的自然权利首先是指自然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然只是由于其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和运行的,[6](P439)自然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本身,而自然的法则也不是外在的,而是来自于自然的必然性。自然的权利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然不服从任何外在的法则,在自然之外也不存在任何约束自然的法则。由此,霍布斯关于权利与法则的区分就自然本身而言是不适用的。
霍布斯把自然法看成只适用于人的法则,把自然权利看成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了自然中的主要关系。虽然霍布斯也说过自然法无疑是神的法,[5](P206)而神是“所有人和所有生物的王”,[5](P449)但从他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则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围绕着人或者以人为中心来界说它们的,他并不认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涵盖人以外的其他事物,因为只有人具有理性,而自然权利是通过理性的运用来行使的,自然法也是理性所发现的。与之不同,斯宾诺莎的自然法理论的出发点不是人,而是自然。在斯宾诺莎那里,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他说:“人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关于人的心灵,我认为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7](P144)实际上,他认为人在自然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自然法并不以人的诉求为依据,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起点和基础,它所适用的对象不仅是人类,而且是自然中的每一事物。
这个起点上的不同导致了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在自然法权学说上的另一个重要差别。霍布斯把自然权利看成人的理性的权利,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5](P87)行使自然权利就是按照理性行事。自然权利作为自由也就是理性的完全自由。斯宾诺莎虽然与霍布斯一样承认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但是他认为自然权利绝非理性自由运用的权利,相反,它意味着理性的阻碍。
根据斯宾诺莎,自然权利首先指的是自然的权利。神即自然,自然的权利就是神的权利,而神具有做一切事情的至高权利,所以,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自然拥有绝对权利做其力量之内的任何事情,也就是说,自然的权利与其力量一样大。其次,自然权利指自然中每一事物的权利。因为自然的全部力量也就是所有个体的力量之总和,而自然的权利也就是所有个体的权利之总和,因此,它们的自然权利都与其力量一样大。由于每一事物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神的力量,它们的自然权利来自于自然的至高权利,因此,每一个体都有至高权利做其力量范围之内的任何事情。一个事物按自己的力量行动就是按最高的自然权利即自然法则行动。
斯宾诺莎把自然状态下的权利等同于力量。这里所说的力量并非专指人的理性的力量,也包括欲望等各种冲动的力量,还包括人以外的其他各种事物的力量,所以在斯宾诺莎看来,就自然权利而言,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事物并无不同,具有理性的人和不知理性的人也没有什么差别。一个只在自然法则支配下生活的人,如果他既不知道理性命令,也不具有道德品质,而只根据欲望法则来生活,那么他所拥有的权利与依照理性命令而生活的人是一样的。“就像智者有至高权利去做理性所命令的任何事情或者依照理性法则去生活一样,愚人和无知者也有至高权利做欲望所要求的任何事情或者依照欲望法则去生活”。[4](P527)由于自然的最高法则是每一事物都尽其所能地保持其存在,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无论一个人是为理性所支配而保持其存在还是为欲望所驱使而保持其存在,他都是在依照自然法则行事。
虽然自然状态下人的理性和欲望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是斯宾诺莎进一步认为,“较之受理性的指导,人们更多地受盲目欲望的驱使”,[8](P11)因为并不是所有人生来就被决定依照理性法则而行动;相反,人是生而无知的,即使受到良好的教养,在其认识到真正的生活原则和具有道德品质之前,生命的许多时光也已经过去了。这期间,他们必定也在生活,并尽其所能地保持自身的存在,即只在欲望的推动下保持自身的存在,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自然并没有给予他们别的东西,并没有给予他们依照健全理性而生活的现实力量。所以,“他们必定不能依照健全心灵的法则而生活,这就像一个猫必定不能依照狮子本性的法则而生活一样”。[4](P527)此外,即使理性具有和欲望同样的权利,也会发生欲望排斥理性的状况,因为在他人根本不按照理性行事而为所欲为的环境中,一个奉行道德原则的人等于自取灭亡。
虽然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就自然状态下人是否受理性支配这一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由各自的观点出发所演绎出的自然状态却非常相似。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保全生命,抵抗敌人。“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对每一事物都拥有权利,甚至对彼此的身体也是如此。”“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5](P87)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不论如何强壮和聪明,都难以保障过完自己的自然寿命。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性死亡的恐惧与危险之中,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5](P84)同样,在斯宾诺莎看来:“一个只受自然律支配的人,他认为对他有益的——无论他是在健全理性的指导下还是在情感的推动下做出的这个判断,根据至高的自然权利,他都可以以任何方式,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欺骗还是恳求还是任何其他方式,去争取和获得这个东西。因此,凡是阻碍他达其目的者,他都可以把他视之为敌人”。[4](P527-528)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欲望的驱使下做任何事情,像争斗、怨恨、愤怒、欺骗,甚至把他人作为敌人而杀死。
尽管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悲惨境况的描述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为之做出的归因却又大不相同。根据斯宾诺莎,自然法则是支配每一事物的法则,自然权利并不专以人的保存和利益为目的。一个人的死亡与一匹马的死亡,对自然而言都是一样的。自然并不排除伤害人或者让人自相毁灭的状况。因此,自然并不限制使人们相互敌视的欲望,也不赋予使人们追求真正利益的理性以任何特权。斯宾诺莎以自然权利的非理性特征,以及欲望排斥理性的必然性,解释了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存的危机状况。
如果我们承认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充分使用理性的自由,那么我们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类恶劣的生存状况的原因就要给出与斯宾诺莎不同的解释,即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是每个人的理性行为的结果。霍布斯正是这样说的: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5](P87)既然每个人的行为都受理性指导,理性何以会让人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
遵从理性的指导,在斯宾诺莎那里意味着追求对人真正有益的东西。真正对人有益的东西不是只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所有人都有益。也只有对所有人都有益,才真正地对自己有益。这是斯宾诺莎的一贯观点。而霍布斯所说的按理性行事似乎只在为行为的当事人谋利益,这种理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是个人及其保全。所以,人类的悲惨境遇在斯宾诺莎看来是因为理性受到排斥,而在霍布斯那里则正是因为理性的自由运用。
进一步的考察发现,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下人人相互为战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表述,这就是人的天性,“在人类天性中,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有三种: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5](P83)竞争使人为了求利而进行侵犯,猜疑使人为了求安全而进行侵犯,荣誉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人的这些天性使人们相互离异和相互摧毁,所以霍布斯又说人人相互为战的恶劣状况完全是人的天性造成的。霍布斯所说的这些天性实际上是人的恶劣的自然欲望。由此,我们可以说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也存在着两个人性要素,一个是自然欲望,一个是自然理性。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这两个要素的作用的表述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仔细分析就会看到,他实际上把他所谓的人的天性即自然欲望看成对他人进行侵犯的原因,而把自然权利即自然理性看成自我保全的条件,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意味着人人都利用能够得到的一切手段“抵抗敌人,保全生命”。[5](P87)但是,毫无理性的侵犯和不择手段的自卫都会造成人人相互为战的状况。也许这样理解,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状况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如果是这样,欲望的权利从何而来呢?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欲望的权利来自自然的最高法则,自然权利就包括欲望的权利,它是自然法则赋予的。而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欲望的权利并不来自于自然法则。他所说的自然权利不是自然欲望的权利,而是理性的权利。那么自然欲望的权利来自何处呢?它有什么权利在自然中为所欲为?透过霍布斯的文本,我们发现他是将自然欲望的权利诉诸人的自然能力的平等,“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5](P81)“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5](P82)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西方近代的自然法观点与传统的自然法观点(如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之间的原则区别在于:“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与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约束性次序。而近代的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或倾向于是起源于人类意志的一系列‘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9]根据施特劳斯的这个区分,作为近代自然法理论代表之一的斯宾诺莎的自然法学说似乎不属于近代的范围,他显然把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法学说看成了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典型形态。
二、自然状态的悖论与超脱条件
作为斯宾诺莎与霍布斯自然法权学说的出发点,人人平等又相互为战的自然状态是他们的纯粹想象,还是人类的一种真实生活写照?有人认为:“历史科学否认了: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资产阶级所描绘的那种‘自然状态’存在。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揭示了:在未来,也不会有那种状态的生活”。[10](P7)近代西方的一些哲学家认同自然状态,但是他们对自然状态的阐述却不同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孟德斯鸠说:“霍布斯认为,人类最初的愿望是互相征服,这是不合理的”。[11](P4)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软弱、怯懦和自卑,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爱慕。洛克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自然状态,他说:“全世界的独立政府的一切统治者和君主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不论过去或将来,世界上都不会没有一些处在那种状态中的人”。[10](P11)但是,洛克认为人类基于自然的平等是人类互爱义务的基础,他从人的自然平等首先引申出的是对他人义务的平等,而不是像霍布斯那样首先是人对一切事物的占有权利的平等。因此,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人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对他人义务下的自由。“虽然这是自由的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除非有一种比单纯地保存它来得更高贵的用处要求将它毁灭”。[10](P6)而卢梭在论及自然状态时则说:“人类生存于原始独立状态的时候,彼此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经常性的关系足以构成和平状态或者战争状态;构成战争的,乃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所以,私人战争,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不能存在于根本还没有出现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之中”。[12](P13)
从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著作来看,一方面他们都肯定自然状态在人类历史中的现实存在,不认为它只是对动物世界的拟人化,或者将人类投射到动物世界之中,来探讨那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自然状态不只是指人类进入文明以前的时期,也包括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后的某些阶段,比如,无政府的内乱时期。霍布斯在这方面有具体的论述:“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时代和这种战争状态从未存在过,我也相信决不是整个世界普遍发生过这种状况,但有许多地方的人现在却是这样生活的。因为美洲有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除了小家族式的管理方式,根本没有政府,而小家族中的协调又完全取决于自然欲望,他们今天还生活在那种野蛮状态之中。…… 我们从这种事实——即原先在一个和平政府之下生活的人们往往会在一次内战中堕落到何种生活方式——也可以看出,在没有共同权力使人畏惧的地方,会存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5](P85)斯宾诺莎虽然没有明确地做出这样的表述,但他在描述希伯莱人建立国家的情形时非常明白地显示了这一观点。他说希伯莱人在逃出埃及后,又处于自然状态之中了。[4](P539)就是说,在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并不意味着一个无理性、无知识的蒙昧状态,而意味着不受任何共同权力约束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斯宾诺莎和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状态景象。实际上,国家之间的状况直到今天仍然类似于自然状态。
如果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能够成立,那么这种自然状态就显示出自身的悖论。根据霍布斯,自然权利使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想好的方式做任何事情的自由,结果却是人人都不自由。自然既给了人这样一个权利,又使人无法实现这个权利。根据斯宾诺莎,自然的最高法则是每一事物都尽其所能地保持其存在,但是这一法则在自然状态中的通行却使每个人都难以生存。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呢?
在霍布斯看来,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欲望和其他激情并没有罪。在人们不知道有法律禁止以前,从这些激情中产生的行为也同样是无辜的;法律的禁止在法律没有制定以前他们是无法知道的,而法律的制定在他们同意推定制订者前也是不可能的”。[5](P84-85)他还说在人人相互为战的情况下,“是与非以及正义与不义的观念都不可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义。暴力与欺诈是战争中的两种主要美德”。[5](P85)
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见解是近似的。依照斯宾诺莎的观点,这个悖论只有在人看来才是悖论,也就是说,只有把人的生存看成整个自然的目的,而自然律的结果与这一目的相矛盾时,才会成为悖论,但是,普遍的自然律并不是只为了人的生存,从整个自然来看,人类的上述命运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就像自然状态中的动物,自然中发生的一切即使对它们不利,甚至使它们灭绝,也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自然状态中人的命运与它们是一样的。斯宾诺莎认为,就自然本身而言,这种状态既非罪也非恶,因为自然事物本身没有善恶,“善与恶不存在于自然之中”。[6](P93)
尽管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存危机的描述非常相似,对于自然状态非善非恶的论述也很相近,但是他们对自然状态非善非恶的解释却又不同。在霍布斯看来,只有法才能衡量出善恶,自然状态中之所以没有善恶是因为没有法。罗素认为这也是斯宾诺莎所持的观点,他说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什么‘对’或‘错’,因为所谓‘错’便是违反法”。[12](P570)罗素显然没有注意到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在这点上的重要区别。首先,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然状态中的行为之所以无所谓善恶,不是因为没有法,而是因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是自然法。自然的权利和命令,人生而受其支配,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其支配下生活。正是由于这条永恒律令的必然性,所有的人都被决定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和行动。而自然法允许每个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而采取一切手段,并不禁止人们按照欲望去生活,并不禁止争斗、怨恨、愤怒、欺骗,或者欲望所要求的任何东西。所以就自然而言,所有这些都不是罪或恶。其次,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并非只有公民社会的法律才能判断善恶,理性法则也是(并且是最初的)衡量善恶的准绳,但是“自然并不为人的理性法则——其目的只是人的真正利益和保存——所制约,而是为无数的其他法则所支配,这些法则与整个自然的永恒律令相关联,而人只是这自然的一小部分。”“因此,如果自然中的任何事物在我们看来似乎荒谬可笑或者邪恶,那是因为我们只是部分地认识自然中的事物,不知道整个自然的次序和联系,而又想要一切事物都受我们的理性指导。理性认为是邪恶的,就自然整体的次序和法则来看并不是恶,而只是就我们的本性的法则来看才是恶”。[4](P528)
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尽管自然状态中人的生活对自然来说无所谓善恶,但是在人的理性看来确是悲惨而又邪恶的。理性对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性质界定是人摆脱自然状态的前提。同时理性也让人认识到,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是由于欲望的为所欲为造成的,要摆脱自然状态就要约束欲望的权利。也就是说,超越自然状态所需要的条件已在自然状态之中。理性不仅让人认识到自然状态是一种需要摆脱的状态以及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摆脱自然状态的道路,这就是依照理性的法则和命令而生活,从而人人都享有和平与安全,都免于生活在敌意、仇恨、愤怒和欺骗之中,都不为恐惧所扰,因为理性法则的目的只是人的真正利益和保存。
但是只要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只要给予理性的权利和给予欲望的权利同样多,理性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的唯一指导,就不可能有安全和平的生活。因此人们必须赞同对每个人都有益的目标,将每个人根据自然所拥有的对所有事物的权利变为共同拥有,不再根据每个人的暴力和欲望而是根据所有人的理性和意志来决定和运用这种权利。然而,只要人们服从欲望的驱使,这个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每个人的欲望各不相同,不同的欲望将每个人拽向不同的方向。因此人们必须找到一种约束欲望的手段,这就是签订契约,“只根据理性的命令来管理每一事务(没有人胆敢公开反对,因为那样显然会被认为愚笨无知):如果欲望驱使他们去做对别人有害的事情,就克制这些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像捍卫自己的权利一样捍卫别人的权利”。[4](P528)毫无疑问,霍布斯也认为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前提是理性,因为在他看来通过契约转让权利是以订约双方都具有理性为基础的,契约必定是在具有理性的人中间订立的。野兽不能通过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人和野兽也不能订立契约,这都是因为野兽没有理性。另一方面,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们的悲惨命运虽然是由人的恶劣的自然欲望引起的,但是人的理性是充分地、自由地参与其中的,这就说明自然理性的运用尽管不是人们生存危机的根源,但它自身也不可能终结自然状态。要超脱这种状态就一定不能单靠理性,相反,必定要限制理性。由此,霍布斯认为脱离自然状态依靠两个条件:“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5](P86)在这个意义上,契约就不只是理性法则的实现,也是个人激情或欲望的实现。
至此,我们看到霍布斯实际上认为人有两种自然欲望:一种倾向于让人相互离异,相互争斗和相互侵犯;另一种让人畏惧死亡,避免死亡,倾向于和平。前一种欲望造成自然状态中人人相互为战的处境,后一种欲望则使人力图摆脱这种处境。而理性也有两种运用:一种是在不能得到和平时,寻求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卫自己;另一种运用是为因为了实现和平,“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条件……也称为自然律”,[5](P86)超越自然状态就要取消或约束第一种欲望以及理性的第一种运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非常接近,但是由于他们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使得他们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存危机的归因不同,由此所提出的摆脱自然状态的依据也彼此相异。
三、权利转让的限度
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在超脱自然状态方面都主张走社会契约的道路,都认为社会契约需要一个共同的强制力量;而且,他们都从同一个人性法则为这样一个强制力量进行论证。这个法则,用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无人不追求他认为好的东西,除非他希望获得更好的东西或者害怕一个更大的伤害;无人会屈从任何恶,除非为了避免一个更大的恶或者希望获得一个更大的善”。[4](P528-529)也就是两善相权取其大,两恶相权取其小。斯宾诺莎把这样一个原则看成无人不晓、深入人心的永恒真理。霍布斯也认为“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一条真理”。[5](P95)
但是,这一法则既会使人立约,也可能使人毁约。霍布斯认为:“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因为最容易破坏的莫过于人们的言词)而是由于畏惧毁约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P88-89)斯宾诺莎更为具体地进行了论证。他说,根据这一法则,除非害怕一个更大的恶或者希望一个更大的善,否则无人会答应放弃他对一切事物所拥有的权利。人们正是为了更大的善或者避免更大的恶,即为了自己的安全和保存或者为了免于争斗、怨恨、愤怒、欺骗和被杀,人们才愿意订立契约,放弃自己的权利,组成一个团体或国家。但由这同一个法则也必然得出,除非害怕一个更大的恶或者希望一个更大的善,否则无人会信守他的承诺或契约。如果一个人认为违背承诺比信守承诺带给他的利益更大或者危害更小,他必定不再坚守诺言。斯宾诺莎与霍布斯都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裁判官,他有至高权利为自己制定、解释和撤销契约,只要他认为对自己有益。正因为这样,斯宾诺莎说:“如果你不能使违你约的人所受的伤害大于他守约所得的利益,那么要求他永远忠于你是愚蠢的。在国家制度方面必定更是如此。即使人们订立了契约,成立国家,但是由于根据自然权利,每一个人都可以行骗,他遵守契约必定只是希望更大的善或者害怕更大的恶”。[4](P529)因此,这份契约便随时有可能失效,从使而国家随时有可能解体。
那么,怎样订立的契约才能长久有效?怎样建立的国家才不会随时解体?霍布斯说:“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力保障一个人的安全。”[5](P115)在自然状态下,契约订立之后,“如果在双方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并具有强制履行契约的充分权利与力量时,契约就不是无效的。……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就不能约束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由于所有人都彼此平等,而且都自行判断其恐惧失约的心理是否有正当理由,这种强制性权力是不可能设想的”。[5](P93)这也是斯宾诺莎的观点。但是,保障契约的力量或国家的武力来自哪里呢?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自然权利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力量,因此无论是被迫还是出于自愿,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转让多少力量,他就必然交给这个人多少权利。在一个国家中,所有人都把权利转让给国家,国家就拥有了极大的力量,也就拥有了至高的权利。它能够以暴力强制支配每一个人,能够用每一个人都害怕的最大惩罚所引起的恐惧来压制人们,这就使得人们不会轻易背弃与国家订立的契约,从而使国家不会轻易解体。也就是说,只有在订约各方之上有一个共同的能够强制履行契约的权力和力量时,契约才会有效和长久。霍布斯的主张基本上与此相同。
每个人是否将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转让给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斯宾诺莎与卢梭的见解是近似的,而霍布斯的观点则有些类似于格劳秀斯的看法。卢梭认为:“说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12](P11)“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斯宾诺莎说:“没有人能把他的力量,也就是,他的权利转让给另一个人,以至于他不再是一个人”。[4](P536)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自然权利,除了听从统治者的意志之外毫无作为,那么统治者对他施以最凶暴的统治也绝不会受任何惩罚。这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这与转让自然权利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
格劳秀斯认为,为了设立更好的政府和得到更可靠的保护,全体人民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权力转让给一个人或数个人。[13](P63-72)霍布斯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所有人就都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土地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他说:“当一个人认为和平与自卫需要这样做时,他应该自愿(如果别人也愿意)放弃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权利”。[5](P87)而且,霍布斯认为,人们一旦授权就不能反悔,而主权者一旦获得授权,其权力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不可转让的。主权者统治下的人们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即便对于一个暴君,也没有反抗和革命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霍布斯又说有些权利是不能让渡的。
那么,转让出去的是哪些权利?哪些权利不能转让?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看一下权利的构成。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力量就是权利,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权利。什么是力量呢?斯宾诺莎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澄清,但从他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性是力量,欲望也是力量。既然自然状态下造成人们生存危机的是每个人的欲望的权利,那么,人们转让出去的就是根据欲望行事的权利,也就是为所欲为的权利。具体一点说,由于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各自决定善恶,进行报复,又为情感和欲望所驱使,因而造成相互敌对,所以,为了和平相处,安全地生活,人们必须把判断善恶和进行惩罚的权利交给社会来执行。另一方面,既然国民仍然是人,人之为人的东西即理性的力量是不能转让的。人的理性的权利也是不能被剥夺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斯宾诺莎的著作推出,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行使理性的权利,国家是理性发挥其职能的平台。国家不能剥夺人的理性权利。
霍布斯认为,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时总是因为考虑到对方将某种权利回让给他,否则就是因为他希望由此得到某种别的好处。因为这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某种好处。“放弃权利、转让权利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为了使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并且保障他拥有既能保全生命而又不对生命感到厌倦的手段。”“所以,有些权利不论通过言词还是其他方式都不能认为人家已经放弃或转让了。首先,如果有人以暴力攻击一个人,要剥夺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放弃抵抗的权利,因为这样就不能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任何好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伤害、枷锁或监禁”。[5](P89)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让出或放弃自救于死、伤或监禁的权利,因为避免这类事情是放弃任何权利的唯一目的。“因为一个人虽然可以这样订立信约:‘除非我做某件事,否则杀我’,但是他却不能这样订立信约:‘除非我做某件事,否则你来杀我的时候我不抵抗。’因为进行抵抗而死的危险是小害;不进行抵抗就肯定要死,这是大害,人类根据天性会两害相权取其轻”。[5](P94-95)
但是,由于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使人们相互为战的因素既有自然欲望也有自然权利,所以当他说“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时,这句话的含义就不仅包括放弃恶劣的自然欲望的权利,也应该包括他所说的自然权利即自然理性的权利。这是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之间的又一重要差别,它导致了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在政体上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据斯宾诺莎,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每个人的理性的充分运用,法律应是所有人或多数人理性的体现,所以他主张共和制。霍布斯虽然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但是,由于他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人相互为战的状况也是每个人都极力运用自己理性的结果,所以要避免这种状况,一定不能让所有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根据他的观点,权利分散必然导致战争和破坏和平,因此法律不应是所有人的理性而只应是一人理性的体现,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
斯宾诺莎和霍布斯都认为每个人在国家中都有思想自由。斯宾诺莎强调“每个人对于他的思想都拥有不可剥夺之权”,[4](P555)内在的心灵权利即人的情感好恶、人的内在信仰、人的理性思考是不可转让的。霍布斯也明确表示“一个人的信念和内在思维不受命令的控制”,[5](P206)但是在国民是否拥有言论自由以及拥有什么样的言论自由方面,两人的观点又是有差别的。霍布斯并不完全否认国民有言论自由,但他将言论自由限制在法律的界限之内,他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是:“说话的人没有法律限制他以别的方式说话”。[5](P148)他认为主权者有权审定学说和意见,“决定哪些学说和意见有害于和平,哪些有利于和平,决定对人民大众讲话时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程度内应受到信任,以及决定在一切书籍出版前,其中的学说应当由谁来审查等都属于主权范围”。[5](P123)他的理由是,人们的行动来自意见,很好地管理人们的意见就是很好地管理人们的行为。在学说问题上所应尊重的虽然只是真理,但并不排斥为了和平加以管理。和平是最高的目的和尺度,“与和平相冲突的学说就不能成其为真理”。[5](P124)斯宾诺莎也承认言论自由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不可消除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斯宾诺莎认为言论自由不是发泄欲望和情绪的自由,尤其不是发表煽动民众的言论的自由,而是发表理性思想的自由。并且言论自由只是发表言论的自由,而不是行为的自由,即不能运用武力来强行介绍和推行自己的思想。此外,言论自由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它是国家改进的一个基础。所以,斯宾诺莎认为,每一个国民都应拥有不可转让的言论自由权利。他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一再强调,在共和国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国家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它们绝不会危及虔诚与国家的和平,而且只要虔诚与共和国的和平不被摧毁,它们也不可能被取消。[14](P3,P7)
综上所述,斯宾诺莎与霍布斯都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支配人的自然法则是尽其所能保持自己的存在。但是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然法则是自然中每一事物的法则,不止是人的法则;保持人存在的自然权利是人的自然力量,这力量不仅包括理性的力量,也包括欲望的力量;根据自然法则,欲望和理性有同样的权利,而且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实际上不是由健全的理性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欲望的力量决定的,这是造成人们生存危机的原因。因此,要超脱自然状态就要限制或取消欲望的权利,而充分行使理性——其目的只是人的真正利益和保存——的权利。为此,需要创造一个理性行使权利的条件,即通过订立契约建立国家。这个条件的实现也要依靠理性,也就是理性自身为自己的充分运用提供条件。既然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国家的成立是为了每个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理性力量,理性权利就是不可转让的,相应地,法律应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的理性的体现,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制。国家不应限制公民的理性权利的使用,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而根据霍布斯的观点,自然法则似乎是为人定制的,人人相互为战的状况是理性充分参与的结果,因此要摆脱自然状态就不是理性自身所能胜任的。由于每个人自由使用理性的状态是人人为战的状态,走出自然状态也就意味着对理性的约束,自然权利的转让就包括交出理性权利。所以法律就不应是所有人的理性的体现,而只应是一个人的理性的体现,最好的国家就不能是民主制而是君主制。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理性要服从和平而不能危及和平,因为和平是判断真理的标准。
参考文献:
[1]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eds.).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M].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72.
[2]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72.
[3]埃德温·柯利.我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A].王承教译.刘小枫,陈少明.阅读的德性[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4]Spinoza. Complete Works[M]. trans. by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5]Hobbes. Leviatha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6]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Vol.1[M].ed. and trans. Edwin Curl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书信集[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斯宾诺莎.政治论[M].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M].trans. by Elsa M. Sinclai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0]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2]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M]. trans. by A.C.Campbell . New York and London: M. Walter Dunne Publisher, 1901.
[14]Spinoza. Theological Political Treatise[M]. trans.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