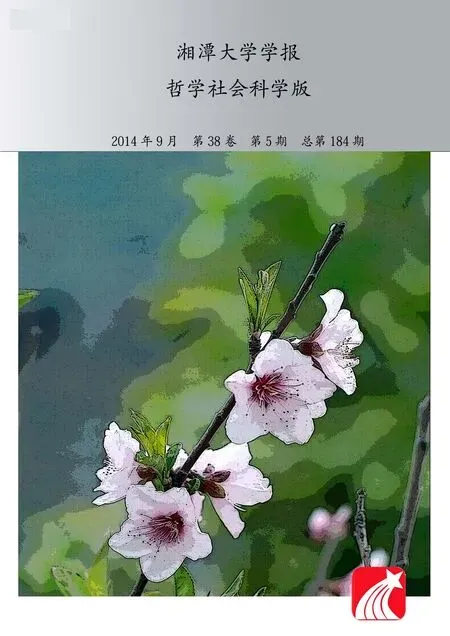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1
荣晓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法律政策研究室, 北京 100726)
一
“无被害人犯罪”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学者埃德温·舒尔1965年出版的《无被害人犯罪》著作中。该书作者首次提出了“无被害人犯罪”即“人们有强烈的需要,主要在成年人之间依自由意志积极交换的行为,如果属于不为社会承认且被法律所禁止买卖的物品或服务,即构成(无被害人犯罪)。”[1]14
在西方国家,“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是从刑法学意义上说的,主要包括在轻罪和违警罪中。而在我国,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界定,要区分不同的论域,分别从刑法学意义上和犯罪学意义上进行界定。在刑法学意义上,“无被害人犯罪”是指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表现为双方自愿或自损,除本人外无直接个人被害人的刑事违法行为。而在犯罪学意义上,“无被害人犯罪”则是指违反伦理道德但社会危害性小,双方自愿或自损,对象涉及违禁品或禁止服务,除本人外无直接个人被害人,除国家外无其他控告人的行为。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内涵比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内涵要丰富,前者强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法益侵害性,后者则彰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的外延则比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的外延要广,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除了包括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外,还包括大量的违反行政法律、行政法规、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
从对不同论域“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内涵、外延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如果我们根据社会治安形势需要,突出强调行为对社会、对国家的社会危害性,使它上升到刑事立法中,它就具有刑事违法性和法益侵害性,从而转化为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而随着犯罪手段、犯罪方式的不断更新,随着犯罪形式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的犯罪行为、对同一种犯罪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中的某些具体的行为也会演变成法益侵害性消失(指对他人个人法益的侵害性消失),直至社会危害性很小的危害行为,这些危害行为经过非犯罪化实践,会从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转化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
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来说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是指:1、行为除了给自己造成损害,没有具体的侵害对象;2、行为虽然也侵害了社会法益,但并没有侵害到他人的个人法益;3、犯罪被害人不包括国家和社会,而仅限于个人被害人;4、犯罪被害人虽然存在间接被害人,但却没有直接个人被害人。无被害人犯罪这四点含义直接决定着前述不同论域“无被害人犯罪”内涵的界定,也决定着无被害人犯罪的具体特征,即发案量大、犯罪黑数大、难以控制、惩罚成本高。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与无被害人犯罪特征相适应的犯罪对策(指刑事政策)。
二
半个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将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如1957年英国《沃尔芬登报告》和1962年《美国模范刑法典》就已经提出将卖淫及通奸罪非犯罪化的主张。从各国刑法的发展看,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呈现出非犯罪化或轻刑化两大趋势,[2]69-70即对无被害人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犯罪化的趋势越来越少,而且,即使在现有刑法中所保留的那些罪名,如赌博、卖淫、吸毒等,其处罚力度也越来越轻。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在一方面将个别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的同时,更多地是在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彰显惩治犯罪的不同刑事政策需要。我们应当深刻反思西方国家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
西方国家对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或轻刑化刑事政策,其理论基础是刑法谦抑性原理,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刑法的补充性来看,“无被害人犯罪”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相抵触,应属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刑法只能调整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并且只有在道德等其他调整方式不奏效的情况下作为补充调整手段适用。对于“无被害人犯罪”这些并非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刑法应该让位于伦理道德来调整,即将其作非犯罪化处理,或者,即使刑法迫不得已进行干预,也只能作轻刑化处理。第二,从刑法的不完整性(即经济性)来看,“无被害人犯罪”所涉及的行为大多是公民的私人生活,属于公民隐私范围的事务。这些行为不仅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必要成为刑法的调整对象,而且行为的秘密性特征很明显,如果以刑法加以惩治,会遇到案件线索来源枯竭、证据难以搜集的实际问题,需要耗尽大量的司法资源,有违刑法经济性原则,故将其非犯罪化不失为一种比较适当的选择。第三,从刑法的宽容性来看,“无被害人犯罪”大多涉及公民自由、权利,且并未伤及他人的权利,刑法对这种行为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和宽容,应当尽可能地尊重个人自由,刑法即使介入其中,对行为的惩罚也应当是比较轻缓的。
西方国家对“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或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有其自身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价值观念基础。首先,西方国家刑法中的犯罪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无被害人犯罪”大多属于轻罪或违警罪,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轻罪和违警罪,在我国,则相当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这样,西方国家刑法中作非犯罪化处理的“无被害人犯罪”行为,就可以变成合法行为,而在我国,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处理,则变成违反行政法律、行政法规的违法行为或者变成悖逆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而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或道德谴责。其次,刑法干预的限度与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刑法具有各自不同的使命,对人们行为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也不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为政治国家所取代,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略或蔑视,刑法对涉及个人自由或权利的事务干预较多,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和上升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形成二元社会结构,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刑法只能调整个人进入政治国家范围内的行为,而不能触及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所以才出现对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或轻刑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刑法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在强调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突出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在对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或轻刑化刑事政策的同时,也从其他方面加强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力度。再次,西方国家强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念,这种尊重个性、不干涉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念在国家立法者和社会民众中根深蒂固。受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西方国家对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或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如,某些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对卖淫行为、赌博行为以及吸食软性毒品行为,逐步实行合法化政策。
三
在我国,我们应当将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与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结合起来,树立大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观”,将“无被害人犯罪”与相关的“有被害人犯罪”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分析治理“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预防对策。
(一)在关联思维中,树立“抓根本问题、打基础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大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观”看来,涉“黄”、涉“赌”、涉“毒”三类无被害人犯罪内部各种具体的无被害人犯罪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着的,另外,有的无被害人犯罪与相关的有被害人犯罪存在着重要联系,因此,要想有效遏制、减少各类“无被害人犯罪”,就应当运用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厘清导致各类无被害人犯罪存在和多发易发的根本问题,搞清楚有关的有被害人犯罪赖以产生和凶猛发展的根本原因,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有效打击基础犯罪。如在涉“黄”无被害人犯罪中,通奸行为是根本问题,相对于卖淫、秘密聚众淫乱、婚前性行为而言,是基础犯罪;在涉“赌”无被害人犯罪中,容留、容忍(他人)赌博行为是根本问题,是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存在和发生的基础原因,是基础犯罪;在涉“毒”无被害人犯罪中,吸毒行为是为自己吸食、注射非法持有毒品罪这一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毒品犯罪和所有刑法学意义上有被害人毒品犯罪的根本问题,是基础犯罪,因此,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就必须抓住通奸、容留、容忍(他人)赌博和吸毒行为,下大气力,狠狠整治,分别将它们归入《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典中,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有效治理。
(二)根据国情和社会治安形势,有所为,有所不为,科学惩治“无被害人犯罪”。就涉“黄”无被害人犯罪而言,在我国建国初,通奸行为是作为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处理的,那时,新生政权刚刚建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为了有效根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现象和混乱的治安形势,维护新社会的社会秩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到了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该部刑法典没有规定通奸为犯罪(指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实际生活中,通奸行为被列入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范围,让社会主义道德调整和谴责,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通奸行为除罪化(指不作为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对待,下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强奸罪的发生,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通奸行为除罪化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包括诱发、引发大量的卖淫、秘密聚众淫乱、婚前性行为,恶化了社会治安秩序,引发家庭不和、家庭暴力甚至情杀案件,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我国应加强对通奸行为的管控。可行的办法是,将通奸行为交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就涉“毒”无被害人犯罪而言,我国对吸毒行为的处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90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首次规定吸毒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单处或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首次将吸毒纳入司法行政机关劳教范围,并规定在劳教中强制戒毒。为了落实强制戒毒的措施,国务院又于1995年1月颁布了《强制戒毒办法》,对强制戒毒的主管机关、强制戒毒对象、戒毒措施及期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2000年3月,公安部颁布了《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对公安机关的强制戒毒工作进行了规定。2003年5月,司法部颁布了《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对属于司法机关的劳教机关的强制戒毒工作进行了规定。2005年8月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吸毒人员的处罚与《关于禁毒的决定》保持一致,即规定处以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2007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禁毒法》,规定吸毒成瘾人员必须配合有关机关检测、进行登记和接受为期三年的社区戒毒。对于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在社区戒毒期间吸毒、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以及经过社区戒毒、强制戒毒后再次吸毒的,公安机关可作出为期二年的强制隔离戒毒。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实际上奠定了我国对吸毒行为的刑事政策思想基础,即,在治病救人的理念上,以自愿戒毒为主,以强制戒毒为辅,以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行政罚款为常见,以司法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为最后手段。这些法律法规对吸毒行为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减弱了社会吸毒人员的毒瘾,但并没有根除吸毒现象,大量的反复的吸毒行为不仅诱发、引发了更多的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引发了许多暴力、侵财犯罪,引发了大量的卖淫行为,形成以贩养吸、以抢养吸、以盗养吸、以卖养吸,而且,现有的社区戒毒、强制戒毒、行政拘留和罚款的治理处罚措施,对吸毒成瘾人员来说,适用效果并不理想,[3]86-89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吸毒行为规定为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运用刑罚手段,治理吸毒,杜绝吸毒,并以此推动对其它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的有效治理。就涉“赌”无被害人犯罪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两种犯罪,其中,赌博罪是公认的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而开设赌场罪虽然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但也没有直接的个人被害人,也不失为一种刑法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在现实生活中,赌博罪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他人开设了赌场为聚众赌博制造了条件(这种情况少见),更多的是由于有人为他人聚众赌博提供秘密场所,或者是居委会、村委会组成人员对社区、邻里公然的赌博行为一味容忍,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容留、容忍他人赌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尽管这种行为也没有直接的个人被害人,因此,要有效制止、减少涉“赌”无被害人犯罪,就应当稳妥处置明知他人聚众赌博却仍然容留、容忍他人赌博的行为,将容留、容忍他人赌博行为归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进行调整,使这种行为成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无被害人犯罪。
(三)充分发挥家庭、社区、学校、单位的积极作用,着重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由于“无被害人犯罪”大多是关涉私人领域的自由、权利的犯罪,它的有效治理需要借助、依托家庭、社区、学校、单位温馨、可以信赖的人文环境的积极参与,需要通过家庭成员、社区工作人员、学校老师、单位领导、同事进行耐心细致的正面思想教育和健康的心理疏导,使犯罪人认识到各种“无被害人犯罪”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或消极作用,自觉建立健康人格,与犯罪行为彻底告别,引导他们自觉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走出不良心理定势和生活习惯的阴影,教育他们热爱劳动、勤奋工作、遵纪守法,通过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的公民。
(四)重视对相关犯罪的综合治理。“无被害人犯罪”中各类犯罪、各种犯罪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无被害人犯罪”与相关的“有被害人犯罪”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有效治理“无被害人犯罪”、提升治理“无被害人犯罪”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就不应当局限于为了治理某种“无被害人犯罪”而进行治理的思维,而应开拓视野,将同类不同种的其他“无被害人犯罪”结合起来,将“无被害人犯罪”与相关联的“有被害人犯罪”结合起来,同步谋划,协同推进,既集中精力依法惩治和有效预防发案率较高的显形犯罪,也重视对各种相关的隐形犯罪的治理,通过惩治和预防“两手”,通过对明处犯罪和暗处犯罪平衡用力,有效遏制和逐渐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五)认真开展“黄赌毒”专项整治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弥补法制环境。“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是涉及“黄赌毒”方面的犯罪,因此,要有效治理“无被害人犯罪”,必须在“长、常”二字上下功夫,通过定期组织开展“黄赌毒”专项整治活动,建立起治理“无被害人犯罪”的长效机制,使治理“无被害人犯罪”工作常态化。通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大力宣传“黄赌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普及有效预防各种“黄赌毒”犯罪的法律常识,逐渐消除滋生、诱发各种“无被害人犯罪”的社会诱因、社会基础和弥补法制漏洞,为公民生产、生活、学习、工作、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通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使每个公民都自觉养成制止“黄赌毒”现象的社会责任,在全社会凝聚起同“黄赌毒”现象作斗争的强大正能量,有效遏制、逐渐减少各种“无被害人犯罪”。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王恩海.无被害人犯罪与未成年人保护[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2).
[2]肖怡.中西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万志鹏,杜雄柏.浅谈我国对吸毒行为刑事政策的应有调整[J].犯罪研究,2011(2).
——许春金先生
——张荆先生
——张荆先生
——张黎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