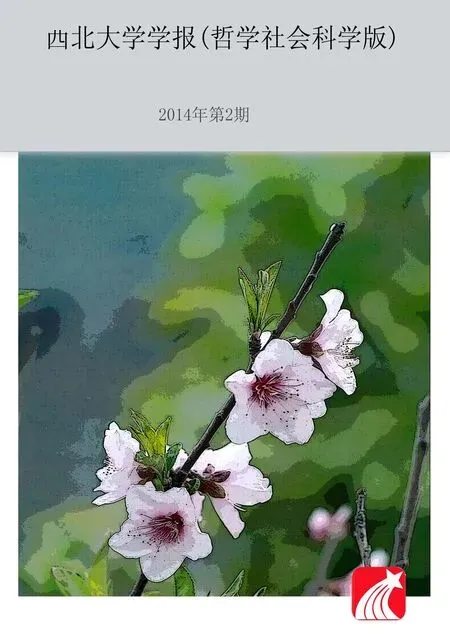政府绩效合同本源性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交易成本分析框架
卓 萍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引 言
政府绩效合同是政府公共管理学科中前沿的研究主题,正如美国学者库珀(Phillip J.Cooper)在其所著的《合同制治理——公共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府被建议精简、放松管制、权力下放、分权、去制度化、重塑、规模恰当和再造,建议从命令控制的运作转向谈判驱动、以激励为基础的过程和绩效评估的运作。不管我们做什么,趋势总是日益从使用权威机制走向协商治理……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加强。所有这些趋势和发展的一个共同点是通过政府机构来行使政府权力的行动转向了通过合同来治理。”[1](P50)美国学者贝恩和康德(Robert D.Behn and Peter A.Kant)甚至将传统政府规制合同向政府绩效合同的转变喻为政府合同管理的新哲学思想(A New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Contracts)[2](P470-489)。所谓政府绩效合同,是指政府与内部组织、社会公众及组织等,通过相互协商签订具有明确相对方应达到绩效标准及类型的协议,并依据该协议评价相对方职责履行的效益与效果,达到优化公共管理和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3](P116-120),它是政府诉求协同治理、绩效发展等价值取向的新型治理形态。但要使政府绩效合同的协同治理宗旨得以实现、绩效合同工具效应得到有效发挥,就有赖于识别政府绩效合同的影响制约因素。国外学者主要从政府绩效合同履约机制[1](P111)、政府绩效合同类型与政府绩效合同目标设定[4]等视角入手,分析了政府绩效合同影响因素及潜在风险,研究结论具有高度聚合性,归纳为绩效合同目标设定、交易期限、评估周期、合同信用、商誉信用、合同监管方式与力度等方面,这一方面反映该研究逐步系统深化,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瓶颈所在,即研究视角多样化与影响因素结论高度聚合性之间的不对称性。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依托于合同治理与政府合同理论框架,较为关注于国外前沿性的绩效合同实践与理论成果[5](P30-37),开始探索性厘清政府绩效合同内涵[6](P7-9),研究主题尚未涉及到政府绩效合同类型、绩效合同评估体系及绩效影响因素等核心领域。
文章的研究对象为政府绩效合同本源性影响因素,其含义是指影响政府绩效合同双方的策略行为、交易成本大小及绩效目标得以实现的本质要素,是诸如交易期限、评估周期、合同信用等外在影响因素的内生性解释变量。文章基于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试图在以下两点进行创新:第一,基于仍处于“襁褓”阶段的国内政府绩效合同研究,文章试图抽离于基于“经济人”假设下对绩效合同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提出了“反思理性的复杂人”是探讨政府绩效合同本源性影响因素的逻辑起点的观点;第二,以期突破过程、类型及运行机制等视角,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框架探讨影响政府绩效合同实现的本源性因素及作用机理。
二、“反思理性的复杂人”:分析政府绩效合同本源性影响因素的逻辑起点
“反思理性的复杂人”是政府绩效合同治理区别于传统政府合同管理的行为假设,是分析政府绩效合同本源性影响因素的逻辑起点。传统政府合同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合同签订的假设前提,具体表现在从其拟定、协商、达成签约直至履行过程当中,基本沿袭了合同法的精神实质,即要求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都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与以理性官僚制为基础并建立在法律原则之上的公共行政体系是相吻合的。因此,政府在与社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签订合同之时,往往诉求于自身算计合同相对方行为后果的能力,权衡自身与其他行为方的利益,估量奖惩的限度。于是,在这种个人理性的对抗型文化所主导下的政府合同,造成了合同双方在订立之初就处于相互对立、相互猜忌、不关心终极目的的氛围之中,相应地也就导致合同方仅仅是抱着完成任务、不折不扣遵守合同规定的态度去执行合同,结果导致政府合同方如社会组织、公众等仅作为法律秩序建构的手段而存在的,政府与合同方之间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这种“经济理性人”的契约思维一方面能使政府合同双方更为关注显性契约,从经济理性角度思考如何规避机会主义、道德、责任等风险;但另一方面虽然正式的防范机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抑制不讲信用的行为,但也可能会激发出一些对付防范措施、更严重的不讲信用的行为和进一步的正式防范机制,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防范措施本身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其结果必然扭曲资源配置[7](P9-16)。
国内学者陈振明在《公共管理学》一书中,将“反思理性的复杂人”作为网络治理的核心特征,其基本含义表述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取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公共利益)的一面,但是由于行为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来实现共同利益。”[8](P84)这与政府绩效合同中平等协商、关注结果导向、战略发展等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反思理性的复杂人”的理性定位同样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分析基础上的,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半强的理性是一致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区分强的、半强的和弱的理性精神是有用的,强理性精神赞同超理性,而半强的和弱的理性则根植于有限理性。半强理性分析使有限理性与有远见的缔约相结合,弱理性分析则把有限理性和短视的缔约结合起来。交易成本理论则是一种半强的理性构造,认为由于有限理性,预料未来所有情况并在合同中进行规定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可能但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成为不可行的选择;但同时又认为在长时间合作和互动过程中,合作双方有能力学习、预见并感知风险,在合同关系中予以考虑,在谈判过程和合同条款中予以反映。因此,置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反思理性的复杂人”的理性就被解释为不完全但又具有远见思维的合约,是处于代理合约理论趋向于自我履约协议理论、关系性合约理论的过渡区间。依循威廉姆森所认为的契约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受到不确定性、实现交易所需要特殊投资的专有程度及交易频率的理论依据,政府绩效合同的实现主要受到合同双方目标不一致性、资产专用性及合同评估目标转换性等本源性因素的影响。
三、双方目标的不一致性制衡政府绩效合同实现
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目标的不一致。交易成本及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政府合同实施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及目标不一致的根本性问题。而逃避问题只会导致合同委托人监控代理人履约绩效及制定正确评估标准的难度。有些学者认为,与具有使命驱动性的组织如非营利性组织或其他政府部门相比,作为政府绩效合同当事人一方的私营部门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9](P275-297)。对于私营部门来说,一个供应链的网络可以组建一个生产汽车或卡车的汽车工业,也可以组建一个生产计算机或路由器的高新技术产业。不论在哪一种行业,价格、及时性和质量等度量标准都相对简单明了,而且其终端产品也很容易确定,如果合作网络中断,通常都能够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尽快予以修复[10](P37)。不同类型的私营部门在履约中虽有不同的营利追求,但实质层面的目标或价值性却是统一的,即通过营利以获得市场的生存和发展权。为此,基于政府与私营部门所签订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合同、政府租赁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等,作为代表政府一方的法人代表就应该认识到二者目标的差异,通过招标、议标、合同谈判、合同实施等环节不断调适二者行为,以减少私营部门签约前和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所付出的决策成本、签约成本、监控成本及实施成本。这也正如劳埃德·伯顿(Burton)所指出的,私营部门谈判者与公共行政人员在价值、先后重点和责任等方面的重要差别意味着谈判桌两边存在着不同的谈判文化[11](P23-40)。这些差别有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会产生伯顿所界定的“会妨碍沟通、谈判以及最终重要问题解决的‘伦理中断’”[1](P69)。也就是说,在政府与私人部门合意难以达成的情形下,绩效合同的协议谈判成本可能就会很高,与决策息息相关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越激烈,即合同商的目标和行为愈渐偏离公共利益的价值轨道,政府绩效合同的签订、实施及目标实现的难度就愈大。
政府与非营利性机构间的目标不一致性。非营利性机构一方面扮演着弥补政府缺陷、市场失灵的角色,成为承接政府部分社会职能最理想的单位,但另一方面其组织形式、组织使命却具有多元性,如有正式的、高度专业化的大型组织,也有把非正式和活动性看的高于专业管理价值的小团体[1](P74),在目标追求上,它们通常是单一利益的倡导者,相比之下,政府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则必须关心更多问题,关注民生,回应公共诉求。故库珀(Cooper)认为,政府在某些方面与非营利组织建立合同关系,比同私营部门建立合同关系更为复杂。关键原因在于“非营性”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出非营利机构的目标导向性,换句话说,非营性所涵盖的视域是非常广泛的,它们目标多元,人员机构庞杂,因而相应地具有各种不同的组织文化和能力,从而增加了政府与其达成绩效合同的交易成本。此外,政府有时会为了扶持非营利性组织而与其签订合同,随着非营性组织群体的扩大直至竞争市场的初步形成之时,政府与其所签署的非营利机构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过高的期待或目标的强制转移,因此,也会导致合同双方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进而影响了政府合同绩效的实现。
政府部门间目标的不一致性。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或职员签订合同,同样也存在着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在美国,政府与政府的协议传统上被视为州际合同或者辖区间的协议,要求符合宪法并获得国会的批准。而之所以需要国会对其进行严格审批,原因在于:首先是防止一些州与其他州以冲突的方式加入进来,各州对合同有效性的争议可在国会中提出来,而不必通过法律行动来解决;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合同成立,参与州就会受到合同束缚,合同的管理机关具有重要的立法和行政权[1](P78)。但就是在有宪法制约的前提下,政府之间的绩效合同或协议仍然存在着目标不一致性及分歧,突出体现在部门利益化、政府职员的个人理性行为、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如亨利(Henry)指出,在美国政府契约制中广泛存在一种被称为“旋转门”的现象,当联邦官员从政府退休或辞职时,特别是如果他们离辞前所从事的是与私人部门签订合同的工作,他们时常成为过去担任联邦政府行政人员或立法者所来往互动公司的高薪主管,这为牺牲政府利益而使自己将来有利可图创造机会,而且,有资料说明,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的“旋转门”越转越快[12](P557)。
四、资产专用性制约政府绩效合同实现
根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论述,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解释经济组织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工具,资产专用性是与契约合同相伴而生的,即交易方为履行契约所作的专用性投资,如果契约不能成功履行,则将这种投资转为其他的用途的困难比较大[13](P114-118),其与沉淀成本的概念相关。一般认为,合同的交易成本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高而增加,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黄禹锡(Hwang)认为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的作用受组织间信任水平和合作期限长短等环境因素的影响[14](P60);而雷(Lui)等人认为单方面专用性投资会造成对方“要挟”,增加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及交易成本,与之相对的是双方相互专用性投资,则表明了双方合作的意愿和承诺,成为退出的障碍,双方更倾向于从长远利益考虑进行合作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从而减少交易成本[15]。
此外,威廉姆森还认为资产专用性对事后交易费用即执行成本、监控成本等具有特殊意义,并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专用性投资:第一是地址专用性(site specificity),即买者和卖者相互靠近,这表明一种最小化存货和交通费用的事前决定;第二是有形资产专用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即合约一方或两方在设备和机器方面所进行的投入在设计上具有交易专用性的特征,但其他使用价值则较低;第三是人力资本专用性(human capital specificity),即它的产生是因为边干边学、投资以及转让专用于特殊关系的技术;第四是专门性资产(dedicated assets),这些包括其他情况不会发生的、主要是为了向一个特定客户出售一笔数量较大的产品所作的一般性投资,如果合约永久性终止,则会导致供应者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16](P168-169)。在政府绩效合同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政府与私营部门所签订的公共服务类供给性合同、采购合同、租赁合同,还是政府与政府部门所签订的资源共享互补协议或工作绩效合同等,都具有资产专用性的属性,基本上是上述四种专用性投资的交叉组合形态,相应地造成了政府绩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一般来说是政府绩效合同中受要约的一方)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地址、人力、有形或专门性资产专用性特质,使其在该领域具有垄断的特质,从而强化了他在签约前讨价还价的力量,使合同原本所强调的平等、自由原则出现了向拥有资产专用性特质的一方倾斜。
在签约之后,拥有资产专用性的一方会通过评估其守约或被“煎熬”、终止合约风险系数,在其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形下,会采取在签约时所提供不合理的底价的地方,或者在投标过程承诺过多绩效要求的地方寻求高价补偿和降低标准,从而大大影响了合同绩效,违背了合同订立的初衷,使政府及合同的公共管理者陷入窘境。关于此,库珀列举了一个小镇修理桥的例子,合同中标价格总共大约46 000美元,政府合同管理者为建设项目的资金申请了两种资金补助,一种是基于该方案的资助,另外一种是一年只提供一次标准资助,最后选择了46 000美元的资助方案,然而,工作才开始不久,承包商就告知管理者实际需要的开支将是最初估计的两倍[1](P120)。此时在当地也没有其他的投标者,也就是说承包商拥有专业资源,社区只能继续和这个承包商合作,相应地社区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被动接受承包商在价格上、工期及质量上的不合理要求。从上述分析中看出,随着绩效合同的不断运行,对于首先赢得政府要约的合同当事人的优势也会愈加明显,但也因此造成了其他组织进入该垄断市场的壁垒,致使有合同要约行为的政府愈发处于不利地位,并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9](P275-297)。此外,资产的专用性导致处于被动地位的政府部门很难制定出评估对方实施结果的标准或是监控到合同方所应提供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发政府合同管理者滥用手中权力,无论是否有效力都会坚持要求供应商完成合同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对产出或成果的监督权力往往会导致政府合同监管人员干涉合同对方的工作程序,而这种干涉经常会出现在执行法律、质疑供应商技术合理性或其他许多用来为难私人和非营利组织的机制中”[10](P39)。此外,这种监控模式也会随着相对方的执行情况产生“钟摆效应”,即要约的政府这方首先疏于充分的监督,然后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又反应过度,转而试图微观管理它的合作方,出现了力求制定事无巨细式的合同现象,设置太多的标准、太多的数据要求,而有些标准和要求更多涉及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10](P40),导致了政府绩效合同谈判成本、决策成本、信息搜寻成本、执行成本的耗费,束缚了政府绩效合同的实施与开展。为此,要缩小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性,应该通过制定出具有结果绩效导向性的评价标准。
五、绩效目标及行为的转换制约政府绩效合同实现
目标不一致性和资产专用性这两大影响因素主要是基于政府合同交易谈判、成本控制及合同绩效实现这样的逻辑关系所提出的,侧重点在于合同属性。而绩效合同目标及行为的转换风险这一因素则是基于“绩效管理及实施机制”的动态过程所提出。目标及行为的转换风险与政府绩效合同异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绩效管理非但没有成为改进合同实施过程、提升合同有效性的催化剂,反而会造成绩效合同目标及行为发生置换,成为合同绩效实现的绊脚石。正如考夫曼(Kaufman)所指出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绩效合同并不像理论所界定的那样简单和神奇,并且伴随着一些陷阱,”[17](P24)这些陷阱往往会成为创新与获得成功的障碍,造成政府合同代理方的“旋转门”现象。为此,不断优化政府绩效合同实施机制,制定出抵制目标转换的评估指标,有利于降低绩效合同中的风险系数。
第一,绩效目标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政府绩效合同双边策略行为。利益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主体,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18](P105-111)。对于具有“反思理性的经济人“属性的政府来说,会表现出两种对立的属性,即公共性和自利性。政府在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中,政府自身、政府部门机构和政府行政人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性,即政府的自利性,其中公共性始终制约着自利性,自利性始终具有突破公共性束缚的冲动[19](P176)。如在拨付公共资源的绩效合同中,绩效合同是维护公共目标达成的监控性工具,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政府自利性的驱使,往往会诱发政府将绩效评估等作为截留资金、变相修改协议目标的手段。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全国20多个省份,3 000多名村医进行了生存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4.8%的受访村医获得了药品零差率补偿,46%的受访村医拿到了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贴,而且他们实际拿到的补贴金额不到政策规定金额的一半,其原因为从县卫生局到乡卫生院都以绩效评估为名层层截留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从本该发放人均8.75元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最后到村医手中仅有1.5元[20],进而诱发村医违规输液、出售基本药物目录之外的药品,导致大量村医流失,背离了政府供给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政策初衷。因此,政府在实施绩效合同时就需合理平衡公共性与自利性间的冲突。
对于政府绩效合同的相对方(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来说,政府绩效合同中的绩效目标设定一方面激励了合同相对方要努力达到目标,但另一方面诱发其采取保守策略,单纯以目标数据为指挥棒,缺乏创新精神去探讨更有益于实现合同目标的方法,使绩效合同的签约、决策及执行成本处于消极的耗费状态,致使绩效合同违背初衷。即使合同相对方能寻求更好的实现合同目标的方法,但这方法往往是削减成本、而不是提供服务的方法。因为在现实状况中,相对方知道有更好实现合同目标的方法,但该种方法却需要支付比约定资金更高的额度。为此,当作为委托方的政府如果采取支付最小化服务报酬的话,就会导致合同商忽略服务质量与效益。此外,由于现有政府绩效合同更多是强调目标标准的实现,而对产出及结果缺乏相应的奖励机制,从而诱发相对方隐藏某些成果,以便在新一轮的合同谈判中享有更多的优势,力争通过履行一般产出及结果就可获取更多的报酬,存在签约前及实施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二,政府绩效合同的首席执行官处于既要与合同商保持距离以维持公平,又要为了获取更多的绩效信息与合同相对方保持密切关系的二难处境。政府绩效合同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选择“优秀的”首席执行官的能力。政府如何选择一个好的管理者,并指挥他按照预定的方式去有效地履行合同,其间存在着搜寻信息成本、谈判协商成本、执行监控成本等。绩效合同体现一种信任,它是交易的前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为维持和增进自身利益而将公共服务管理委托为首席执行官和经理。之所以出现这种委托行为主要基于三种因素:一是以首席执行官或经理依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对公共服务进行良性运营为条件;二是信任代理人的能力,确定其足以胜任合同运营之责,能有效履行政府课以的合同管理任务;三是如果首席执行官讲诚信,认真履行合同监管责任,诚实且成功地履行了委托——代理契约,获得委托方政府的持续信任,那么政府绩效合同中的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就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对于政府绩效合同的首席执行官或监管主体来说,如何处理好其与合同承包商的关系,成为确保委托责任实现的重中之重。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则以确保合同相对方之间竞争的公平性、而不偏袒于任何一方。但现实的选择是,政府往往会选择以往同它合作的承包商,加剧了合同交易规则的不确定性。此外,绩效合同的制定及达成有赖于政府熟悉合同承包方的行为动态,需要合同双方达成密切合作的关系,但这往往也会给政府合同的首席执行官制造寻租的机会,如合同承包方利用游说、行贿、拉关系、走后门和“回扣”等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影响监督者决策。另外,公共服务领域回报率的确定、成本的核算、价格的确定具有较强的专用性[21](P676-680),政府与合同承包商、政府与首席执行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首席执行官隐藏谈判和缔约的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将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破坏交易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合同绩效的实现。
再者,评估政府同绩效实现程度有赖于绩效数据搜集和处理,但由于对绩效信息及数据处理能力的欠缺,导致绩效合同盲目搜集使用数据,出现了“DRIP”综合症——数据丰富但信息贫乏(data rich but information poor),致使协商谈判、监督及执行等交易成本的扩大。之所以会出现“DRIP”综合症,一方面是因为涉及到公共属性的政府绩效合同难以衡量其产出及结果效益,并且政府缺乏竞争性市场也导致合同监管者较少有动力在工作中注重节约,也不必做出服务实际成本的精确数据。如曾经当过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副市长的斯基普·斯蒂特(Skip Stitt)就提及,“我不记得在签署过的大量承包合同中,内部供应商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提供一项服务所需要承担的全部费用,在某些情况下,围绕绩效测评的明确性要大一些,但即便是这一部分也不是所有领域都很清楚明白。”[10](P43)另一方面绩效合同中的“反思理性的复杂人”假设同样遵从了西蒙(Simon)所界定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决策者并非无所不知,而是在信息的加工方面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即要准确区分出绩效合同的产出、效益及影响存在着较大难度,从而导致合同的存量、质量及变更交易费用的耗费,如那些以政策为导向的绩效合同,政策对结果的实际影响常常难以区分出来,也因为这些结果通常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都很难体现出来,因此,像“结果”这样的年度指标,就会显得没有意义,或者只是简单地被提及一下而没有实际的价值[22](P20)。
六、结 论
本文以威廉姆斯所界定的交易成本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结合政府绩效合同所固有的合同契约属性、绩效管理与评估的动态属性,发现政府绩效合同双方目标的不一致性、政府绩效合同资产专用性以及政府绩效合同目标与行为的转化风险是影响政府绩效合同得以实现的本源性因素,是政府绩效合同当事人出现毁约、资源浪费、绩效评估形同虚设等外显问题的本源性因子。为此,正确运用政府绩效合同这一新型政府治理工具,客观认知政府绩效合同的本源性影响因素,从绩效合同目标设立、绩效指标体系制订、绩效合同监控与改进等方面构建规避政府绩效合同风险与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将成为政府绩效合同、政府协同治理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在日益凸显合作与信任的政府生态治理环境中,政府绩效合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文章所探讨政府绩效合同的本源性影响因素,其研究启示在于:(1)政府绩效合同是一个双边策略的行为机制,其绩效的实现应该是合同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绩效合同双方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为此必须正视合同双方目标的不一致性,运用绩效诊断、绩效沟通等方式创新合作机制,减少目标不一致性的负面影响;(2)鉴于政府绩效合同在委托签约时合同相对方所具有的地址、有形资产、人力与专门性资产的专用性,应该分解合同签约要素,评估合同签约方的资质,通过制定具有结果绩效导向的评价标准与条款,缩小资产专用性的影响力;(3)政府绩效合同自身的组织实施绩效是政府绩效合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据此应正视实施绩效策略所面临的目标转换、本身实施的“无绩效”等风险,注重目标设定的战略性导向性、评估监控的简易性等,确保政府做个“精明的买主”。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库珀.合同制治理[M].竺乾威,卢毅,陈卓霞,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BEHN ROBERT D, KANT PETER A. Strategies for Avoiding the Pitfalls of Performance Contracting[J].Public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 Review,1999,22(4).
[3] 卓萍.从政府合同到政府绩效合同:政府绩效合同内涵的演进逻辑[J].理论与改革,2013,(2).
[4] SAKO M.Price,Quality and Trust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5] 陈振明,贺珍.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J].东南学术,2007,(3).
[6] 薛恋鼎.引入政府绩效合同管理[J].江南论坛,2009,(11).
[7] 叶初升,孙永平.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05,(3).
[8]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 BROWN TREVOR L, POTOSKI M. Managing Contract Performance: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03, 22(2).
[10]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 BURTON L. Ethnical Discontinuities in Public/Private Sector Negotiation[J].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990, 9(1).
[12]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张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3] 李学.不完全契约、交易费用与治理绩效[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14] HWANG P.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Fear of Exploit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2006, 60(4).
[15] LUI S S,NGO H Y.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and Process Factors on Partnership Satisfaction in interfirm Cooperation[J].Group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5,30(4).
[16] 埃里克·弗鲁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7] STANLEY K.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OFPP's Performance-based Service Contracting Pilot Project[J].Contract Management,1996,(3).
[18] 金太军.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J].江海学刊,2002,(2).
[19] 张舒航.浅析政府自利性恶性膨胀的危害及对策[J].科技经济市场,2006,(9).
[20] 村医.你过得还好吗[EB/OL]. http://news.cntv.cn/2013/05/03/VIDE1367584080238546.shtml,2013-05-03.
[21] 吕志奎.合同治理的风险分析:委托——代理理论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22] 西奥多·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M].肖鸣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