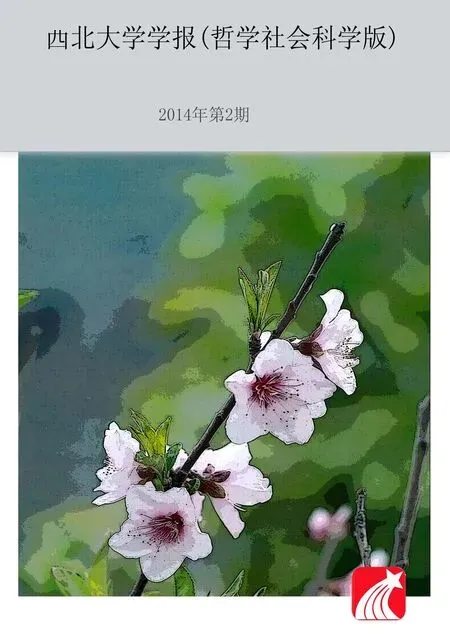历时性生成与共时性分析
——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异同辨
张 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众所周知,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支系占据主流位置。学界一般认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西安·戈德曼(Goldmann)继承自皮亚杰(Piajet)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虽受到索绪尔传统结构主义(戈德曼与皮亚杰称之为“Linguistic Structuralism”,即“语言学结构主义”*戈德曼将其表述为“建立于语言学基础上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based on linguistics)。)的影响,却与之存在明显差异,弗·詹姆逊(Jameson F.)甚至提出:“以语言体系的隐喻或模式为基础”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这一术语与发生学结构主义并无联系。[1](pix)但与此同时,亦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曾从语言学结构主义中汲取过灵感,因此两者明显具有理论姻缘关系*例如冯宪光提出:“戈德曼的成功,是他既吸收了结构主义的观点,又并不盲从于结构主义”,见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页;亦有学者认为戈德曼的理论思想“有很明显的结构主义成分”,见高建为等著《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两部论著此处提及的“结构主义”均指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界随之以此为据,指出戈德曼理论具有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某些“结构主义符号学”特征。然而,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间的异同到底是什么?前者如何以后者为纽带而体现出符号学特征?国内学界对此似罕有深入讨论。本文拟从对发生学结构主义概念的考察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结构观差异
戈德曼曾表示,其理论建立在对社会文化实际状况的考察(positive research)基础上[2](P6),主要表现为对皮亚杰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援引与借鉴。因此,欲辨明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关系,必须从对皮亚杰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剖析开始。
作为人文社会思潮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知识界一度蔚为“文化时尚”[3](P1)。由于这一思潮中许多结构主义支系都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征,故被皮亚杰与戈德曼统称为“语言学结构主义”或“非发生学结构主义”。皮亚杰将其理论命名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发生学”(genetic,“缘起的”、“演化的”)这一称谓表明皮亚杰采取一种动态眼光来审视结构的生成与演变的意图。因此,皮亚杰始终质疑语言学结构主义未能有效阐释“结构”的生成过程这一关键问题。众所周知,作为语言学结构主义始祖,索绪尔为语言学结构主义奠立了其“结构”概念的基础,同时却因提倡以“共时性”维度审视对象而将“结构”问题“本体化”(ontologizing structure)[4]P179,故从未对“结构”生成问题作出有效解释。此后,作为文化思潮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经过一系列发展,始终秉承着从“共时性”维度去分析对象结构的方法论,因此无一例外地未能对结构的动态生成机制作出有效阐释。例如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仅仅指出结构人类学的“结构”与结构语言学的“结构”存在同构关系,两者都属人类心理领域[5](P58),却因此回避了“结构如何生成”问题。[6](P107-108)正如法国学者多斯(Dosse)所言:列维-斯特劳斯已“彻底将这一问题(结构的生成)从结构人类学中清除了出去”[4](P179)。
皮亚杰在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分别进行批判后总结道: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其所采取的共时性维度,阻碍了对结构生成的有效阐释。他对人类心理认知结构建构过程的表述,事实上表达出其以历时性方法考察结构动态形成过程的基本态度,诚如某些学者所言:“皮亚杰……更重视结构的历时性发展。他所谓的‘建构’,就是指结构不断改变和更新的进化过程。”[7](P134)显然,以历时性的动态眼光描述和阐述结构的生成问题,是皮亚杰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等结构主义派别最为本质的区别。戈德曼在继承了皮亚杰对认知结构生成缘由的心理学阐释时,提出人类心理结构的形成受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接受了其对结构生成问题的历时性理解,由此与语言学结构主义结构观的差异同样被延续。然而,戈德曼的结构观较之皮亚杰亦存在差异。皮亚杰从人类心理认知结构的发生学角度来探讨主体性之形成的做法,将对人类主体性的理解局限在个体心理结构范畴,而无法阐释人类主体性在社会历史整体中的体现方式。戈德曼由此将皮亚杰发生学结构主义,从对个人心理认知结构范畴的认识,扩展到对特定社会群体及阶级的集体认知结构的考察。戈德曼认为,身处某种社会环境中的诸多个体在特定因素影响下形成特定社会群体,并在该群体中逐渐磨合成在思维及认知方面相对恒定的集体心理认知结构,戈德曼称之为“集体性心理结构”;同时,个人也受所在群体的集体性心理结构的制约,“这些习惯与心理结构不仅支配其行为,还支配其心智、思想和情感”[8](P86)。结合戈德曼对结构动态生成性的阐述,可知在其看来,这种集体性心理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集体性心理结构虽源于社会历史,但在它的导向和指引下,人类能够以集体组织形式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并由此改变和创造社会历史。因此戈德曼提出: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以具有集体性心理结构为特征的“集体主体”,而非具有个体心理结构的“个体主体”:“历史现实总与大量习惯、活动和心理结构紧密相连”[8](P86)。这种理论,显然是戈德曼对皮亚杰未予阐明的主体的社会属性的充分诠释。
结构生成观与“集体主体”观,共同构成戈德曼对语言学结构主义发起批判的逻辑依据。在谈及列维-斯特劳斯、福柯(Michel Foucault)及阿尔都塞(Althusser)等学者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倾向时,戈德曼抨击他们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抽象的结构作用,而消解了作为“集体主体”的人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指责列维-斯特劳斯只是“根据语言学模式来研究超历史结构的形式”,福柯则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局限于“疯狂和无意识领域”[9](P88),而阿尔都塞则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归因于抽象的“社会结构”,而淡化了“人”(集体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8](P149)。由此可见,戈德曼与语言学结构主义对结构的功能及社会属性的理解甚为不同。戈德曼从人类集体认知心理角度,将结构视为一种受社会诸多因素影响的、且为群体所共有的心理结构,并将拥有共同心理结构的集体主体视为历史的真正主体;而语言学结构主义则从共时的角度悬置结构的生成,且将历史的主体性归于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结构。不难看出,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的“集体性心理结构”所体现出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观念,与语言学结构主义对结构的“非历史化”理解迥然相异,而这正是两种结构主义类型在结构观方面的分歧所在。
二、对整体性方法与共时性方法的运用
尽管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仍明显具有某些语言学结构主义特征。有学者将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具体实践方法归纳为对结构的整体性观照和共时性考察[10](P57-58),这一总结事实上十分恰切地描述了两种结构主义类型在方法运用层面的共同特征。
整体性观念是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重要特征,这一观念认为:“(实体的)组成因素遵守一系列内部规律,这种规律对实体及各组成因素的属性起决定作用”[11](P5),亦即认为由于这种整体性规律决定了各组成部分的属性和意义,因此对各组成部分意义的认识不能脱离对整体的观照。与之相似,戈德曼同样十分重视将整体观作为考察文学等精神现象的社会学方法。这种方法首先体现在对文本内部形式的审视。就词、句等语言因素而言,由于“貌似相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一致的词汇、句子、段落,在被用于不同语境时能够具有不同涵义”[12](P10),因此只有将它们置于文学文本的整体结构语境中,才能对其意义进行有效理解和阐释。同理,理解某个文学文本,必须以将其置于作家整个精神历程的整体结构为前提:“作家的观念或作品,只有在被视为生命历程和行为模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并得到充分理解。”[12](P7)戈德曼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理解任何一种精神现象,都必须将其作为较小结构置于更大的思想结构之中,并在这一作为整体的思想结构中审视较小结构所体现出的意义,“只有在被置于整体之中,个别事实或观念才能获得意义”[12](P5)。戈德曼在阐释17世纪作家拉辛的悲剧作品及哲学家帕斯卡尔的论著时具体应用到了这种整体方法。戈德曼提出:对拉辛和帕斯卡尔的著作意义的理解,必须以将其置于冉森主义的思想结构、并通过对拉、帕二人著作与作为整体思想结构的冉森主义观念相对照为前提;而欲理解冉森主义的思想结构,则必须将其置于穿袍贵族的历史这一更大的思想结构中[13](P240-241)。这种对意义的整体性认识方式,显然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整体性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
戈德曼认为,尽管任何形式的结构都形成于动态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但对其内部形式的考察却依赖于共时性方法,换言之,只有在某个划定的静态时间片段内才能有效考察结构的内部形式:“历史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 processes)对象,这些过程必须在建立起某种模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研究”,同时“共时性方法是开始进行研究时必须采取的手段”[8](P50)。戈德曼以文学研究领域为例,对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的优越性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考察文学现象的形成,必须首先从文学史的历时性角度认识到文学活动始终伴随时代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例如各种体裁(genres)就无一例外地是文学史发展的产物;但如果从共时性角度来静态地剖析不同体裁作品的内在结构,便可从中归纳出“细述”(recit)这一共同性质:“总而言之,细述即全部这些体裁共有的东西”[8](P51),从而有效地总结出各体裁范畴所共有的文学性特征,共时性方法的优越性由此可见一斑。戈德曼将共时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和历时性的历史主义方法辩证地结合起来,既是对语言学结构主义方法的借鉴,一定程度上又是对包括语言学结构主义文论在内的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补充与修正。
三、对“语言”/“言语”二分法的使用
语言学结构主义在被作为方法论时,强调从共时性角度、通过“语言”/“言语”的二元格局途径来审视结构的内部形式。戈德曼对在分析结构形式方面共时性方法的肯定,为其发生学结构主义采取“语言”/“言语”的二分研究方法奠立了逻辑基础。
“语言”/“言语”的对立实际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对立,这组对立是所有结构主义的理论关键:“语言/言语二分法是索绪尔为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可以说,承认这个二分法,把这个二分概念用于自己的学科,就成了一个结构主义者。”[14](P15)在作为语言学结构主义源头的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语言”是“言语”以横组合和纵聚合方式形成具体语义链所依据的语言规则集合。此后,当这组基本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受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时,“语言”被理解为研究对象的物质材料得以进行形式组合的规则体系,“言语”则成为物质材料的具体组织形式。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语言”/“言语”二分法时有运用。例如曾对结构主义方法青睐有加的伊格尔顿(Eagleton)提出,作为文学“语法”(grammar)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够生产文学语言(speech)[15](P66),赵毅衡暗示,这事实上正是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所谓文学“语法”实际是作为文学“语言”的意识形态,而文学语言(speech)是作为“言语”的文学叙述[14](P17),前者为后者提供基本行文逻辑或思想模式,使其围绕这一思想模式而得以展开;另外,马舍雷(Macherey)曾以相似思路,对文本结构中意识形态与文本间的冲突特征进行了分析*详见马舍雷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一书第19、20章,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p.p.105-158.。总之,将为文本提供思想模式的意识形态,和以之为据的叙述展开方式间的关系理解为“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运用方式之一。
事实上,在戈德曼以发生学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学社会学中,同样体现出对“语言”/“言语”二分法的应用。戈德曼将由诸多群体构成的社会阶级所具有的统一集体性心理结构称为“世界观”(world vision),指出世界观是一种“能够团结一个社会群体(多指社会阶级)的所有成员制衡其他社会群体的所有观念、情感和感受”[12](P17),这一定义几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界定,“世界观”正是“意识形态”的同义语。戈德曼在阐述发生学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应用方式时,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学生产过程与作者所属阶级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世界观是群体意识(consciousness)的产物,这种意识能够最大可能地触及一位诗人或思想者的思想(mind)表达”[12](P19),集体性心理结构(世界观)对属于本阶级的作者施加心理影响,使作者得以形成与其一致的心理结构,并使其以与心理结构“同构”的形式体现于作品文本中[16](P65-66);同时,这些被设置于作品文本中的心理结构又往往能够作为某种思想模式,支配文学叙述的基本格局与情节发展。
戈德曼重点考察了拉辛一系列具有“明显的冉森教派特征”[12](P317)的“真正的悲剧”(genuine tragedies)。戈德曼发现,冉森教派曾在1669年前奉行否定世俗世界的宗教观念,而作于1669年前不久的《昂朵马格》《勃里塔尼古斯》*剧名及角色名译法系采取于《拉辛戏剧选》,齐放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等剧恰恰体现出对世俗欲望的反感情绪,因此戈德曼称其为“拒斥型悲剧”(the tragedies of refusal);1669年后,冉森教派开始犹疑不决地考虑与世俗世界实现妥协,而作于1677年的《费德尔》中出现了主人公在信仰与情爱的两难抉择间痛苦徘徊的情节,戈德曼遂称之为“突转与承认型悲剧”(tragedies with peripeteia and recognition)[12](P374-375)。戈德曼由此认为,各剧中的角色在其剧中分别与“对神的信仰”“世俗观念”两种因素共同组成“上帝、世界和人”的三元结构*冯宪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称这种结构为“三角结构”。本文改作“三元结构”,以呼应于学界对列维-斯特劳斯“二元结构”的译法。,这种分析视野与列维-斯特劳斯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据考证,拉辛本人正是一名冉森教派成员,同时也是穿袍贵族的一员[17](P365-366)。因此,拉辛一系列剧作中角色对待世俗态度的变化,实际正体现出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冉森教派的世俗态度的转变。17世纪法国王权政治的波诡云谲,使得身为穿袍贵族成员的拉辛在各种政治势力间立场难定。冯宪光指出:拉辛的这两种身份,使其与那个时代其他冉森教派和穿袍贵族成员一样,分别陷入了由“上帝权威”—“理性主义”和“王权专制”—“个人主义”两组思想观念形成的冲突中。[17](P365-366)因此,当两组作为世界观的思想观念同时影响到包括拉辛在内的冉森教派和穿袍贵族成员时,便使其在思想意识内形成了由两组世界观与其本人共同构成的“上帝、世界与人”的心理结构。作为剧作家的拉辛在进行具体创作时,将这种心理结构设置于剧作中,使剧作中同样呈现出三元结构,具体而言,是使剧中角色与拉辛本人一样,在“权威崇拜”与“世俗迷恋”的罅隙间展转游移,并使戏剧情节围绕这种结构展开。
当然,拉辛的三部剧作所分别蕴含的三元结构,在其具体主旨倾向上截然不同。作为“拒斥型戏剧”的《勃里塔尼古斯》,依据“菲斯大神”—“尼禄”—“朱妮”,即以朱妮“对菲斯大神的敬畏”和“对尼禄求爱的拒绝”为基本结构,推动戏剧情节的具体叙述;而作为“突转与承认型戏剧”的《费德尔》,则依据“太阳神/米诺斯/奈普顿”诸神—“伊波利斯”—“费德尔”,即以费德尔在对“神祗的信仰”和“对伊波利斯的挚情”间的两难处境为基本结构,展开费德尔谋杀伊波利斯的戏剧情节。两剧的结构所蕴含的对待“世俗”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直接导致了戏剧情节向不同结局发展。这一现象归根结底是由冉森教派集体性心理结构(世界观)的变化导致拉辛心理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所致,同时也再次体现出戈德曼对结构处于动态建构过程的理解,并印证了他对共时性和历时性方法的辩证性态度。
这样,从伊格尔顿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运用方式角度讲,这个过程实际上便可被表述为:作为“语言”的世界观(集体性心理结构)/意识形态,通过作者环节,为文学文本提供了作为情节推动原则的思想模式,使“言语”层面的文学叙述得以具体施展。由此可见,戈德曼在运用发生学结构主义进行文学批评时所采取的策略,与伊格尔顿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言语”二分法的应用如出一辙。对二分法的运用,应是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所体现出的又一语言学结构主义特征。
四、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间虽在“结构生成”等问题上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两者间亦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关联或相似性;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以其对结构的社会性生成来源所作的阐释,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补充。同时,两者在对待整体观照方法及共时/历时方法、以及对“语言”/“言语”二分法的应用方面的相似性,使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随之带上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理论特质,也因此具备了学界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因素。曾经兴盛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结构主义思潮曾影响过包括戈德曼在内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关系的辨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漫长而复杂的形成历程的有意义的还原。
参考文献:
[1] JAMESON F.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4.
[2] BOELHOWER W. Essays on Method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M].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1980.
[3] SCHAFF A. 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M]. Oxford an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8.
[4] DOSSE F.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he Rising Sign, 1945-1966(Vol. 1)[M].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5] LÉVI-STRAUSS C. Structural Anthropology[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3.
[6] PIAGET J. Structuralism [M]. New York: Harper&Row, Publishers.
[7] 陈晓希、王志元.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M]∥现代外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8] GOLDMANN L. Essays on Method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M].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1980.
[9] GOLDMANN L. Lukács and Heidegg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10] 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2.
[11] HAWKES T.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12] GOLDMANN L. The Hidden God: A Study of Tragic Vision in the Pens?es of Pascal and the Tragedies of Racine[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13] 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M].吴岳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 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前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5] EAGLETON T. Criticism and Ide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76.
[16] 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M]. 罗国祥,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17]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皮亚杰文集》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