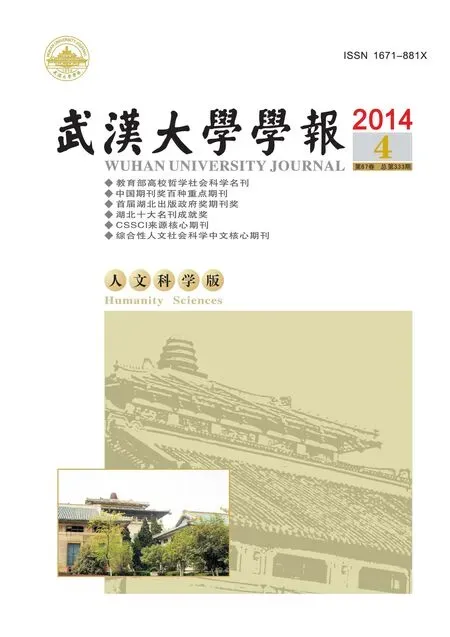生存哲学如何是生存神学的前理解
姜 韦
生存论解经或解神话以生存哲学为前理解。然而,这一断言却导致各种误解。尽管布尔特曼声称他的解经以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前理解,但解神话却非把生存哲学作为一套框架体系移植过来,从而把圣经转变成哲学理论,那么,这里的前理解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呢?为了探明此问题,必须将眼界扩展到生存神学与生存哲学的关系上。
论到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有必要避免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能像有些批评者那样,认为生存神学无非是把神学哲学化,解神话是“把《圣经》变为基督徒生存的分析,即差不多是《存在与时间》的基督教版本”*麦奎利:《存在主义神学——海德格尔与布尔特曼之比较》,道风书社2007年,第197页。;另一方面,也不可矫枉过正,把海德格尔的思想视为“基督教思想架构的拙劣模仿”*David Cairns.A Gospel without Myth?London:CM Press Ltd.,1960,p.69.,从而完全否认它对布尔特曼的实际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二者间关系,还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之间有交互影响。6年马堡生涯,海德格尔与布尔特曼一直保持着有益的思想交流。他们积极参加对方的研讨和讲课,共同研读《约翰福音》。在海德格尔开始着手写《存在与时间》时,两人固定会面探讨克尔凯郭尔和狄尔泰的思想。海德格尔在他的《现象学与神学》的演讲中表达了许多布尔特曼关于神学的观点,正如李丽娟教授所言:“他们在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之间的密切思想交换,已经很难分出到底哪些是谁的原始观点了。”*布尔特曼:《信仰与理解》卷1,道风书社2010年,中译本导言第xxi页。鉴于此,我们不能局限于将二者思想的结论外在地并置和比较,而不顾他们思想发生过程中的交互影响。
二者的交互影响使得上述两种意见均难以立足,尤其是后一种直接背离了事实,因为生存哲学对神学的意义是布尔特曼亲口承认的。那么能否因此断定布尔特曼只是海德格尔的誊写员?如若不能,生存哲学究竟对生存神学有怎样的意义?
一、 对人的重新理解
虽然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复杂,但首先不得不承认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的确深深吸引了布尔特曼,使他面对种种诘难竟不厌其烦地为生存哲学的神学意义辩护。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
布尔特曼认为,任何时期的神学尤其是解经总受到世俗思潮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例如19世纪,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神学产生深刻影响。那时,圣灵的意义基本上是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的意义得到理解的,而自由神学的发展与康德伦理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然而,立足于辩证神学精神,布尔特曼绝不能任凭上帝与人之间界限不分,不能让神学变成一种彻底的人学,让解经变成一般历史文献的考究。问题之症结因此在于:如果没有神学和解经能免受世俗哲学的影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世俗的哲学能让我们在“理解上帝必须理解人”这一基本事实下进行神学和解经工作时,不致模糊神人的差异?
生存哲学能够担此职责。与巴特不同,布尔特曼并不担心神学与世俗思潮染指,但是为之担心的是某种哲学模式或者说思维方式。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解释世界和人自身,但恰恰是这样的哲学不适合作为谈论上帝和理解圣经的前理解,因为它们都自称对人是什么给出一个确切答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不假思索地认为人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把握。但是,“不会有一种具有绝对完善体系的正确哲学,也没有一种能对一切问题提出答案和澄清所有生存之谜的哲学”*布尔特曼等:《生存神学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7页。。因此,生存哲学所以能担此重任,在于它跳出了这个窠臼。“如果生存哲学如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试图提供一种人的生存的理想模式,那我们就无所收益。”*布尔特曼等:《生存神学与末世论》,第38页。那么,生存哲学是怎样理解人的呢?
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篇,海德格尔一上来就给此在下了一个定义:“这种存在者(此在)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49页。照此看来,这与其他哲学有什么不同?它不是也企图为人之为人给出答案吗?不错!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也是一种定义。但不同的是,如果其他哲学的定义是要告诉我们人是什么,那么生存哲学要表达的则是人是什么。换言之,前者将人封锁在某个“什么”上,后者则让人保持敞开状态,它“是什么”是在这种敞开中获得的,即“必须从它怎样去是,从它的存在(existentia)来理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9页。“生存”的德文词是“Existenz”,与上面的拉丁词“existentia”对应。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实存,海德格尔在这里使用它们来特指此在的存在。但为了与“Sein”区别开来,故将之译为生存。。所以,此在与物不同,“它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9页。,因此不能像对待物那般把握此在,因为它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现成存在着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9~50页。。可见,虽然海德格尔也给出定义,但它的旨趣与传统的定义截然相反,因此对后者构成一种摧毁的力量,因为它向那些绞尽脑汁企图一劳永逸地理解人是什么的哲学宣告:人不可把握。
在某种意义上,生存神学是在与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之人观相抗衡,直到生存哲学那里,它才遇到知音。生存哲学不仅提供一种适合谈论上帝的人观,而且是理解圣经,即把圣经当做上帝之道去聆听的前理解。只有“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种能在。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不由他支配、占有”*布尔特曼:《信仰与理解》卷1,第151页。,因而始终向着他者敞开,才可能去理解上帝与人相遇的事件;同样,圣经才可能对他成为打开并实现他的某种可能性的启示之道。“生存哲学试图通过区别作为‘生存’的人和一切现世存在物的存在来表明生存的含义”*布尔特曼等:《生存神学与末世论》,第38页。,这对布尔特曼来说极为重要,可以说是他解神话的根基。
尽管如此,却不可认为布尔特曼是认识海德格尔之后才学会这种理解的。布尔特曼对人的理解有其自身的传统,因此在共鸣之余难免存在差异。这需要另外撰文讨论。故而严格说来,在人的理解上志趣相同是二者对话的潜在前提,而他们就生存哲学对神学的意义所进行的具体对话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的关系问题上,即存在论—生存论层次和存在—生存状态的层次。
二、 海德格尔的意图:为实证科学奠基
生存哲学是一种存在论—生存论的建构,其目的是为所有实证科学奠基。任何一门实证科学总是以某些特定的存在者的实质领域为探索对象,但是这些实质领域并非现成就有,而是“已经先于科学工作而由对存在畿域的经验与解释完成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1页。,或者说,所有实证科学的工作都活动在事先对存在经验的某种领会中。所以,存在论—生存论的任务是解释存在者及其实质领域,但不是以实证的方式,而是通过澄清存在的意义“按照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2页。,以便“把赢获的结构交给诸门实证科学,使实证科学能够把这些结构作为透彻明晰的对发问的提示加以利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页。。鉴于存在论—生存论的追问是为澄清实证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它比后者的追问更加原始。
那么,神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神学也需要哲学或存在论—生存论工作为其奠基吗?当然需要。因为神学作为“信仰的科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但是,与其他实证科学不同的是,神学作为信仰之科学,不把信仰或上帝当做存在者来研究,相反,“神学本身起源于信仰。神学乃是信仰根据自身来进行说明和辩解的科学”*海德格尔、奥特等:《海德格尔与神学》,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12页。。那么,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个基督教特有的事件——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在此事件中,此在与十字架上的上帝相遇。所以,信仰“作为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的生存关系,乃是历史性此在的一种方式,即人类的生存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奥特等:《海德格尔与神学》,第12页。,神学作为信仰的科学之目的在于,将始终只能与生存活动本身发生关系的信仰生存勾勒出来。就其总是涉及到上帝的启示事件和此在的生存活动而言,神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它不是以存在者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客观化实证科学,相反,那些客观化的实证神学,如教义神学、系统神学、历史学神学、教牧神学等都要从中寻找根源。也就是说,在神学领域内,与信仰生存相关的神学为在存在者层次上发问的神学学科奠基,前者是后者的源泉。既然如此,神学是不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生存论哲学处于同一层次呢?不是。因为信仰虽然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但是“是在那种首先在信仰中并且只为信仰而揭示自身的历史中的历史性存在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奥特等:《海德格尔与神学》,第12页。。也就是说,信仰已经是某个特定领域的生存经验,尽管这个领域不是存在者的实质领域,但也不在以澄清存在意义为基本任务的存在论层面上。所以,“根据其特殊的实证性和由此而先行标画出来的认识形式,神学乃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存在状态上的学科”*海德格尔、奥特等:《海德格尔与神学》,第17页。。那么这种存在状态上的*“存在状态上的”德文词是“ontische”。在《存在与时间》的汉译本中,被译作“存在者层次上的”。然而,在《现象学与神学》一文中,孙周兴先生将该词译为“存在状态上的”。鉴于本文语境,取后种译法。科学与存在论—生存论哲学又处于何种关系中呢?它们之间的奠基关系有什么不同?
神学既然绝对地源自信仰,它便无需也不可借助非神学的学科。不仅其内容的获得,而且其命题的证明都需从神学本身中生长出来。如此,哲学当怎样面对此等仿佛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科学?实际上,神学的这种“绝缘性”只是存在状态上的。就现实的生存经验而言,罪、恩典、救赎等基督教特有的存在方式只有在信仰的生存活动中才是可领会的。一个信仰者不需要求助于信仰之外的经验或科学便能充分理解这种生存。然而,这并不表示在存在论层面上,信仰的生存与前信仰生存经验毫无关系。哲学对神学的奠基意义毋宁在于指示出信仰与前信仰的关联,以便神学在概念上阐明信仰时,注意到它所使用的“一切基本概念的阐明恰恰都致力于在其原始整体性中去洞察的原初的、自足的存在联系,……并且不断地把这种存在联系保持在眼帘中”*海德格尔、奥特等:《海德格尔与神学》,第19页。。哲学能够指示这种关联,因为它关注的不是此在在某个特定领域中的生存方式,如信仰,而是将存在的意义展现出来的此在之生存结构。由于这种存在论的眼光,哲学可以看到信仰作为此在的生存恰恰包含着可纯粹从理性上把握的前基督教的内容,而神学概念也必然蕴含着对存在的领会,因为信仰中的此在只要生存着,就有从自身而来的存在领会。
神学与前神学、信仰与前信仰的连续性是不是说神学必须以生存论分析为范例来阐明信仰呢?这样理解与其说伤害了神学,不如说伤害了海德格尔。因为它的前提是,生存论分析是在生存状态上探讨此在的生存方式,它们作为具体的生存经验相对于信仰而言是前信仰的。虽然按照海德格尔的意图,此在的基本结构越是原始地得到存在论上的揭示,就越能明晰地阐明信仰的内容,但是哲学只是从存在论上作为引线指示神学,而不是从此在的生存结构中直接演绎出信仰的内容。哲学之所以能充当引线,因为它把此在的生存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收入眼帘,从而能看见信仰作为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处在哪一个存在论的区域,以及它与其他生存方式的关联。就此而言,存在论哲学对神学的意义在于指明这种形式关联,而根本不涉及生存状态上的经验,更不提事实层面的存在者。这种形式化指引“起源于纯粹姿态关联本身的关联意义,而决不起源于‘一般什么内容’”*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赖堡文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69页。,从而“不受制于事实状态”*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赖堡文选》,第68页。。因此,神学的内容仍由启示的信仰决定,生存哲学为神学奠基丝毫不损害后者的独立性和启示性。
三、 布尔特曼的主张:哲学指引神学
尽管一再遭到误解,布尔特曼却不遗余力地为生存哲学之神学意义辩护。原因在于,他看到前者作为一种“形式指引”对后者而言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神学自身不可能去讨论的,因为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
与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神学也以某个实在(Positum)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然而,布尔特曼所说的“实在”不是现成对象,相反,它作为神学之课题必须是使得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或历史现象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的(神学的)对象不是作为历史现象(Erscheinung)的基督教,而是那使基督教首先成为基督教,然后把基督教和神学本身建构起来的东西。”*Rudolf Bultmann.Theologische Enzyklopädie.Herausgegeben von Eberhard Jüngel und Klaus W.Müller,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84,S.12.这个东西,布尔特曼称其为“基督性(Christlichkeit)”。
布尔特曼不认同把基督的十字架事件视为一个历史上的事情,他提出解神话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化解历史耶稣的考证工作对神学和信仰带来的危机。布尔特曼用宣道的基督替代历史的耶稣作为神学的中心:基督不是我们可以置身其外加以考证的对象,而是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在生存中证实的历史性启示事件。信仰的关键在于“基督是历史性的事件”*布尔特曼:《信仰与理解》卷1,第316页。,而这是通过宣道得以实现的。基督性不是关于基督的思辨学说,而是“宣道、召唤。……在宣道中,救恩事件在倾听者面前成为当下,上帝通过基督设立的复和对他来说成为当下现实”*布尔特曼:《信仰与理解》卷1,第318页。。之所以是“当下现实”,因为基督事件同时是宣道的倾听者参与其中的生存事件,是过去与当下的相遇。所以,仅仅对基督采取某种观点,甚至发生某种情感算不上信仰,因为信仰只能是信者不断去顺从基督的生存活动。故此,扎根于这种信仰生存活动之中的神学,即生存神学,必定是一种存在—生存状态上的实证科学。
既然神学是实证科学,那么就必须以生存论分析为“指引”。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首先,哲学向神学指引人是一种能在。无论哲学与神学在旨趣上如何相去甚远,它们共有同一个研究主题——此在,即人。哲学虽不以信仰的此在为探讨主题,但是“因为有信仰的此在无论如何还是此在;即使信仰者也是能产生信仰的宣道以人言的方式所遭遇到的人”*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Ausgewählt,eingel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Andreas Lindemann,Tübingen:Mohr Siebeck,2002,S.63.。信仰绝非魔幻式的变换,并没有把某种全新的品质或超能力带给我们,一个决定相信基督的人,没有变成超自然的人,以至于生存论分析所揭示的结构对他失去意义。毋宁说,“如果此在通过不断把握他的可能性而生存着,那么信仰就是此在的一种不断重新把握的可能性”*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6.。信仰者在存在—生存状态上的活动可能发生改变,例如脱掉过去的生活习惯,转变思维方式等,但“这不是说,生存的生存论—存在论的条件不复存在了”*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6.。因为,无论一个人如何去存在,他首先总是在世界中的可能性存在,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切科学包括神学的探索才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所以当布尔特曼声称“神学作为科学可以从哲学的此在分析中获得累累硕果”*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3.,这绝非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毋宁说,他不得不关注生存哲学,因为后者揭示了他的神学工作必须以之为出发点的事情本身。如果这里还要在旧神学的窠臼中,为了保卫神学的纯洁性而意气用事,那么必将错失“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当我们把眼光落实到现实生存时,信仰的此在和信仰前的此在,以至于神学与哲学之间并没有断然鸿沟。故而当神学与哲学发生关联时,其实并不损害前者的独立性,更不会损害上帝的启示恩典对信仰的决定性。因为探寻存在意义的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同一层次上的内容的替换或增添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毋宁在于,当神学就此在与一个特定的存在者(基督性)的关系探讨此在的生存或此在之“在”时,必定还是由某种存在领会所引导,因此必须预设某种存在的意义,而哲学的任务正是探寻存在意义的源泉。
其次,生存哲学从存在论的层面向神学指引此在的各种可能性条件。生存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存神学的前理解,同时又不损害后者的独立性,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存在论的标志;也就是说,哲学家根本不考虑,在此在中是否可能发生信或不信这类的事情。如果哲学家去反思这类现象,那么他就只能说,他的分析指明了一个人采取信或不信的可能性条件”*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0.。换言之,信和不信是一个具体的此在在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宣道而做出的两种回应。单从存在—生存状态上来看,仅有当下的发生:要么接受相信,要么拒绝不信,因而“根本无法就存在状态上的可能性说些什么”*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3.。 但是一个此在即使选择不信,也并不排除他在存在论—生存论层面具有成为信仰者的可能性,反之亦然。所以说,只有对在存在论—生存论上是可能性存在的此在而言,他的存在—生存状态上的选择——信或不信——才是有意义的。和一个不信者谈恩典、赦罪,即使他仍旧不信,却是有意义的,但这种谈论对一个物或动物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尽管“哲学的主题实际上不是生存而是生存性(Existentialitaet),不是实际而是实际性;它着眼于生存性研究生存,但它不谈论具体的生存”*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2.,但是“每一个存在状态上的经验在此在的结构中拥有它的可能性的存在论条件,因此可以从这个结构出发作为可能性被理解”*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72.。尽管揭示此在生存结构不能产生信仰,但是,哲学的工作对于从理论上说明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生存哲学向神学指引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存在论—生存论的分析是为探寻存在的意义,但它不是有关存在的理论演绎体系。如果这种分析声称自己已经完全把存在的意义摆于眼前了,那么这样的哲学是不能用的,因为“它想为此在的问题,即‘真理是什么?’提供一个普遍的答案”*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72.。生存哲学之所以吸引布尔特曼,恰在于它拒绝了这种哲学模式。生存哲学拒绝就生存提出一个普遍有效的定义,真理不是在生存之外指导我们如何去生存的原则,而就是生存本身的展开和澄明。对于主宰西方哲学几千年的形而上学思维,这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思维革命。所以严格说来,生存哲学令布尔特曼看重的从根本上说不是它的具体内容,而是它所蕴含的这种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摧毁性力量。哲学的此在分析“恰恰要指明唯有具体的此在本身能追问它的‘意义’,即提出‘什么是真理?’,而且不得不做出回答。对哲学而言,这恰恰意味着指明此在的‘意义’,亦即指出,当谈论此在时,此在意味着什么,存在具有何种‘意义’”*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4.。所以,当主张神学应该向哲学学习时,其实根本谈不上学习,因为这样的哲学并没有向神学提供理论体系。神学“不是要把哲学的体系或教条接过来,而是让哲学把现象指示于它;让现象来教导它,即让此在来教导它”*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4.。
让现象来教导神学,何谓现象?我们都知道布尔特曼关注生存哲学,可能不知他也很关注现象学,他甚至认为不关注现象学是巴特的一大失误*Cf.Bernd Jaspert.Karl Barth-Rudolf Bultmann Letters 1922-1966.Translated by Geoffery W.Bromiley,Michigan: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71,p.38.。因为现象学因其全新的哲学旨趣和思维方式终结了旧有哲学的宏伟抱负。“今天根本不再有可以包罗万象的科学系统和世界观体系,一切都是从存在的根据出发得到理解的。”*Rudolf Bultmann.Theologische Enzyklopädie.,S.7.追问存在就是履行现象学的宣言:面向事情本身。在传统的哲学体系中,事情本身被忽略了,只有现象学能赋予我们一种态度使我们从自己构建的哲学大厦中苏醒过来,回到现实的事情本身,即“在不同生活领域中发生效用的生活的实在性(Realitat des Lebens)”*Rudolf Bultmann.Theologische Enzyklopädie.,S.7.。可见,布尔特曼之所以关注生存哲学,是因为它所指引的现象。神学一旦学会去看这个现象,它既不会期待“哲学为自己提供一个它可以任意拿来使用的终极的规范存在论”*Rudolf Bultmann.Neues Testament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S.64~65.,也不会指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达到绝对的知识。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一样,布尔特曼的解神话也永远是在途中的经验活动,这不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看到的现象所致。
结 语
神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较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当这个问题通过海德格尔与布尔特曼的关系再现于20世纪时,能否从他们共同关注的解释学问题为它注入新的生机呢?我们不妨从解释学的角度来总结生存哲学与生存神学的关系。第一,从解释学经验来看,由于信仰经验与前信仰经验都属于人的历史性,因此它们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就此而言,信仰经验同样是在生存哲学所描述的生存论结构中发生着的。神学必须向哲学学习不代表向哲学屈服,或把神学人本化,因为后者展现的是神学必定扎根其中,从而以之为前理解的事情本身,而不是某种与信仰毫不相干甚至截然对立的生存状态上的经验,更不是某种关于信仰的理论知识。第二,从解释学方法来看,生存哲学是在“形式指引”的意义上作为解神话的前理解,即在不涉及具体经验和内容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指示生存经验的可能性条件来导引圣经解释。因此,生存论的解经必须把生存论结构的分析始终保持在眼帘之中。生存论解经实际上是遵循生存论分析的形式指引谈论圣经自身所描述的生存经验。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后者对所有生存状态上的经验都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