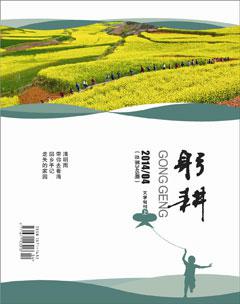青铜器上的冷艳
◆ 路 军
青铜器上的冷艳
◆ 路 军
此时,冬的残影依然固执地印在北方的山川田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沉积的历史符号到底有多少种,每每在历史的深邃时空中眺望,凝视,我的心灵都像一根颤动的弦,不时发出嘤嘤嗡嗡的声音,有时候,又好像一道智慧的光焰瞬间照亮你的迷茫与无知,一扇门就此重重地打开了。
山戎民族成为我的一个聚焦点,虽然,他们的身影早已经消失在漫漫的北国,当沉下心来,我仿佛依然能听见他们的絮絮话语,依然看见他们烈烈勇武的擎天之剑,在美丽的时空中智慧地妆点。纷乱与沉静,粗犷与细腻,力量与柔软,许多无以言表的词汇一起在我的脑海中碰撞,交织,就像3000年前,他们在北国的天空中纵横驰骋、疾如闪电的震颤。
或许应该感谢自己执着地创作《一座山的历史厚度》等历史文化散文,得以认真地阅读与思考。杂乱琐碎的史料,凌乱如麻的思绪,智慧的激情火花,虔诚的膜拜,舒心漫卷的笑容,种种情愫如山涧之风,浩浩荡荡而来,又席卷而去,消失的背影之后,则清晰地灼刻着或深或浅的对于冀北一些古老民族的解读。
有多少种草就有多少个民族。冀北草原的温厚养育了一个个民族,无论他们身处草原、山地还是平原,就像山间溪水,不能阻挡它坚毅而憧憬的脚步。
当黄河流域的唐尧夜观天象、设置谏鼓、协调九族、以鲧治水之际,离黄河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茂密的丛林,云天之下高高的草甸,孕育出生了一个民族----山戎。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面对苍茫寥廓的草原,郁郁菁菁的森林,山涧跳跃的溪水,团团如星的小花,皴染如墨的树林,他们的心中一定会生发出许许多多的属于民族孩童年龄特有的天真与幻想。美丽属于民族的天性,纵然世间横亘着多少的崎岖山岭,陡崖之上盘旋着多少的猎鹰,山谷激荡着多少的雷鸣,似乎都不能阻挡任何一个民族对于未来生活的美丽憧憬与梦想。
只是,这样的梦想就像在刀锋上跳舞,稍不留意就会割裂肌肤,酿成血淋淋的苦酒。在山戎的身旁,还有猃狁、荤粥等民族,在看似广袤实则举步维艰的环境中,一个个孩童的憧憬眼神中夹杂着迷乱、惶恐、挣扎、奋争的光焰。自然几乎没有馈赠,有的只是浩荡奔流的河水,茂密幽深的树林,虎豹出没的哮吼,苍鹰展翅的孤独,水中腐烂千年的一根根木头……这片区域不会安静,美丽像一颗天生孱弱的小草,在疾风劲雨中经受考验。
在民族的野性因子的驱使中,争斗与杀伐不可避免。仿佛河边厮杀不已的角马,在沉重的撞击声中穿透草原的宁静。一幕戏剧的开始并非只有欢歌,而是野蛮和惨烈。同时挤压与碰撞又如草原上奔驰的骏马,瞬间的力与美完全地释放。我一直以为战争与美丽水火不容,而仔细审视山戎民族的有限记载,不断的抗争与侵伐提升了美的高度与厚度。然而有限的能量也大大延缓了美的长度,就像一位饮鸩止渴的壮士,在埋头一饮而尽的时刻,他的目光最初闪烁的火花顷刻就像在山崩地裂中倾覆的房屋,苦心修筑,却荡然无存。乱石瓦砾埋藏于厚厚的尘埃泥土之中。
山戎民族的臂膀在与周围的其他民族的较量中越来越粗壮,民族的审美细胞越来越丰富,那是凭借石头的硬度与锐利磨砺而成,是与自然的风雨搏斗而砥砺而成,与异族的角力中淬火而成。我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天,男人与女人的角色一下子明晰如天空中的太阳与月亮,如山间盘旋的苍鹰与大雁,如同溪水中的游鱼与细石,如河畔绽放的兰花与展翅翩飞的蝴蝶。
当山戎一路向东,像桑叶上的春蚕不断咀嚼,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激烈碰撞开始了,在烈焰烽火中,美丽的种子落在冀北大地上,如遇甘霖,开始慢慢发芽滋长。
或许,那一炉炉的青铜冶炼的火光像暗夜中的启明星,早已经吸引了山戎的目光,或许,在与中原民族的激烈角逐中,石箭簇的奔跑脚步总是远远地被犀利的青铜箭矢落在后面,疾驰如飞的烈烈战马上的勇士如击穿胸膛的苍鹰,飞落于地。在紧紧抱起死去的士兵的那一刻,他们注意到了死者身上的一枚枚青色血色交织的箭矢,山戎的士兵惊骇的眼神中放射出探求的光亮,窘迫与伤痛像一堆散乱的木柴,一道划破天宇的雷电瞬间可以点燃一个民族的奇异思维火花。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明智慧的浸润一点一点被山戎吸收。斗转星移,青铜冶炼的符号被山戎民族慢慢破解,当第一炉青铜水的冷艳光芒闪耀在漆黑的夜空,一个民族的新时代到来了。骑术剽悍的部族士兵如虎添翼,一柄柄寒光四射的青铜短剑,一枚枚锋利无比的青铜箭簇,一件件坚硬锐利的长戈在与冀北外族的较量中占据上风。当骁勇善战的山戎骑兵拓疆扩土时,居于后方的女人们渐渐有了平静呼吸的空间,审美细胞像远山升起的太阳洒下的万道光芒,一点点投射在眼前。在一次次锻造打磨短剑、戈、箭簇、球形敦、鼎、马镫、铃铛等等器物的劳作间隙中,她们的目光时常在溪水河畔游走,像疲倦的小鸟栖息在树上。
自然界如高明的魔法师,以奇幻斑斓的色彩,舒展如云的轨迹,繁密如星的花草,灵动的野兽,凝固震撼的死亡,席卷天空的雷暴,等等,一次次或激荡、或平静地启迪着工匠们的艺术灵感。在与自然的审美交流中,山戎的艺术创造力如雨后春笋,拔节生长,仿佛田野中盛开的花儿,璀璨夺目。
他们的眼神一次次停留在自然的广阔舞台上,如同汲泉而饮的壮士,吸取着无尽的营养,青铜的冷艳光芒与自然界的活力与神秘融合在一起,散乱的艺术碎片在时间的长河中衔接、定型,如同缝制一件精美的衣衫。第一束艺术的光芒落在寒光冷艳的青铜短剑上,在蓬断草枯,烽火狼烟的冀北战场,它早已经锐不可挡,威震北国,他们希望再给青铜短剑平添一份力量,于是,深受祖先膜拜的“龙”的图案嵌在短剑之上,流畅的线条,蟠曲回旋的姿态,就像神秘的符号与暗示,根植在勇士们的心里。我不知道,那些手执短剑厮杀的勇士们在鼙鼓惊雁中左突右杀,擎天一剑劈长空,驰骋疆场之际,是否有一丝微笑献给站在家园门前深情凝望远方的那些女人们。
艺术细胞一旦在深厚的泥土中发芽、破土而出,即使怎样的风雨波折也似乎不能阻挡它的成长,山戎民族在冀北极大地释放自己的艺术力量与想象力、创造力。只是这一回,在戎马倥偬的间歇,他们与妻子儿女漫步野花草丛间,溪水流石畔,耳畔飘来嘤嘤鸟鸣,林间闪跃小动物的身影,平静的生活养育着温润的艺术。忽然,他们的审美情趣久久地停留在自己身上的兽皮衣服上,单调中需要美丽的装饰,那一瞬间,艺术的思维彻底打开。
这真是一个爱美到了极致的民族,我在一部短片中看到,他们凭借耐心与细心,凭借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在冀北的山地中、丛林中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饰物,这样的美丽妆点与战场上的彪悍与惨烈竟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既崇尚勇武,崇尚力量,崇尚胆魄的民族,又是一个憧憬美好生活,祈望神灵护佑,追求时尚与美丽的民族。山戎民族的多重性格真像冀北山地中的团团的山花耀眼夺目。
冷艳的青铜,温润的玉石,无痕的虎骨,小巧玲珑的贝壳,稀缺贵重的金子等等,都在精巧的艺术构思中得到完美的组接与呈现,美得冷艳,美得华贵,美得令人震撼而又令人深思。
2、3千年前的冀北,远非今天的景象,山峦叠嶂,绿意葱茏,溪水鸣唱,野兽出没,即使惨烈的战事惊天动地,在自然的广袤空间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寥廓与苍茫,神秘与威严,从容与豁达,影响着冀北山戎民族的审美心理。

或许,站在溪畔想以缯网捞鱼的那一刻,一只只鼓腮而鸣的青蛙,河水中游来游去的数不清的小蝌蚪摇曳着他们的心扉,于是,一连串的奇幻符号在思维的河流中徜徉,荡漾起层层的水波。跳跃灵动的姿态,弱小而不断繁衍的生命力在他们的头脑中如流星一一闪现,一枚枚圆形的青铜牌饰在熊熊的烈火中淬炼而生,女人们神圣地缝制在出征的男人的衣服上,一针一线,一线一针,缝得那样地仔细和缓慢。她们祈求神灵护佑自己的丈夫在战场上安然无恙,平安归来。
或许,当细碎急促的马蹄声消失在远方,思念如同夜空中的月亮,愈发的明澈,银辉流泻多少个不眠之夜。女人们一次次领着孩子站在瑟瑟秋风中远眺隔着群山隔着云海的出征日久的丈夫,头顶上南归的大雁啁啾的鸣声拨动了心中那束颤抖的琴弦,泪眼模糊中一次次打湿那份难舍的牵念,于是,在青铜器的冷光中打磨出一只只振翅欲飞的小鸟,丝线相系,待丈夫归来,亲自将它佩戴在他的身上。只是,透过历史的迷雾,又有多少男儿血染疆场,留给远方妻子孩子的只是斜阳老树,光影迷乱,撕心裂肺的呐喊,手中冰冷的青铜小鸟的配饰。当她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眼里的最后一束光芒已经化作了一只飞翔的青铜小鸟。
艺术的想象力空间充塞着许许多多世俗而又高贵的祈望,它就像滋养艺术审美力的情感符号,虽然历经千年的掩埋,依然闪着冷艳的光芒。
青铜之火在冀北燃烧了很久,山戎民族守着一份沉甸甸的上天的赏赐,守着一份祖先一代代传下的荣耀,守着越来越精美的青铜装饰,也守着冷艳的短剑,长戈的光芒。骁勇的骑兵如北方的苍狼,在草原横行无忌,聚集的能量如膨胀的气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当他们的眼神落在农耕文明的富庶之地燕齐时,他们不知道凶险就在眼前。
他们或许早已经淡忘了冀北田地中生长的谷粟景象,早已经忘记了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时,石犁的难堪,石锄的蠢笨,石镰的羞涩,石刀的无奈与叹息。农耕的田野几乎望不到一点青铜的影子,刀剑碰撞的冰冷已经淹没了田野中谷粟拔节的清脆声音和温暖。粮仓中曾不盈寸的谷粟并没有唤醒山戎民族的觉醒,他们的眼睛早已经盯上了远远的燕国与齐国,希望以掠夺拯救逐渐胀大的胃口。
冀北山地的青铜之火彻夜燃烧,蓝色烟霭中步履艰难的青铜仿佛误入迷途的臆想者,疲惫地在两条道路上艰难地爬行:青铜短剑,长戈;青铜饰物。可以想见,内聚之力贫乏的以游牧为主的山戎民族在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与精神,元气大伤乃至病入膏肓,直至走向死亡已成必然。勇敢与时尚如刀锋之舞,只需一瞬间刺入咽喉。
战国晚期,当燕齐大军高举寒光闪闪的铁制刀剑,长矛,挥师北上,累累秋风中的山戎手中的青铜短剑再也无力阻挡,清脆而又沉重的碰撞声中,一只只青铜短剑如秋风中折断的树枝,与死去的士兵一同落在泥土上,在时空中零落成泥碾作尘,锈迹斑斑裹住了冷艳的光芒。
一个时代结束了,铁器的光芒开始闪耀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