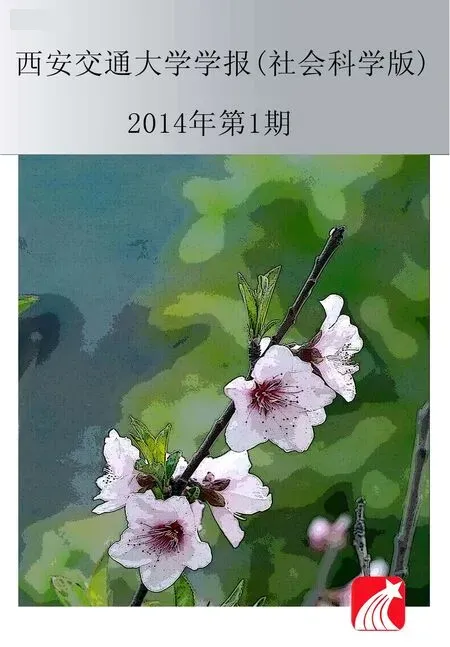论宋词与宋杂剧的交流互动
曲向红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杂剧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李德裕《李文饶文集·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曾提及唐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南诏攻掠成都,“音乐伎巧,无不荡尽”[1],其中就有“杂剧丈夫两人”被掳走。此处的杂剧当指百戏、参军戏之类的伎艺。至宋,对杂剧及驳杂的定义仍然不严格。本文试图探讨宋词与宋杂剧的互动关系。
一、宋词对宋杂剧的影响
(一)宋杂剧充分吸收宋词的词调
宋代对杂剧的定义并不严格。从广义上讲,杂剧就是对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宋末,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了“官本杂剧段数”280种。这里的杂剧即指歌舞戏。而文人笔记谈录里记载的滑稽片段,都是滑稽戏的一部分。如《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2]其中的杂剧即是傀儡戏。明祝允明在《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3]徐渭在《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4]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所指均是南戏。这些包含驳杂的宋杂剧在演唱歌舞时就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宋词词调。王国维考证《武林旧事》记载的280个官本杂剧,指出:“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5]47可见,吸收了词调的杂剧占了官本杂剧的一半以上。这充分显示出了当时流行的文学样式宋词在音乐曲调上对杂剧的支撑作用。有温州杂剧之称的南戏在词调上也来源于宋词。如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实乃“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4]。其音乐也与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词俗曲有解不开的渊源关系。因为文献缺乏的缘故,这些词调如何镶嵌在杂剧中现在仍难以考证的,但就像说话艺术吸收的词大多为俗词一样,进入杂剧的中的词调多半也是民间流行的通俗词调。
(二)宋词的题材为后世杂剧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元素
俳谐词中有以才疏学浅的举子应试时的困窘落魄取乐的《青玉案》(咏举子赴省):“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试盝袱头谁与度。八厢儿事,两员值殿,怀挟无藏处。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6]4638该词以漫画般的笔法对汲汲功名的士人打趣取笑,并予以有力地嘲讽,滑稽万分又有余味。其中有“八厢儿事,两员值殿,怀挟无藏处”。描写进考考生想挟带小抄度过难关,无奈进入考场时有兵士严格审查、武官监督,无法将小抄带入考场的着急窘迫。“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叙说考生作弊无望又腹中空空,在场屋中只能文思枯竭,一筹莫展,胡写几句敷衍了事的愁苦无奈。“半盂馊饭”则显示出考生的困窘落魄、苦不堪言。这一幅幅画面连接起来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效果。此词为明代冯惟敏《不伏老》杂剧所吸收,成为戏曲史上首部以科举考试为题材的作品。《不伏老》以科举为表现内容,描绘了北宋初年文士梁颢一生白首功名,屡试不第,虽双鬓皤然,仍壮志长存,气概不灭,终在82岁时高中状元的故事。《宋史》列传第五十五有传,记载梁颢活了92岁。冯惟敏即据此虚构,创作《不伏老》并融入了作者自身科举失意的感慨以及对科举考试的反省。因为故事背景发生在宋代,又是以科举为主要表现内容,所以宋代俳谐词中对科举考试以及赶考士子的揶揄理所当然地被吸收进这部杂剧,成为其插科打诨、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如《不伏老》第一折写科场里应试举子进考场先要忍受搜身之辱,“进了门,耳边厢,喝一声‘仔细搜’!则被他捏捏挪挪,搜检那袖儿里排筵(夹带、小抄)。”[7]479从而使夹带的小抄无处可藏。考生在答题时一个个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一个家丧气消魂,不是病,不是痛,可又早皮里抽肉;一个家搜肠刮肚,不知饥,不知渴,只觉得口内生烟。”[7]480痛苦之状不可名状,让人哑然失笑;快到交卷时间了,又有人不断地催他们抓紧时间,快点答题,“过了晌,头直上喊几阵‘上紧写’!则被他击击聒聒,比并得眼儿中灼火。”[7]479考生考试时的饭菜伙食更是猪狗不如。“半生不熟干饭团,这的是太仓多年老米;连泥带土托腮骨,元来是天津道地干鱼。放下的你一双,我一双,隔年陈,那讨一个儿可口馒头;端着的东半碗,西半碗,腥泔水,却有几点儿连毛汤料。”[7]479-480这些以被功名折腾得鸡犬不如的举子为嘲笑对象的长篇诨白,完全是以他们考试时的绞尽脑汁、困窘难受来制造笑料的,并与俳谐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很显然,《不伏老》是吸收了宋代俳谐词的营养,或者说宋代俳谐词为其提供了虚构、构思的灵感与源泉。
二、宋杂剧对宋词的影响
(一)宋杂剧的流行使宋词的内容得到充实和扩展
1.宋词中出现了表现宋杂剧以及杂剧艺人的内容。黄庭坚有《鼓笛令》四首,其第四首下片云:“副靖传语木大。鼓儿里、且打一和。更有些儿得处啰。烧沙糖、香药添和。”[6]526副靖(副净)、木大(木头疙瘩、木头木脑的人,即副末)就是宋杂剧的两个角色,如《梦梁录》卷二十云:“且谓杂剧中以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8]177,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五个角色中副净、副末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接下来“鼓儿里、且打一和”即“打和鼓”以及“更有些儿得处啰。烧沙糖、香药添和”的“叫果子”吆喝卖沙糖,这显然是“属于嘌唱、散耍之类的宋杂扮演出”[9],即宋杂剧的散段。宋杂剧往往前有艳段,中间是正杂剧,末尾有散段。如《都城纪胜》云:“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城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10]10即是说像“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等皆在杂扮即杂剧散段表演的伎艺之列。
南宋张炎《蝶恋花》(题末色褚仲良写真)写到的则是宋杂剧中的末色。即末泥这一角色的表演情况。“济楚衣裳眉目秀。活脱梨园,子弟家声旧。诨砌随机开笑口。筵前戏谏从来有。戛玉敲金裁锦绣。引得传情,恼得娇娥瘦。离合悲欢成正偶。明珠一颗盘中走。”[6]4426这首词表现的就是杂剧中末色上场时的妆扮及其表演时要念白、打诨、歌唱,等等,堪称研究宋杂剧的重要资料。还有无名氏《贺圣朝》(预赏元宵):“太平无事,四边宁静狼烟眇。国泰民安,谩说尧舜禹汤好。万民翘望彩都门,龙灯凤烛相照。只听得教坊杂剧欢笑,美人巧。”[6]4653这是宋词经常表现的对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的讴歌。一方面,宋杂剧包含谐趣的表演效果,深受当时人们的喜欢;另一方面,宋词在表现太平盛世景象时也对当时杂剧的演出作了反映。这是杂剧对宋词题材的开拓,使宋词的表现内容更加广泛。由此,宋词不再仅仅是男女私情的吟唱,也不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襟怀抱负的抒写,而是成为还可以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底层的杂剧艺人及其表演。
2.宋杂剧艺人的角色扮演。宋杂剧这种舞台上的戏剧人生也使当时的词人生出了人生如戏之感。同时这也是继宋词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等感慨之外的又一种对人生的不同感受。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仕宦上的起伏荣辱,乃至国事上的无奈悲愤,皆可以用人生如戏加以消解。南渡词人朱敦儒有一首《念奴娇》:“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蕲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6]1082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到了年纪老大之时,他说自己看透了人间的名利愁苦:“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逢场作戏就是杂剧中非常流行的即兴表演。他叙说自己的人生就是在演出一场杂剧,演完了,戏衫就脱下还给班主,所谓的国事、社稷等都与自己无关了。很显然,宋杂剧的流行既丰富了词人的人生感受,也丰富了宋词表现的内容。还有“年少疏狂今已老。宴席散、杂剧打了。生向空来,死从空去,有何喜、有何烦恼。”(倪君奭《夜行船》)[6]4201“自在狂歌,□□□□,一场杂剧”(沈瀛《柳梢青》)[6]2139,“脱了戏衫还”(刘克庄《水调歌头》)[6]3309,“七月政成如戏剧”(毛滂《玉楼春》)[6]867,“逢场戏剧”(吴泳《摸鱼儿》)[6]3209,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在文人生活中有重要娱乐作用的宋杂剧对宋词的影响,使宋词在感慨人生时也可以借助宋杂剧的特点来表现其主题。
(二)宋杂剧插科打诨的表现手法被俳谐词所吸收
宋杂剧的主要特征是滑稽逗乐。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副净)发乔者,盖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而(副末)打诨,则益发挥之以成一笑柄也。”[5]62宋杂剧中的副净是假扮愚谬滑稽之状,副末是以伶牙俐齿、机智幽默对副净予以嘲弄取笑,使其滑稽之状愈发显而易见,惹人开怀。可见滑稽逗乐是宋杂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云,杂剧“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8]177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亦言,宋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10]9他们均指出宋杂剧具有滑稽幽默的特性以及娱乐消遣的作用。
宋代瓦舍勾栏的演艺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常常是互相影响和借鉴。《都城纪胜》载:“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10]11傀儡戏吸收了小说、讲史、戏剧等其他演艺形式的优点,影戏也吸收了讲史的优点。同样,在共同的文化土壤和表演环境里,小词也有可能吸收宋杂剧打诨的手法。今人赵万里在《校辑宋金元人词》“箕颖词”附录按语中云:“谑词见于小说、平话者居多,当时与雅词相对称。”宋世诸帝如徽宗、高宗均喜其体。《宣和遗事》、《岁时广记》载云。此外尚有俳词,亦两宋词体之一,与当时戏剧,实互相为用,此谈艺者所当知也。”[11]赵万里先生明确地指出了俳谐词与当时戏剧相互为用的关系。
1.宋代俳谐词以滑稽幽默的笔触叙述一件事时,在字里行间又透出嘲笑取乐的口吻,极像杂剧中副末的“发乔”与副净的“打诨”。俳谐词中的主人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别人的穷困窘迫、愚蠢荒谬为表现对象。如《青玉案》“钉鞋踏破祥符路”、无名氏《滴滴金》“当初亲下求言诏”[6]4638以及太学生《南乡子》[6]1933等词即是此类。另一类则是以自己的滑稽可笑、不合时俗为表现对象。如无名氏《结带巾》“头巾带”[6]4639等词,即是自我解嘲型的。第一类中的主人公极似副净这种扮丑搞笑的角色,而唱词的人除了要表现出其滑稽之状外,还要在字里行间通过伶牙俐齿对副净予以尽情揭露嘲讽,使其滑稽之状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产生幽默搞笑、令人捧腹的效果。第二类则是词作者将自我分身为二。一半表现自我的困境,一半则自我嘲弄,以此慰藉心灵,平复失衡的心理,同样可谓副净、副末的角色集于一身。无论是宋代俳谐词、宋杂剧,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它们要制造谐趣,首先必须要有滑稽可笑之人或事,其次还要能把这种丑拙滑稽当作“美”予以“欣赏”。因而,只有把这两方面相结合才能表现出嘲笑打趣的思想感情,才会产生滑稽之意趣。宋杂剧的两个角色副净和副末可谓分别担当了这两方面的功能,而俳谐词要制造谐趣、娱乐听众也必须要具备这两点才能插科打诨。因此,俳谐词类似副末“发乔”、副净“打诨”的写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词体发展中的自成,也可以看作是俳谐词与宋杂剧在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地互相靠拢。
宋俳谐词中还有一类对话体词,是直接以二人对话表现谐趣的,更能凸显戏剧功能。一方面,我们从中则能活生生地感受到杂剧中副净和副末的调侃取乐;另一方面,这也是俳谐词在发展过程中从宋杂剧吸取了营养的证明。辛弃疾的《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6]2471、《沁园春》(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6]2471都是采用主客问答的对话方式,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制造幽默戏谑的意趣。辛弃疾这种写法既有前代俳谐诗文赋的滋养。如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的《逐贫赋》、班固《答宾戏》等都是采用主客论辩的方式;还有唐代韩愈《毛颖传》等则采用拟人化的寓言,为毛笔立传封爵。这些都被辛弃疾创作时所吸收,从而首次创作出对话体词,采用大量的散文化句式大发议论,令人解颐。同时,则是当时兴盛的宋杂剧滑稽诙谐的表演方式给了他创作灵感与营养。如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词不怪自己贪杯,反倒怪罪酒杯跟随自己。词中有作者对酒杯严厉的谴责,其中也夹杂着对酒杯申辩的复述。其中最后三句“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呈现是酒杯唯唯诺诺、俯首听命,说麾之则去,招亦须来,表示愿随叫随到,这番“我”与杯的对答,活脱脱是杂剧中副净与副末通过语言、动作等娱人,而且其对话还有潜台词,富有余味。因此,这首词在宋词中堪称别树一帜之作。辛弃疾《鹊桥仙·赠鹭鸶》:“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任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6]2508《西江月·遣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6]2509等俳谐词中也吸收了对话体的手法。他在词中煞有介事地与鹭鸶、松树对话,这样既出人意料,也刻画了富有戏剧性的情节。
2.宋词吸收了杂剧“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的写法,喜欢以出人意料的转折语境以制造谐趣。如康与之《望江南》:“重阳日,四面雨垂垂。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路上水平脐。淹浸倒东篱。茱萸胖,黄菊湿齑齑。落帽孟嘉寻蒻笠,漉巾陶令买蓑衣。都道不如归。”[6]1687这首词是写重阳遇雨后狼狈不堪的景象,泥土溅到了肚皮,积水没到了肚脐,头上插的茱萸被雨水泡胖了,待赏的菊花被淋湿了;就连古代名士孟嘉、陶潜也是一副狼狈模样,一个急着找箬笠挡雨,另一个则急着买蓑衣披上,还都声声喊着“不如归”。“都道不如归”,这是对陶渊明千古流传的归隐之辞的引用,但置之重阳遇雨的语境中,便成了不如回家避雨之意。这就是采用了“打猛诨出”的写法,谐趣顿生,富有余味。
辛弃疾作为俳谐词写作的大家,他的很多词都灵活运用了“打猛诨出”的手法制造谐趣。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6]2428虽然结句“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是从白居易《白鹭诗》中化出来的,但如此收尾毫不拖泥带水,且浓挚深切。这也是采用了“打猛诨出”的写法。如其《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上片末句“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6]2539《洞 仙 歌 》结 句“争 知 道,他 家 有 个 西子。”[6]2498均是用“打猛诨出”的写法,突然收尾,从而产生了既滑稽戏谑又意犹未尽的效果。
宋词作为抒情性文体与宋杂剧等民间叙事文学交流互动,不仅吸收了宋杂剧的插科打诨,而且学习了宋杂剧的打猛诨出——以出人意料的转折结束全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宋词的俗化,而这些俳谐词作为俗化了的宋词也为杂剧提供了构思的灵感和源泉。同时,宋词中那些通俗的曲调也为杂剧吸收,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我们厘清雅词是以文为词、以诗为词,与抒情文学诗文互相学习;而俗词则是与杂剧等叙事文学交流互动。由此,我们即可看出:宋词发展具有雅化和俗化两条线索,雅化是为学界所公认的,而俗化则是为人所忽视的。俗化虽然是词坛潜流,但如果忽略宋词的俗化,那么从愈益雅化的宋词一下子到金元时代俗文学铺天盖地的繁荣,这其间的骤然转变是难以解释的。文学的发展毕竟有自身的规律,这不是朝代更替、时代变化等外因就能解释的。
[1]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三部第四册[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7996.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32.
[3] 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65.
[4] 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585.
[5]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6]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 冯惟敏.冯惟敏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8]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9] 苏子裕.宋杂剧、杂扮与南戏、北杂剧的行当体制:兼考酸孤旦[J].戏剧.1998(2):105.
[10] 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11] 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