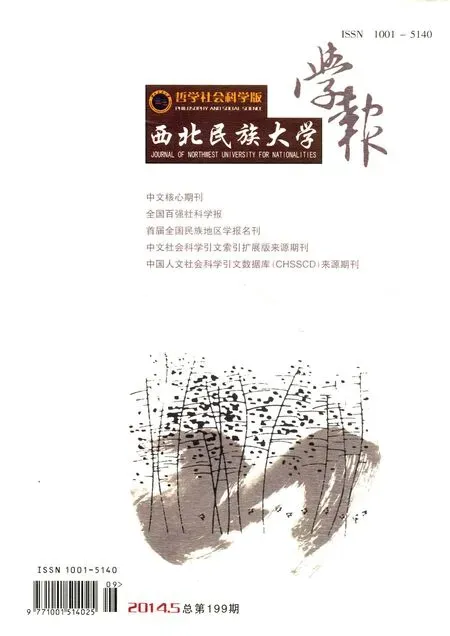彼得·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
张计连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云南 昆明650091)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种族主义,不管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他者”表现,还是文学经典刻意使得种族差异边缘化的做法,都对澳大利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的澳大利亚是欧洲种族主义扎根、疯长、泛滥的根据地。殖民地澳洲的一位政客撰文写道:“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喀纳喀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1]澳大利亚公开宣称,为了保持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不允许在它的人口中加入任何本性和品质低劣的成员。……绝对不能促成或准许其他种族的人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选举权、公民权以及包括婚姻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给予他们之中的任何人”[2]。19世纪末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新闻公报》喊出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3]“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亚真正施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基础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的,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民族精英集团仍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和成就的象征。”[5]彼得·凯里那些反映澳洲历史的作品充分展现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这些种族主义症候。
今天的澳大利亚是个多民族的、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在澳大利亚2 000多万人口里包含了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在短短200多年的历史里,经历了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三个阶段。澳大利亚从英国的罪犯流放地到独立的民族国家,期间澳大利亚人的心路历程颇为曲折,有被影响的焦虑也有反影响的行动。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是指一个国家中不同种族的人群或不同族裔的人群的社会政治认同。这是一个国家内部认同研究的一个关键文化维度,民族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民族文化的再现和作用下形成并且不断变化的。正如拉腊因所说,“阿尔都塞认为主体的产生和存在依靠意识形态,福科认为主体是权力关系产物,利奥塔认为主体是交往系统的‘结点’。这些思想要么怀疑潜在统一体的存在,要么怀疑某种能产生知识和实践的物质。”[6]由此,后现代主体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感,它已裂解为残破不全的一堆思想碎片。在后现代语境下探讨的民族认同,正如ethnic这个词包含了种族、民族和族裔三个方面的维度。因此,本文讨论的ethnic identity也包含了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和族裔认同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凯里小说反映的民族认同问题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殖民的移民社会,又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其民族认同问题非常复杂。澳大利亚历史上对澳洲土著人实施了屠杀、驱逐、隔绝、同化的种族主义政策,“白澳政策”的实施也给华裔等其他有色人种带来了种种灾难,就是白人内部也并非是全然和谐一致的认同,爱尔兰裔、德裔、意大利裔、犹太裔等族裔的澳大利亚人也在不同时期受到殖民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区别对待。因此,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包含了欧洲白人遭遇澳洲土著人之后形成的种族认同,澳大利亚人为与英国人、美国人等相区分而形成的民族认同,白澳内部的爱尔兰人的认同以及华裔、德裔等不同的族裔认同。彼得·凯里那些取材于澳大利亚历史和现实的小说,建构了一个丰富的民族认同世界。在凯里的那些小说里有白人和土著人的冲突,有白人对华裔的压制和迫害,也有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裔顽强不屈的抗争。
首先,彼得·凯里小说中反映了澳大利亚种族认同问题。“种族”(race)这一概念的主要功能在于区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范畴中,这一术语被译为“人种”,即根据基因导致的人体外部遗传标记,结合地理分布、生态和形态特征(如肤色和体质特征)、共同拥有的信念、习俗等因素,对人类群体进行某种分类[7]。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界说,“racial16世纪出现在英文里,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race及razza,最早的词源已不可考。……race这个词在现代社会、政治意涵里的暧昧性是导致它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之一。在种族的分类中,这个词一直被用来贬低非我族类的不同群体。”[8]英国学者布鲁克(Peter Brooker)在讨论“种族”时开篇就指出,种族是个有问题的范畴。……如果我们接受遗传表现的差异为种族认同的证据,就会发生复杂的麻烦,即不变的种族性质和类型,可以用来合理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假定的生物性之既定智商能力层级。生物上的区别在文化领域里,被挪用来确认种族的优越性。其结果便是某种形式的种族歧视[9]。
种族问题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和属性、社会、文化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相关的问题涉及身份、差异、文明、表征以及文本中大量有关种族化再生产的陈述话语。生活在澳洲大陆长达四万年之久的澳洲土著人遭遇了白人入侵者的屠杀、驱赶、隔绝、同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和联邦政府这些政策实施的基础就是种族主义。发源于西方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欧洲的种族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奥瑟罗》和《威尼斯商人》中可以看到16世纪的英国社会就盛行着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康德在他的《自然地理》(1802年)中强调地理环境对种族的影响,他说:“人类最完美的典范是白种人。黄种人、印第安人智商较低。黑人智商更低。部分美洲部落位于最底层。”[10]黑格尔将人类分为高加索人、埃塞尔比亚人和蒙古人,他说:“黑人头骨比蒙古人和高加索人要窄,额头呈拱形,有隆肉,下颌悬生,皮肤呈不同程度的黑色,头发黑而卷曲。”[11]欧洲这种强调种族文化内涵,譬如文化标准、价值、信仰与社会实践等,为种族主义的盛行提供了价值理念和衡量标准。此种观念认为,种族群体的形成依赖共通的文化符号,历史、语言与文化是构成民族特色的三角支架。斯图亚特·霍尔说:“种族这个术语承认:所有话语都依其地点、位置与情景而定,所有的知识都有其特定的语境,同时它也承认历史、语言、文化在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12]彼得·凯里的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和散文集《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30Days in Sydney:A Wildly Distorted Account)着重探讨了澳大利亚的种族认同问题。
其次,彼得·凯里小说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问题。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是指澳大利亚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不同族裔和族群在认同的冲突与融合之后达成基本一致的社会政治认同。虽然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种族、族裔由于不同历史境遇造成了他们的族群身份认同有很大的不同,但澳大利亚历经了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运动,成立了联邦政府,实行高度自治并且逐渐发展以移民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显然,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一种文化心理认同。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一方面依靠国家维护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作为想象共同体,它又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确保其文化统一。这些传统包括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文化象征、宗教仪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和暴力》中说,“民族主义本质上是18世纪晚期之后产生的现象。”[13]而殖民地精英阶层是后殖民认同的主导力量,它“为政治共同体提供了统一的心里聚集点。”[14]当然,探讨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必须回归到这个民族的历史之中。彼得·凯里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中发现了澳大利亚民族认同诸多症候,并且以小说故事的形式赋予其活生生的内容。《奥斯卡与露辛达》《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和《凯利帮真史》(The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3部取材于澳洲殖民史的小说分三个阶段展示了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
再次,彼得·凯里小说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族裔认同问题。族裔散居指以种族为纽带、生活在宗主国和第一世界的少数族裔,例如美国的黑人和华裔群体等。吉尔罗伊指出,族裔散居是一种混合身份认同,它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异体合成、混合以及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不纯文化形式。”[15]历史上的爱尔兰长期受到英国的侵略和压制,所以在澳洲同是白人后裔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经历了更加曲折和悲惨的命运。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这种历史遭遇使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为争取自由、民主权利不断反抗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凯利帮真史》这部小说的创作使彼得·凯里成为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之后的又一位两次荣膺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布克奖的作家。这部小说从民族政策方面质疑了澳大利亚的历史真实。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是“白澳”内部的“他者”[16]。从16世纪英国征服爱尔兰之后,爱尔兰人那种受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一直持续了下来,随着英国的海外扩张也扩散和撒播到澳洲大陆。《凯利帮真史》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小说主人公内德·凯利短暂的一生见证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悲惨生活及其受到的诸多不公正待遇。
现代性是造成族裔散居身份问题的主要原因。现代化、全球化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生死相搏、欧洲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狭路相逢。“它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结成异质关系,又与当下各种政治、经济、科技等问题纠缠不清,形同乱麻。”[17]拥有众多散居的族裔是澳大利亚社会中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华裔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华裔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直作为被看、被评说的对象,是在澳洲深受歧视和压迫的一个族裔。澳大利亚的这些社会问题,反映在在彼得·凯里的小说中表现出澳大利亚族裔认同的复杂性。澳国华裔研究可以从“形象学”入手。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专指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学问,法国学者巴柔(D.H.Pageaux)将其界定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18]因为一个作家或一群作家对异域进行的描绘是与作家生活在期间的社会紧密联系的,即巴柔所说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因而,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应注意与之相关文化领域的各个学科的材料。
异国形象可分为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换个角度说是对异邦的妖魔化和理想化。因此,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形象,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大利亚人的焦虑和憧憬,也有助于了解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建构中的中国形象,从而有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看待自身。虽然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彼得·凯里的作品中一直是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但几乎存在其所有的作品中。《美国梦》(American Dreams)中的中国劳工,《凯利帮真史》中由于语言文化的交流障碍常被白人攻击的华人,《魔术师》(Illywhacker)里神秘、超能的华人……彼得·凯里的创作打破了澳大利亚文学传统中类型化了的华人形象,揭示了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的真实处境。因此,他塑造的华人形象,既有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惯有的华人形象的某些特点,又有凯里自己的一些创新。
二、澳大利亚民族起源神话遭遇挑战
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里,“白澳政策”实际上实施了100多年,因此白色神话是澳大利亚人建构的民族起源神话。当代澳大利亚人面对澳洲土著争取公民权和土地所有权运动的时候,开始反思那段土著被驱逐和被抹杀的历史。他们发现,“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澳大利亚”不再变得那么理所当然,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四万年之久的澳洲土著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土著主题在彼得·凯里集中于他摘下1988年布克奖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奥斯卡与露辛达》以奥斯卡的曾孙为叙事者,这位叙事者在故事的开始以自己的家族史和周围的澳洲土著人的存在和言说为证,对澳大利亚官方记载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从而解构了澳大利亚的白色民族神话。格林布拉特在《回声与惊叹》中明确地说:“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19]凯里的所有创作都采取了一种介入姿态,时刻关注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土著问题是当代澳大利亚政坛各界领导人都必须关注的无法绕过的问题。
正如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澳洲土著人被排除在外一样,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澳洲土著人一直沉默,直到20世纪60至70年代才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从此土著作家、土著文学、土著主题开始引起澳大利亚文坛的注意。20世纪末,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白澳政策的取消、同化政策的消解、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澳洲土著人土地权和公民权的争取,澳总理为澳大利亚历史对澳洲土著的不公而郑重道歉等,越来越多的澳洲土著人、土著作家和作品得到关注。而彼得·凯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创作反映那段曾经被涂抹过、被消音过的历史,呈现曾经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被隐形的“看不见”的土著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与澳洲土地的深厚情感,他们的“梦幻时代”,他们的艺术创作……土著不再是澳大利亚社会的禁忌,是可以公开表达和被表达的澳洲社会中的一员。1988年,当澳大利亚人在纪念他们建国200周年的时候,土著人也在举行他们的一种纪念仪式——那是对白人入侵历史的纪念,他们哀悼的是澳洲土著人苦难历史的开端,正是从那时候起,他们被屠杀、被驱逐、被妖魔化,被从历史记录中消音。在这片古老大陆上演奏了四万多年的土著交响乐被白人的征服曲给压制了,被披上教袍、手持《圣经》的教士和枪炮给镇住了。
1770年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发现了澳洲东部,这是澳大利亚历史的开端。他描述道:“我们所看到的这片国土处于自然状态,人类和它毫无关系。”这种“无主之地”的假设为英国殖民者的入侵铺平了道路,也为他们剥夺土著人的土地找到了充分的理由。1788年1月26日,阿瑟·菲利普船长(Captain Arthur Phillip’s)率领11艘舰船数百名英国犯人在波坦尼湾(Botany Bay)登陆,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悉尼。澳洲大陆的宁静从此被打破。英国殖民者初抵澳洲大陆时,凭借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不理睬土著人的抗议,不经商量就宣布以英王的名义占领这块本来属于土著人的大陆。这些新来者从欧洲带来了传染病,成千上万的土著人死于天花、麻疹、流感和其他传染疾病。英国殖民者还对世代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人进行屠杀,并将他们赶到贫瘠、蛮荒之地,在那里建立保留地,强迫他们定居。在澳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存了几万年[20]的土著人从澳洲的主人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岛民来说,欧洲人的入侵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对其生活方式、健康、福祉和身份都造成了持久的后果。
历史毕竟是历史,无法重写。今天的澳大利亚现实就是澳大利亚是以白人为主的,包括澳洲土著人和其他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移民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是融合了白人主流文化和各少数族裔文化包括澳洲土著文化在内的集合体文化。发觉曾经被遗忘的历史,正视曾经被伤害过的人群,这才是正确对待澳洲土著的方式。作家彼得·凯里深谙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无数“谎言”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个谎言就是“澳大利亚是欧洲白人发现的无人居住的土地”,这个谎言掩盖了白人在入侵和开发澳大利亚过程中的所有暴力,屠杀、灭绝、强奸、驱逐……那么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澳洲土著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澳洲土著自己原有的文化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这些文化在今天的澳大利亚文化中又是怎样的处境,土著人怎样看待入侵这片大陆、剥夺他们的土地、屠杀和驱逐他们的白人,土著人怎样看待基督教文化,土著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两百年的澳洲历史?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感觉,现在有一部分土著作家在表现、表达和展示,但是这种声音需要回应,这种视角需要检验,这种感觉或情感需要共鸣,澳大利亚当代白人作家对土著主题的重视和挖掘使他们不再孤单。今天,作为澳大利亚人的白人和土著人在历史的伤痛处找到了对话的基点。
三、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危机和转机
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对土著居民的反映经历了一个从敌视、排斥到同情、理解的过程。早期作品中的土著居民一概被脸谱化,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是白人征服自然过程中面临的危险敌人之一。即使偶有同情土著居民的作品,如珍妮·冈恩(Jeannie Gunn)的《小黑公主》(The Little Black Princess,1905年)和《我们都脱离现实》(We of the Never-Never,1908年),作者也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感进行创作的。当然,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也出现过扎维尔·赫伯特的《卡普里柯尼亚》(Capricornia,1938年)那样的描写澳大利亚土著人、白人、华人之间的交融与冲突的力作。原始的生活、种族歧视、野蛮的行为、无法忍受的偏狭,故事对白人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所建立的“文明”的虚伪、冷酷和残忍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澳大利亚文坛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情况才发生了真正的改变,涌现出一批关注土著问题、代表土著居民呼声、反省白人过去不公正对待土著居民的作品。其中包括扎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1901年~1984年)的小说《可怜虫,我的国家》(Poor Fellow My Country,1975年)、玛丽·杜拉克(Mary Durack)的《留住他,我的祖国》(Keep Him My Country,1955年)、伦纳德·曼(Leonard Mann)的《混血维纳斯》(Venus Half-caste,1963年),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土著作家也开始在澳洲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著名的澳洲土著女作家凯思·沃克(Kath Walker,1920年~1993年)的诗歌《我们要走了》(We Are Going,1964年)标志着土著文学的开始,诗歌反映了作者对土著居民过去的怀恋,对白人所实施的种族清洗政策的愤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土著小说家柯林·约翰逊(Johnson Colin,1939年)的《野猫掉下来了》(Wild Cat Falling,1965年)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彼得·凯里并不孤单,《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年)出版的前一年,土著作家萨利·摩根(Sally Morgan,1951年-)的《我的位置》(My Place,1987年)在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销量达50万册。凯思·沃克在1988年为表示她对澳大利亚200周年庆典的抗议,改用自己部落的名字Oodgeroo Noonuccal,这与《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对土著问题的关注是相呼应的。近年来,澳大利亚土著问题成为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关注澳大利亚的焦点之一。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1936年-)的《石乡行》(2002年)继他的《浪子》(1992年)之后又一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这部小说站在历史的高度,展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随着历史的沿革、时代的发展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及为维护他们的权利进行艰苦的斗争,而曾经的殖民者的后裔也在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不懈努力。而他的《别了,那道风景》(Landscape of Farewell,2007年)则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高度对澳大利亚乃至全人类从古到今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些大屠杀包括二战中希特勒政府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白人对澳洲土著人的种族清洗,土著人对白人报复式的屠杀等。
1997年4月,人权及平等机会委员会(HREOC:the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的一份《带他们回家:关于土著和托雷斯岛屿居民的孩子和家庭分离的全国性调查报告》被提交给澳大利亚议会。这份报告给予777份呈递书,是对数千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屿居民的孩子从他们各自的家庭里被强行迁移的事实进行的问询(其中500份保密)。这是一份对后来被命名为“被偷走的一代”①“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澳大利亚白人政府于1910年至1970年间所实行的“同化政策”所影响的几代人。当年政府认为澳洲土著“低贱无知”,因此强行把总计十万名土著儿童永久性地送到白人家庭或政府机构照顾,以“白化”土著居民。不少白人家庭歧视、虐待、侵犯或迫使他们忘记其语言和文化,令大部分土著儿童及其家庭受到严重伤害。的人们在情感和身体上所受伤害的记录,令人感动且痛苦。“迁移”孩子的联邦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1992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裁定:英国政府在宣布主权时所用的“无主土地”的概念,“基于对土著居民的歧视诋毁之上”。6个月之后,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eting)对土著听众发表讲话说:“我们拿走了传统的土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带来了疾病和酒精。我们进行了杀戮。我们将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我们实行了歧视和排斥。”[21]基廷出于和解的精神列举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错误,坚称“承认历史真相无须恐惧,也无损失。”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基廷所说的每一点都受到了挑战,他的继任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拒绝了和解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1997年4月,在墨尔本召开的澳大利亚和解大会上,约翰·霍德华总理拒绝为过往政府的虐待而向澳大利亚土著道歉。大会听众起立,把他们的背转向总理,以身体沉默的抗议羞辱他。自那以后,霍德华总理还在很多场合拒绝说“道歉”。①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陆克文在国会三度正式向土著居民表示歉意,并承诺会改善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如减低其幼儿夭折率、提高其识字率和平均寿命等。
彼得·凯里对基廷敢于正视历史错误的态度极为赞赏,他早在小说《魔术师》《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已经发出了要澄清谎言、正视历史的号召,在《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中则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说:我们的总理可以拥抱,可以原谅曾经杀害了我们挚爱亲人的人们,所以他应该,但实际上没有也不会,向被屠杀和虐待了两百年的土著澳洲人道歉。他在加利波利说,和土耳其人的战斗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他在国内说,和土著澳洲人的战争很久以前就发生了。战斗塑造了我们,而赢得了大洲的战争最好忘掉[22]。
盖尔·琼斯(Gail Jones)的《抱歉》(Sorry,2007年)以小说的形式为白人过去的所作所为向澳洲土著人道歉。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在国会三度正式向“被偷走的一代”表示歉意,并承诺会改善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如减低其幼儿夭折率、提高其识字率和平均寿命等。作为作家的彼得·凯里是非常敏感的,在写作《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等我2000年回到悉尼时,整个火棍农业问题已愈演愈烈,火不仅界定了土地,也界定了政治气候。”[23]毫无疑问,澳洲土著问题成为彼得·凯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他的《奥斯卡与露辛达》则是对种族主义的控诉,对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重新审视。
[1][3][5]王宇博.珀西澳大利亚19世纪的民族认同[J].世界历史,2007,(6):111-121.
[2]M.威拉德.1920年以前的白澳政策史[M].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7.196.
[4]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33.
[6]Larrain,Jorge.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M].Polity Press,1991.149.
[7]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9.
[8][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75-378.
[9][英]彼得·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M].王志宏,李根芳 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324-325.
[10][11]Krell,David Farrell.The Bodies of Black Folk:From Kant and Hegel to Du Bois and Baldwin[J].Boundary2,vol27,no.3(2000):109.
[12]Hall,Stuart.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C].ed.D.Morley and K.Chen,Lodon:Routledge,1996.46.
[13][1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 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44,322.
[15]Woodward,K.Identity and Difference[C].Sage Publications,1997.335.
[16]陶铁柱.第二性·译者前言[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
[17]Gilroy,Paul.The Black Atlantic[M].Harvard UP,1993.163.
[18]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19]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70.
[20][21][澳]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历史[M].潘明兴 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8,5.
[22][23][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M].于运生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