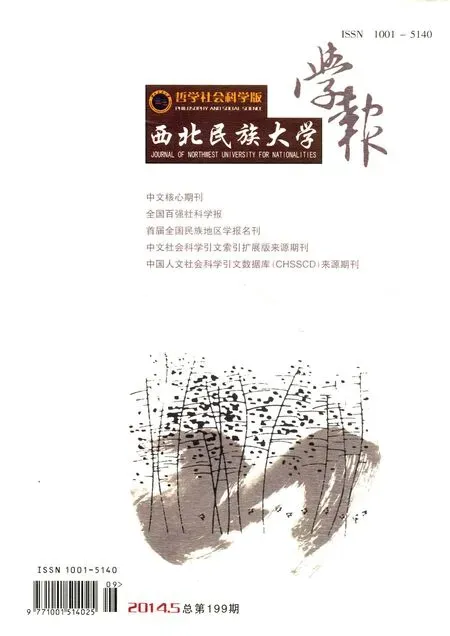《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及其作者情况评述
彭 博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吐蕃时期的古藏文碑铭文献,是研究吐蕃王朝政治文化及其对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中外史学研究者皆非常关注对古藏文碑铭材料的解读和运用。近年来随着中外学者针对吐蕃碑铭文献的研究逐步深入,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中李方桂、柯蔚南两位先生合著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Fang kuei Li and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一书颇具代表性。这部著述综合前人研究的各项成果,凸显出自身鲜明的特色,具有研究方法方面的指导意义。
一、《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概况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书原版为英文,1987年6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收入该所研究专刊系列,编号九十一[1]。全书共一册,十六开本,黄色纸封面,共504页。1996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再版,仍分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此书的中文版由王启龙译出,并在2006年交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这是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本。200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方桂全集》,将其收录为丛书第九卷以繁体字发行,十六开本,初版印了1 200册[2]。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共分为3个部分16章。第一部分为导论,共两章,由柯蔚南撰写。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藏语的创制和分类情况,吐蕃王朝的历史、宗教和对外关系。第二章梳理了自19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对古代西藏碑铭文献所作的重要研究成果,并扼要地作了评论。
第二部分为正文,共14章,每一章对应一种西藏碑铭文献,对14种碑铭材料进行了研究,包括引言、藏语碑文的拉丁文转写、转写的校勘注、译文和对译文的注释。每章篇首的引言部分包括碑刻建造时间、存立地点、存留状况和前人的研究状况、碑文拓片、照片。第三、四章是对《唐蕃会盟碑》和《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原书称为雪碑)的研究,此部分内容主要由李方桂撰写,柯蔚南对部分注释提供了新的解释,篇幅占到正文部分的一半。第五章到第十六章文稿出自柯蔚南之手,内容包括《桑耶寺碑文》《工布刻石》《琼结桥碑》《赤徳松赞墓碑》《谐拉康碑》《楚布寺碑》《噶迥寺建寺碑》《桑耶寺钟铭文》《昌珠寺钟铭文》《札叶儿巴寺钟铭文》以及洛札摩崖刻石和敦煌石窟中的一段藏文铭文。
第三部分是碑铭文献词汇表,以藏文首字母的转写字母为顺序,将全书中出现过的所有词汇进行了排列。
二、《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作者的学术成就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的作者之一李方桂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教授,曾任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美国《国际语言学》杂志副主编。因为他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成就,而被誉为中国的“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李方桂祖籍山西昔阳李家沟,1902年出生于广州一个中级官员家庭。幼时随母亲移居北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岁时考入清华学校,就读预科,1924年李方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公费赴美深造,进入密歇根大学学医。在学医期间,李方桂因修习拉丁语、德语而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转入语言学系学习,1926年他获得语言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李方桂进入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师从卡尔·勃克、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等语言学大师,系统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连续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赴美留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1929年末,李方桂回到中国,被中央研究院聘为研究员,此后8年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傣语和古藏语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语言学研究人才。
1946年,李方桂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编写《哈佛燕京词典》,随后又去耶鲁大学访问一年,1949年他开始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一直到1969年第一次退休。1972年,李方桂应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系之聘,开始在该校任教,3年后,李方桂正式退休。1987年李方桂因病逝世于加州伍德莱市。
李方桂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四十多年来著作等身,留下10本学术专著和近百篇学术论文,其研究成绩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方面。
(一)关于美洲印第安语的研究
在美国求学阶段,李方桂受到导师萨丕尔的影响,萨丕尔当时正致力于研究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的语言,他常常让李方桂在课余时间帮助他整理相关的语言资料,一年后李方桂从整理的资料中写出硕士论文《沙尔西语言动词词干的研究》,此文成为研究美州印第安人所讲的阿塔巴斯堪语的里程碑。在攻读学位期间,李方桂还跟随萨丕尔去加州考察印第安语,并独自调查濒临消亡的马佗里印第安语,以此为材料撰写了博士论文《马佗里——一种阿塔巴斯堪语》,这篇论文于1930年出版,这是现存对该语言研究的唯一成果。李方桂关于印第安语方面较为重要的论文还有《阿斯塔巴堪语比较的某些问题》《赤坡岩语词干表》《赤坡岩语辅音》《赤坡岩语文献材料》等。他在1946年发表的《赤坡岩语》被誉为是介绍阿塔巴斯堪语言结构中最好的一篇经典之作。
(二)关于汉语上古音和方言的研究
尽管李方桂自称不想研究汉语方言,但他在汉语音韵方面的研究依然有独特的价值。他从1931年开始陆续发表了《切韵ā的来源》《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等论文,1937年他在英文《中国年鉴》发表的《语言和方言》一文提出的中国语言系属分类的意见,至今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1930年李方桂和赵元任、罗常培一起翻译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这本书是中国现代音韵学和方言学的开山之作,首次应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重构了中古和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方桂在长期教授汉语和音韵学过程中形成一个构拟上古汉语“音系”的设想,最初他并不打算将它公诸于众,但他的学生已经将它整理成文本私下流传,他只好将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发表出来,198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以《上古音研究》为名正式出了单行本。晚年的李方桂“似乎越来越热心于上古汉语的课题,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3]。
(三)侗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
李方桂在侗台语的研究方面付出了最多的精力。从他进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开始,即已选定将少数民族语言作为调查和研究的重点,他跑遍了中国西南各省,调查了大约10到15种广西台语方言,并对其中的两种方言作了更加广泛的研究。陆续完成《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纪略》《剥隘土语》等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通过对各种方言材料的比较,李方桂从音韵特点、词汇分布和某些词汇的语音演变现象对侗台语进行了详细分类。在1977年出版的《比较台语手册》里李方桂选取3支最具代表性的台语方言,佐以数十种其他方言材料,成功地构拟了原始台语的声调系统、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观点明确,例证丰富,说服力强。这是李方桂四十多年来深入调查、参证对比、反复构思、形成理论的结晶,这本书奠定了侗台语研究的基础。1985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授予李方桂银质奖章,以表彰他在侗台语比较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
(四)藏语方面的研究
李方桂对藏语的研究同样肇始于他的导师萨丕尔,萨丕尔最早建议他学习藏语。后来,李方桂在哈佛大学选修了斯特尔·冯·霍尔斯顿教授的梵语课,从那里学到了一些藏语。1929年他在德国游学期间结识了西门华特教授,和他一起讨论汉藏语言问题,后来他们经常就藏语问题互相通信,维持了终生的友谊。
李方桂关于藏语研究的首篇论文是《藏文的前缀字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藏语中众多“词头”对字根声母的影响。1956年他在《通报》第四十四卷上发表了《唐蕃会盟碑研究》,这是一项极富创见的艰难工作,因为他不仅对唐蕃会盟碑上的可见的文字作注,而且根据藏文文义把日久残泐的古藏文设法复原,用拉丁文字母进行转写,再加以翻译和注解。当时黎吉生的专著已经出版,但是通报仍刊载了他的文章,就是因为他的工作超越他人处甚多。
在藏语研究方面李方桂的另一篇重要作品是《敦煌汉藏词汇》,他选取了玄奘所翻译瑜伽师地论汉译文和敦煌出土的藏文本,将两种文本进行了逐字的对照,每个藏文单词都标明拉丁文转写,并按照藏文字母的次序编写索引附于书后。此外李方桂对西藏的重要历史人物考证和一些关于词汇现象讨论、藏语语音的联音变化等问题的文章,对后学也多有启发。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是李方桂在藏语研究领域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在1981年将自己对《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的研究资料交给柯蔚南,并且建议两人合作出版一部关于古藏文碑铭的书。这项研究进行了很久,书直到1987年李方桂去世前不久才出版。他对这项研究倾注了很多心血,当他在病中手捧着印好的书,感到十分欣喜,“顾盼自豪,指告往来朋友以及医护人员等”[4]。
美国语言学家W.South.Coblin出生于1944年,柯蔚南是他为自己所起的汉文名字。他是李方桂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时教过的学生。1972年他完成论文《藏语动词形态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被爱荷华州的衣阿华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聘用,此后一直在此任教并于1985年升为教授,现为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
柯蔚南主要从事汉语言音韵研究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关于前者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说文读若声母考》,这篇文章统计了《说文解字》中820个读若资料,拟出的复辅音声母主要是带l和带s两类,并且第一次对复辅音作了断代的描述。《郭璞注中的魏晋声母系统》推测郭璞生活的时代存在一套现已亡佚的舌面前音声母K、KH、G。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东汉声训手册》是他为汉语历史语言学课程编写的参考书,书中收录了大量东汉时期的声训材料。他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注释。《汉语西北方言的历史分期》一文根据一些具有特征性的音韵指标对从魏晋时期到宋代的瓜州地区汉语方言作了断代,同时为敦煌出土的音书文献的年代定位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线索。
关于后者的研究则有1986年出版的《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这部书在搜集到的大量词汇对应材料的基础上构拟了汉藏语的原始形式。关于汉语中古音,此书采用了经李方桂修订过的高本汉的构拟形式。关于汉语上古音,采用了李方桂的构拟形式。这些构拟形式都具有相当高的可信程度,此外还有《白狼歌新探》《八思巴文手册》等著述[5]。
三、《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出版后不久,王尧先生就撰文赞誉此书从深度和广度上将吐蕃碑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并指出本书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具有3个鲜明的特点,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即为其一[6]。《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书后参考文献胪列了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关于藏学研究的120部著作,这些著作中的相关意见都在书中得到了体现。除了前人的研究著作,两位作者还充分利用了各种词典工具书如《藏汉大辞典》《藏语新旧字辨异——丁香宝帐》《翻译名义大集》《语法字汇明镜》等。在考订碑文中出现的人名、职官称谓时,不仅参阅《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汉文史书,还参考了《尚书》《战国策》等藏文译本,引征材料极为丰富,真正做到了无一字不有出处。
严格恪守学术规范是《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的显著特点,凡是引征的材料必定言明出处,对未能证实的释义只列出各家不同的说法,不轻易否定,也不盲从。比如《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南面碑文第三十三行中出现“野猫川(dbyar-mo-thang)”一地,王尧据藏文史籍《五部遗教》言其地在青海湖侧畔。李方桂注文并录托马斯、乌瑞、谭其骧、威利4位学者的不同说法,这样既方便了读者全面了解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也为后人继续研究该问题提供方便。作者即使赞成所引用学者的某种说法,也能用新材料加以补充说明,如对工布刻石(第穆萨摩崖石刻)第六行中“gnyan-po”一词历来的解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派认为它是专有名词,尤伯赫、常凤玄、黎吉生将它译为“妖厉、神灵”,麦克唐纳将它理解为“地妖”,斯纳尔格罗夫译为“复仇女神”;另一派认为它是形容词,如王尧将它译为一个形容词“灵应”,《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作者赞成王尧的观点。他们从藏语本《尚书》里找到gnyan-po与汉文《尚书》中对应的词义,又联系碑文的上下文含义,认为将该词译为“强大的”比较符合原文语境。对凡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的,绝不妄加推断,显示出作者的严谨的学术态度。
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是本书的最明显的特点。正如柯蔚南所说,在王尧和黎吉生都出版了吐蕃碑铭方面的重要著作之后,再出一部碑铭文献集依然有其必要。“王尧和黎吉生都是藏学家,他们从自己的学科立场去处理文献材料,我们主要是对藏缅语和汉藏语言学有特殊兴趣的汉学家。我们的背景和倾向导致我们得出的观点——有时候是某些结论不同于我们的学术前贤,我们希望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对文献作出新的解释”[7]。《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的研究方法上体现了李方桂的老师勃克的考释法和萨丕尔对语言文本分析的方法,他在原始材料充分的前提下对碑文的每一处细节都尽可能地仔细校订,然后逐字逐句地作出翻译,列出注释,最后将文献中出现的全部术语按照字母顺序编排成为词汇表,每个词后都标注出它的意思和在文献中的位置,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西藏碑文集的初步的词典,方便研究者检阅核对。
在书中具体的注释里,语言学方法应用的非常广泛。藏文文献中有的词义并不明晰,研究者只能通过文意和背景材料推断它们的含义,李方桂、柯蔚南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些词汇作了深入的分析,提高了对文献认识的准确性。以《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为例,《吐蕃金石录》对其南面碑文第九行内容注释说:“赤德祖赞赞普死因已详于碑记,实为臣下所毒毙,有藏文dard乃一古词,今已失原意,惟在文中按上下词义推求,乃作此解。”[8]《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的注释说:“Dard是srog vdor-ba(危及生命、剥夺生命)里vdor-ba的完成式。[李方桂]古代藏语里vdor-ba(抛弃、扔掉)的完成式是dor。短语srog vdor-ba似乎基本上是抛弃生命的意思。dard作为dar-ba(传播、扩张)的一种形式,在古代藏文文献中有例证。此句碑文的另一种解释可把sku-la dard理解为‘他波及到(赞普的)生命安全’。[柯蔚南]”[9]这就从语法演化的角度解释清楚了Dard一词的含义。又如碑文第四十一行译文为“对社稷裨益”[10],《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在这里有个注释:“[sems]dkav-ba。这里sems的意义不明确,怎样校补还是问题。……不见的那个词可能是legs(好事、善业),因此这个短语意为他艰苦致力善业……另外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新发现的洛札碑里一段非常相似的碑文:“glo-ba nye-nye sku dang chab-srid la dphen-phavi rjeblas dkav-ba byed-byed…(对于我们的人和政府,他一直忠诚,他一直履行有益而困难的义务)。这个并列句表明这里丢掉的词可能是rje-blas(义务、责任)。”[11]
两位作者在考证碑文词义时应用了藏汉语言比较方法,这对于处理铭文中的疑难词语极有帮助。比如在东面碑文的第七行有rje-blas一词,白桂滋将其理解为“一种负责军队中奖惩事务的高官”,这就使得原文的意思变得不易理解。柯蔚南利用敦煌藏文文书《尚书释文残卷》中对应的句子“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确认rje-blas的意思为“义务、责任”,这样就合理地解释了碑文中所说的达扎路恭因坚持和履行了rje-blas而受到赞普的褒奖这一事实。再如北面碑文第三十行关于pu-nu-po的解释,现代藏语拉萨方言中是“兄弟”的意思,安多方言中则有“亲属、亲戚”的意思,罗那塔斯考察了所有phu-nu和pu-nu-po在各种藏文文本中的例句,认为这个词在古代藏文里表示“亲属”,而不是“兄弟”。作者参考了藏文《尚书》和《战国策》里出现的phu-nu例句,发现它们表示“王父母弟”“国王的父母”,最终采用了罗那塔斯的解释。
两位作者在考证名物方面也极具考据家的严谨和宏富。书中任意一条对《唐蕃会盟碑》中吐蕃官职的注释,都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考据功力,以“mngan-po khab so vo chog gi bla vbal blon klu bzang myes rma(岸奔盍苏户属劫罗末论矩立藏名摩)”为例。李方桂认为:“岸本大概是头目或首领,是负责财务的本官。……从属于mngan的职官有khab-so,其主要职能是征收税金和关税。Khab-通常被理解为‘王子、宫廷所在之地’。-so这个音节经常用来表示so-pa‘守卫、看守、士兵’,因此khab-so应为‘宫廷侍卫、宫内官员’;请比较变体khab-so-pa。不过,‘宫廷侍卫’这种翻译并没有反映出khab-so已知的职能。乌瑞认为–so衍生于gso-ba bsos和vtsho-ba bsos‘喂养、滋养’等词的词根。于是整个合成词khab-so或许可以译成‘皇室的食物征发官’,即可以反映出他们为政府征税这一事实。这是一种可能性,不过我们希望能找到其中-so表示‘滋养者、承办者’等意思的合成词。另一方面可能khab-so作为中央税收官员的这一职能有可能是由宫廷军事人员或武装人员发展而来,后者的职能有时涉及没收财产或强制征税等。较早的‘宫廷侍卫’大概经历了好些变化,在职能上更趋于专门化。……khab-so在《藏汉大词典》里被注释为‘内库、王室内库’,这种注释的来源没有注明;但其后紧跟着khab-so nang-pavi khrims‘内库家法’这一词条说明两个词条都是来源于《贤者喜宴》ja函第二十二页B面。总之,乍一看‘库’这个解释显得有点突兀,因为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认为khab-so一词是指人。……在工布石刻第十行,我们发现khab-so dpon-sna这个短语,明显是指税务官员这个集体。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短语khab-so-pa,其实际含义是‘负责人员’。因此,khab-so一词的基本意义是指吐蕃王朝政府的税收机构或部门,即皇家财务部,其次才表示负责这一部门工作的khab-so-pa(税务人员)或khab-so dpon-sna(税务官员)。其组成部分-so的实际语源尚需深入研究。”[12]再如,李方桂对《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的考证与注释非常细密,早在1956年他就撰文对恩兰·达扎路恭的不同译名进行过研究,指出汉文史籍中出现的马重英即达扎路恭[13]。该碑文第二十六行~第二十七行,译文作“复任为往攻(唐地)州县堡寨之先锋统军元帅”,注释考证khar-tsan一词,认为它是一处军事要塞,并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判断此处是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碑文第六十四行译文“唐宰相***等潼关……”[14],并未说明宰相姓名,李方桂考订出vByevu为唐侍中苗晋卿的藏文转写。诸如此类细微的考订,文中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是目前对西藏碑文研究最全面的学术论著,它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融合了前人研究的各项成果,并在许多具体研究点上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见解。两位作者既注重应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藏文词义,又能以传统历史考据方法对碑铭文献进行注释,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今后研究同类文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参考文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Fang kuei Li and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Nankang,Taipei,Taiwan,ROC.
[2][7][9][11][12]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M].王启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100,102,77,78.
[3]柯蔚南.追忆李方桂先生[A].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M].王启龙,邓小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90.
[4][6]王尧.评李方桂、柯蔚南新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J].民族语文,1988,(4):54,51-54.
[5]柯蔚南研究著作列表[EB/OL].衣阿华大学官方网页http://clas.uiowa.edu/dwllc/asll/people/w-south-coblin.
[8][10][14]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90,84,84.
[13]李方桂.马重英考[J].龙达瑞译.西藏研究,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