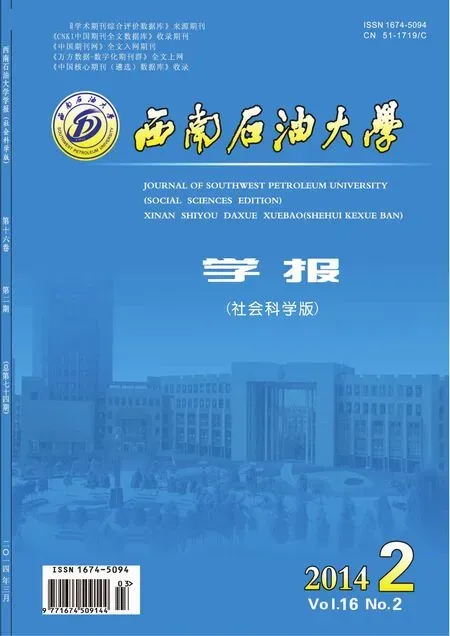西美尔对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影响
王园波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江苏 连云港 222047)
西美尔对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影响
王园波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江苏 连云港 222047)
西美尔是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主要源泉。西美尔指出,现代文化的分裂造成了文化悲剧,青年卢卡奇象西美尔一样对现代文化的危机作出了诊断,将其视为异化的表征。西美尔认为劳动分工是主客观文化分离的动因,虽然马克思等也曾对劳动分工有过精辟论述,然而青年卢卡奇却是透过西美尔的眼睛来认识劳动分工的。西美尔文化悲剧的本质在于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青年卢卡奇同样将其视为自己思想的基础型结构,并试图在资本主义异化面前打破心灵与现实的壁垒,探索并建立新形式,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
西美尔;青年卢卡奇;异化;劳动分工;文化悲剧
引 言
人们习惯认为卢卡奇的异化思想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得到阐释,而卢卡奇也宣称自己对异化的分析源自马克思,但是从卢卡奇早期著述《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等可以发现,异化早已经是他经常使用的概念,并且是卢卡奇“1912年前的作品的基础性用语”[1]。人们往往将卢卡奇视为马克思的学徒,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层面的异化分析以及消灭私有制的异化克服具有彻底性,而卢卡奇的异化则是对马克思的某种倒转,回到了马克思曾经克服的黑格尔阶段,并且将异化克服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意识之上也是一种虚妄,从而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论述。然而,这正是卢卡奇的独特之处,他“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2],而是转向了哲学、文化领域,虽然以马克思为参照系可认为卢卡奇的异化是对马克思的补充或再发现,但是倘若以文化异化分析见长的西美尔为参照系,则可以发现卢卡奇与西美尔的异化思想之间有着更为亲密的关联。谢胜义在谈到影响卢卡奇异化思想的思想家时就认为按影响深浅可排序为:“席默尔、韦伯、马克思、黑格尔与恩格斯”[3],就将西美尔放在了首位。但是由于西美尔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卢卡奇研究中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不足,学界不仅极少关注卢卡奇早期的异化思想,而且也疏于清理西美尔在卢卡奇早期异化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1 异化的表征:现代文化的危机
现代文化就是伴随着分立、冲突、悖论的危机文化。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形成时期,生活在此一时期的西美尔敏锐地把握到了现代文化的危机。在他看来,文化由自然发展而来,但是自然按其本性的发展并不能自发形成文化,必须经过人的培植,而只有“一切培植不仅是超越其天性所能及的形式阶段的本质性开发,而且是对其内在原始核心方向的开发,使其本质趋向其本义标准的完善,趋向其最大能动力方向”[4]85才能形成文化。文化首先是人的文化,只有人才是文化的对象,人的灵魂自一开始就要求自我完善,但是灵魂自身在纯意识的范围内并不能达到完善,而只有经过自我完善的阶段和手段,借助于客观条件才能实现。而客观产物自身也并不具备文化价值,只有当它以人的本质理想为目的,能够协助灵魂达到统一时才能形成文化。因此,没有客观文化就没有主观文化,因为只有当主观文化能够将创造出的客观文化纳入到主观之中才能形成文化,然而,客观文化却存在着不能够被主观充分吸收的状况。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文化发展的繁荣,客观文化会渐趋完善,越来越符合灵魂内在的目的,于是主观文化就不必升华到相同的程度;同时,人的主观也是在无止境地膨胀,也没必要同客观文化保持同一发展程度。也因此,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的危机就在所难免,“客观文化内容在明确性与明智性方面跟主观文化极不相称,主观文化对客观文化感到陌生,感到勉强,对它的进步速度感到无能为力”[4]96,文化危机就产生了,而这正是现时代的文化状况。人总是处于主客观文化的冲突的危机之中,正如艾茨孔所言,在西美尔的思想中,“人类总是处于被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但已失去其人类有机协调因素的客体杀戮的危险之中”[5]。
西美尔抱持的文化观念正是现代意义的文化观念,他虽然也采用了原始文化概念中的培植词义,但是将其运用到了人类自身,将文化视为对自我的完善,他将文化视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二元关系之时就实际上隐含了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如他对货币经济的分析,“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依据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6]。人创造的文化本应服务于人,却在货币的操纵下摆脱了人的控制,成为压迫人的外在力量。文化的发展越成熟,客观文化的独立性就越强,最终成了一股压制主观文化的力量,“首先,生活的目的臣服于其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许多不过是手段的事物被人们认为是目的;其次,文化的客观产品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二者都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而且它们发展的速度已经将后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7]。除非文化发展能够得到主体文化的不断反抗或者通过社会动荡暂时挽救走向解体的文化生活,不然文化将会发展到灭亡。
受西美尔影响,青年卢卡奇也将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问题。在卢卡奇的视阈中文化问题与生活问题同义,文化就是生活的内在意义。卢卡奇曾说:“文化……是生活的统一,是提高生活和丰富生活统一的力量……所有文化都是对生活的征服,用一种力量统一了所有生活现象。”[8]只有在真正的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内在信念与外在体制才能达成统一,人类和事件才会变得有意义,因此,对卢卡奇而言,文化同样是充满内在冲突的问题,文化问题也是文化危机问题,“在卢卡奇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一种关于世界‘善’和‘恶’的对立与冲突的判断:一端是‘幸福年代’的完整的文化和自由的人;一端是‘罪恶年代’的分裂的文化和异化的人”[9]。卢卡奇分析文化问题的目的就在于寻求一种摆脱异化生活的途径。在马尔库什看来,卢卡奇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是通过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方式和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但是其面对的是同样的时代生活状况,其结果也无非是时代文化状况到底是形而上的文化悲剧的表达还是历史危机的表达,然而最终卢卡奇得到的却都是否定的答案。通过前一种方式,他认为:“为文化而奋斗,即人追求‘要让自己在生存巅峰的水平上过自己的生活,要使其意义成为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的永恒的和永不休止的渴望,是悲剧性的、毫无希望的。”[8]通过后一种方式,他认为:“文化危机是当今世界的这一历史地决定的事物状态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在这个词真实的意义上的文化是不可能的。”[8]
由此可见,早年卢卡奇对文化危机的诊断无论是在文化的观念上还是在分析的结果上都与西美尔十分相似,西美尔指出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文化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客观文化的过度发达带来了人的异化,卢卡奇像西美尔一样对现代文化的危机作出了诊断。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发展能够与人的发展完善达成同步的和谐,那么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西美尔将其视为以货币经济为代表的客观文化过度发达使然,而卢卡奇同样认为完整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以艺术来说,伴随着资产阶级的衰落和瓦解,这个昔日有足够勇气去设想自己的观念、价值和规范的新兴阶级的创造力也衰微了继而消逝了,虽然资产阶级艺术在技巧上十分成熟,然而“越发成熟的艺术技巧并不能确保作品或艺术产品令人感兴趣”[10]。就此而言,无论是西美尔还是卢卡奇,最关心的问题是文化问题,是文化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面对现代文化的分化冲突他们不约而同陷入莫大的悲情之中,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对文化依然保持着希望才在看到现代文化危机之时流露出了失望,这种失望在卢卡奇的《现代戏剧发展史》中有着明确的表述:“始于18世纪的戏剧时代已经结束了吗?我们所见到的戏剧形式(以悲剧为顶点)究竟完结了吗?或者我们在此所论及的只是凭依与戏剧无关的才能所产生的悲剧,由于特别偶然的原因达到戏剧形式了吗?我们仅仅感觉到这些疑问的沉重,也只是感到唯有时间才能予以回答……”[11]49-50
2 异化的动因:劳动分工致意义丧失
社会学的知识背景使西美尔将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分工。在他看来,现代文化的客观化进程是通过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在劳动分工的作用下,现代文化的内容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客观内容;而随着文化客观化的日益严重,主观文化也越来越滞后于客观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不断加大,客观文化成为压制主观文化的力量,造成了文化危机的出现。
具体而言,西美尔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讨论了劳动分工的作用。从生产而言,传统的生产是按照自我的形象来塑造对象的,是通过劳动者将自我的形象投射到对象中来完成的,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具有统一性,也内蕴着生产者的精神性,能够保证自我的完善和统一。然而,随着劳动分工带来的大规模专门化生产则切断了劳动者与产品之间的精神性联系,产品的意义不再是从生产者的心灵中衍生,也丧失了应有的精神性特征,而是越来越建立在其他产品以及它和其他产品的关系之上,劳动者在产品中再难发现自己的影子,而产品也似乎成了劳动者存在的十分片面的组成部分,而对人的完整统一性漠不关心。劳动分工还带来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劳动者同自身劳动的分离。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不再是劳动者自己所生产而是由资本家所提供、组织和分配,由此,生产资料对劳动者而言就成为一种客观性的东西。劳动者利用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时,劳动者的劳动可以保留在产品之中直到产品进入交换领域,而当劳动者不再能够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也就变得与劳动者无关,成了一种客观性的东西,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货币的客观等价物,此时劳动者拥有的不再是自己的劳动,而只能拥有劳动交换而来的货币。劳动产品就“具有明确无疑的自主性,具有自身运动规律,和一种生产它的主体也相当陌生的特征”[12]70,以至于劳动者想要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也不得不采用购买的方式。而从消费而言,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的扩大伴随着生产的专门化,因为劳动产品越客观,越普遍化,越没有个性,就越适合更多的消费者。西美尔将消费视为文化的客观性与劳动分工的联结纽带。在他看来,18世纪以前的定制服务保存着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个人关系,因为既然一件商品是为某位消费者量身打造的,消费的过程就体现着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商品就可以像属于生产者一样属于消费者,因为只要客体是由单独的个体创造的或者是为单个的主体所创造的,理论上而言主客体之间就是和谐的,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冲突。然而劳动分工破坏了定制服务的消费形式,对消费者而言,商品成了既定的客观物,商品中的主观性色彩也消匿不见,消费者只能从外部接近商品。劳动分工越分化,商品对消费者而言就越客观,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虽然此时作为中介的经济交换就会越发达,但是在消费交换的过程中,主体性遭到了破坏,相伴而来的却是冷漠的、匿名的客观性。
总之,劳动分工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劳动分工也加剧着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分裂,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文化越来越具有独立的自主性,而主观文化则与客观文化越来越疏远。自由本是要积极地将自我扩张到臣服于它之下的客体里才能实现,主体只能面对无法吸纳的客体,寻觅一丝被压抑、被削弱的消极自由。现代文化的命运“就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面对这场以一己之力无法衡量的浩大危机,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不论是否意识到,这是每一个人灵魂的危机”[7]184-185。在极度的忧虑中,西美尔怀念希腊时代的文化和谐状态,对现代人而言,这种和谐早已成为破碎的旧梦。
其实,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分析也同样精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劳动对工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不再属于工人的本质,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工人在劳动中得到的不是对自己的肯定而是否定,不是得到幸福而是不幸,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然而西美尔1900年发表《货币哲学》之时,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尚未面世,并且西美尔早在1890年的《论社会分化》中就对货币与劳动分工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从《货币哲学》中的引用来看,西美尔对劳动分工的看法可能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我们对西美尔的早年生涯了解太少了,甚至还不知道西美尔究竟研究过马克思著作的哪些内容或者从同代人那里得到了什么关于马克思的营养[14]。何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层面来描述劳动分工的,而西美尔在《货币哲学》的规划中说:“本书的这项研究没有只字片语是国民经济学式的”[12]2,而是力图“从生活的任何细节之中寻求生活意义的整体的可能性。”[12]3很明显他是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待劳动分工的。
卢卡奇十分欣赏西美尔对劳动分工的看法,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卢卡奇曾说:“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现代分工的一个基本方面可能就是使工作不再依赖于工人非理性的、并因此只能定性地界定的能力,而使它依赖于与外在于个体工人并与他的个性没有关联的功能相关的客观因素。工作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工人在工作中投入越来越少的个性,而工作也越来越不需要完成它的人的个性。工作呈现出一种独立的、客观的自我生命,与个人的个性相分离……”[15]28-29卢卡奇虽中学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大学期间也阅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但是当时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只限于经济学,特别是只限于‘社会学’”[16],甚至他当时仍未分清辩证唯物主义和非辩证唯物主义,他一门心思迷倒在了新康德主义的怀抱之中,尤其是痴迷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直到1914年,出于研究黑格尔的需要才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等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至少已经是1918年之后的事情了。因此,早期卢卡奇的劳动分工观念正是来源于西美尔,或者说是透过西美尔的眼睛受惠于马克思。192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再次论述了劳动分工:劳动过程从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是合理化支配下的劳动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精细的局部的操作,劳动者的工作演变成了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劳动者与整体产品之间的关系已被斩断,而整个劳动过程以及劳动产品都被纳入到了计算的范围之中,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中介。“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17]。虽然卢卡奇此时在劳动分工的论述中掺杂了韦伯的合理性,但是劳动分工在此依然同西美尔一样是作为异化的动因出现的,然而此时距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仍有9年。由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异化思想虽然“转弯抹角地”承认曾受惠于西美尔,却“多半应归功于”西美尔[18]。
3 异化的本质: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冲突
西美尔将文化划分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造成了文化危机,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造成了文化悲剧,然而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不过是文化危机的外在表征,其本质却在于主体的生命与形式的冲突。“文化的自相矛盾在于我们在它不断的流动中感受到的,并驱动它自己朝着内在的完美发展的主观生活本身并不能达到文化的完美。只有通过完全相异、具体化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形式,它才能真正养成,提出这一点的最明确的方式是说文化是由两个要素的相遇形成的,两个要素本身都不包含文化:它们是主观的灵魂和客观的精神产品”[19]30。生命与形式的冲突不仅是西美尔生命哲学的主要构成,也是贯穿西美尔整个思想的主线。“它既然是生命,那就需要形式;它既然是生命那就需要比形式更多的东西。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它只能在形式当中找到一席之地,但又无法在形式中找到立锥之地,因此,它既超越,又打破构成生命的任何一种形式。”[20]“生命只有通过形式才能表现自身,实现其自由;但形式也必然会窒息生命,阻碍自由”[19]24,“心灵创造了无数的对象,这些对象却以独立于创造它们的心灵、独立于可能接受或拒绝它们的心灵的方式自足地存在着。如此一来,个体就处于对立之中,就像艺术与法律、宗教与科学、技术与习俗之间的对立一样……精神一旦以固定的、僵化的、永恒的形式成为客体之后,就会与涌动的生命、内在自我以及冲突不断的个体灵魂形成对立……不断涌动且时间有限的主体生命和它一旦创造就从此固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之间的深刻对立造成了无穷的悲剧……”[21]。因此生命与形式的冲突是永恒的冲突,当生命与形式的冲突超越生物层面进入精神领域并进入文化层面的时候就形成了文化冲突,所以文化的冲突也是永恒的冲突,文化悲剧是普遍的悲剧。主观文化需要吸纳客观的文化形式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而客观的文化形式却不断地反抗主观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紧张关系,只能不停地搏斗。正如弗里斯比所言,西美尔文化异化的主要矛盾是“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因为客观文化不被看做是内在冲突和过渡的,所以除了永恒的现在,不可能有面向个体的世界。”[22]然而,这种矛盾在前现代的社会中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才成为一种突出的异化现象。在西美尔看来,生命与形式构成了文化的整体,文化的内容必须通过形式表现出来,而生命的运动又是无止境的,总是想突破现有的形式,因此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种种基于生命与形式冲突的文化矛盾。生命与形式二元冲突的哲学观念是西美尔受康德影响的结果。如果说先验形式在康德那里是绝对的,是认识的必须的条件,是纯粹理性的形式的话,那么西美尔则更多是借助一个对形式的假定试图达到认识社会、认识生命的目的。西美尔将艺术、技术、经济等一切人的活动都纳入到形式的考察之中,在他看来,一切文化都是作为人的生存形式而被创造出来的,而形式又以自己的逻辑展开,有着自足的特性。因此,西美尔对异化的分析采取的是由内而外的思考方式,从生命与形式二元冲突的生命哲学推演出了主客观文化之间的分裂,异化对于西美尔而言首先是心灵的异化,正如他对现代性的判断“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主义,是依据我们内心生活的反应,实际上也就是作为内在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在心灵流动因素中固定内容瓦解了,由此一切本质性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其形式仅仅是运动的形式而已。”[23]波德莱尔开启的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思考社会的方式在西美尔这里得到了延续,也因此可以认为,西美尔虽然提出了文化悲剧,也指出了文化悲剧背后的生命与形式的冲突,然而他更为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异化造成的个体生命感觉的丧失。
而对青年卢卡奇而言,生命与形式的二元结构同样是具有决断性的理论命题。卢卡奇曾说“文学中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是形式。”[11]39他模仿西美尔的做法,将艺术作品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形式同样是先验的东西,任何体验在形式上已经被体验了。卢卡奇将西美尔的生命与形式概念类比到了自己的《心灵与形式》之中,西美尔接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将生命看成持续不断的绝对延续,生命的每个瞬间都是生命的全体,生命的不间断流动就是生命所具有的唯一形式。而卢卡奇则在1908年《关于易卜生的见解》中写道:“所谓形式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穿上和脱下的衣服,它在本质上并不独立于穿衣服的人,因为形式、技术是从最深层的心灵的主要因素中产生出来的东西。”[11]39在此,他对生命形式的看法与西美尔如出一辙。如果说卢卡奇对形式有什么超越西美尔之处的话,可能仅是因为他将形式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之中,《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等都是以形式为核心展开的著作,因此,卢卡奇的形式也是一种审美形式。比如他曾说:“形式把生活的素材组织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规定了它的速度、节奏、起伏、密度、流动性、硬度和软度;它强调那些可感受的重要部分而排出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它将事物或者置于前台或者置于背景之中,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模式。”[24]但是艺术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属于生存形式的外化,卢卡奇无论是从小而言之的艺术形式还是从大而言之的文化形式对戏剧、小说展开的研究都有着更为深刻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的异化面前,他试图打破心灵和现实的壁垒,探索出真正的形式存在的可能并建立一种新形式,创造一种新文化,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
卢卡奇不愧为西美尔的大弟子,对西美尔文化悲剧的理解直接击中了本质。不过与此同时,卢卡奇也将西美尔的生命与形式概念做了少许置换。卢卡奇有时会采用心灵与形式的冲突的说法,他曾说“所谓形式是指心灵的现实性,与心灵的生命息息相关……不只是对生命起作用,作为改造体验的因素起作用,作为通过生命被形象化的因素也起作用。”[11]41在此可以发现,卢卡奇同西美尔一样是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认为生命只有通过形式的外化才能形成文化,而卢卡奇对文学艺术的探讨正是以此为基点试图寻找能够保证主体自由的合适的形式。正如他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唯美文化试图转入内心躲避异化,实质上却加剧了文化异化,因为过分强调内在性,使得艺术家只注重内心世界,面对客观现实成了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卢卡奇有时也会采用心灵与生活的冲突的说法,他曾说:“所有个别事物,一旦进入生活,就具有一种不依赖其创造者和任何预期目标的自己的生活……它自己的生活(人类创造的所有产物的生活)脱离了其创造者的生活,也脱离了所有预期的目标,它具有自己的生活……它或许会转而对抗它的创造者并破坏那些它本打算强化和支持的东西。手段变成了目的,并且不管是前瞻还是回顾,没有人能够获知存储在对象和事物里的会影响局面和事态的巨大力量到底是什么。”[15]12而在《心灵与形式》中卢卡奇则写到:“生活是苦难,生存是悲凉,工作是无聊”、“人注定是要异化的”[1]。虽然卢卡奇有时也提及内在生活的说法,但是他的生活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类似于西美尔的生命形式或者客观文化。在他看来,生活中充满了非人的规范性因素,虽然心灵创造了生活,但是生活已经僵化,失去了活力,文化作为心灵与生活的统一则陷入危机,由此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的嗟叹“为了生存必须否定生活”[25]就不难理解了。
西美尔的生命与形式的冲突观念虽然有着康德的影子,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却属于生命哲学的体现。西美尔曾深受叔本华、尼采以及柏格森等生命哲学家的影响,成为当时德国生命哲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人们习惯只将西美尔晚年的《生命直观》视为其转向生命哲学的标志,然而在费尔曼看来“生命的概念在他的文化哲学中占有如此中心的地位,所以这一概念必定是贯穿了西梅尔的思考”[26]。而卢卡奇也在《理性的毁灭》中对当时生命哲学的兴起作出了描述,在帝国主义宗教衰落的时代,一方面科学知识致使知识分子远离了宗教活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不安定、无保障等)却使他们感到有宗教信仰的必要,“我的个人生命本身,从其内在方面来看,是完全无意义的,外在世界对我说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科学知识已使世界‘丧失了神性’,社会行为的规范已失去了任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哪里去寻求我的生命意义呢?”[27]生命哲学就从这种需要中应运而生了。从卢卡奇的描述中可以推测,西美尔走向生命哲学可能是基于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西美尔采用生命哲学的方式将生命视为文化发展的动力,从生命结构中演绎出了对文化结构的分析。生命与形式构成了文化的整体,生命是文化的内蕴,形式是生命的外化,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导致了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然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无论对于哪个时代的思想家而言都是自觉会肩负起的使命,不同之处在于,不同思想家思考的方式和最终寻求的道路会有不同,然而对于卢卡奇而言,其早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明显洋溢着生命哲学的味道。卢卡奇曾激情洋溢地写到古希腊星空朗照下的一切“既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28]然而拥有那样的心灵的却是希腊人,那个时代是属于荷马史诗的时代,而现代的哲学总是要表现为内与外的分裂、自我与世界的区别、心灵与行为的失调,如果说古老而美好的年代是幸福的年代,那么现代就是痛苦的年代。希腊人的纯真可以只知答案而不知问题,只知谜底而不知谜面,只知形式而不知混沌,却依然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完美,然而现代的心灵却必须在心灵与形式、认识与实践、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去把握,虽然理性的发展使人类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更好地设定自我,然而却丧失了希腊人般的生活基础,于是只能孜孜以求地在对总体性的追求中缅怀那已逝的乌托邦。
4 小 结
由此可见,西美尔是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主要源泉,无论从异化的表征、异化的动因还是异化的本质上都深刻影响着青年卢卡奇的异化思想。西美尔指出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文化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客观文化的过度发达带来了人的异化。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发展能够与人的发展完善达成同步的和谐,那么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西美尔将其视为货币经济为代表的客观文化过度发达使然,而青年卢卡奇同样认为完整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对二者而言,现代文化就是一种异化的文化,现代文化的危机就是异化的表征。劳动分工被西美尔认为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分离的动因,现代文化的客观化进程是通过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在劳动分工的作用下,现代文化的内容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客观内容。而随着文化客观化的日益严重,主观文化也越来越滞后于客观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不断加大,客观文化成为压制主观文化的力量,造成了文化危机的出现。虽然马克思等也曾对劳动分工有过精辟论述,卢卡奇自中学起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然而青年卢卡奇却是透过西美尔的眼睛来认识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的。西美尔文化悲剧的本质在于生命与形式的冲突,生命与形式构成了文化的整体,文化的内容必须通过形式表现出来,而生命的运动又是无止境的,总是想突破现有的形式,因此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种种基于生命与形式冲突的文化矛盾。青年卢卡奇承继西美尔将生命与形式视为自己思想的基础性结构,试图在资本主义异化面前打破心灵与现实的壁垒,探索并建立新形式,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
[1] 衣俊卿.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4.
[2] [英]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5.
[3] 谢胜义.卢卡奇[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35.
[4] [德]齐美尔.桥与门[M].涯鸿,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 夏征农.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三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88.
[6]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8.
[7]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8] [匈]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J].孙建茵,译.求是学刊,2011(5):26-31.
[9] 衣俊卿.一位伟大思者孤绝心灵的文化守望:布达佩斯学派成员视野中的卢卡奇[J].求是学刊,2011(5):10-11.
[10] 周宪.文化现代性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95.
[11] [日]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M].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
[14] D Frisby.Georg Simmel[M].London:Routledge,2002:132-135.
[15] [匈]赫勒.卢卡奇再评价[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6] 杜章智.卢卡奇自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10.
[17]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3-154.
[18] [英]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M].翁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7.
[19] G Simmel.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M]. trans K P Etzkorn. New York:Teathers College Press,1968.
[20] [德]西美尔.生命直观:先验论四章[M].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9.
[21] E Cassirer. The logic of the humanitie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191-192.
[22] [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1.
[23] 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M]. London: Routledge,1992: 66.
[24] 刘象愚.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1):79.
[25] G Lukács. Soul and form[M].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74: 153.
[26] [德]费尔曼.生命哲学[M].李健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10.
[27] [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王玖兴,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397.
[28] G Lukaá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M].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71: 29-30.
(编辑:余少成)
Simmel’s Influence on Young Lukács’ Thoughts of Alienation
WANG Yuan- bo
Party Committee Office,Jiangsu Kanion Pharmaceutical Co. Ltd,Lianyungang,Jiangsu 222047,China
Simmel is the main source of young Lukács’ thoughts alienation. As Simmel had pointed out that cultural tragedy was caused by the division of modern culture,young Lukács also attributed the crisis of modern culture to alienation. Simmel held that it w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at separated subjective culture from objective culture. Karl Max had an incisive argument about the division of labor,but young Lukács followed Simmel’s views on it. The essence of Simmel’s thoughts on cultural tragedy lies in the conflict of life and form which was inherited by Lukács a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his early thoughts. Facing the alien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Lukács tried to break the barriers between mind and reality in order to end the capitalist cultural tragedy by exploring and creating new forms.
Georg Simmel;young Lukács;alienation;division of labor;cultural tragedy
1674-5094(2014)02-0103-07
10.3863/j.issn.1674-5094.2014.02.018
B516.59
A
2013-05-13
王园波(1987-),男(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
本文已由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优先出版。
王园波.西美尔对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影响[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103-109.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