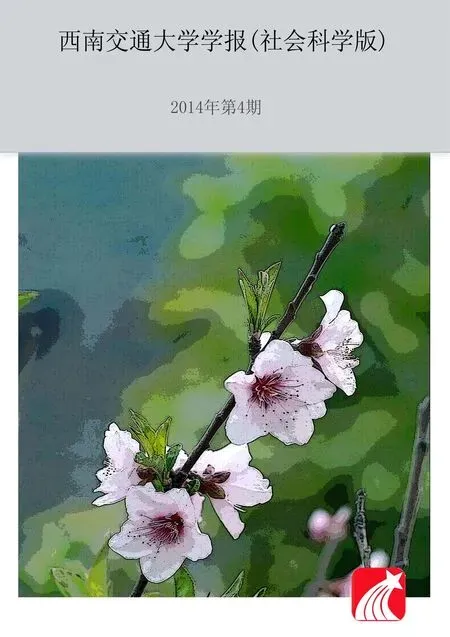抗战时期大后方基层保甲的困境——以四川南溪县兵役纠纷及其解决为例
张 艺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民国时期的保甲组织虽为“半官方”性质,却是抗战时期国统区进行基层社会控制的主要组织。这一基层组织利于国家与民众之沟通,对战时政令之推行以及最为紧要的征兵工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关于民国保甲制度之利弊,保甲对抗战之贡献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其中有多本专著,更有数十篇论文①。很多学者在论及抗战时期之保甲时,都将其与征兵问题联系起来,对保甲之评价渐渐由否定到部分肯定,特别是对保甲在战时征兵工作中的贡献评价趋于客观,如龚喜林、冉绵惠等人②。然而,民国保甲群体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仍需开拓,相关史料尤其是地方档案仍有待挖掘,“分区域、划时期、定专题”〔1〕的研究十分必要。龚汝富《民国时期江西保甲制度引发的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以宜丰、万载两县保甲诉讼档案为中心》〔2〕一文,利用县级司法档案对保甲引发的经济纠纷及其弊病进行讨论,就十分典型。
受此启发,本文将以对抗战兵源贡献最大且保甲制度最完善的四川省为例,以民国四川南溪县档案中的兵役诉讼档案为依据③,对战时大后方保甲与乡民之间“兵役纠纷”之现实进行描述,以展现当时保甲群体之困境以及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之控制状况。
一、兵役纠纷的产生背景
“生儿子是老蒋的,有银子是保长的”这句俗语,反映了民国时期保甲征兵之弊病和民众之痛苦。有学者指出:“基层保甲既是兵役的主要执行者,同时也是兵役的破坏者”。〔3〕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只能从史料与档案中寻找答案。
笔者有幸搜集到南溪县民国兵役诉讼档案。抗战时期的这类案卷共80个④,其中72件是关于保甲人员与乡民之间的纠纷的,另外8件虽不涉及保甲与乡民间的纠纷,但保甲人员也多以被告、证人、承保人等身份参与其中。由于保甲既是征兵主体,又是诉讼当事人,因而要了解这类纠纷的产生,就不得不从民国兵役制度与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说起。
1936年国民政府正式实施《兵役法》,由募兵制转变为征兵制,即义务兵役制。抗战时,国统区实行兵役管区制的征兵体制⑤,在各县政府设军事科(兵役科)负责征兵。民国二十八年(1939)3月,南溪县始设兵役科,佐理县长办理兵役政务,后改为军事科,由国民兵团副团长兼任科长⑥。县兵役机关将征兵任务分配到各乡、镇、保,由乡镇督促各保甲征送壮丁。
保甲为传统社会国家控制基层之工具,清末废止。1930年中原大战后,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为配合“剿共”,蒋介石希望以保甲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控制。1932年,豫鄂皖“剿匪”司令部一纸公文使得保甲制首先在“剿匪”区复苏。1939年新县制推行后,保甲是乡镇之下,“融自卫与自治于一体,发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多种作用的基层组织”〔4〕。
1935年川政统一后,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作为“剿匪”区,保甲制度始在四川推行。经过数次整编,四川的保甲编制相对完备,可谓民国保甲制度的“集大成者”。全面抗战时期,四川保甲已是综合性的基层组织。1939年,时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的胡次威谈及保甲制度时称:“值此抗战建国之际,举凡前方人力物力之补充,后方秩序之安定,莫不赖于保甲组织,及人事之健全”〔5〕。征兵可谓战时保甲工作的重中之重。“保甲长是办理征兵的最下级人员”,保甲整编的方方面面都与征兵息息相关〔6〕,更有时评称保甲“易于推行征兵制度”,“由募兵进到征兵制,实为保甲最大的功劳”〔7〕。此评论在当时多有政治宣传的色彩,但也足见基层征兵离不开保甲。
抗战八年,四川共征兵257万余人,加上当时划出的西康省,总数近300万,为全国之最,比排在第二的河南多出一百余万⑦。实行新县制后,1941年至1944年,四川年均征送壮丁35万人以上。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豫、湘两个兵源大省几乎全部沦陷。1944年底至1945年初,国民政府又紧急征兵以求大反攻之兵员,要求后方提前交清1945年之兵额,后方征兵压力倍增。根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统计,南溪全县人口只有286220人,而“八年抗战,南溪共征送壮丁16492名”〔8〕,征丁人数约占其人口总数的十七分之一。此数据还包括了妇女老幼,可见南溪县对抗战兵源之贡献以及当时征兵任务之沉重。作为征兵工作实际执行者的保甲,其所作的贡献与承受的压力无疑也都是巨大的。
四川保甲征兵对抗战虽然贡献不小,但由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不容忽视。征兵过程中,保甲常常估拉雇顶、徇私舞弊,而民众往往逃避兵役,甚至抗征行凶,更有聚众抗征引发暴动者。1939年,四川省办理首届征兵的直接抽签,因受地方恶势力操纵,引起群众不满,抽签会场被捣毁,隆昌、新都等县发生民变,群众包围县城,反对征兵,震动全川〔9〕。此类暴动虽不多见,但因征兵而引起纠纷进而产生诉讼的情况则不在少数,类似“王保长拉壮丁”的故事,在南溪县司法档案中屡见不鲜。
二、南溪县非法拉丁案件的情形
民国二十七年(1938)以后,南溪县每年壮丁配额均在2000人以上,年年有增无减。至抗战后期,征兵压力与矛盾不断上升。抗战时期的80件兵役纠纷,均为1939年以后发生,其中发生在1944年至1946年1月的多达65件⑧。虽然各级政府及兵役机关严禁估拉壮丁,但完不成征兵配额的保长将面临严厉的处罚。保长既要遵循上级命令,又不想因严格征兵而得罪土豪绅士以及多丁大户,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南溪县兵役案件中,除4例因壮丁抗征引发的案件外,其余皆可归为因非法拉丁或舞弊兵役而控告保甲的案件。
例如,民国二十九年(1940)“邓海三违反兵役”一案,白云乡民舒敏贤告保长邓海三于县府。舒敏贤认为其弟已经过继给叔父,其弟兄二人都是独丁,不应征送,因此控称:
民弟舒友文于民国二年抱继胞叔舒灴祖名下为嗣(抱约临审呈核),现家仅余三岁小孩及纤弱弟媳共计三口,住居一保七甲,务农为生。突于本年七月,由本乡丁强迫到联保办公处,旋即申送,现在本城帝王宫充役。窃查独丁及维持家庭最低生活者,现不服役,法有明文。该保长等藐法如斯,则兵役前途不堪设想。是以依法恳请钧府将维持家庭最低生活之独子舒友文提存,严传保长邓海三及丁讯究,以维役政而矝弱小,不胜顶祝。⑨
县府面对此控告,认为依照当时的规定,过继之事已经废止,征送合法,便批示道:
呈悉,查本案业经本府电饬该乡联保办公处查照呈复后,称该丁弟兄二人,系七七事变后分居,家境尚能过活,依法自应征送服役。呈称该丁曾过继胞叔为嗣一节,查廿八年五月,军政部解释“宗祧继承,民法已经废止,某甲所生二子,其一继承他人为子,其一留作己子,均不能认为独子,予以免常备兵役”,据请停止申送之处碍难照准。⑨
无论该壮丁过继之事是否成立,已知其家族人丁不旺。此案也并未就此了结,舒敏贤显然不甘心控诉不准的结果,于是搜罗证据,并以法不溯及既往的原理继续呈控:
查民弟舒友文即敦藻,早在民国二年凭证抚抱于胞叔舒灴祖名下,“据约载,灴祖所有家具银钱一切由敦藻受用”(抄粘呈审)等语。据此可见民等分居早在民国二年,依法独丁不服常备兵役。至于抚抱另居亦在法律有效之先,当不能究其既往。为此重申理由请予依法停止申送,倘如事实未明,仍恳传讯,是沾德便。⑨
因其诉由补充恰当,县府难以拒绝,只得批示:“既据再恳,姑准传案讯明后再夺”⑨。此案后来移送司法处,经士绅调解而撤销上诉⑩。诸如此类强拉独子或不符合征送条件的案件还有很多,反映了当时拉壮丁的对象多为穷困小户,正是“穷人免不了‘独丁也首当其冲’”〔10〕。
另外,当时控诉估拉别保甚至外地人员顶替的案件也有不少。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孙树全等告郭子舟等妨害兵役”一案中,被拉壮丁系长宁县长马乡第一保农民,经南溪县江南乡亲戚林顺卿介绍去江南乡何木匠处学艺,被当地保长郭子舟拉送,因而产生纠纷⑪。可见在基层“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11〕,保甲人员执行征兵任务时,也会顾及地方整体利益及其本人在保内的影响,不愿得罪乡邻,因此才会估拉别保甚至外地壮丁。所以有学者称:“保甲拉丁并非因本属无丁可征,而是出于本位保护意识的行为”〔12〕。
还有些案件中,保甲搕索缓役金、代役金后又估拉壮丁,如民国三十一年(1942)“罗友臣妨害兵役”一案。中兴乡第四保保民阚俊臣、陈焕章、何经学、陈伯希四人均以搕索缓役金之词呈控该保保长罗友臣。据阚俊臣呈控:
可恶伊藉公搕诈民财,并不给民缓役票,据以至今古正月二十七日,复将民缓役之丁阚吉三捉送。窃思既收缓役,何得估拉,违反兵役,诈搕无疑。⑫
民国三十三年(1944)“董姜氏告董荣书等妨害兵役”一案以多次搕索代役金之词控告其保长与乡长⑬。与此类似,贿买壮丁、保甲贪污侵吞之事也常引发兵役纠纷,例如民国三十四年“陈遂清告舒荣生妨害兵役”一案,以吞蚀安家费、优待谷之词状告保长⑭。又如“邬光荣妨害兵役”一案,壮丁家属“以估拉单丁,贪污侵蚀补助安家费具控保长”⑮。可见部分保甲人员借征兵的机会为难乡民,趁机敲诈而发国难财。
很多乡民状告保甲违反兵役,呈诉罪状时还要加上“包庇”一条。“包庇同胞”、“包庇兵役”等词在案卷中频频出现,同样表现出当时保甲人员浓重的本位观念。如民国三十三年“陈映堂告李树三妨害兵役”一案,告诉人因独子被征送深感不公,在呈文中哭诉道:
民风闻法令由人多者先征,况本保保长之子锡廷有子有孙,未能申送,又保长之弟德三膝下五子均该适龄,亦未申送。民单生独子,并无大男小女,何以至此征丁,岂不闭目受死矣。况兵役法推行,亦无此项规定,实系该保长反行命令,违法征丁,包弊子侄不虚,倘有虚伪,愿受反坐。民实无法想,只得具文前来,泣恳钧府垂怜,并请依法惩办,以儆将来包庇等事,如蒙俯准,顶祝不忘矣。⑯
三、兵役纠纷解决过程及其反映的役政腐败之表象
上述案件多以“舞弊兵役”、“籍丁搕财”、“贪污侵蚀”之词状告,似乎体现了当时役政之腐败。但南溪县档案中,兵役纠纷解决的全过程却并不足以证明保甲征兵腐败的现象。因为绝大多数非法拉丁案件以撤销案件和不起诉的结果收场,只有3例被提起公诉并最终以判决结案,而这3个案件中也只有1例对保甲人员做出了有罪判决。
大量非法拉丁案件在经过士绅调解和息或控诉人利益得到满足后自愿撤诉,司法机关或是撤销案件,或是在侦讯后作出不起诉决定。“陈映堂告李树三妨害兵役”一案即是如此,壮属陈映堂同被告保长李树三联名呈文,以求息讼:
窃映堂同保长李树三为兵役纠纷呈控县府在案,沐蒙地方士绅解劝,双方不再兴诉,映堂愿领安家费洋六千元自此和息,倘有意见情事,甘受法律制裁。为此联名呈请钧所鉴核,俯予转呈司法处备查,实为德便。⑰
南溪县司法处顺水推舟,批示道:“呈悉,查舞弊兵役与和解规定,该告诉人既甘息事,本处为减少纠纷,请准备查”⑰。可见司法机关对此类纠纷仍有息事宁人、减少诉累之取向。
又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陈夏氏告李绍文妨害兵役”案,裴石乡第十一保孀妇陈夏氏之独子被该乡第四保保长李绍文拉送,控告后因得到补助费及安家费,自甘息讼,撤回了告诉⑱。因为乡民在自身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后,也不愿纠缠诉讼,费时费力。同年的“姜大顺等告张耀卿等妨害兵役”一案中,告诉人以违法征丁为由状告前任保长。经乡长包析城、乡民代表主席包仲烈及本乡士绅李竺君等调解,“告诉人明了大义,以其征送之子,系为国家服役,按照规定,均有优待实物可领,甚属光荣 ,情愿接调解认诺了息”,便与人证联名声请撤回告诉。司法处虽认为“本案犯告诉所论之罪,依法不得撤回”,但侦讯之后,仍不予起诉⑲。
还有一些案件虽然未申请撤诉,却因犯罪嫌疑不足而不起诉。如前述“罗友臣妨害兵役”一案,司法处即批示:“被告罗友臣犯罪嫌疑不足,着即依法予以不起诉处分”⑳。民国三十四年(1945)“陈兴发告蒋占元妨害兵役”一案中,告诉人有四子,被征送一子,后逃回,又被征送一子,告诉人即以“非法拉丁,鲸吞勒派”之词控告保长,乡公所则呈函为保长证明。侦讯终结后,司法处批示:“被告犯嫌不足,应予不起诉处分”㉑。此类不起诉的案件不在少数。
由于民国时期仍未实现司法独立,基层长期实行“兼理司法制度”。南溪县抗战时期实行司法处制度,县政府附设司法处,与县长共同处理司法事务。这样的制度设计虽有审判独立之名,但作为上级的县政府仍有干涉司法之便利。而基层司法仍在延续传统的审断方式,即“综合运用情、理、律,以最便捷有效,也最能为当事人接受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13〕。如“袁绍武告张耀卿等妨害兵役”一案,经调解,告诉人甘愿撤诉,司法处批示:“申请撤回于法未合,但本处尚息事宁人,姑准所请”㉒。又如“赵绍卿告郑少云违反兵役”一案,判决理由称:“犯罪事实及证据既属明确,自应按罪论科。姑念该被告乡愚无知,犯罪后又颇知忧悔,属情不无可原,特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以示薄惩”㉓。此类批词、判词都体现了传统审断取向。
抗战时期,役政的好坏是战时基层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为保障兵役政务的畅通,县政府既要顾及征兵主体保甲之利益,也要适当维护乡民利益,因此面对兵役纠纷时,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平息纠纷,而不是适用法律。于是,在战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与近代“实用型司法”〔14〕的现实下,乡公所、乡绅都参与调解,乡民多因能得到经济补偿而申请撤诉,大量兵役纠纷以撤案或不起诉收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司法机关是否包庇保甲长,乡民是否捏词诬告,在司法档案中并不能得到确凿的证据。但是乡民为了胜诉,常夸大冤屈,在状词中罗列罪状,极力贬低保甲长,动辄扣上影响役政前途、国家命运的帽子。例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刘宏才告刘烈城妨害兵役”一案,诉状中列举了保长七项罪行:“(一)包庇兵役,(二)籍丁搕索,(三)黑暗专横,(四)吞蚀安家费,(五)贪污卑鄙,(六)派款不均,(七)私擅派款”。但其后的状词只是说:
该保长刘烈城包庇兵役,伊同胞三弟兄,胞伯八壮丁,佃户四子,内姪三子,余难枚举,皆未抽调一次,误国肥私,应何处分。其搕索民刘宏才去代征费洋四万三千元,张君禄去二万元,刘勋芳去三万元,应悉数追出缴案归公。㉔
可见该案被告虽被冠以七宗罪名,但事实主要是包庇同胞和搕索代征费两项。时人就曾谈到,有些反对保甲的不良分子“利用土律师、恶讼棍虚构案情,捏造事实,向军法、司法、行政各机关诬控”〔15〕。由此可见,这些纠纷的真实情况可能要比档案中展现的更加复杂。
总之,兵役纠纷中作为征兵主体的保甲虽多是被告身份,但从纠纷的解决过程来看,保甲并非只有非法拉丁、徇私舞弊的一面,也不能以此作为役政腐败之依据。毕竟在南溪县征送16492名壮丁的背景下,只有80例兵役纠纷案卷,这些兵役案件只是役政腐败的表面现象。
四、兵役纠纷背后保甲群体的困境
兵役纠纷的背后,存在各类具有社会优势和特权的群体。他们在征兵过程以及兵役纠纷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以维系自身或其团体利益。如作为优势群体之一的地主富户就因常与同样作为优势群体的保甲相互勾结、贿买壮丁、规避兵役而有在兵役纠纷中成为被告的案例。例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蒋向氏告刘春阳妨害兵役”一案,告诉人以“贿拉独子,顶替兵役,图饱私囊”㉕之词控告保长刘春阳及富户熊荣五等。最后,判决认为其控告实属空言,宣布被告无罪。
民国时期,基层乡村的土豪劣绅也极力谋求保长之位以获取利益,即便置身保甲之外的贤良正绅,仍可影响甚至左右基层权力运作。在兵役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传统的士绅团体自然也不甘寂寞,屡屡参与其中,扮演纠纷调停者的角色,对很多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影响。在其调解下,纠纷往往可获得事实上的解决,上文中相关案件的和解即是佐证。更有士绅与保甲联合为涉案保长作证,如“罗友臣妨害兵役”一案,第四保保长罗友臣涉案,第三保保长孟益臣联合七名甲长与五名乡绅为其证明并作保,该保状称:
甲长绅民等闻此冤抑,不忍缄默。伏思保长友臣,自奉委接办,迄今其人不苟。每遇公务欵,事事公开,照所奉公文数目当众分派等第,如数照派,不多不少,人众咸知。所有兵役花红等费,并未前闻何尝有买丁卖丁之说,亦未闻有贪污不法行为。是以切结证明,如蒙准保,鼓励贤能。倘有伪证,自甘同罪。⑫
多种社会势力在纠纷中的利益角逐,使得此类案件更加复杂。如士绅的参与,有时利于解决纠纷、安定乡里;有时则可能使保甲获得庇护,加剧役政的腐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保甲开展征兵工作,势必受到地方固有势力的影响,其自然不愿得罪强势群体,于是将征丁对象锁定在穷苦乡民身上,这便导致征兵的不公平,进而产生纠纷与社会矛盾。时人就已认识到保甲征兵之难处,指出他们“不敢得罪有钱有势者,又怕人家说不公平,日夜焦思着抽哪一个,更怕以后出征者家属来争吵安家费”〔16〕。
穷苦大众本身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加之遭遇征兵的不公,抵触情绪极易产生。而民国时期,民众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日渐增强,对征兵稍有不满即会诉至公堂。南溪档案中,保甲涉案虽很少被判刑,但却不得不承担因诉讼而产生的成本。更有不法之徒暴力抗征,南溪档案中即有4例案件,案情中保甲人员多无辜受伤。民国二十八年(1939)“南溪县一区区署告发王兴发抗拒兵役”㉖一案,被征壮丁之家属多人“到保长家内兹闹,估要穿食”,并辱骂保长,之后又滋扰区署办公处。又如民国三十三年(1944)“杨明春妨害兵役”一案,壮丁杨明春兄弟三人应予出征,但却抗拒征送。乡公所呈文中如此描述其抗征过程:
该杨明春一声暗号,居然指挥邻舍男男妇妇,不下数人,有持棒者,有持菜刀者,有持鸟枪者,蜂拥而至,方错愕间,鸟枪一响,刀棍随之。㉗
此案中三名队丁受伤,且被抢走步枪两只。杨明春“更系妨碍役政、严令归案之旧犯”,一年前就有聚众抗征之前科,后逃逸他乡。此次又聚众抗征,且动用枪支,足见其势力之大,顽劣之极。另外2例抗征案件中,被征者亦是聚众持刀行凶,砍伤保甲人员㉘。
虽然国难当头,但作为征兵对象的各类群体都不情愿应征入伍。壮丁逃避兵役的手段很多,如取得独子身份避役,伪造缓役、免役证书,去厂矿、盐场避役,入校读书避役,吸烟以避役,甚至自残以避役〔17〕。例如上述南溪县“罗友臣妨害兵役”案中,告诉人之一阚俊臣即有立假抱约以图避役之事。
保甲在征兵工作中阻力重重,而来自上级政府兵役机关的征兵压力却日益沉重。自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39~1944),南溪县每年的征兵配额平均在2700名左右,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而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统计,全县只有甲级壮丁11015名、乙级壮丁11305名。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39~1944)间,南溪县每年的配额任务均未完成,民国三十年(1941)欠额最多,达1818名〔8〕。而抗战后期又实行紧急征兵,南溪县国民兵团部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三月曾电令李庄镇镇长督促各保如期完成每保5名之紧急配额,否则将处分相关人员㉙。面对上级沉重的征兵压力,加之基层社会各方面之阻力,保甲采取非法拉丁的手段似乎更像是无奈之举,却会因此而受诉累。
不仅是征兵,保甲在各项工作中都面临类似的困境。四川民政厅厅长胡次威认为保甲因经费问题,“不得已而按户摊筹”,而“揭发奸宄,搜捕人犯,征兵,催科,派款”等常使其因公事结私怨〔5〕。还有文章称:“凡属下达于民众的事项,件件都要保甲长负责,件件都要经过保甲长方能有所成就,保甲长责任既如此繁重,事实上保甲长的地位又怎样呢?不客气的说,低到不能再低了!”〔18〕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保甲群体评价极低,有人称:“多数保甲长,在目前已成为民众的剥削阶级”〔19〕,亦有人评论保甲“依权仗势胡作乱为,鱼肉乡民,恶贯满盈……保甲长实在是要不得”〔20〕。
传统社会中在基层地位很高的乡绅往往不愿充任保长,除了不愿将绅权置于政府公权之下的缘故,想必也考虑到了保甲出力不讨好的困境。时人将保甲长难当的原因总结为:“有责任而无待遇,两三元办公费,仰不足以孝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此其一;工作繁难,责任无限,此其二;地位卑贱,勤受惩处,此其三;所做工作,如征兵、征粮、征工、收捐等,最易遭人毒怨,此其四;于公务外,尚须顾及本身之旧业,此其五”〔21〕。而当保甲者不外乎出于以下四种原因:一是富户为逃避捐税,再转派给他人而挺身出来当保长;二是因保甲长可缓役;三是因宗族间不和,为获得保甲征兵、派捐之权而打压异族;最后就是地痞流氓、失业巫道专以舞弊为目的,揩油捞摸〔22〕。正是“好人不当保长”,更何况威望甚高的士绅呢!
五、余论:近代化的国家与延续传统的基层
认识到保甲群体的困境之同时,我们也可以发觉造成其困境之种种缘由,如待遇低、经费少、任务重等等,但最为关键之一点,乃是其责重而权轻。
以南溪县征兵为例,保甲本无征兵权力,却要承担责任。军事科设立前,县政府第一科兵役股负责征兵,后来专门成立了军事科(兵役科)这样的兵役机关负责兵役。但军事科人员配备很少,南溪县设立兵役科时只有科长1人、科员1人,办事员2人,雇员2人〔8〕。四川各县军事科最多也不过配备9人。这样少的人员配备,靠其自身根本无法完成征兵工作,于是只能通过保甲。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新县制中,保甲是乡(镇)之细胞组织,并非独立之一级,因之保甲长只能在乡(镇)公所指挥之下,去协助政令推进而已”〔18〕。作为“乡镇内部之编制”,保甲只是受基层政府与兵役机关之委派协助征送壮丁。征兵虽属国家行为,但可比照现代行政诉讼之法理。保甲在执行政府委派之任务时,即便有违法之处,也应由委托者或授予其权力之机关承担责任。而在兵役纠纷档案中我们发现,民众的不满所针对之主体只是保甲人员,真正享有征兵权力并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兵役机关(军事科或国民兵团)却可置身事外。可见,基层政府部门的责任转移给保甲后,规避了行使公权力的风险。
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月,南溪县国民兵团代电嘉奖第二区区队长以及多个乡长在紧急征兵工作中督促努力,如期完成了任务㉙。在此类兵役机关嘉奖役政工作人员的电文中,往往只提到督促征兵的区队长、乡长,而几乎不涉及对征兵实际执行者保、甲长的嘉奖鼓励。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保甲群体的责权不对等。
透过兵役纠纷,我们看到了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基层保甲群体的困境。民国保甲人员有善有恶,其存在于战乱年代,长期生活在政权与绅权的夹缝中,是“夹缝下面的牺牲者”〔23〕。面对上级政权、地方传统势力与民众抵触等多重压力的保甲,其委屈难以被世人理解。
实际上,保甲在其他工作中一旦有违法情形,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例如保甲还负有乡村警察之职责,此职责本应由警察部门担负,但当时警察机构之人力物力有限,也无法在基层乡村发挥其作用,所以保甲在行使缉捕盗贼之职时,同样承担了相应责任。县政府之下,同样有田赋粮食管理处、税捐处,但征粮、派捐的具体工作均离不开保甲。可见民国基层政府虽成立了各负其责的种种部门,但其实际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很少承担责任。
罗志田教授提出,“国进民退”是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国家的“职责和功能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步步退缩”〔24〕,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国家政权机构的扩展与延伸。中国自清末便开始了督抚衙门幕职“分科治事”的改革,“初步实现了具有近代科层制特征的嬗递”〔25〕。之后,与督抚司道层级的分科治事相适应,府厅州县也进行了房科划分的官制改革。“与传统的六房(吏、户、礼、兵、刑、工)相比,官制层面的职能扩展与分科治事,反映了行政机构逐渐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26〕。
中华民国建立后延续了这一趋势,基层县署组织进一步健全,近代化的科层制逐步建立。与此同时,县之下还成立了乡一级政权。这些延伸的新机构本应是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工具,但如上文所述,基层政府的各部门无力行使职能,更不愿承担责任,于是要依靠社会转型中的非正式机构——保甲。可见其时虽有近代化之行政体制,国家整体上由“小政府”转变为“大政府”,但基层政府“权大责小”,延续了“国责不下县”的传统㉚,并没有真正实现近代化。
不仅是基层政权延续了传统,基层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没有摆脱传统,在司法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南溪县已有司法机关,却不能独立于政府,此即传统社会司法与政务不分的变相延续,而在审判中也同样延续了传统的审断方式。
随着“国进民退”的大趋势,代表民间权威的乡绅逐渐淡出。乡绅退出地方事务后,科层制无法落实的基层政权仍需要与乡村社会联系的中介,保甲应运而生。半官方性质的保甲不同于乡绅,其职责繁重得多,且要听命于政府,这似乎是“国进民退”的表现。但是乡绅在基层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从南溪县档案中可得知,乡绅参与纠纷调解,使两造息讼的情况还很常见,这是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传统的延续。然而在传统乡土社会的背景下,受政府委派的保甲也要遵照乡土规则办事,因而发挥了传统乡绅的一些作用。这些传统因素在民间是不可能迅速改变的。
“国进民退”是一个持续的趋势,其从近代持续至今,不是经过一两场政治变革即可完成的,基层的变化尤其缓慢。在民国时期,虽有了近代化的法律与政治体制,但在实践中基层政权却没能使之得到有效的实施。申言之,近代化的国家与延续传统的基层社会之间是联接失败的。因此,政权需要保甲这样的组织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保甲显然也难以完成不应由其完成的职责。保甲“责大权小”,而基层政府部门“权大责小”,这与近代国家政权变革之趋势不符,也是国民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失败的原因之一。秦晖教授认为,权力大而责任小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27〕。我们今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避免这种“权大责小”的政府。同时我们应当吸取民国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不能衔接的历史教训,在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建设中,所立之法律与制度要考虑基层实际情况,并且要关注已推行之法律和制度在基层的实际效果,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治理。
(本文在档案收集和文章写作中承蒙四川大学法学院里赞教授、刘昕杰副教授、王有粮博士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相关专著有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冉绵惠、李慧宇《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冉绵惠《民国时期四川保甲制度与基层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相关论文如:王云俊《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武乾《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李伟中《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载
《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肖如平《从自卫到自治——论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载《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②相关文章如:龚喜林《抗战时期基层保甲征兵的制约性因素探析》,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16期;冉绵惠《抗战时期国统区“抓壮丁”现象剖析》,载《史林》2009年第4期等。
③南溪档案存于四川宜宾市南溪区档案馆,共11486卷,其中诉讼档案7106卷,约占总数的65%。案卷时间从1912年至1949年,跨越整个民国时期。
④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列出这80个案例的档案全宗号、目录号和案卷号(形式为: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分别是:5-01-540,5-01-0548,5-01-0633,5-01-0672,5-01-0703,5-01-0837,5-01-1030,5-01-1519,5-01-1540,5-01-1649,5-01-1668,5-01-1948,5-02-0066,5-02-0076,5-02-0089,5-02-0166,5-02-0279,5-02-0417,5-02-0446,5-02-0459,5-02-0479,5-02-0516,5-02-0518,5-02-0519,5-02-0521,5-02-0548,5-02-0549,5-02-0553,5-02-0594,5-02-0616,5-02-0671,5-02-0682,5-02-0725,5-02-0734,5-02-0737,5-02-0738,5-02-0742,5-02-0753,5-02-0756,5-02-0757,5-02-0774,5-02-0784,5-02-0796,5-02-0816,5-02-0845,5-02-0862,5-02-0864,5-02-0873,5-02-0878,5-02-0880,5-02-0885,5-02-0898,5-02-0905,5-02-0928,5-02-0942,5-02-0946,5-02-0953,5-02-0971,5-02-0979,5-02-0980,5-02-0984,5-02-0991,5-02-0994,5-02-0998,5-02-1017,5-02-1029,5-02-1039,5-02-1057,5-02-1060,5-02-1111,5-02-1125,5-02-1134,5-02-1142,5-02-1152,5-02-1172,5-02-1251,5-02-1277,5-02-1285,4-01-0265,4-01-0492。这些档案均出自宜宾市南溪区档案馆的南溪县司法处档案。以下关于兵役纠纷的讨论,也依据此80个案例进行。
⑤四川于1938年6月成立省军管区,下辖6个师管区,19个团管区。后改为军、师两级制,下辖22个师管区,南溪县属叙南师管区。参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军事志》第5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民国三十三年(1944)7月,军事科裁撤,其业务由国民兵团接管。次年十月国民兵团裁撤,复设兵役科。后改为军事科,负责兵役,直至解放止。参见四川省南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南溪县志》第4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⑦参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历史资料军警特宪类,案卷号3281(1)/1。转引自冉绵惠《民国时期四川保甲制度与基层政治》第1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⑧笔者搜集的兵役诉讼案卷虽有部分时间是在抗战胜利后,但案件事由均发生在抗战时期。案件在1944年与1945年相对集中,反映了抗战后期征兵难度的加大。
⑨“白云乡民舒敏贤以非法拉丁告邓海三的呈报告”,民国二十九年,全宗号3,目录号01,案卷号49,南溪县军法室档案。
⑩“县政府告发邓海三违反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二十九年,全宗号5,目录号01,案卷号837,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⑪“孙树泉等告郭子舟等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742,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⑫“中兴乡公所送吞蚀缓役的保长罗友臣的呈笔录”,民国三十一年,全宗号3,目录号01,案卷号59,南溪县军法室档案。
⑬“董姜氏告董荣书等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三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1029,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⑭“陈遂清告舒荣生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616,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⑮“邬光荣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756,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⑯“陈映堂等以反行命令违法妨害兵役的呈公函笔录”,民国三十三年,全宗号3,目录号01,案卷号68,南溪县军法室档案。
⑰“陈映堂告李树三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三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998,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⑱“陈夏氏告李绍文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737,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⑲“姜大顺等告张耀卿等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774,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⑳“罗友臣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一年,全宗号5,目录号01,案卷号1519,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㉑“陈兴发告蒋占元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816,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㉒“袁绍武告张耀卿等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796,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㉓“赵绍卿告郑少云违反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三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873,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㉔“刘宏才告刘烈城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928,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㉕“蒋向氏告刘春阳违反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四年,全宗号5,目录号02,案卷号1060,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㉖“南溪县一区署告发王兴发抗拒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二十八年,全宗号5,目录号01,案卷号548,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㉗“杨明春妨害兵役的刑事案件”,民国三十三年,全宗号5,目录号01,案卷号1649,南溪县司法处档案。
㉘这两个案例的档案号为:5-02-0417,5-02-0089,见南溪县司法处档案,宜宾市南溪区档案馆藏。
㉙“南溪县李庄镇公所造报壮丁花名册”,民国三十三年,全宗号11,目录号01,案卷号131,南溪县罗龙乡公所、中城镇公所档案。
㉚秦晖教授认为传统社会并非“国权不下县”,而是“国责不下县”,即政府处于“权大责小”的状态。参见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关于政府“大小”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第10页。
〔1〕朱德新.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述评〔J〕.安徽史学,1996,(1):71-75.
〔2〕龚汝富.民国时期江西保甲制度引发的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以宜丰、万载两县保甲诉讼档案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3):90-96.
〔3〕龚喜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研究之回顾及展望〔J〕.军事历史研究,2012,(3):174-180.
〔4〕冉绵惠.民国时期四川保甲制度与基层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
〔5〕胡次威.调查及报告:谈保甲制度〔J〕.新四川月刊,1939,1(1):92-94.
〔6〕张斯麐.保甲与征兵〔J〕.闽政月刊,1938,3(2):29-30.
〔7〕张万年.战时保甲制度掇论〔J〕.胜利,1939,(23):10-11.
〔8〕四川省南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南溪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453,484,474.
〔9〕伍福莲.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政策在四川的实施情况〔D〕.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35.
〔10〕廉 健.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征兵工作——以四川温江县为中心的考查〔D〕.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26.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9.
〔12〕陈廷湘.战时特殊利益空间中的国家、基层与民众——从抗日战争时期兵役推行侧面切入〔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20-29.
〔13〕里 赞.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J〕.法学研究,2009,(5):196-207.
〔14〕刘昕杰.实用型司法: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审判传统〔J〕.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30-37.
〔15〕葛文渊.对于乡镇保甲长应有的认识〔J〕.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团刊,1943,(34):12-14.
〔16〕秦秋谷.农民和保甲长〔J〕.妇女生活,1939,9(12):3-4.
〔17〕龚喜林.抗战时期基层保甲征兵的制约性因素探析〔J〕.历史教学,2011,(16):22-29.
〔18〕刘福沅.目前乡(镇)保甲长的人选问题〔J〕.地方政治,1943,9(1):25-27.
〔19〕白 衣.今日之保甲〔J〕.每周导报,1938,1(13):8.
〔20〕短评:保甲长要不得!〔J〕.职业妇女,1946,2(2-3):10.
〔21〕高亨庸.论乡镇与保甲之任务划分〔J〕.服务月刊,1942,6(7):29-32.
〔22〕吴光甲.保甲人选问题〔J〕.地方政治周刊,1939,2(7):12-15.
〔23〕吴 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上海: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138.
〔24〕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5-19.
〔25〕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J〕.历史研究,2006,(5):88-103.
〔26〕关晓红.清季府厅州县改制〔J〕.学术研究,2011,(9):92-103.
〔27〕秦 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关于政府“大小”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考察〔J〕.社会科学论坛,2005,(2):10-37.
——以成都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