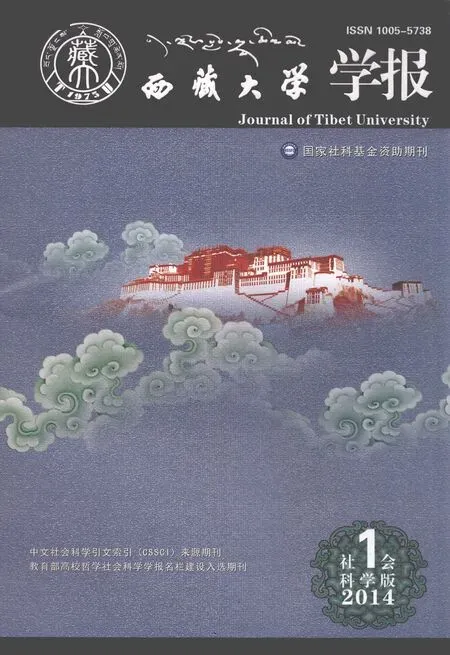论数字三维动画的视觉真实
李翔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北京 100024)
数字三维动画又叫3D动画,是在数字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兴动画形式。数字三维动画的基础是3D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基于这种技术,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立体空间中建立模型、制作材质、添加运动、设计照明,并最终通过一定的视角将整个三维场景渲染压缩为平面的活动影像。作为一种表现能力突出的视觉媒介,数字三维动画在今天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艺术、娱乐、商业、教育、医学、工程、科研等许多领域当中。
与传统动画或实拍影像相比,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数字三维动画还非常年轻,然而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它已经深刻地重塑了整个影视工业的面貌。数字三维动画之所以大受欢迎,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制作流程上有着许多传统动画工艺无法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它在直观的视觉形态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看上去非常的“真实”。事实上,从数字三维动画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和“真实”这一属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回顾数字三维动画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画面真实度不断攀升的历史。有学者指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将艺术视为现实的拟仿物的观念,是数字三维动画技术及其文化的主要思潮。”[1]
一、数字三维动画的认知真实性
用“真实”来评价数字三维动画仿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稍一思考,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悖论。显然,当我们形容《环太平洋》(2013)中巨大的机甲武士和异星怪兽很“真实”时,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它们确实出现在了拍摄现场,相反,大多数观众都清醒地明白这只是一种虚构的幻象。那么,当我们用“真实”来描述数字三维动画时,我们所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这种真实不同于实拍影像的真实。实拍影像之所以真实,不仅在于它呈现的结果,更在于其成像的机制。“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2]在巴赞看来,光学规律不会说谎,因而任何出现在实拍画面中的形象都必然是某样真实事物所留下的痕迹。用罗兰·巴特的话说,摄影与其拍摄的对象是“粘合在一起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存在的证物罢了。[3]反观数字三维动画,显然它完全不具备实拍影像那种“与周围世界的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动画中的星际战舰,在现实中找不到参照物,而即使是仿照真实事物打造的形象,如CG制作的埃菲尔铁塔,它与真实的埃菲尔铁塔也不存在物理上的索引关系。因而,数字三维动画对于现实的再现充其量也就是一种绘画式的模仿,而不是摄影式的复制。
其次,这种真实也不意味着逻辑上的真实。所谓逻辑真实,是指图像在某方面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的状况。例如,一张地图在风格上也许是简略的,但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记录了地理信息,因而在逻辑上地图图像就是正确而真实的。反之,一张广告照片,若对产品进行了过度美化和夸张,它便有了虚假的成分。贡布里希提醒我们,其实“真”和“假”这两个概念只能用于陈述和命题,图像本身并非是一种陈述或命题,因而“一幅画也不可能是真的或者是假的”[4]。图像在逻辑上是否真实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被置入的语境。对数字三维动画来说,其逻辑上的真假需视具体功能而定,例如,应用于医学、工程领域的数字三维动画,逻辑上的真实性就是必需的,而对于那些以创造审美体验为目标的数字三维动画,逻辑的真实就无足轻重了。
再次,这种真实也不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根据胡经之先生的解释,就是“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中主体和客体的审美关系。”[5]它是“人生真谛的窥见”以及“艺术生命的敞亮”。艺术真实是针对作品整体而言的,它要求艺术作品要真实地塑造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时代图景、真实地传递主体情感、真实地表达审美理想。显然,当我们谈及数字三维动画的“真实”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复杂的社会人文因素,我们所说的真实不是作品内容层面的真实,而只是作品外观表象上的真实。
那么,数字三维动画的“真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真实呢?在数字三维动画中,许多形象和场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存在或者无法拍摄到的,我们深知这一点,然而有趣的是,这种理性的认识并没有阻碍我们的感官将那些虚构的画面“当作”是真实的,那些足够精致和细腻的图像完全说服了我们的眼睛,以至于让知觉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不可思议的景物是实际存在的。数字三维动画的“真实”,不是建立在与现实和生活的内在关联上,而是建立在图像本身对我们的知觉系统所产生的作用上,这种“真实”其实是由于错觉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它纯粹是一种“感觉上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三维动画与其说是在模仿现实,不如说是在迎合我们关于现实的感受,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就不是客观化的真实,而是一种认知层面的“视觉真实感”。
二、数字三维动画视觉真实感的达成
数字三维动画是一种虚构的影像,然而,它所呈现出的视觉真实感却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远远超越了其它非摄影性质的视觉媒介——特别是绘画和基于绘画的二维动画。那么,在数字三维动画中,这种高度的视觉真实感是如何达成的呢?美国学者普林斯指出,一个影像要显得真实,就必须包含“经验性的证据”,这些证据会“指使天真的观众根据自己的经验而立即接受那些在经验中很熟悉的事物。”[6]本文认为,在数字三维动画中,为画面赢得出众视觉真实感的经验性证据主要有四个,它们分别是“严格的单点透视”、“合规律的光影分布”、“丰富的视觉质感”以及“完善的运动表现”。
(一)严格的单点透视
人类生活在一个三维的宇宙之中,然而当我们希望用图像来再现某种视觉经验时,面对的却往往是平面的介质,从最原始的绘画,到最先进的计算机动画,大都是如此,因而就出现了一个制图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到底应该按照怎样的逻辑,去将立体的场景翻译为平面的影像?
在历史上,古人对此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其中古埃及人的做法尤为引人注目。如在3400多年前的壁画《内巴蒙花园》中,埃及艺术家描绘了一个被树木环绕的方形池塘,这幅画的奇特之处在于,其中的池塘显然是从天空俯视所看到的样子(一个完美的矩形),而周围的植物和水池中的动物却统统呈现出侧面的姿态。显然,在表现这个场景时,画家为每个物体都选择了最能保留其外形特征的观察角度,这一方面让所有的形象都非常明晰,一方面却也使得整个图像不具备任何统一的空间观念。
古埃及的这一模式在希腊时代开始改变。到公元前6世纪,绘画中已经出现了重叠和透视缩短两个现象,这些画法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们标志着画家不再妄想在一个平面中完整地保留所有事物的形状信息,而是开始尝试着仅仅把肉眼所直接见到的景象记录下来。在西方,这种观念的转变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缓慢发酵,并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单点透视画法的发明。
单点透视画法的关键在于视点的确立。当唯一的视点被选定后,画家就可以想象他是在由这个视点出发透过一个垂直于视线的玻璃板来观察面前的世界。这时,若将视点和景物中所有的物点通过一系列假想的直线连接起来并与玻璃板相交,那么在玻璃板上便得到了一幅直接由现实场景“临摹”而成的平面图像。由于单点透视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几何原理的测绘法,因而人们相信,通过这种方法画出的图像是最正确的,也是最真实的。比起单纯的重叠和透视缩短,单点透视的意义在于它为图像设定了统一、规范的空间逻辑,根据这一逻辑,画面中所有景物的大小、位置、方向都不再是任意的了,它们必须服从空间关系的约束和调配。至此,人类似乎已经找到了将三维现实翻译为二维图像的最佳途径。
数字三维动画的画面完全是通过单点透视的法则组织起来的,这就赋予了它一种摄影式的构图框架。不仅如此,和传统的透视图像相比,数字三维动画中的单点透视又有着先天的优越性。首先,在传统的绘画工艺中,虽然单点透视的原理是通过一套客观的测绘手段来规定的,但是人们一般并不会依赖玻璃板或者暗箱来作画,而是在理解了单点透视的基本观念后,就完全依靠自己的感觉来绘制图像了。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一些绘画虽然有透视的意识,然而从严格的标准来看,其空间关系依然是模糊和松散的,这种现象在卡通风格的二维动画中尤其明显。而在数字三维动画中,透视关系并非手工绘制的,而是由程序依据严格的几何规则渲染出来的,这就令画面的透视有了数学上的精确性。其次,在数字三维动画中,当视点和景物发生任何程度的相对运动时,透视关系也会立即自动更新,表现在画面中,就是相关景物的轮廓会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产生出被称为“运动视差”的效果。相较而言,这种效果在二维动画中却往往是缺席的,这是因为,对二维动画来说,要表现出任何轮廓的形变,就必须实打实地绘制出大量的静帧,虽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由于工作量的巨大,在实践中人们并不总是这么做。很多时候,二维动画在表现物体的运动时,往往只是对轮廓进行了整体的平移或缩放操作,这样一来,画面的空间就容易显得扁平和虚假了。
(二)合规律的光影分布
众所周知,光的存在是一切视觉现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人们在谈论一个场景或者一幅画中的“光影”或“照明”时,指的却并非视像或图像的全部,而是一种与景物本身相游离的成分。根据阿恩海姆的形容,照明就仿佛是覆盖在物体之上的半透明“薄膜”,这层薄膜或亮或暗,密度或大或小,它的存在并不会改变物体的轮廓和本色,而是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一种阴影梯度或者说亮度分布。在图像制作领域,这种把形象基底和照明作用进行人为剥离的视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恩海姆指出,正是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照明理解为景物的一种附加属性,所以“在早期的视觉艺术中,光线得不到表现是毫不奇怪的。”[7]
到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在画面中填充灰阶能让形象显得更加立体生动,于是一种涉及明暗的绘画模式便出现了。有趣的是,明暗原本是照明的产物,但是当人们在熟练地应用明暗画法时,却往往不去顾及光学规律本身。如在一些中世纪的绘画中,观众完全无法判断光源位于何处,因为不同物体上的高光方向根本就是冲突的。在这里,明暗的存在虽然带来了阴影梯度,然而它在本质上却不是照明的结果,它仅仅是一种习得的绘画技法,而非源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模仿。
对真实光影的再现直到15世纪才被重视起来,在之后的数百年间,现实主义油画实现了摄影术出现之前对形状和照明最细致入微的刻画,而印象派绘画则干脆舍弃了景物的轮廓,直接进入到一片最纯粹澄明的光影世界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最精致的绘画杰作中,光影效果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究其根本,这还是由于绘画媒介内在的手工本性。如果说透视法尚且可以通过工具来提高精度的话,那么艺术家在决定画面中某一处的明暗和光色时,则只能完全依赖自己的主观感受了。对二维动画来说,由于需要绘制大量的图像,因而细致、精准的光影再现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看到,在大多数二维动画中,照明效果都仅仅是被十分粗略地示意了出来,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数字三维动画的光影表现则不会面临上述那些困境。在三维场景中,要想添加照明效果,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引入光源。虽然这种光源亦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真正的光学法则。例如,在最基本的三维技术中,“光沿直线传播”的规律就已经被完美地诠释出来了,处于一定位置的光源,可以给景物投射出准确的阴影,并且在那些与光线不垂直的被照物体表面上产生严格基于倾斜角度的亮度衰退。仅只这两点,就已经使得三维动画光影分布的合理性远超二维动画了。而在稍微成熟一些的三维程序中,虚拟的光线则不仅能够在多个表面之间来回地反弹混合,还能进一步与模型发生深度互动,模拟出一些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光学现象。一言蔽之,对数字三维动画来说,画面中任何一个像点的照明程度、阴影效果以及光色混合,都不是创作者根据经验或技巧想当然地决定的,而是软件算法中那些虚拟的光线按照与现实规律相近似的因果逻辑,通过大量的数学运算模拟出来的。如此一来,数字三维动画光影分布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就有了机制上的保证。
(三)丰富的视觉质感
人类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物质世界中,我们身边的事物由各种各样的材料构成,而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独特的物理属性,这种属性反应到我们的视觉中,就形成了视觉质感。现实中不同事物所展现出的视觉质感是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而就某种具体的材料而言,其视觉质感则可以看作是由基本色、反射率、透明度、高光形态、表面肌理以及一些更加微妙的视觉特征混合而成的复杂综合体。
通过绘画完善地重现景物的视觉质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构成视觉质感的因素是众多、复杂的,而画家所能操纵的却只有颜料的色彩深浅和运笔的方法力度而已。也就是说,无论是表现基本色、透明度,还是高光形态或者表面肌理,画家都只能通过控制颜料在空间上的分布这唯一一种途径来实现,这就对观察力和技巧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二维动画中展现丰富的质感就更是件困难的任务了。这主要还是由于它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过高。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二维动画都是以“单线平涂”的工艺绘制出来的,在这种工艺中,只有平整、均匀的色块,而没有细腻丰富的视觉质感。单线平涂的二维动画制作起来相对容易,并且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简明的艺术风格,然而就视觉真实感而言,它显然就大打折扣了。
与传统二维动画不同,数字三维动画对视觉质感的追求往往是毫不妥协的。在三维动画中,对质感的呈现是通过“虚拟材质”的应用而非颜料的堆砌来实现的。事实上,计算机图形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对各种“着色程序”的开发。在三维软件中,不同的着色程序对应着不同的材质类别,它们有着不同的基本属性,如有的可以用来模拟金属的独特光泽,有的则能再现出透明材料的内部折射。此外,这些着色程序一般都是参数化的,它们具有许多可调项目和贴图通道,当这些设置更改后,它们又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视觉外观。计算机图形技术发展到今天,现实世界中几乎任何一种特定材料的质感都已经可以被着色算法还原出来了。当三维模型被赋予了虚拟材质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可以再次交由渲染过程去自动完成。在这个阶段中,每种材质都按照特定算法所规定的逻辑去和场景中的光线进行互动,并最终给出与现实视觉经验相符合的质感效果。
(四)完善的运动表现
在如实地展现事物的运动这一方面,数字三维动画相比传统动画媒介同样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首先,在数字三维动画中创造运动的原理是“关键帧插值”,而非是传统动画那种“逐格拍摄”。这就意味着完全不用为了压缩成本而在影像的帧率上作出任何的牺牲。因此,数字三维动画中的运动总是平滑而流畅的,相较之下,传统动画中的运动则容易出现不连续感或者跳跃感。
其次,在数字三维动画中,动作的添加和调节是以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的。传统二维动画的运动是在平面的介质上被“画”出来的,动画师所直接面对的是大量逐渐变化的线条和色块,这些变化的过程很难以数学的方法去量化和描述,它更多地依赖于创作者对运动原理的领悟以及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而在数字三维动画中,运动的设计则是在立体的空间中进行的,这和现实世界的情况毫无二致,因而运动也就可以通过位移、速度、向量、角度等客观的物理和几何参数加以描述。正因如此,人们不仅可以像移动现实物品那样移动虚拟模型,还能够通过运动捕捉系统一类的设备,将真实事物的运动参数记录下来,并用这些数据直接控制动画物体的动作。
再次,在数字三维动画中,还有大量的运动不是手工调制出来的,而是由程序自动驱动的。而这些程序在开发时一般都研究、参考了现实事物运行的力学法则,因而通过这些方法创造出来的运动的真实性也就得到物理上的保证。例如,我们常常在三维动画中看到建筑或山石崩塌的场面,这时,那些坠落的石块和飞溅的碎屑的复杂运动都不是人工调节的,而是由计算机根据一定的初始状态和参数基础解算出来的,这些破碎物就像在真实世界中那样受到各种“力”的作用,互相摩擦、碰撞,最终呈现出非常合理、逼真的垮塌过程。随着计算机仿真技术的进步,这种自动动画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无论是布料的变形、肌肉的收缩,还是液体的流动、烟雾的升腾,动画师只需要进行简单的设定,软件就能自动给出十分可信的运动效果。
三、数字三维动画视觉真实感的价值和意义
拉斐尔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此乃拉斐尔之墓,自然之母当其在世时,深恐被其征服;当其谢世后,又恐随之云亡。”[8]作为对一位伟大画家一生成就的总结和赞美,这段墓志铭想要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拉斐尔能够十分逼真地绘制出世间万物的形象。
在人类制造图像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伴随着一股追求“形似”的冲动。“从古代起,人们就把艺术品看成是现实事物的真实复制品。在评判一幅画时,如果这幅画被认为与实物极其相似,甚至酷似到可以乱真的程度,就是对这幅作品的最高赞扬了。”[9]事实上,在很长的时期中,人们是如此习惯于用“再现的准确度”来评价画作的优劣,以至于在西方美术界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把艺术史解释为向视觉真实的进展。”[10]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现代主义绘画的兴起,这个传统仿佛逐渐瓦解了。然而,如果以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艺术史,就会发现人类在追求形似的道路上并未停下脚步,只不过写实的接力棒已经从绘画传递给了摄影、电影以及计算机生成的图像。
既然古往今来“形似”在图像的制作中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命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画面的写实如此重要?而人们孜孜不倦地在图像中追求视觉真实感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巴赞曾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美术的原始功能:“如果用精神分析法研究造型艺术,就可以把涂防腐香料敛藏尸体看成是造型艺术产生的基本因素。精神分析法追溯绘画与雕刻的起源时,大概会找到木乃伊‘情意综’”。[11]当艺术摆脱了巫术职能后,这种情结便演变成一种“用摹拟品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这就是说,图像在心理层面可以被当作是现实的副本,它能让事物突破原有的时空局限而与观看者同在。正如桑塔格说:“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12]我们也可以说:“拥有某物的图像就是拥有某物本身。”既然生产图像的目的是为了创建外部世界的代用品,那么图像被制作得越逼真,这种替代关系也就越自然。
“形似”的必要性也可以通过符号学理论加以说明。图像无非是人造的符号,而对于任何一种符号,其基本的作用就是能表示出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对于不同的符号现象,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自然语言中,词和词义关联是任意的,它们仅有文化层面的限定关系,而对于图像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要用图像来表现某件事物,就必须让画面的结构与这个事物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正是基于这个特征,皮尔士在划分符号的类型时,就把图像称为是一种“相似符号”。那么,如果说相似性是联系图像能指和所指的“粘合剂”的话,那我们自然可以宣称,图像与指称对象的相似程度越高,它作为一种符号所传达的信息也就越完整,而图像的认识论价值也就越发能够得以体现。
在视觉艺术中,“形似”还具有技术美学的审美意义。自古以来,制作逼真的图像都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摄影除外)。风景画大师康斯坦布尔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13]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图像能否被制作得逼真,取决于制作者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他自身的技艺技巧。例如,用透视法画出的图像就要比古埃及的壁画显得真实,而老练的画家也要比初学者更容易准确地重现景物。由于图像的逼真与否与制图技术的高低有着紧密的联系,写实的水平便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是反观制图技术的一把标尺,而对视觉真实感的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了一种对于技术或者技巧的审美。在这样的背景下,画面中的景物是什么反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如何被巧妙地再现了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艺术家制造写实图像的目的并非为了欺骗眼球,“而是要通过达到的逼真程度来展示技巧。”[14]正是由于图像再现是件颇具难度的事情,因而成功的写实就标志着对这种困难的克服——它是技术和技巧的胜利,是对创作者的智慧和劳动的肯定,是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再造自然的能力的确证。
对数字三维动画来说,视觉真实感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也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加以分析。从心理接受的层面看,视觉真实感拉近了受众和画中景物二者之间的距离。动画和实拍影像不同,其中的形象大都源于艺术家的想象。在二维动画中,这种假定性是显露无疑的;而在数字三维动画中,由于被赋予了完善的真实感,假定的形象便披上了视觉合法性的外衣,它们不再以一种自甘虚假的面目示人,而是通过大量符合现实经验的视觉线索,来力证自身的存在感。视觉真实的呈现让数字三维动画进入到了传统动画和实拍影像之间的空白地带,它既能够“突破传统动画的接受障碍,与实拍电影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15],又能够摆脱实拍电影那种物质索引的束缚,让影像的书写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从而实现了新的“完整电影”的神话。从技术美学的角度看,人们对数字三维动画视觉真实感的热情可以视为是一种技术崇拜。当面对屏幕上以假乱真的动画形象时,我们一方面沉浸于这种亦真亦幻的光影世界之中,一方面也由衷地感慨数字科技的威力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惊人的地步。我们享受技术的成果,并赞叹科学的进步,我们目睹了时代生产力的伟大突破,并发自内心地为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新成就感到振奋和自豪。
[1]Patrick Power.Animated Expressions:Expressive Style in 3D Computer Graphic Narrative Animation[J].Animation,2009(4):108.
[2][1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衍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1,6.
[3][6](美)S.普林斯.真实的谎言——感觉上的真实性、数字成像与电影理论[J].王卓如,译.世界电影,1997(1):212,219.
[4][10][13](英)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M].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59,12,29.
[5]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4.
[7][9](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32,160.
[8](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23.
[12](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
[14](美)斯蒂芬·戴维斯.艺术哲学[M].王燕飞,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65.
[15]孙振涛.视觉真实:作为3D动画美学特质的确立[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