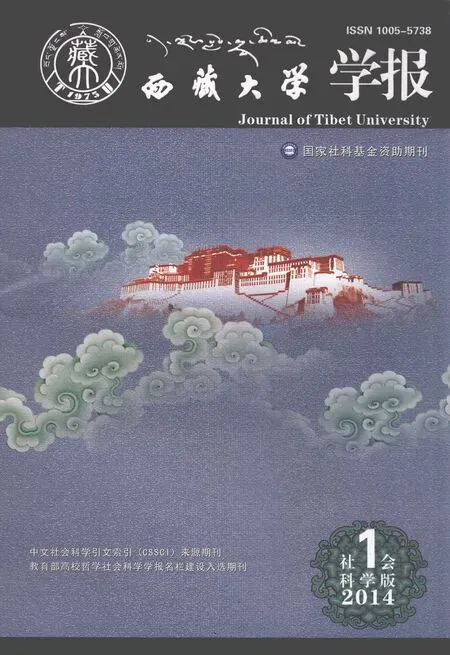西藏浪卡子出土金器的再认识
吕红亮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 四川成都 610064)
一、既存认识
西藏古代的黄金曾经是一个谜,希罗多德曾经提及在印度河上游的“蚂蚁金”[1],德国藏学家弗兰克(A.H.Francke)曾经就此问题在西藏西部拉达克一带做过调查[2],把蚂蚁金的起源归结于这一地区。虽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汉藏文献的相关记载,且多集中于吐蕃时期,对于吐蕃以前的西藏黄金制品的了解,限于考古发现的薄弱,仍然相当粗疏[3]。
2000年4月,西藏山南地区文物局在浪卡子县工布学乡查加沟的谷地冲沟清理了一座已被人为破坏的残墓,出土4件金质马饰和若干残陶片,并从当地牧民手中追回出土文物108件,包括饰件、武器、陶片等。这批材料已于2001年公布简报[4]。查加沟遗址共计出土17件金饰,是西藏首次通报考古出土且数量较多、时代较早的一批金器,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霍巍教授曾撰文对这批材料予以讨论,为这批黄金制品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早期金银器有较多相似性,其时代应当是在大体相同的一个年代幅度以内,相当于中原的汉、晋时期,属于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的遗存”[5]。但西藏艺术史学者Amy Heller提出这批金器更像属于吐蕃时期(7-9世纪)。其理由如下:
第一,这批金器中的焊接(Granulation)、掐丝(Filigere)工艺并不见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金器传统中;
第二,与金器共出土的陶片与吐蕃时期相仿;
第三,浪卡子加查沟出土的铜饰件可能属于马鞍(SaddlePlaues),类似的马具见于青海都兰吐蕃墓葬中;
第四,所有的突点都表现为连珠纹,与之相仿的耳环见于钮瓦可(Newaark)博物馆的一件镶嵌天青石的耳环,这件耳环被断代在吐蕃时期[6]。
看来加查沟的金器在不同学者中尚存在相当不同的认识。而在上述发现、研究论文出版不久后,2002年山南浪卡子县多却乡境内再次发现一处已被破坏的墓葬,又清理出一批金器,数量、类型较2000年发现者还多。这一资料尚未见诸于正式报道。仅在2005年西藏博物馆的夏格旺堆先生曾就此做过简单介绍,可推断这一地点为一处古代墓葬,现将其介绍引述如下:
“由于受到较大的山体滑坡、雨水冲垮等自然因素的破坏,给寻找墓葬准确的位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从墓葬现存葬具、结构、葬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其葬具应为一独立的木棺材,似无头箱等其他的结构,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从墓主人的骨骼特征判断,可能为女性。墓主人仰卧于木棺材之内,其额部有一黄金制作的圆形装饰物,厚约0.15厘米左右(2001年查加沟简报中认为,此种金制品为‘圆形盔饰’,但从2002年清理出同样实物的现场情况看,此类金制品应为妇女头顶的装饰品,而非头盔的饰件),面部罩一层薄金片,颈部环绕有好几排用金子、珊瑚及玻璃器等制作的装饰品,其中最精美的是用黄金做成盘羊造型的小件装饰品,有十几件,应为牌饰,与2000年发现的马形牌饰属同一种用途;在身体右侧腰上系挂的1件青铜短剑,一直垂到膝盖部位。另外在墓主人的头部背后发现1件金管,直径约2-3厘米,长度约13厘米,估计这件金管为束发之用,2001年的简报中认为这是一件头盔上的装饰物,但从此次发现来看,它应为脑后长发的束发装饰”[7]。
上述新的发现促使我们再次检讨这批金器的年代和族属问题。由于第二次发现的材料尚未公布[8],以下仅以目前可见介绍的材料中就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略作尝试归纳,并与其他地区的金器做粗略交叉比较。
二、地域与遗迹
从墓葬所处区域考虑,上述两个地点都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山南地区的浪卡子县。浪卡子县地处西藏南部的喜玛拉雅山中段北麓,地形属于藏南山原湖盆宽谷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属于西藏著名的畜牧区。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意外发现的墓葬都处于山南地区的第一大湖羊卓雍错南岸,该湖被当地群众视为“圣湖”,多却加查沟和麦朵工布学两地的直线距离约30千米左右,距琼结藏王墓约80千米。这一区域是传统认为的吐蕃雅砻部落的发祥地,就此而言,这两处墓葬应处于悉补野王系统治地域。从地理景观上考虑,这两座墓葬的选址是相当讲究的,有理由推测羊卓雍错南岸地区可能为一古代畜牧部落的墓地。杜齐曾在《西藏考古》中提及羊卓雍错一带存在古代墓葬[9],再从相关记载和调查资料显示,山南地区曾是古代金器的一个重要制作中心[10]。
从墓葬形制考虑,由于上述两批金器出土都非考古发掘,调查者虽根据现场判断为墓葬,但墓葬的形制却不很清楚,只能依据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报道略作推测性复原。工布学乡地点,地表不见封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本来就没有封土,或者封土为晚期所毁。这一地区历来为考古学者关注,杜齐等都在这一带做过考古调查,如果有高大封土,不可能为杜齐等人所不见。从有关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的沿革考虑,浪卡子出土金器的两处墓葬与吐蕃墓葬具有高大封土的特点颇不相同;再者,据报道,墓葬发现处地表还残存着用直径20厘米左右的砾石围砌成的梯形边框,其中一条边的长度大约为7米左右,原先的墓葬规模应当接近50平方米左右。且在石砌框的中央,残存有一边长约2米、高1.35米的方形砾石堆。可以推测这处墓葬为仅有石砌梯形边框而无封土,石框中部很可能还有砾石堆砌的方形纪念物。这也与目前所见的年代较早的曲贡石室墓[11]、阿里的皮央·东嘎墓地大不相同[12],而与阿里地区近几年发现的古鲁甲寺墓地的结构类似[13]。后者的年代已被确认属汉晋时期,且亦出金器。
关于墓室结构,工布学墓葬经清理后发现,在地表下约0.9米深处,分布有一层厚度不等的黑色炭灰,炭灰之下深约1米处有两层平面排列成“工”字形的砾石遗迹,从中发掘清理出零散的陶器残片、人骨及动物骨骼和金牌饰。上述介绍未能说明墓室内壁的情况。但可见这处墓葬的墓室底部离地表至少有2米,从“两层平面呈工字形的砾石遗迹”推测,这处墓葬不排除为有两个墓室的合葬墓。但2002年发现的多却乡墓葬的结构则不甚明了。另外,夏格旺堆先生认为金器出于一座木棺中。木质葬具在西藏高原古代早期墓葬中发现不多,目前见于阿里地区汉晋时期墓葬或更晚时期的青海都兰吐蕃墓中。根据霍巍教授对于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的研究,这一墓葬和山南乃东普奴沟墓葬、乃东县切龙则木殉马坑形制略微相仿[14],而上述墓葬的年代都被确定为吐蕃小邦时代。
总而言之,从目前表述模糊的有限报道中,关于墓葬形制本身似并不能得到有效断代线索。不过似可明确,其与目前学界熟悉的吐蕃王系墓葬存在较大差别,也与以阿里皮央墓地、拉萨曲贡石室墓为代表的早期石构墓不同,而更接近阿里地区汉晋时期的墓葬。
三、金器的比较
上述两个地点的出土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的黄金制品。查加沟墓葬共采集17件金器,种类有动物牌饰、圆形片饰、筒形饰件、耳饰、戒指等,都属于装饰品一类。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这些金器和鲜卑系统的金器具有某些相似性,以下分别结合已有考古发现简单讨论之。
从工艺上来说,这一批金器运用了多种制造技术,包括:模铸、锤揲、掐丝。如5件马形牌饰、2件金耳饰,都是模具制造,即将金熔化为汁液,采用范模浇铸,8件指环的戒面缠绕的金丝已经运用了掐丝工艺,即将锤打成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线。以捶揲工艺制造的金器则有圆盔饰、管饰,成形以及表面的突点纹都运用了锤揲。上述几种工艺在中原的战国时期已经完全掌握,在北方草原地带,匈奴金器中已有运用[15]。值得注意的是,未见錾刻、焊接等技术。目前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刚刚展开,我们认为这批金器更多表现出一种较为原始简朴的金工艺,从技术以及形制上来说,与吐蕃金器广泛使用镂刻的传统显然差别较大[16]。值得注意的是捶揲凸点纹(圆珠纹)的技术在鲜卑系统的金器中颇为流行,如辽宁朝阳田草沟出土的金步摇基座便以此法作纹[17]。
浪卡子出土的5件马形牌饰都表现的是侧身马形,细致表现出了马鞍、缰等马具,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现有诸多研究已经表明,马具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具历史的角度对这几件马形牌饰做出讨论。据考古简报提供的线图,5件马牌饰的鞍下都明确地表达出了一个下垂的类似护甲一样的东西。“护甲”指马的防护“具装”,如《宋史·仪卫志》言:“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二者合称“甲骑具装”。据研究,中原地区的具装在曹魏时期已经出现,在东晋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在唐初马具装已经衰落。从这一点看,浪卡子的马牌饰上表现出的具装不早于4世纪。具装马铠分为保护马头部“面帘”、保护马脖的“鸡颈”、保护马前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身”等[18]。从浪卡子的马牌饰鞍下的表达来看,首先不太可能是马镫,当属于“马身甲”。吐蕃的“具装”尚未发现,自青海海西州郭里木木版画上的图像材料以及都兰吐蕃墓中,当时的马匹似未有具装,这提示出其可能早于吐蕃。另外一点,虽然这四件马牌饰对于马的细部表现得较为写真,但并未见马镫。马镫在东亚的出现被认为是在公元4世纪以后,起源于中国东北鲜卑人的活动区域[19]。目前,考古材料所见西藏的马镫最早见于公元8世纪左右青海都兰吐蕃墓中[19]。据以上对比,我们或可判断这批金器的年代区间大致在公元8世纪以前。
浪卡子发现的几类金器,在西藏考古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物与鲜卑系统的金器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21],这是值得特别讨论的,这也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对遗物的年代给出一定的参考,并进而考虑其文化史意义。
从技术上来看,浪卡子的五件马牌饰都为模铸。简报划为I式的4件可能出自同一铸模。2002年据说还出土了一些盘羊牌饰,这类牌饰无疑是一种服饰用器[22]。与之类似的牌饰可举出1979年青海文物部门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公社征集了一件模铸青铜牌饰。这件青铜牌饰高5厘米、宽7.5厘米、厚0.3厘米。造型为一蜷伏的大马背负一小马,腹部还刻画出“马镫”[23],起先被认为属于东汉时期,与匈奴牌饰相关。后乔梁、林沄对此做了改正[24],认为这类造型的牌饰实际上在吉林、辽宁、山西、河北、内蒙古都有出土[25],多见于目前公认的鲜卑遗存的墓葬中,可视为鲜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26]。据林沄先生搜集,这类马形牌饰大致可以分为单马牌饰和大马驮小马两类,多为模铸,以铜质者为多,金质者也不鲜见[27]。虽然其最显著的特点马头部的“菌形饰”并不见于浪卡子所出的马牌饰,但其中有些关联也有迹可循。如鲜卑马牌饰都较小,长度在5-6厘米之间者居多,整体上虽都非长方框形,但底部几乎无一例外有一横栏将马蹄和马尾连接在一起,马的刻画都近似剪影式,马首细部刻画并不明显,这既是模铸技术的限制,也是制造者的整体设计。
另外,青海互助出土的铜马牌饰的表面据言还铸有“太阳”、“连珠”等形状纹饰,由于未有公布线图,照片相当模糊,此处的连珠纹和浪卡子的金马饰的连珠纹是否相仿当再讨论。林沄先生认为青海互助出土的马形牌饰,应该与慕容鲜卑的吐谷浑西迁有关,其年代大致不会早于在永嘉之乱后吐谷浑西迁青海的年代,即公元4世纪[27]。
浪卡子工布学墓葬中出土一件圆形片饰,以金片捶揲而成,直径10.5厘米,正面边缘饰两圈凸圆点纹,中部为直径4厘米的凸圆点纹与4个“T”字形凸点纹构成的图案,这四个“T”图案字以垂直交叉为十字形状,中心有两个穿孔。这件器物的用途最先推测为头盔饰件,但据2002年发现,应该为额头部装饰[28]。在西藏境内迄今尚未见同类者,与之相仿的器物可举出内蒙古陈巴虎尔旗完工墓地出土的一件金饰[29]。这件金饰以金叶捶揲而成,近圆形,正面有五个凹窝,较大的一个居中,其余四个两相对应,呈交叉十字形状,在牌饰外边沿,有两圈细小的圆孔,直径依据线图推算当在6-7厘米左右。完工墓地的这件金圆牌饰未见进一步详细资料,但就描述和线图推断,和浪卡子的金圆牌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二者都为圆形,所谓凹窝(圆孔)当为捶揲工艺制造的凸点装饰。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心的凸点的排列,都为围绕中心的交叉十字形状。完工墓地一般被认为属于拓拔鲜卑的遗存,年代在东汉后期[30]。
浪卡子工布学墓葬出土筒形饰件1件,长7.3厘米,两端直径分别为1.3和2厘米。系金片捶揲而成,呈圆筒状,圆筒周身饰有五条纵向排列的凸圆点纹,在两端亦各有一条类似的圆点纹。直径稍大的一端折口处有穿孔两个,也可穿系缀连。原报告认为系与上述圆盔饰配合使用的头盔饰件。2002年在墓主人的头部背后发现1件金管,直径约2-3厘米,长度约13厘米,夏格旺堆先生估计这件金管为束发之用。这件金管饰为捶揲技术制成,表面饰有凸点纹,类似的金管饰亦曾见于辽宁的鲜卑墓葬中,例如辽宁朝阳田草沟曾出土一件金管状饰(M1:011),系金片捶揲而成,两端各以带中孔的圆片封闭。体表粘贴4行纵向凸起的菱形小框,每行4个,首尾顺接。在这些嵌框上又以框间隔、行间相错的布局嵌入墨绿色玉石。每行嵌框之间和管饰端绕上再以金丝和金珠粘贴成纵横纹带,全长3.1厘米、径0.9厘米[31]。
此外,浪卡子出土有金耳饰两件,系采用模具铸造,略呈圆形,下端有可连接坠饰的桃形穿孔,上端为椭圆形的挂钩,耳饰上有凸圆点纹饰,背面无纹饰。这两件金耳饰的性质非常独特,目前尚未能得见与之完全雷同者。艾米·海勒(A.Heller)举出一件收藏于美国纽瓦可博物馆的镶嵌天青石的金耳饰,这件耳饰据说来自西藏,被认为属于吐蕃时期。虽在大型构造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镶嵌宝石的做法在技术上显然要比浪卡子的复杂得多,很难视为同一时代的产品。再者,尽管金质耳饰早在夏商时期已经自域外传入中国[32],多见于北方草原地区,匈奴鲜卑的金耳饰都很发达,但并未见到与之相似者。
四、结语
西藏浪卡子发现的金器,显示出与鲜卑系统金器接近的技术传统和装饰风格,我们认为这可能与距离吐蕃最近的吐谷浑有关。吐谷浑属于西迁的鲜卑,曾在公元4世纪左右占据青海湖一带的广大地域,史载其疆域北达塔里木盆地南缘,东达川北,在中西交通上占据重要位置[33]。吐谷浑出现在藏文史书中较晚,但藏文史料记载,早在松赞干布之前悉补野王室就与吐谷浑有联系,如《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祖父第三十一代赞普达布年塞生而眼盲,是延请吐谷浑医生才治好了眼疾[34]。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6世纪初,西迁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已经与处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前吐蕃邦国有联系[35]。我们认为,浪卡子出土的金器具有某些鲜卑因素,其可能和公元4-6世纪活动于悉补野北部的吐谷浑关系密切。正如仝涛指出青海海西州郭里木棺板装饰传统是中古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36],浪卡子金器也具备某些鲜卑因素,只不过这种鲜卑因素已经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深入到西藏腹心地带,且经过了一定的调适和改造。反映出青藏高原腹心地带与其北部草原区域的文化互动,早在西藏的小邦时代已经展开。这一时期正是西藏古代史记载中最不明朗的时段,进一步的讨论尚需要更多的材料。在此,我们期待浪卡子2002年抢救清理材料早日刊布。
[1](法)布尔努瓦.西藏的黄金和银币[M].耿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2]A.H.Francke.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M].London.1914:13-14.
[3][10]陈波.公元10世纪以前西藏的黄金、黄金制品及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2002(2).
[4]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J].考古,2001(6).
[5][22]霍巍.西藏新出土的早期黄金制品及其相关问题初探[J].西藏研究,2001(4).
[6]A.Heller.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form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J].Orientations,2003(4).
[7][28]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J].中国藏学,2005(3).
[8]2012、2013年笔者在山南调查期间,曾蒙山南文物局强巴次仁先生关照,得见2002年浪卡子新出金器,收获颇多。目前这批资料正在由强巴次仁先生整理,本文暂不涉及。
[9]杜齐.西藏考古[M].向红笳,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2]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J].考古,2001(6).
[13]仝涛.西藏阿里“象雄考古”新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2-08-27(8).
[14]西藏文管会.西藏郎县列山墓地试掘[J].文物,1985(9).
[15]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J].文物,1998(2).
[16]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中国藏学,1994(4).
[17]王成生,万欣,张洪波.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J].文物,1997(11).
[18]杨泓.中国古代兵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94-96.
[19]齐东方.中国早期马镫的有关问题[J].文物,1993(4);王巍.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J].考古,1997(12);王铁英.马镫的起源[J].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76-100.
[2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21]张景明,赵爱军.鲜卑金器及相关问题[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1).
[23]许新国.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汉墓葬出土文物[J].文物,1981(4).丰洲.文物杂记[J].考古与文物,1983(1).这件马镫曾被认为是国内所见的最早的马镫形象,但后来多被学者否定。
[24]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M]//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25][27]林沄.鲜卑族的金、铜马形饰[G]//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45-151.
[26]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虎尔旗完工墓地清理简报[J].考古,1965(6).
[30]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J].考古,2007(9).
[3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J].文物,1997(1).
[32]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G]//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12.
[33]周伟洲.吐谷浑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M].黄颢,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9.
[35]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348.
[36]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G]//藏学学刊(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6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