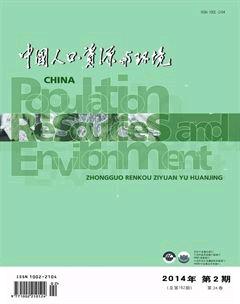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
邱俊杰 李承政
摘要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生命周期储蓄率模型逆推出居民消费率模型,利用中国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人口性别比系数为正,但稳健性较差,养老保险覆盖率的上升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并在制定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进来。
关键词消费率;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2-012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2.0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却呈现持续下降,近十几年降幅尤为明显。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1年的33.78%,年均降幅接近1.3%。现阶段,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已对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代表性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预防性储蓄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价格波动、国企改革等导致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改革提高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以防患于未来[1-2]。二是流动性约束观点,认为我国居民深受流动性约束的限制,为避免未来出现融资困难,居民只能现期大量地增加储蓄,从而导致消费不足[3-5]。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了总消费的不足[6-8]。尽管上述研究对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但以往的研究较少从人口结构的视角加以考察。居民消费不足可能源于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变化,年龄、性别不同,消费特征和方式往往存在差异。如果社会中男性、女性、儿童和老年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社会的居民整体的消费率也可能因此而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与1982年后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已经导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的变化。此外,中国“重男轻女”生育倾向,导致人口性别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变化可能已对居民整体的消费造成重要影响。
1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的关系,西方学者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Modigliani和Brumbreg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 简称LCH),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其一生中的储蓄路径为童年和老年时期负储蓄,盛年时期进行正储蓄,以熨平其一生的消费。从宏观角度上看,如果一个社会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上升,那么这个社会的储蓄率将下降,相反则反[9]。然而,之后有研究发现他们的理论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老年人的消费和储蓄时发现,老年人有很强的遗赠动机,这种动机不完全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父母可能通过留遗产来控制子女,希望子女更多地探望自己,有研究表明这种“战略性遗赠动机”非常明显[10]。此外,老年人存在较强的谨慎动机。他们的寿命可能比预期的长,年迈时可能会支付大额医疗账单,由此,他们保有额外的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以预防各种不确定性支出[11]。因此,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不一定使社会储蓄率大幅下降。关于孩子数量与家庭储蓄(消费)的关系,存在两种略微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来自于Samuelson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ousehold Saving Demand Model),认为孩子是家庭储蓄的替代物,如果家庭拥有多个孩子,那么可以减少家庭储蓄而不必为养老担忧,而孩子数量较少的家庭,父母只能通过增加储蓄以防老[12]。另一个观点来自于Becker关于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关系的讨论,他认为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培育高质量的孩子(以质量来替代数量)。现在的家庭相比于过去的家庭,生养了数量更少但是质量更高的孩子[13]。孩子的质量更多地体现在营养水平和教育水平上,这意味着家庭用在孩子身上的消费支出大幅增加。依照Becker的观点,一个社会中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家庭消费率会下降。
近些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Kraay利用中国宏观数据的估计发现,老年抚养比(old dependency ratio)对储蓄有显著的负影响,然而对中国城乡家庭调查数据的估计中却发现,抚养系数对储蓄的影响不显著[14]。而Modigliani和Cao利用中国1953-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却发现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少儿抚养系数下降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现象[15]。Horioka and Wan利用中国家庭调查的省际面板数据(1995-2004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是滞后储蓄率、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而只有四分之一的样本支持人口年龄构成与储蓄的关系[16]。
关于人口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并未实施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对于男孩和女孩也不存在特殊的偏好,因此,这些社会中的人口性别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波德里亚提出了支配消费的两种范例:男性范例和女性范例,“女性范例在消费领域中的扩张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并且这种扩张撑起了国民计算的美丽天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女性已经成为了消费力量的核心,中国未来消费市场的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女性消费者手中”[17]。与上述观点不同,有学者发现家庭用于孩子的消费支出(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孩往往受到歧视。例如,Schultz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女孩入
学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比男孩高[18]。Garg和Morduch发现,加纳的低收入家庭中,存在对女孩营养摄入的歧视[19]。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依然主要依靠儿子养老,因此,拥有较多儿子的家庭可以适当减少储蓄以支持消费欲望,而纯女户家庭则不得不缩减消费以期持有足够的储蓄以防老无所依。因此,中国人口性别比例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率,是提高还是降低居民消费率?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尚不清楚。中国部分家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别行为导致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出现失衡,本文将人口性别比例变动纳入到研究中,尝试分析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与之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同:第一,从生命周期储蓄率模型出发,利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逆推出了居民消费率模型,并将各潜在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使模型兼具传统消费模型和储蓄模型的优点。第二,在消费率模型加入了“性别比”指标,以检验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第三,通过系统GMM估计方法,克服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邱俊杰等: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2期2模型设定及数据描述
2.1基本模型
Modigliani和Cao的模型中国民储蓄率S/Y与长期收入增长率的关系如下:
S/Y=△W/Y≡w△Y/Y≡wg(1)
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g,国民财富与国民收入成比例,即W=wY。w为常数且独立于收入,但它可能依赖于收入增长率g=△Y/Y。只要收入的增长率非常稳定,生命周期模型暗含的储蓄函数可以表述如下:
S/Y=s0+s1g+e(2)
式中:s0近似地等于0,s1显著为正,e为随机误差项,满足独立同分布条件(iid)。
按收入法计算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为Y=C+S+T+Kr,它在数量上与支出法核算的国民收入相等。其中Y为国民收入,C为消费,S为储蓄,T为政府净收入,Kr代表本国居民对外国人的转移支付。恒等式两边同时除以Y并通过移项得:
C/Y=1-S/Y-(T+Kr)/Y(3)
将等式(2)带入等式(3)可获得:
C/Y=1-(s0+s1g+e)-(T+Kr)/Y(4)
通过合并整理,可获得等式(5):
C/Y=[1-s0-(T+Kr)/Y]-s1g-e(5)
令β0=[1-s0-(T+Kr)/Y],β1=-s1,ε=-e,等式(5)可以简化为:
C/Y=β0+β1g+ε(6)
式中:β0>0,β1<0,ε为iid。根据上文的分析,居民消费率模型应包含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变量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反映人口构成的变量:少儿抚养比(YD)和老年抚养比(OD)和性别比(Sex),这三个变量的定义如下:少儿抚养比为儿童人口/劳动人口,老年抚养比为老年人口/劳动人口,性别比由男性人口/女性人口表示。本文的基本模型表述如下:
CRit=β0+β1git+β2YDit+β3ODit
+β4Sexit+ui+εit(7)
式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u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应,CRit表示i地区居民在时期t的消费率。
2.2扩展模型
本文的扩展模型再将地区通货膨胀率(INF)、实际利率(IR)和城乡收入比(URR)、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IND)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S)等因素纳入研究中,以考量物价波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等潜在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根据上述定义,扩展模型表示如下:
CRit=β0+β1git+β2YDit+β3ODit+β4Sexit+β5INFit
+β6IRit+β7URRit+β8INDit+β9FISit+ui+εit(8)
2.3动态模型
居民的消费行为会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惯性(inertia)。通常以消费(储蓄)率滞后一期代表居民的消费(储蓄)习惯[20-22],因此,通过加入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率将上述静态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并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和消除可能存在的识别性偏误。考虑了习惯后的动态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CRit=β0+λCRit-1+∑βX+ui+εit(9)
式中:CRit-1为地区i的居民在t-1期的消费率,X表示与静态模型相对应的解释变量。由于动态面板模型中包含了滞后期被解释变量,所以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必须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Anderson和Hsiao提出,在一阶差分消除随机效应后,可以用滞后被解释变量更远的滞后期或者被解释变量的差分作为动态面板模型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工具[23]。Arellano和Bond借鉴了这种思想并注意到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工具变量,由此发展出差分广义矩(differenceGMM)估计方法[24]。然而,这种估计存在一定的缺陷,差分转换会导致一部分样本信息的缺失,并且当被解释变量高度自相关和个体效应波动远大于常规干扰项的波动时,估计的有效性较差。系统广义矩(systemGMM)估计由于同时利用了差分和水平方程的信息而比差分方程更有效[25-26]。这种有效性建立在新增工具变量整体有效的基础之上。动态识别中通常使用Sargen检验或Hansen检验来判断模型是否过度识别,而Hansen差分检验可用于检验工具变量集是否外生。由于经过了差分转换,所以残差项必定存在一阶自相关,但如果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则不能拒绝原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的原假设。本文将使用两步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动态模型进行估计在对标准误进行调整后,两步估计优于一步估计,因此,实践中一般使用两步估计。。
2.4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199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缺少重庆1997年之前的数据,西藏自治区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存在较大程度缺失,所以本文的分析没有将这两个地区包括在内。居民消费率(CR)由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与各地区人均GDP之比计算得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各地区GDP的比重(IND)和各地区财政支出占各地区GDP的比重(FIS)均通过类似方式计算得出。居民消费、地区GDP、地区工业总产值、名义利率、消费价格指数和财政支出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省份(直辖市)的数据来自200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1991-2001年的部分取自于《1990年以来的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7],其余部分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均来自199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1991-2001年的数据来自《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002-2008年的数据取自2003-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201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地区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来源于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由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统计年末各地区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因此该年的年末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和相应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分别从各省(直辖市)的统计年鉴中获得。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值见表1、表2。表2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地区间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在样本期内呈现显著差异。少儿抚养系数
sign居民消费率4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占地区人均GDP的比重4人均收入增长率4实际人均GDP增长率4+少儿抚养比4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4不确定老年抚养比465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4不确定性别比4男性人口/女性人口(女性=100)4不确定工业/GDP4地区工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4-财政支出/GDP4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4+城乡收入比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通货膨胀率4地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1004不确定实际利率4名义利率-地区通货膨胀率4不确定养老保险覆盖率4养老保险投保人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4+
3估计方法与结果
3.1基本模型
表3中第1和2列给出了基本模型(7)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的P值为0.98,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每上升1%,居民消费率将下降约0.15%,少儿抚养比下降1%将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0.13%,老人抚养系数上升1%将引起居民消费率下降0.57%,性别比的系数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中均不显著。因此,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来,经济增长率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好地符合了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期,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则更好地支持了关于老年人口具有很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观点。
3.2扩展模型
扩展模型在基本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工业产值占GDP比重(IND)、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S)、城乡收入比(URR)、实际利率(IR)、通货膨胀率(INF)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等潜在解释变量以检验上述基本模型识别的稳健性。扩展模型(8)的估计结果见表3第3、4列,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2,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人均收入增长率、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的参数符号均与基本模型相同但少儿抚养比的系数在扩展模型中变得不显著了,人口性别比系数仍不显著。新增解释变量中,城乡收入比(URR)、工业/GDP(IND)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著,然而城乡收入比(URR)系数符号并不符合理论预期。工业/GDP的上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率。
3.3动态模型
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均没有将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考虑在内,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偏误。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作为消费习惯的代理变量,将静态模型转为动态模型。分别利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了动态模型(9),结果见表4第2-5列。二阶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原模型残差不存序列相关。在Sargan检验表明,差分广义矩(一步和两步)所使用的工具变量集整体上无效,而系统广义矩(一步和两步)所使用的工具变量集外生且整体上有效。因此,主要分析系统广义矩的估计结果。动态模型中,城乡收入比(URR)、工业/GDP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储蓄增加并不是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养老保险覆盖率变得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我国养老制度还不完善,居民对现有的养老保障水平缺乏信心,仅仅单方面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并不能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无法真正有效地提升居民消费率。
2.4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199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缺少重庆1997年之前的数据,西藏自治区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存在较大程度缺失,所以本文的分析没有将这两个地区包括在内。居民消费率(CR)由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与各地区人均GDP之比计算得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各地区GDP的比重(IND)和各地区财政支出占各地区GDP的比重(FIS)均通过类似方式计算得出。居民消费、地区GDP、地区工业总产值、名义利率、消费价格指数和财政支出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省份(直辖市)的数据来自200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1991-2001年的部分取自于《1990年以来的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7],其余部分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均来自199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1991-2001年的数据来自《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002-2008年的数据取自2003-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201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地区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来源于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由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统计年末各地区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因此该年的年末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和相应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分别从各省(直辖市)的统计年鉴中获得。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值见表1、表2。表2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地区间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在样本期内呈现显著差异。少儿抚养系数
sign居民消费率4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占地区人均GDP的比重4人均收入增长率4实际人均GDP增长率4+少儿抚养比4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4不确定老年抚养比465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4不确定性别比4男性人口/女性人口(女性=100)4不确定工业/GDP4地区工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4-财政支出/GDP4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4+城乡收入比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通货膨胀率4地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1004不确定实际利率4名义利率-地区通货膨胀率4不确定养老保险覆盖率4养老保险投保人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4+
3估计方法与结果
3.1基本模型
表3中第1和2列给出了基本模型(7)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的P值为0.98,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每上升1%,居民消费率将下降约0.15%,少儿抚养比下降1%将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0.13%,老人抚养系数上升1%将引起居民消费率下降0.57%,性别比的系数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中均不显著。因此,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来,经济增长率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好地符合了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期,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则更好地支持了关于老年人口具有很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观点。
3.2扩展模型
扩展模型在基本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工业产值占GDP比重(IND)、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S)、城乡收入比(URR)、实际利率(IR)、通货膨胀率(INF)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等潜在解释变量以检验上述基本模型识别的稳健性。扩展模型(8)的估计结果见表3第3、4列,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2,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人均收入增长率、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的参数符号均与基本模型相同但少儿抚养比的系数在扩展模型中变得不显著了,人口性别比系数仍不显著。新增解释变量中,城乡收入比(URR)、工业/GDP(IND)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著,然而城乡收入比(URR)系数符号并不符合理论预期。工业/GDP的上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率。
3.3动态模型
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均没有将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考虑在内,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偏误。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作为消费习惯的代理变量,将静态模型转为动态模型。分别利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了动态模型(9),结果见表4第2-5列。二阶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原模型残差不存序列相关。在Sargan检验表明,差分广义矩(一步和两步)所使用的工具变量集整体上无效,而系统广义矩(一步和两步)所使用的工具变量集外生且整体上有效。因此,主要分析系统广义矩的估计结果。动态模型中,城乡收入比(URR)、工业/GDP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储蓄增加并不是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养老保险覆盖率变得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我国养老制度还不完善,居民对现有的养老保障水平缺乏信心,仅仅单方面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并不能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无法真正有效地提升居民消费率。
2.4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199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缺少重庆1997年之前的数据,西藏自治区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存在较大程度缺失,所以本文的分析没有将这两个地区包括在内。居民消费率(CR)由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与各地区人均GDP之比计算得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各地区GDP的比重(IND)和各地区财政支出占各地区GDP的比重(FIS)均通过类似方式计算得出。居民消费、地区GDP、地区工业总产值、名义利率、消费价格指数和财政支出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省份(直辖市)的数据来自200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1991-2001年的部分取自于《1990年以来的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7],其余部分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均来自199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1991-2001年的数据来自《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002-2008年的数据取自2003-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201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地区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来源于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由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统计年末各地区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因此该年的年末养老保险投保人数和相应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分别从各省(直辖市)的统计年鉴中获得。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值见表1、表2。表2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地区间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系比、老年抚养比和性别比在样本期内呈现显著差异。少儿抚养系数
sign居民消费率4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占地区人均GDP的比重4人均收入增长率4实际人均GDP增长率4+少儿抚养比4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4不确定老年抚养比465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4不确定性别比4男性人口/女性人口(女性=100)4不确定工业/GDP4地区工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4-财政支出/GDP4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4+城乡收入比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通货膨胀率4地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1004不确定实际利率4名义利率-地区通货膨胀率4不确定养老保险覆盖率4养老保险投保人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4+
3估计方法与结果
3.1基本模型
表3中第1和2列给出了基本模型(7)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的P值为0.98,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每上升1%,居民消费率将下降约0.15%,少儿抚养比下降1%将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0.13%,老人抚养系数上升1%将引起居民消费率下降0.57%,性别比的系数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中均不显著。因此,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来,经济增长率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好地符合了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期,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则更好地支持了关于老年人口具有很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观点。
3.2扩展模型
扩展模型在基本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工业产值占GDP比重(IND)、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S)、城乡收入比(URR)、实际利率(IR)、通货膨胀率(INF)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等潜在解释变量以检验上述基本模型识别的稳健性。扩展模型(8)的估计结果见表3第3、4列,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2,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人均收入增长率、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的参数符号均与基本模型相同但少儿抚养比的系数在扩展模型中变得不显著了,人口性别比系数仍不显著。新增解释变量中,城乡收入比(URR)、工业/GDP(IND)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著,然而城乡收入比(URR)系数符号并不符合理论预期。工业/GDP的上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率。
3.3动态模型
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均没有将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考虑在内,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偏误。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作为消费习惯的代理变量,将静态模型转为动态模型。分别利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了动态模型(9),结果见表4第2-5列。二阶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原模型残差不存序列相关。在Sargan检验表明,差分广义矩(一步和两步)所使用的工具变量集整体上无效,而系统广义矩(一步和两步)所使用的工具变量集外生且整体上有效。因此,主要分析系统广义矩的估计结果。动态模型中,城乡收入比(URR)、工业/GDP和养老保险覆盖率(PCR)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储蓄增加并不是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养老保险覆盖率变得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我国养老制度还不完善,居民对现有的养老保障水平缺乏信心,仅仅单方面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并不能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无法真正有效地提升居民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