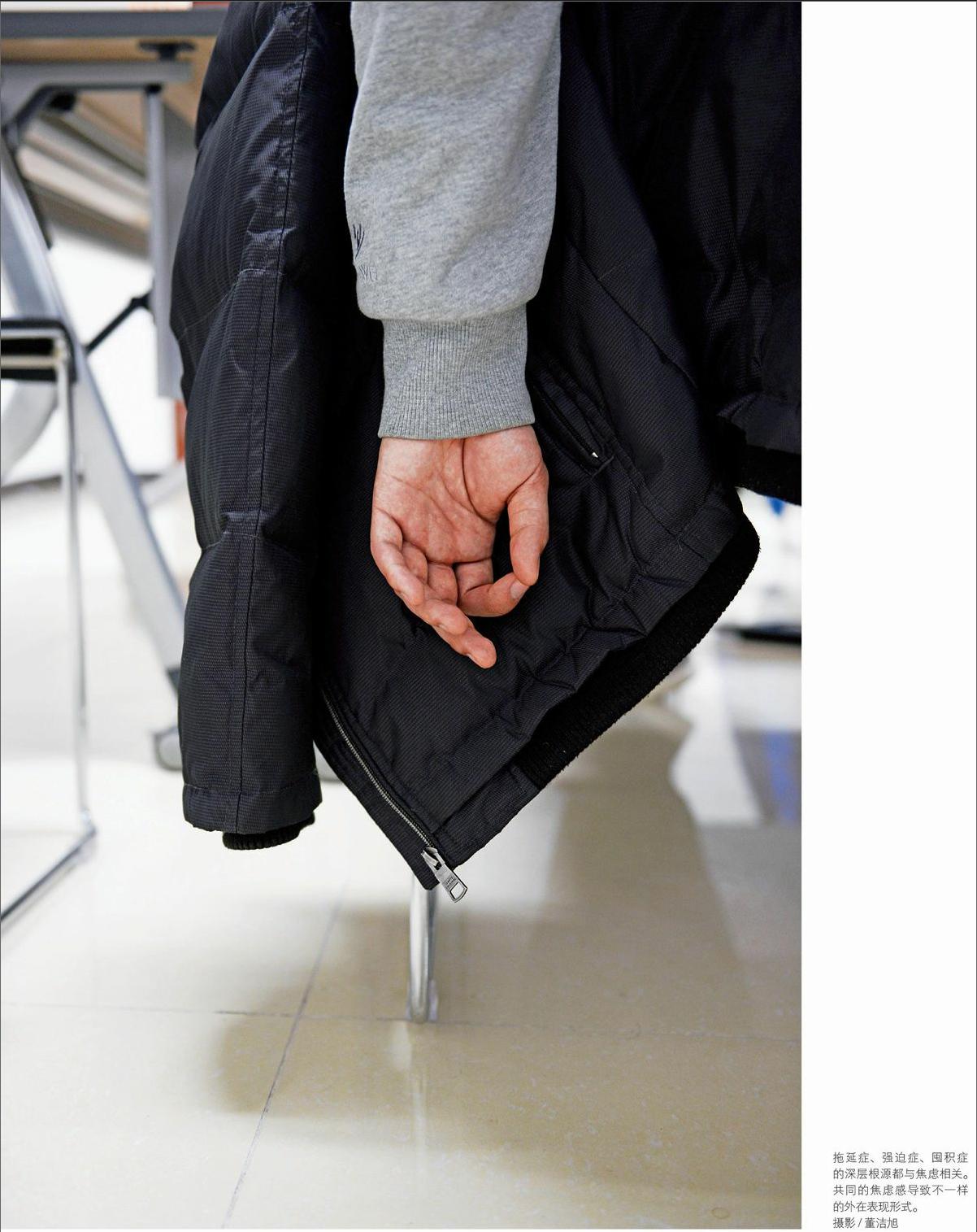“重症”如何改变了我们?
周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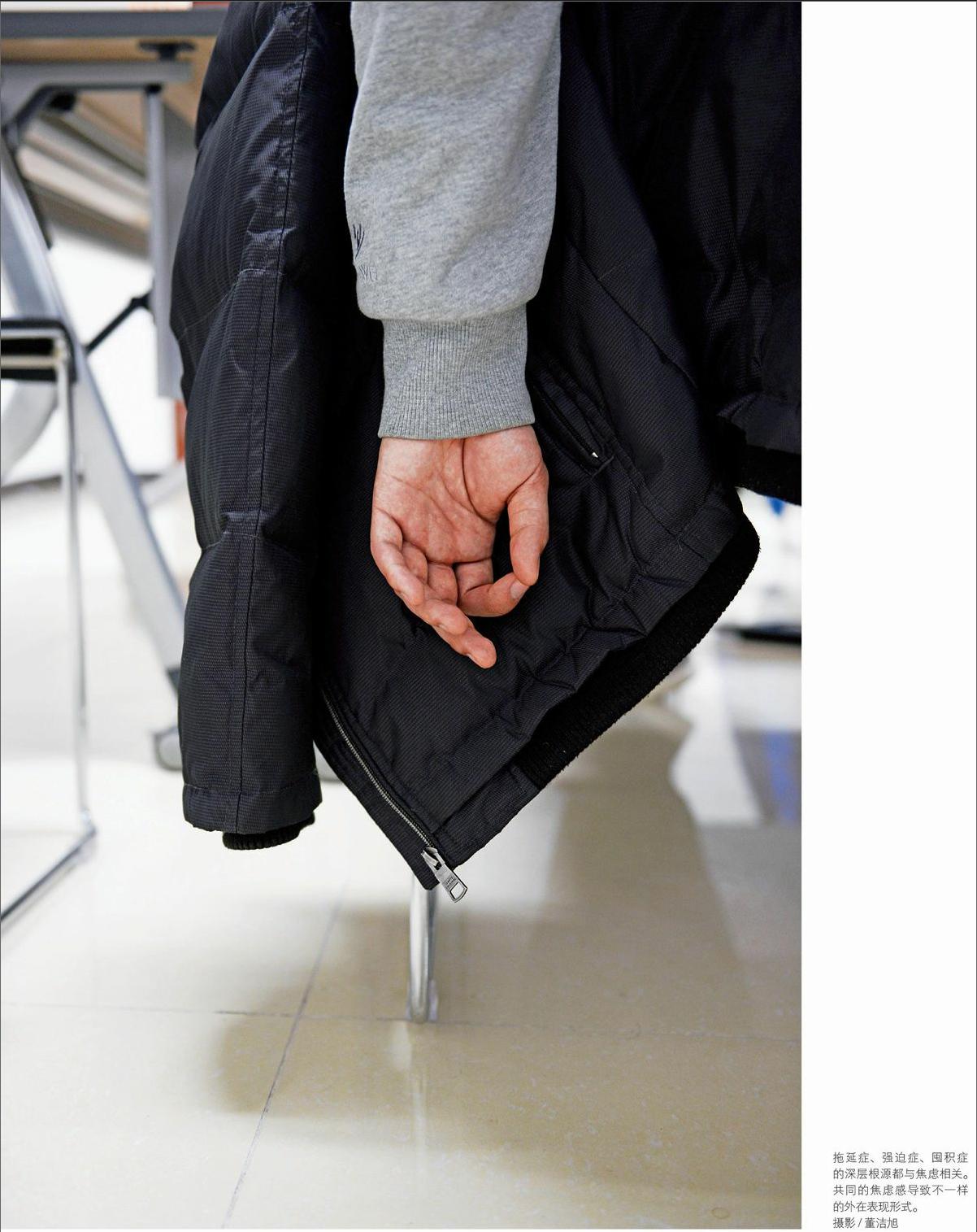
18岁的刘西(化名)刚上大一,他来到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找心理咨询师师晓霞。她坚定地说:“我有严重的拖延症,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十多年。”
咨询了一段时间,师晓霞发现刘西的拖延其实没有对她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每每拖到最后一刻,她总能把事情做完,只不过都会有一些不够完美的遗憾。媒体上一直在报道拖延症,她也就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才来做心理咨询。
师晓霞与刘西尝试了很多办法,但刘西几乎没有变化。一个学期的咨询过后,眼看她的学习、社交没有受任何影响,也没有焦虑和烦恼,师晓霞跟她协商:接受自己拖延的这一事实。最终,刘西坦然面对了这个现实。
实际上,一些心理问题的“痊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的来访者工作效率会提高,有的人则调整心态,从心理上接受了自己的状态。“两者我们都可以称为痊愈,”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说,“他们做咨询是来取得比较好的心态,没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
在拖延、选择焦虑或囤积症者中,像刘西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与绝大多数“病人”们的想象不同,这些病症并非会完全改变一个人。
“如果你不想让这些心理问题对你产生影响,基本上就不会影响”
“我越查越觉得资料还不够。”博士生周杨(化名)走进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时,他的同届同学们已经顺利毕业两年了。因为博士毕业论文一直拖着没能写完,他只能延期毕业。
事实上,周杨从很早就开始下手进行论文的资料查阅工作,十分努力。可他的问题在于,他竟然将整整两年的时间全都花在了查资料上。
他在电子期刊网上输入论文的各种关键词,就能发现上千条相关文献。他将它们一篇篇地保存下来,分类放进各种文件夹里。有的按年代,有的按主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数据库。
周杨每次打开自己的电脑,看到上千篇论文,都会苦恼自己看不完。怎么办呢?他返回头上网,再去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论文和资料。于是,他的两年时间完全陷入了信息搜集和建立一个完美小型数据库的循环里,但他一篇论文都还没有开始看。
这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见过的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周杨的“完美主义”是拖延行为最重要的一类成因,他的生活也因此被完全改变了。
李松蔚在咨询过程中,让周杨接受更为现实的想法:保证信息永远更新到最新一篇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文章写得如何,即使会漏掉很多东西,首先都得写出来。在打断他完美偏执的同时,他为周杨制定了一些更为现实的计划,先找到几篇重要的文献读完,并且开始构思论文。
最后,周杨终于毕业了,方式是写了一篇自己非常不满意的论文。在搜集的一千多篇文献里,他只用了十分之一不到——90%没有读,就写完了这篇文章。
“战拖会”会长高地清风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他见过最严重的拖延:7(天)×24小时全天候拖延,吃饭拖延、睡觉也拖延。白天玩或休息时会觉得自己有工作要做,但是打开电脑之后又不工作,反倒开始刷网页、刷微博,或者用手机刷微信,或者去玩游戏、逛淘宝,一直逛到要剁手。一切能够帮他转移注意力的东西都会显得极其有诱惑力,时间全部贡献在纠结上。
心理咨询师师晓霞认为,更为严重的是拖延、囤积、选择焦虑等心理问题所引发的焦虑或抑郁。如果引发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必须去精神类专科医院做治疗。
但对于更多的轻微拖延、囤积或选择障碍人群来说,他们各自的“症状”并不会严重影响生活。
如果一个学生假定自己的拖延行为让他的论文得到了C——他本来可以花100小时来做这件事,可因为拖延,他只花了5个小时,损失了足足95个小时。他因此十分焦虑。
然而,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个学生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特别的影响。不能说论文得了C,他的生活就被毁掉了。心理咨询师碰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反问他:你为什么首先假定自己就是那个得A的人呢?
“大部分人只是自己不能接受这件事。但其实这件事就是可以接受的,”李松蔚说,“如果你不想让这些心理问题对你产生影响,基本上就不会影响。”
但对于大部分咨询者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咨询师让自己“立刻不要再拖延”“立刻停止选择恐惧”。
“其实这个表述本身就会导致他们继续拖延下去,”李松蔚说,“看上去他们很想要自己变好,但是冲动、自责、压力会让他们继续拖。”
在实际咨询中,一些咨询者无法平静地“接受”,有时候甚至会因为不接受、痛苦而诱发出更深的心理症状,变成非常严重的焦虑,甚至抑郁、自杀、酗酒成瘾。
碰到这样的情况,心理咨询师们都会十分为难。“他们应该放轻松,没必要非得拿第一,首先要接纳自己的状态,然后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慢慢去调整的,稳定下来。”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患病”?
近几年来,零星几篇研究“拖延症”的学术性论文开始在国内出现,其中有一些对国外拖延文献的总结、综述,也包括一些个案研究。如2010年,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陈娟等在2011年心理学与社会和谐学术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慢性拖延症的接受与实现治疗个案》。但总体而言,对类似拖延症等“病症”的研究性论文还是非常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心理问题不太容易用实验、问卷的方法量化研究,可操作性不强。
而有拖延、选择焦虑、囤积等心理状况的人群数量、范围几乎无法统计。在更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领域,从1993年以后,中国已有近20年没有开展全国性调查,直到2012年底,中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项目才再一次展开。虽然如此,但它的调查重点仍集中于程度较重的精神障碍病患。
目前,人们能看到的“拖延病人”或“囤积病人”大多数都是豆瓣小组成员等网友。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
高校的免费心理咨询师们也能碰到很多这样的案例。近几年来,各个大城市相继出台措施,要求全日制高等院校配备专业心理咨询教师。比如在上海,专职心理咨询教师与全日制在校学生的比例被要求不低于1:3000。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指出,在他的印象里,拖延者占到他在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接待来访者的50%左右。
而社会付费咨询时,这样的“病人”则很少见。心理咨询师师晓霞回忆,她的来访者50岁以上的人不多,其他人也几乎不会问到拖延、囤积问题,因为在中国当下,大部分人只会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花钱咨询。
在“战拖会”组织者高地清风的主观印象里,有拖延行为的人很多是学生、创业者、自由职业者或半自由职业者,因为“时间安排越自由,可供拖延选择的节点也越多”。此外,脑力工作者比体力工作者更容易拖延,“拖延是大脑的功能”。他认为,这批人大多在15岁到35岁中间,“年轻人选择很多,困惑、迷茫也很多,35岁之后他可能不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了。”
“这类人群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眼界很开阔,所从事的工作不是特别有保障、不按部就班,他们自我要求都还挺高的,”李松蔚总结,“他们从事的都是那种有点需要创造力的工作,需要写文章、做研究、做实验,做很多有创意的事情。”
而以拖延行为为例,它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亚型。很多人会拖延运动计划,健身年卡用一两次就废掉——这样的拖延就不局限于上述年龄、人群。
“首先你的生活得先好起来,你才能摆脱拖延”
在心理学上,有时候生病是会令病人获益的。师晓霞曾经遇到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姑娘和父母一起过来做心理咨询,她发现这个姑娘的父母关系并不好,姑娘是用自己的病来维系父母之间的关系。
心理上的“获益”也许能说明目前很多人争相往身上安放各种“病症”的现象。一些愿意给自己贴上“病人”标签的人会获得借口,“很多人跟我一样”,这样他们可以稍微缓解焦虑情绪。
李松蔚在北大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了7年,他回忆,从网络上得知“拖延症”一词、自己对号入座前来咨询的学生“太多了”。
人们都会有这样的“对号入座”心理。李松蔚回忆起自己在学校里学习《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也译为异常心理学)》课程时,第一堂课老师就对他和同学们说:“你们学的时候肯定会一边学一边对号入座的,千万不要这样。”书中涉及到的异常心理里有意志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等十几种表现形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当下,人们更是特别热衷于寻找这样一些症状、贴标签。一些对自己现状不满的人了解到囤积症、拖延症或选择障碍之后,立即会觉得自己就有这个病,也想找一些方法去解决,好像他们一旦治好了,生活就会好起来。
“可往往他们贴标签的过程就会让自己的状态越变越严重。贴标签后他们会愈发关注这个问题,经过自我暗示、自我强化,越敏感,压力就越大,问题也会更严重,” 李松蔚说。
大部分来访者一开始来咨询中心时,其实都已经跟这个问题死磕了很久了,在李松蔚看来,这个“死磕”的过程本身就是他们的问题变严重的过程。
现在,李松蔚觉得拖延跟幸福感很有关系。前几天,他在知乎网上这样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拖延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们不幸福。但大多数人会反过来想:是因为我拖延、工作没效率,所以我才不幸福。如果这些人倒置因果的话,拖延只进一步加深:“首先你的生活得先好起来,你才能摆脱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