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之玫瑰红,我之鱼肚白
秦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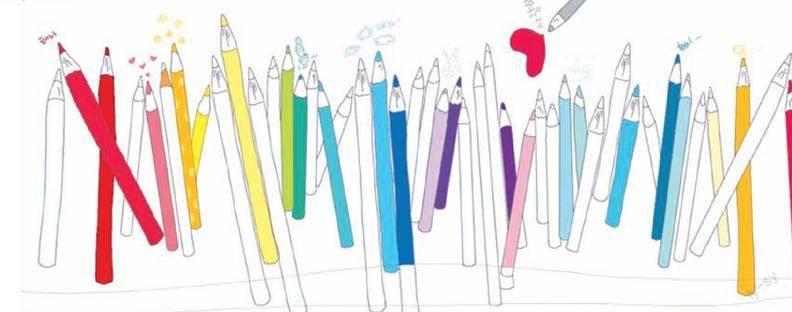
这不是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却是第一次科学地描述宇宙的颜色。
2002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名天文学家在研究了20万个星系光谱之后,宣称宇宙是绿色的,“比淡淡的青绿色稍绿一点儿”。
这种听上去有点拗口的颜色,受到纽约曼塞尔颜色科学实验室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天文学家设定的参考白点错误,这一概念是指在特定照明环境下人眼所看到的最白光线,它会随着施加的环境光照不同而发生变化。曼塞尔颜色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认为,要想在真正的意义上谈论宇宙的颜色,应该假想观看者置身一个黑暗的背景中,而不是天文学家所设定的红色。
最终,科学家撩开了百亿岁高龄宇宙的神秘面纱——近米色。
“还是不准啊!”超过300位社会各界人士在各自的手机、电脑、iPad上反复品味着那团略黄的白,然后将电子邮件发给科学家们,附上自己的定名:“银河金”、“宇宙土”、“天文杏仁色”……
最终,“拿铁色”成为获选者。
想必,读到这里,地球上最人多势众的中国人要皱眉头了。除了那些国际范儿的公子小姐,没几个人知道,拿铁不是铁,而是一种多加牛奶的咖啡。
在他们眼里,这团宇宙之光可能更像宣纸、饺子皮儿或是年轻姑娘的后脖颈——淡淡的象牙白。
苍穹之下,有多少双眼睛“好色”,就有多少种针对同一颜色的不同描述。跨文化研究者认为,各民族在认识颜色和使用颜色词汇的过程中,差异和共性都很显著。比如黎明时的天空,英语划入“玫瑰红”,而汉语则作比“鱼肚白”。
人类学家Berlin和Kay调查了98种语言,他们发现,各民族在定义颜色时,都会在光谱中先找到“焦点色”——比如红,以此为参照,再区分粉红、玫红、高原红。
对英语和汉语来说,哪怕“黎明时的天空”这种边界颜色归类分歧再大,但红、白这些焦点色却是共同而持久的。可能自文明之前就有,来自人类拥有红绿蓝三种视锥细胞的视网膜。
这两位人类学家还发现,各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不超过11个颜色范畴,并且能自我进化、依序演变。如果某种语言只拥有两个基本颜色词,那么一定是黑和白。如果有第三个,红舍我其谁。要是有四个,那么非黄即绿。再加一个,那黄绿都跑不了。蓝色、褐色和紫色随之列队而来。
中国语言学者张志毅上穷古汉语,下搜各地话,在上古汉语中找到了作为准基本颜色词的“紫”,先于“褐”出现。看来,有的民族除了不喝咖啡,连语言描述颜色的发生顺序也与众不同。
这些颜色语言家族还拥有超强的繁殖能力。根据统计,秦汉《尔雅》出现色彩词数量117个;到了清《康熙字典》,这个数字暴涨到934个。1880年以前,拉丁语里还没有“褐”。爱喝酒的英国佬为了鉴别啤酒的品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色度计,用刻度决定各种各样的“褐”——到底好不好喝。
酒喝干,诗来了。颜色词汇在不同文化中,承载着不同的审美偏好。台湾学者谢欣怡比较汉语新诗和英文诗歌后发现,西方人用色彩词营造崇高、悲壮和优美的美感,基本上三分天下。然而色彩词到了中国人手里,压倒性地用来打造优美,君不见“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正当中国人感悟写意之时,西方画家则在追逐新颜色的路上一骑绝尘。1886年,美国人编定了系统的《博物学家的色彩命名法》;很快,《色彩辞典》集大成而诞生。商业利润的刺激则将颜色的分类系统推向极致。
上世纪60年代,美国颜料商赫伯特的颜色帝国初建。为了让顾客打个电话就能准确获取自己想要的那种颜料,他的团队打造出超过1000种色度。这家全球最大的颜色分类公司不仅能给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马赛克地砖提供翻新意见,还给英国、日本国旗制定过官方标准。如果这都不够牛,那么,他们还发明了鉴别移植肝脏脂肪比例的色卡。
红灯停,绿灯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我们拥有越来越多,同时却越来越专一的颜色语言,这让我们生活便捷。可文化差异带给我们的“好色”体验,却仍在我们记忆深处。
就像不管是否认识拿铁,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在那里,没有牛奶加咖啡,却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极品咖啡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