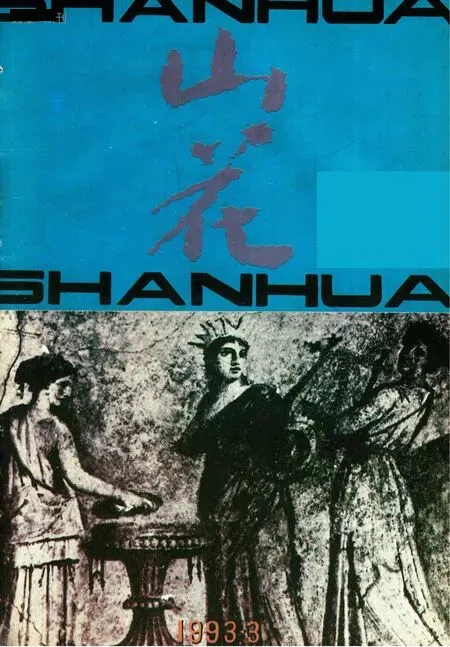用你的恐惧唤醒一场大雪
阎逸
《安魂曲》就是一部在濒于发疯时不断保持平衡的作品,它不是因悲剧而生,不是因失去儿子而生,而是因精神分裂症,因分裂——不是意识而是良心的分裂——由于痛苦者和写作者的分裂而生。这部作品的卓越之处正在于此。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一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对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名字不会感到陌生,但听过阿赫玛托娃本人朗诵她的代表作《安魂曲》的却并不多,我也是前不久才听到这部作品的录音。听阿赫玛托娃朗诵《安魂曲》,自是要从网上找来这首诗的俄文版对着听,只是眼中的俄语与耳中的俄语都犹如天书,仿佛一人独语而众口无言,隐藏其间的秘密信件一样从未拆封,无奈只好再去书中翻阅它的汉译,在阿赫玛托娃深沉、缓慢的声音中,一首又一首诗读将下去,这“大恐怖”时期的悲惨迎面袭来,恐怖是那个充满奇迹的粗人吗?从当代分身出一个古代,一个文字狱?这俄罗斯的、时代的、所有人的安魂曲,在今天听来依然惊心动魄,整部作品从里到外都在散发出死亡的气息,人们始终生活在濒临死亡的边缘。这是一组描写苦难的诗作:一个妇人的儿子被捕了,她带着为他准备的包裹等候在监狱的大墙下,她踏破了政府机关的门槛,探听她儿子的命运。阿赫玛托娃的描写是纯自传性质的,但《安魂曲》的力量却在于它描述的事情太普遍了,它哀悼那些哀悼者: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成了寡妇,或是像作者一样一同遭受这两种苦难。这是一出歌队先于英雄而毁灭的悲剧(布罗茨基语),它的悲剧性不在于人的毁灭,而在于幸存者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毁灭。
阿赫马托娃这部在20世纪6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被传阅的《安魂曲》,无论在政治上、道德上、还是审美上,都在这个过于喧嚣的时代中反复回响着那些不合时宜的音符,在永生与亡灵之间,被称之为诗中的音乐的元素,实际上是一种重构的时间,是时间的挽歌,它承载着精神的加速度,告诉世界一些它所不知道的东西。只是,这诗的音符到了音乐中会发出何种声音,音乐会把诗句领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吗?像用火焰照亮一段水的渴意?那么,我们是否真的知道鲍里斯·季先科(Boris Tishchenko)是谁?约翰·塔文纳(John Tavener)是谁?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Christopher Willcock)又是谁?在国内找不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谱写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的唱片,哀泣的缪斯仿佛被遮蔽在谜一般的浓雾里。我有时怀疑这无尽的现时就是隔世感,就是眼未见而心已思的神秘冥想。如果来日有人拍摄一部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超现实主义电影,我想象中应该有这样一个穿越的场景:阿赫玛托娃听过三位作曲家为之谱曲的安魂曲唱片后,开始逐一给他们打电话,与他们谈论自己的聆听感受。但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因为这部电影始终也没人拍摄完成,所以,阿赫玛托娃把自己对音乐的认识写在一首叫做《音乐》的诗里:“她的内部燃烧着莫名的神圣之火,/她的眼中游移着无穷的边缘。/别人都害怕走近我,/唯独她在和我交谈。/当最后一位朋友移开目光,/唯独她和我待在墓地,/像第一声春雷歌唱,/又像所有的花朵般絮絮低语。”这首献给肖斯塔科维奇的诗歌,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诗歌与人、音乐与人的关系——时间不需要慰藉,时间鲜嫩的耳朵无论是否张开,黑夜的花朵都在怀抱里悄然绽放,而挽歌之云已从头顶飘过。
事实上,阿赫玛托娃在生前已经听到,或者最有可能听到的,无疑将是鲍里斯·季先科为之谱写的安魂曲片断。作为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意门生,季先科与阿赫玛托娃相识是必然的,或许也只有他才能更准确地抓住那个时代所独有的黑暗质地,抓住阿赫玛托娃一生中众所周知的诸多事件,然后赋予音乐一个新的层次。在他那里,铁一样的事实从不曾柔软下来,除了苍凉就是荒诞,有点像他的钢琴奏鸣曲,内在的紧张感永远不会消除。但《安魂曲》的戏剧性不在于它所描绘的可怕事件,而在于这些事件转化为你个人的意识,你关于自己的观念,它的含义既是现实的和传记的(阿赫玛托娃和她被捕儿子的命运),也是象征性的(圣母玛利亚和他的儿子耶稣)。1968年,在阿赫玛托娃逝世两年后,季先科创作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问世,这首安魂曲不仅表达了作曲家对阿赫玛托娃的怀念,更充满了对斯大林大清洗时代受难者的悼念。“这怎么可能发生,/他们之中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在一个没有女主人公归来的时代,《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用“活着的幽灵”应答着《安魂曲》中“已经到来的暗夜”。
在学者迈克尔·约翰(Michael John)的德文版著作《走向新教会主义?苏联的安魂曲作曲(1963-1988)》中有一篇作者对季先科的专访,在访谈录的最后,季先科说:“如果你对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进行思考,你就会意识到苏联时代的精神生活并没有死亡,而是比革命前更加丰富,更加怒放。俄罗斯文化所能产生的最伟大的作品,正是在严酷政权的统治下傲然出世的。我相信,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消极现象并没有影响到这些艺术家。我常常喜欢拿地质学进行类比:最珍贵的钻石金刚石是在高温、高压和施加极大能量的条件下在火山中形成的。在苏联时代被压制的并不是精神,而是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当外在自由被压抑的时候,它就转而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如阿赫玛托娃或肖斯塔科维奇这般的金刚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季先科这段话说的是诗的结果,音乐的结果,看似轻描淡写,但如果与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言加以印证,便不难理解他们在斯大林时代的境遇:“除了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歌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局是可以允许抒情诗存在的,条件是抒情诗必须:1.开朗;2.不含任何超越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思想元素(实际上是指描写自然,表达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情感);3.直白,因为不许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自由思想,如果他有表现完美形式的倾向,就会被指控为形式主义。”阿赫玛托娃先后被官方媒体指称为“资产阶级贵族女诗人”和“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长期无法写作,她的第一个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处死,儿子被流放。而一生都在等待枪杀的肖斯塔科维奇,他全部的音乐更像是自悼。
1942年6月21日,阿赫玛托娃与朋友拉涅夫斯卡娅一起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排练。“多么可怕的作品……”阿赫玛托娃这样描述她的感受,“第二和第三乐章需要听几遍,以便体验它们,而第一乐章立即就理解了。这些可憎的小军鼓是多么恐怖……那里有一个骷髅跳狐步舞的地方……没有任何欢乐的乐谱和胜利的喜悦:接连不断的恐惧。天才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天才,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而一旁的拉涅夫斯卡娅则如此讲述交响曲:“如此可怕,就像阿赫玛托娃的长诗……有几个人也这么说”。这里所说的长诗,就是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毫无疑问,阿赫玛托娃听懂了肖斯塔科维奇,听懂了他表述的恐惧——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惧,与希特勒无关。而肖斯塔科维奇将同样无愧于她的知音之解,他说:“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是我的安魂曲。”
对于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说:“……尤其是《安魂曲》;我尊敬它,认为这是对恐怖时代的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碑。它写得那么纯朴,没有一点感情上的夸张……我是非常愿意把它谱成音乐的,可是音乐已经有了,是鲍里斯·季先科写的,我认为写得极好。季先科使《安魂曲》具有了我认为它所缺乏的东西:抗议。在阿赫玛托娃的原作中,你感到一种对命运的屈服。也许这是世世代代的问题了。”可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张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的唱片呢,我们该用诗的耳朵,还是音乐的耳朵去听?当然这世界上是没有这张唱片的,唯一的补偿方法是去听老肖作曲的《茨维塔耶娃诗六首》,把茨维塔耶娃的声音当做阿赫玛托娃的声音来听。但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买到了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的唱片,我也不会感到任何意外,因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的注视或不经意间早已发生了。
二
英国作曲家约翰·塔文纳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作于1980年,为女高音、男低音和管弦乐队而作,1981年由BBC交响乐团在伦敦逍遥音乐节上首演。在许多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中,诗人们的声音都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塔文纳也不例外,除了这首《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其他的还有:《约翰·多恩:十四行圣诗3首》,《T·S·艾略特<四首四重奏>中的3段》,《萨福:抒情诗片断》,《塞菲瑞斯的徘句16首》,《3首超现实主义歌曲》,《西班牙诗歌》以及《阿赫玛托娃歌曲》。诗歌文本进入音乐的内在语境,会使诗句自身的意义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天与地的回声,像一段茫茫歌哭,自有月光下或浪漫或悲凉的气氛一点点渗透出来,而最具安魂力量的是内外两个世界的对照和类比。
约翰·塔文纳的《安魂曲》完全按照阿赫玛托娃原来的诗歌结构排列,但由于全诗是在1987年才发表在前苏联的《十月》杂志上,所以作曲家使用的诗句应该是1963年前后流传到西方,并在慕尼黑出版的单行本的部分章节,“手抄本”虽有断章取义之嫌,但这首诗像“域外的雨”击打在约翰·塔文纳上,他感到时间过于腐朽,而哀悼者带着歌声歌唱着。用你的沧桑感动我的灵魂,用你的恐惧唤醒一场大雪,而用你的悲伤呢?纸上的白发在疲倦的往事里回过头来,我们无法宽恕历史的青春和老年。《安魂曲》写于1935―1940年,篇幅不是很长,它由4行题诗、代序、献辞、序曲和写于不同年代的10首短诗以及两首短诗组成的尾声构成。全诗不到200诗行,而不到100字的代序却写于1957年,第一首短诗则写于1961年。据诗人好友列沃尔德·班丘科夫说,序曲是在1962年列入《安魂曲》的,另一好友柳鲍夫·达维多芙娜·波尔申卓娃说,尾声是阿赫玛托娃在1964年刚刚写出并给她吟诵过的。所以,如果严格一点儿说,阿赫玛托娃的这首长诗实际上是从1934年12月1日开始的苏联大清洗时期写起,一直断断续续写到了她辞世前。(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大清洗,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胆战心惊,逮捕、流放和处决的人数高达500万以上,仅1937-1938年间被处死的,据赫鲁晓夫承认,就有681692人,对这次大清洗死亡人数的最保守估计也有140万之多,而这几年被捕的作家也是空前的,有6000人之多,占作家协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阿赫玛托娃创作《安魂曲》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危险,她时刻都处在被全日制监视的星空下,所幸的是她身边并没有告密者犹大出现。而这首诗不需要笔和纸的记录,甚至也不需要打字机,它当时仅仅保存在诗人和七个密友的记忆中。汪剑钊在《阿赫玛托娃传》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札记》中,女诗人莉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来看望我时,给我读《安魂曲》中的片断都得小声,而且在自己的喷泉屋里连小声读都不敢,她总是在谈话中突然停下来,用眼睛示意我注意天花板和四壁,随即拿起一小块纸和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想喝茶吗?或者‘您晒得可真黑呀,并迅速在小纸条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太早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大声说,划着火柴,在烟灰缸上把纸条烧掉。”那个时期,阿赫玛托娃时刻活在监狱的阴影下,那个无论醒着还是睡梦中的思想的监狱,那个从报纸向每一个栏目延伸的、从广播的每一支喇叭里喋喋不休散播着的谎言的监狱,仿佛不存在但又近在咫尺。
和阿赫玛托娃一样,塔文纳也信奉东正教,他的作品几乎都充满宗教意味,这使得他在音乐中阐释《安魂曲》时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契合点,因为《安魂曲》中的抒情女主人公就是一个东正教信徒,她的宗教生活通篇皆是。她将在黎明前早早醒来到监狱外边排队和习惯性地去教堂“我们起床,仿佛是去赶早晨的弥撒”进行比较。她和被捕的丈夫在“神龛前烛炬泪流”的房间里告别,吻别时她可以感觉到他唇上还留有刚刚碰过的“一丝圣像的冷漠”。“香炉的声音和痕迹”伴随着她对被监禁人健康的祈祷,而《尾声》中“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不仅是对当年女伴的回忆,更是对亡者悲伤而又“永恒的怀念”。塔文纳在乐谱前面的说明中,明确指出由男低音演唱的章节使用了东正教葬礼中祈祷仪式的音乐。除去大众文化的意义,阿赫玛托娃这首长诗的宗教涵义像旧约全书中的诅咒,在命运中秘密回响。如果说她早期作品中有一种絮语的表达和倾听,那么,汇合在这首诗中的众多的无名声音则是一种呼喊。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说话的不是您,而是俄罗斯。”早在1916年,曼德尔施塔姆就指出她的写作已经开始“转向祭司性文体,转向宗教的朴素和庄重”。顺便说一下,《安魂曲》第二章的首句“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淌”,说的就是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流放的日子,阿赫玛托娃曾于1936年初去那里探望过他。
塔文纳患有马氏综合症,这是一种罕见的结缔纤维组织疾病,会感染人的骨骼、眼睛、心脏和血管,其最明显的特征为骨骼发育异常,从而导致四肢及手指过长。拉赫玛尼诺夫也患有这种病,他那双“如同章鱼的触角覆盖在键盘上”的大手,便是病发后的结果,而塔文纳则是个子突然增高到186公分。1980年,塔文纳的健康状况恶化,医生说他活下来的机会只有50%,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塔文纳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他习惯了与死亡相处,认为每天的睡眠都是在做死亡练习。因此,他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需要用不断的重复来祈祷,需要用简约的十二音序列去一遍遍打开听者的心灵。诗人和作曲家,都在用真正的方式来体验自己即他人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描写,并非真正的眼泪,也并非真正的白发,这只不过是在接近现实的反应,真正的大众意识上的“觉醒的疯癫”。
约翰·塔文纳的音乐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是博采众长,不仅涉猎交响音乐和电子音乐,还涉及流行音乐。在他的乐谱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语、波斯语、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甚至印地安语,他认为什么语言不重要,好的音乐胜过语言。斯特拉文斯基和梅西安对塔文纳早期的创作影响至深,他曾写有一首室内乐《纪念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n memoriam Igor Stravinsky),两支中音长笛、管风琴与手铃的遥相呼应,像在风中呜咽的哀歌。塔文纳有一句名言:“音乐的最初目的是治愈心灵的创伤。”我想,诗歌也是如此。只是,谁带着累累伤痕与诗歌秘密见面,谁又躲在收音机里远远地眺望音乐通知?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而犹太女诗人奈丽·萨克斯则说:“我以世界的变迁作为我的故乡”,这里面存在着某种相似的东西:我们无法生活在自由里,那就生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之中吧。
我在youtube上看过塔文纳作曲的《阿赫玛托娃歌曲》的演出视频,我喜欢那个女歌手,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有时觉得她就像一个怀旧的局外人,既迷人又沧桑,她把另一个安魂曲性质的阿赫玛托娃还给了大提琴,把黑夜还给了白夜,而这揣测的听——大提琴和诗,它们彼此安慰。但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想起了斯克尔索普的《孤独的大提琴安魂曲》,雅诺什·斯塔克(Janos Starker)和彼得·威斯帕维(Pieter Wispelwey),如果他们为阿赫玛托娃的朗诵伴奏,谁会为一道微弱的闪电全身战栗?世界日渐衰老,俄语口音中的中文旅馆,空无一人。
三
接下来,慢慢进入我们听觉世界的,是澳大利亚天主教作曲家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和他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乐迷来说,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无疑是个令人感到非常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个注定要进入音乐史,但直到目前却仍被音乐史家们忽略掉的作曲家,即使在读者广泛的《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中,你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文字,这里面存在着某种有意无意的粗心、排斥和不恭敬。但在澳大利亚,威尔科克的境遇另当别论: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天主教作曲家,除了一系列广受赞誉的礼拜仪式音乐,他最受人称道的作品是那些他为之谱曲的现代诗歌。
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为女高音、弦乐和打击乐而作,2001年10月在墨尔本圣保罗大教堂首演。如前文所述,阿赫玛托娃这首长诗的三部声乐作品,我在国内找不到其中任何一张唱片,但我却拥有它们在某时某地的现场演出录音,这很奇怪,不是吗?尽管在录音中时不时能够听到现场听众的咳嗽声,但那是不是在提醒我,还有另一个我坐在观众席上侧耳倾听?重听即是回忆,即是在时间身上重新塑造一个往昔,然后再装入历史的抽屉。这一次,女高音莫琳·奎夫(Merlyn Quaife)带领我们与阿赫玛托娃同行。阿赫玛托娃用诗歌描述的黑夜、树木和河流,莫琳用歌喉使它们获得了时空的真蕴——作为人的象征,它们见证了一切。莫琳·奎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歌手,一个堪称伟大的表演者,从民谣、室内乐到歌剧和清唱剧,从巴洛克音乐到计算机音乐,她都能将其演绎到尽善尽美。她可以捕捉到歌曲内涵和歌中人物性格之间的细微差别,并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种罕见的能力。莫琳·奎夫早年在墨尔本大学学习声乐,1979年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赴慕尼黑攻读研究生课程。回到澳大利亚后,她开始在ABC电视台和国家歌剧院正式登台,并定期到欧洲参加当代音乐的演出,迄今为止,莫琳·奎夫的歌迷已遍布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
2002年,在墨尔本艺术节上,在由理查德·米尔斯(Richard Mills)率领的维多利亚管弦乐团的伴奏下,莫琳·奎夫重新演唱了《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中的六首诗。“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无论是酷烈的寒冬,还是七月的热浪,/我扑倒在瞎了眼的红墙下。”阿赫玛托娃用诗歌指认了一个充满红色恐怖的鬼魅国度,她“倾斜着书写我们”,她俄语名字中那五个开口的A,就是一只呼喊的嗓子,它需要对未来发声,对当下诘问。诗人布罗茨基在注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名字(A.A.A)》时注意到了这点,他说:“就其实质来说,这是一声令人害怕的叫声,——婴儿般悲哀的、临死的叫声”。阿赫玛托娃自己在诗中说“这名字本身——就是灾难。”而另一位杰出的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说“这名字——是巨大的叹息,它向一个无名的深渊掉下去。”早年,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青春和爱情,如勃洛克所说:“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在上帝面前。”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战争,恐怖,被监视,忍饥挨饿……儿子被流放,第一任丈夫被枪杀,第三任丈夫死于狱中)之后,苦难终于进入了她的诗中,“我的笔迹变了,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的声音首次为合唱而歌唱,“您能把这写下来吗?”一个在监狱外排队的女人问她,当她说出“能”的时候,她觉察到那个女人脸上泛起淡淡的笑意。因此,《安魂曲》与其说是一位无名母亲的嘱托,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我认为阿赫玛托娃安魂曲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高潮,”在一篇访问记中,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说:“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文本充满悲剧性,它在俄罗斯东正教的吟唱中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坟墓,这让人想起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十四行诗,铜管乐器和定音鼓,而且还有不断响起的钟声。令人动情的诗歌为音乐带来了灵感,但我觉得它更像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使音乐具有了悲剧性。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用任何一个标准来衡量都是很艰难的,热纳尔迪后来在莫斯科首演,给观众的反应很强烈,他们同情强加在各种意义上的苦行,这更接近于诗的悲剧精神。”谈到自己的创作,威尔科克说:“我每天都和谢尔盖·海克尔(Sergei Hackel)神父在一起狂热地工作,我们反复研究这个非常珍贵的俄罗斯文本,我不想出任何差错。在热纳尔迪·洛德杰文斯基(Gennardi Rodjevensky)首演期间,有一些观众中途走掉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批评家认为我的音乐太容易被拒绝。”
就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的创作倾向而言,他的音乐充满神学色彩,但不乏纯粹透澈的诗意,像酒在人身体里一次次的呢喃低语。他迷恋神性与人性之间那些柔弱的部分,但有时候将内心的火焰表现为冷,仿佛神站在高处漠视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威尔科克引人感兴趣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本人就是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在这个价值丧尽、道德缺失的时代,他的音乐听起来更像是上帝在尘世弥留的最后呼吸。而阿赫玛托娃的这首诗不仅在题目上存在着救赎的可能性(其中的部分章节与天主教安魂弥撒的过程非常相近,它直接面对死亡,抚慰着尘世中的受难者),而且诗的隐形结构与耶稣受难同构,从《题词》中的“不,既不是异国他乡的天底下,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献词》中的“仿佛是去赶早晨的弥撒”、《序曲》中的“无辜的俄罗斯在痉挛挣扎”,到第一章中的“我像出殡似地跟在你身后”、第四章中的“站在克列斯泰监狱的大门口”(克列斯泰的字面意思是十字架)、第五章中的“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冤家”、第六章中的“关于你那高高竖起的十字架”,整个过程读起来不仅像是描写直接发生的事件,而是像描写基督和陪伴他的圣母、拿香膏的妻子、学生在受难途中的各个阶段。所以,在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中,演唱者既是受难者又是哀悼者,音乐忽而激越,忽而沉默,哀思中,一个不幸的时代从俄罗斯大地上匆匆飞过,而声音的尖碑依然停在半空,经久不散。
四
一个音乐中的阿赫玛托娃能阐释那个诗学的阿赫玛托娃吗?或者,一个宗教意义上的阿赫玛托娃能穷尽那个生活中的阿赫玛托娃吗?无论是鲍里斯·季先科、约翰·塔文纳,还是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他们在音乐中打开的只是部分的阿赫玛托娃,时间是一个开关,即使关掉了那段历史,也关不掉全部的阿赫玛托娃。但问题是:历史从来就无法关掉,它的耳朵对着过去倾听,而让现实的耳朵突然聋掉。但在历史最深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不仅仅是用来听的,它更像是一场安魂仪式:为死人,也为活人。就音乐思想上的演释而言,季先科增加了阿赫玛托娃,塔文纳减少了阿赫玛托娃,而威尔科克则有点抽象了阿赫玛托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赋予历史一个可触可感的形状,从中呈现一个深度的阿赫玛托娃,听到一个隐身的阿赫玛托娃。
说到听,还是话回到阿赫玛托娃的朗诵录音。这份向历史提交的声音文献,唤醒了那个睡在诗句中的既美丽又凄苦的女人,很多时候,她有另一个名字:萨福。但现在她叫阿赫玛托娃,她生得太早,而我们来得太迟,所以除了读,我们只剩下听——声音是时间在诗中的座位,诗的内容借助这一背景获得一种立体性质,但它不仅是阿赫玛托娃个人的声音,更是各种无名声音组成的多声部,我们自始至终聆听着各种声音的变身,时而是与“旧俄近卫兵的妻子们”一起恸哭的普通老妇人,时而是诗人自己,时而是在我们眼前的圣母玛利亚。而孩子们的哭声,送行机车的鸣笛声,士兵们沉重的脚步声,监狱看守晃动的钥匙声和儿子身上的锁链声,接见室房门的砰砰声,这些声响敷在死一般的沉寂里,寂静不是没有声音,它像针一样刺痛着人心。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说:“百万人在一根弦上,并且他们所有的样子都在里面。”这是真正的命若琴弦,一弹即断。很多年过去,阿赫玛托娃的声音重现,而经过三位作曲家之手变成了暗红色钟声的《安魂曲》,早已在天地间鸣响不已。如布罗茨基在《阿赫玛托娃百年祭》中所写:
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
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上帝
留存一切;更留存他视为其声的
宽恕的言词和爱的话语。
——致阿赫玛托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