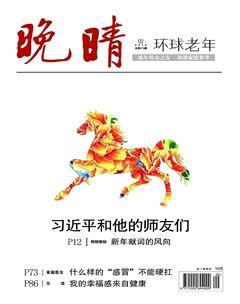80年前中国人的“新年梦想”
鞠晶

80年前中国人在新年梦想的那些事,如今想起,更让我们对现在充满了信心。
1932年冬天,当《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给全国400多位名人写征稿函时,“九一八”事变的阴影还笼罩中国。
因此,胡愈之写道:“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在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自己的生命。”
但没有改变的东西藏在他接下来写的话里。“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却还有明日。”胡愈之写道,“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这份要求“做梦”的邀请函,写给很多名人,他们包括巴金、郁达夫、茅盾、邹韬奋、林语堂、俞平伯、叶圣陶、施蛰存、老舍、梁漱溟、朱光潜、徐悲鸿、周作人。
胡愈之请他们做梦,新年的梦—“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
那一年,东北三省彻底沦陷,锦州满城皆空,早已饥肠辘辘的百姓拨开窗缝就能窥见空荡马路上荷枪驻守的日本士兵;那一年“淞沪会战”爆发,1月29日的日军空袭使上海市闸北区变成火海一片,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大楼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其中几十万部善本古籍化为漫天灰尘弥散在城市中,被仓皇躲避的市民吸进身体里。
此后,商务印书馆宣布停业,其创办近30年、颇具盛名的《东方杂志》停刊。
1932年10月,胡愈之接手《东方杂志》,并在动荡的环境下艰难复刊。在复刊后首期的卷首语中,他郑重写下自己的殷殷祈盼—“创造本刊的心声,创造民族的心声,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力气,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
在这一理念的促使下,上任之初的胡愈之便为即将到来的新年特刊策划了一期无论形式、内容、参加人数及产生影响至今在中国出版史上都绝无仅有的专题—《新年的梦想》。
他写下邀约,一一发送。
在那个冷冬里,梦想之约似乎点燃了一点小小的光亮。各界名人纷纷回应,循着这一点温暖勾勒起自己的梦想版图。
最终,编辑从回收的160多封答案中选出了142人的244个梦想,以83页的篇幅刊登在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中。
这是142个人写下的“新年献词”。
142份答案的作者阵容豪华。其中“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可见,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做梦”活动在当时知识精英中产生的影响。
“在那个昏黑的年头”,“最大的国耻”也许远不止于此。稍后不久,胡愈之被迫离开《东方杂志》,宣告知识分子集体做梦的权利也就此被剥夺。
短短5个月时间里,胡愈之因梦想接手这份杂志,又同样因梦想失去了这块阵地。
作为《东方杂志》“老板”,时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在审阅了《新年的梦想》专刊清样后就马上找到胡愈之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
“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胡愈之顶了回去。
盛怒之下,二人一拍两散。胡愈之随后提出辞职。
其实,反对者绝非王云五一人。在受邀“征梦”的400余位知识精英中,就有许多人拒绝“做梦”。茅盾回绝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俞平伯的回函只有简单的5个字—“我没有梦想”。
在众多“无梦者”中,鲁迅也许是最为激烈的一位。与胡愈之私交甚笃的他非但没有接受征文邀请,还在元旦读完《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夜,就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听说梦》,发表在随后出版的《文学杂志》上。
鲁迅明白胡愈之的良苦用心。他在文章中写道:“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
然而他对这种善意的“越轨”持有异见。
做梦看似平常,“被压抑”却“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但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梦“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胡愈之的确如鲁迅所说,“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1933年3月,在编辑完“新年特大号”后的3期杂志之后,他解除合同,离开了《东方杂志》,也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商务印书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