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乌生活
罗嘉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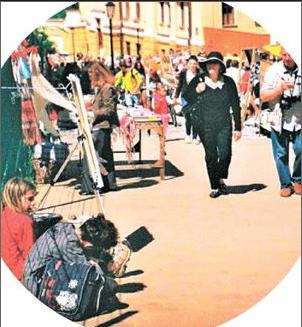
学中文的瓦列
那一天我在宿舍山坡下的车站等车,从旁边走过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都走过去好一段了,他忽然转身向我走来。“你是中国人吗?能教这孩子中文吗?”“能啊,中文怎么不会。”想着既能够赚点外快又能弘扬一下中国文化,我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互相留了电话后,中年男人说他们全家在暑假要去海边度假,等回来后再和我联系。
一晃过了好几个月,都快入冬了,当我都快忘了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喂,你好,我是安德烈。”安德烈就是那个中年男人的名字。于是相约第二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面。见面时我想着不太远,于是披了件外套赤脚穿了双拖鞋就下了楼。可没想到安德烈邀我去他家坐坐顺便认认路,也许黑灯瞎火的他没看清我的装扮,推脱不掉,于是我踩着双拖鞋就去了别人家。
他的妻子蕾拉挺漂亮,又热情,闲聊了一会,确定了以后上课的时间。临走穿鞋时,蕾拉见我赤着脚穿着拖鞋短裤,立马将安德烈骂了一顿,说都这么冷了,也不看看清楚就把我拉了来。我听着也挺不好意思,毕竟是我自己不注意。然后蕾拉从衣橱里翻出一双干净的袜子,让我穿上。于是第一次去别人家里我就顺带拿回来了一双干净的旧袜子和一盒当做见面礼的巧克力。
之后就开始了我的中文教学生活。小男孩名叫瓦列,这算是他的小名了,大名叫伊万,再加上他的姓和他爸的名字,很长一堆,只怕他自己也说不全。刚教瓦列时他说自己4岁了,虽然1年多以后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4岁。4岁的小孩,他爸就把他送进了双语幼儿园学习德语,平常吃饭时他会看英语的动画片,现在又加上汉语,我常怀疑他的小脑袋里是不是时常处于一团浆糊状态。
瓦列不爱学中文,到后来他也能听懂我说的汉语了,只是每次都用俄语来回答。于是经常出现的就是我说中文他说俄语,虽然互相都明白,但总有一种鸡同鸭对话的感觉。天气暖和时他喜欢和我趴在阳台的窗户上,楼下就是一个小型的儿童游乐场。他老问我为什么那些小朋友就可以不学中文在楼下玩,这时我就得搬出一套譬如“你很聪明啊,你以后会说中文人家就不会”这样的说辞。也没办法,不管在哪都会有“虎爸”、“虎妈”。
瓦列还有个小妹妹,叫波利,1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但小姑娘特别臭美,老是会趁你不注意就去穿你的鞋子,有时还会自己带上她妈给她买的小墨镜,手提包,出门时自己推着个小车,车上放着娃娃,俨然一个小大人。
一开始时我总会晚饭吃得饱饱的然后去上课,后来就开始空些肚子了。蕾拉专职在家带孩子,经常会做些蛋糕啊糕点之类,所以每天晚上课上到一半瓦列要吃晚饭时,我就被分配吃糕点,还配上一大杯茶。起初是客气,但到后来发现实在是吃不下了,于是就以减肥为借口推脱。但安德烈老说没什么,就一点怎么会胖嘞。拗不过他们的热情只好硬着头皮吃。后来学聪明了,每次去上课,晚饭就只吃个半饱,空出半个肚子。但也有失算的时候,有时瓦列父母不在家,会让奶奶来看孩子,老人也不会整东整西吃,于是那晚就会挨饿了。
断断续续我教瓦列中文快2年了,现在瓦列会唱好几首儿歌,会背几首唐诗,还学会了一堆中文单词。只是每个暑假过后当我再去他家时,他又会全忘了,冲你傻乐傻乐。
小村物语
小村叫做comtrubeqiki,入口处标示有本村的名字,因此每路过一个村庄一格里老师都会介绍一遍村庄的名字。
有些村庄的名字并没有实际的含义,就如我的老家叫罗家湾,仅是因为这儿都住着姓罗的人,换到别处就自然而然的变为蒋家湾、刘家湾等等,实在、好记。
路过的大部分村庄我都没记住名字,因为实在太长,就像他们当地人的名字:名加姓再加上父亲的名,搞不懂为什么叫一个人时要连同他的父亲一起叫上。
住在comtrubeqiki里,这里是一格里老师的老家。记得曾经告诉过一格里,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一块钱乌克兰币的意思,要是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八毛几分,与他相反的乌克兰语名字则富贵许多,叫伊万(一万)。
一格里的老爸老妈都住在这儿的农舍里,他看样子也想在这小村里长久住下,自己在小村的交通要道上盖起了城堡,虽然已盖了三四年都还没完工,但这正是乌克兰人的性格,有钱时就盖盖,不想盖了就歇着,乐得自在。
小村不大,但有2间杂货店,且比邻而开,看来平日里竞争得挺厉害。我们这些新来的客人就成了主要的客源,每日里都要去杂货店里转转。较小那家店的老板说自己是阿塞拜疆人,只是和老婆结婚了就搬来了这里,说起来大家都是外国人,所以亲切些,也老是送我们些小零食吃。而另外一家店老板的儿子平日里在给我们当绘画的模特,小男孩,正是讨人厌的年纪,爱做些恶作剧,于是就迁怒到他家的店里,很少光顾。
村里有一间教堂,是小村里最气派的建筑,每到周末整个村庄的上空都环绕着教堂里传出的歌声。有时清晨出门画日出,途中会见到三三两两的人群,都盛装打扮,小姑娘们穿上民族服装或是公主裙,小男生也是西装笔挺,妇女们一律要围上头巾,提着小篮的水果或是自家做的糕点前往教堂。
村民很注重自家产这件事。平日里的三餐一格里的老婆一定会强调自家产,鸡蛋是自家生的,面包是自家做的,蔬菜是自家种的,就连那猪肉,估计也是自家养的。一格里的父亲养了3头中国猪,他一直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还问我这中国猪会长到多大。这可把我问蒙了,我一向只吃猪肉,少见猪跑。不过后来见到这3只小猪我才能理解他对它们的热情,这确实是3只长得很奇特的小猪,浑身乌黑,脸也长得肥嘟嘟的,像一个个圆南瓜。都说猪没脖子,但它们圆圆的脸下略微细些像是一小节脖子,总的来说它们与我平日在高速路的货车箱里见到的猪大相径庭。老头给每头猪都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还在小院里挖了个坑,说是给它们游泳用。看老头这么宠爱这些小猪,我第一想到的则是等这些猪宝贝们长大了怎么对它们下狠手。
村里很多户人家都养了奶牛,每天农妇们会赶着奶牛去村外的草地上吃草,傍晚时分再回圈,所以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新屎旧粪,干的湿的一层叠着一层,刚来时我还跟怕踩地雷一样左躲右闪,生怕沾上了一点,几个星期后,我便能轻松自如地踩在牛粪上了。
农村的早上极安静又忙碌,清晨时分背着画箱外出,一切都还灰蒙蒙,连阳光都来不及苏醒。用心听,能听见露珠凝结坠落的声音。紫色的牵牛花早早地开了,吹着小喇叭。嘀嗒嘀嗒,是马蹄的声音,马车上拉着大桶的牛奶,早起的农妇会将挤好的牛奶放在门口,收牛奶的商人挨家挨户地收,清晨的石子路上飘荡着奶香。
旧货日
周六周日的时候,基辅别特里夫书市旁边会摆上旧货摊,长长一条,一直延绵到铁轨上。快毕业了,我也去卖旧货。其实这些旧货大多数都是这几年从人家那继承下来的“遗物”,半旧不新,几块钱便宜卖给别人,来旧货市场买东西的也大都是穷人。
早晨7点出发,因为东西太多还打了个车,此前还一直犹豫这一趟卖下来能不能赚回个车钱。时间还早,但摊子却已快摆满,12块钱的地摊费,交给了一个老太太。其实这可能本不需要什么地摊费的,基辅没有城管,只是很多老太太前个晚上就带上东西把位置都占上了,等有人来时再向他们收取地摊费。
之前也摆过一两次地摊,次次都是这样的情形:刚一摆上时,人群就一窝蜂而上,不是正经的顾客,都是附近摊位的卖主。大概知道我们这些学生不是认真来做生意的,价钱便宜东西也好,于是赶紧拿下,他们好自己再留着转手。于是这个抢那个拿,第一波高峰过去后包里多了一大把零钱,只是好些东西在手忙脚乱中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到底收了钱没有。
外人认为,中国人算是世界上第一精明的人了,但很可惜,我不在这个范围之列。加之数学一直不好,一堆小零碎,乌克兰大妈给我东加西算整整凑成了100块,当时我还挺乐呵,又多了100,但后来想想估计是亏了,不然那大妈也不会连袋子都不要拔腿就走。
如果将女人比作飞机,那乌克兰大妈们可算是飞机中的战斗机了。从前逛北京西单,小姐妹们友情提示,这儿的东西不管价多高,一律出价50。但这乌克兰大妈们更狠,一律出价5块。本都是些旧东西,并无所谓,只是有些大妈看起来太凶狠,偏不卖她,要碰上些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送她也行。
第一波小高峰过后就是长久的等待,偶尔有人路过也只是看看。当时还算是盛夏吧,但基辅的街头却有些凉意,从老姐的旧衣服里翻出一条围巾披上,也许是起了展示效果,刚披上没多久,围巾就被人看上买走了。几次摆摊得出个经验,只有有人在你的摊前询问时,其他顾客才会跟着聚过来。就如你只是仰天打个喷嚏,但因时间过久,你低下头来时却发现周围已聚集了一群人,用和你同样的姿势望着天上。一个大妈看上了一件衣服,还在左翻右看地挑毛病,但旁边的人一伸过手来想要看看,大妈立刻交钱走人。
隔壁摊的大婶一开始一直挑我们毛病,不是说我们的顾客踩着她的摊了,就是说我们的塑料袋没装好,摊在那不好看。心想着:她肯定是嫉妒我们生意好了,而她那门可罗雀。后来时间久了,发现大婶人也不错,可能是自己生意实在太差,闲着帮我们也叫卖上几句。本想卖不掉的东西最后全都给大婶,但是大婶不要,她说她也不是经常摆摊,主要是女儿毕业了,她来把女儿多出来的东西卖掉,这一上午才卖了一件衣服,她可是受够了,不想再来。
中途来了个看上去已经是老太太的女顾客,但和她一起的小朋友一直叫她妈妈,想着应该是听错了,奶奶才对。女顾客包揽了一大堆旧衣服,后来旁边的大婶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有7个孩子,天呐,刚才应该多送她几件才对。
女人们都很爱首饰,同学小杨留下来的一盒首饰销路很好。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品味特别,都喜欢又大又闪的,一个不知道从哪条裤子上掉下来的金属挂件,套上个链子后也被买走了。还有一条项链因为结成了死结,被我烦躁地拽断了,可断成了一截截后竟也有人问价,当做几条手链给卖了。一个大妈说要买个首饰盒给她女儿,于是首饰还没卖光,盒子就先卖光了,剩下一堆杂七杂八的摊在地上。
那时日天空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眼看着头顶乌云越积越厚,决定收摊回家,剩下的东西就送给流浪汉们吧,基辅的流浪汉们总是过着最悠哉的生活。(作者系乌克兰国立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