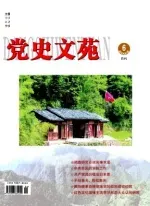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
■曹春荣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在瑞金召开的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围剿’的总结”。如严格按语法表述,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虽然,用博古的话来说,这只是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得到一些并不一般的简单的信息和认识。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严峻形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 “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敌方, “围剿”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投入的兵力、财力、物力之多,战略战术之变,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其先折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再取中央苏区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我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惊人的生长与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为反 “围剿”提供了更坚实、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造成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建立了更统一、有效的指挥和协调。所有这些,都大大优于以前。
另外,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红都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无由参与对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竟也取得了空前伟大、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这是何等鼓舞人心啊! “而这个胜利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尖锐化与紧张化起来”。于是,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将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
为了取得新的决战的胜利,对第四次反“围剿”作一个总结,从正反两方面为决战提供借鉴,以便再接再厉,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诚如博古自己所说: “当我们现在已经胜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 ‘围剿’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来把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一下,这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正当敌人今天疯狂般地准备新的绝望的五次 ‘围剿’的时候。”由此可见,博古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更没有得意忘形、目空一切。
第四次反“围剿”的主要经验
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是从分析击破四次“围剿”的基础入手的。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依据的基础、亦即胜利的条件有四个:
“第一,当然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我们在红军建设上的大踏步的前进”,红军走上了“正规的常胜的铁军的道路”。表现在游击队习气的逐渐克服,战略战术指挥的更新,政治机关的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骨干的建立,以及新的部队的大量增加等。
第二,“就是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奉献于战争的热忱”。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一方面热烈自动地参加红军,愿以生命捍卫红色政权;另一方面积极借谷、退还公债、节省粮食和开支,同时搞好农业生产,来支持革命战争。
第三,是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还得到了国民党区域(即白区)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例如,红四方面军在向陕鄂边和四川的远征中,得到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巴中县城的占领,也有四郊农民暴动的功劳。又如上海工人用尽一切方法来拥护红军,包括反对国民党当局征收“剿赤”捐,发起捐献一个铜板为红军购买飞机的群众募捐,组织对过往红军的欢迎活动,抵制黄色工会提出的组织剿共“义勇军”提议等。
第四,“不能不说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这个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这种正确领导,体现在坚决开展了反对以“罗明路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党的工作方式的改善与党员群众的积极化。
显然,博古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分析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条件的。一般而言,除第四条有些让人费解、甚至反对外,其他三条还是实事求是、颇能服众的。不过,对当年红军的正规化建设的是非功过,后人却有不一样的评判。否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左”倾错误路线在军队建设上的反映,是跟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唱反调的;强调红军正规化,取消了红军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两大任务,使红军成了单纯打仗的机器。肯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红军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大大提高了红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这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得到了初步验证。
笔者无意于就上述看法进行分析论辩,倒愿意翻开当事人当年的言论来说明问题。先看看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的有关论述,他在“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部分,谈到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时说: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红军,主要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
“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的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的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红军正规化的由来、要义及作用。它远比后来某些论者带先验性、倾向性、主观性、随意性的“分析论证”,要可靠得多、权威得多。
顺便提及两件事,也许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在到达中央苏区后的两年多里,“比较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他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对作战方针和红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二是第四次反“围剿”开创了红军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之先例,首次创造这一战法宝贵经验的,是周恩来及红军总司令朱德。毫无疑问,离开了红军“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要实行这一战法并取得完全胜利,是绝无可能的。
再来看博古所说的最后一个(第四个)胜利条件——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鉴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党原则创建的,一般地提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没错的。问题在于这一要求下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一向被认为是博古中央借以打击、排斥毛泽东,而无障碍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性事件。既然如此,这一条怎么能够成立呢?关于当年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是是非非,笔者曾撰文试作澄清(原载《党史文苑》2013年第3期,题为《对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历史回望》)。这里只提及三点:
第一,当年反“罗明路线”,其实就是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进攻路线。不过这个策略并非始于此时,而是更早罢了。“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但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这是1932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决议中,所提出的任务及相关解释。这表明,早在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及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之前半年多的时候,中共中央就确定了这样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思想。同一文件中,中共中央还提醒全党,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要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第二,博古在瑞金对“总的进攻路线”,作了更精确、更本质的说明。他指出,这条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势之下的革命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从中不难看到这条路线的要义所在,是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进取精神;是要求全党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紧密联系群众的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带领群众去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完成革命任务。这样的思路,不仅在动员、组织群众积极自愿地投入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逐渐成为一种革命传统、一种政治优势。
然而,后来的人却往往有意无意把“进攻路线”说成是不顾客观和主观条件,一味要红军硬打硬冲。这跟当年任弼时(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指出的,“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如出一辙,显然是对进攻路线的误解。另一方面,被视为“罗明路线”主要表现的单纯防御路线,其“主要的不是表现于分兵把口,布置后方,而是表现于对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以及敌人力量一贯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表现于这一估计为根据的整个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具体布置。所以反对单纯的防御路线,主要的不是在促使地方武装出击就算了事,而是在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改造我们一切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所提出的战斗任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说的这番话,也是对当时误解进攻路线的一种反正。
明白了其时的进攻路线实质,再来看博古所说的第四个胜利条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三,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中,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在各种报刊发表署名文章,对 “罗明路线”进行笔伐。他们中既有所谓“国际派”的王盛荣、洛甫、任弼时、顾作霖、罗迈、博古等,也有所谓“毛派”的阮山、刘晓、李富春、吴亮平、谢觉哉等,还有毛泽东的同情支持者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等。那些文章的标题、内容尽管不一样,却大都围绕这几个观点而写: (一)揭批 “罗明路线”的表现、实质、危害及其历史、社会根源; (二)拥护党的进攻路线,并积极捍卫之; (三)肯定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反“罗明路线”的结果,要更深入进行这场斗争,来争取第五次反“围剿”的新胜利; (四)苏区、特别是福建苏区各地工作局面打不开的原因,主要是反“罗明路线”不够深入,或者根本没有开展,为此要坚决反“罗明路线”。
就连毛泽东也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署名文章《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肯定基本击破敌人的四次“围剿”,是靠了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革命形势的前面,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关键。为争取反“围剿”的胜利,首先应保障红军数量的继续增加;最后还要“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新的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战争动员中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实际的帮助了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博古当年总结的这条经验,还是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赞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博古的责难、非难,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接受了。
第四次反“围剿”的弱点
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教训 (存在的错误和弱点)的总结,着重于两方面:一是军事战略上的,二是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的。
他指出,在军事战略上我们的错误和弱点是,全国红军还不能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实行互相配合的牵制敌人消灭敌人, “这是在粉碎敌人四次 ‘围剿’中极大的弱点”。具体的事实有两个:一个是中央苏区红军东攻漳州南下南雄,没有能够最大限度牵制进攻鄂豫皖的敌人的行动。另一个是在反“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目的地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面发展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
作为原则要求,博古指出的军事战略上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并妥为解决。但他列举的第一个具体事实,即中央苏区红军未及时有力策应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反“围剿”,恐怕要另当别论。一是中央苏区红军自顾不暇,在蒋介石军队开始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时,在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亦集中了40多个师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经过南雄、水口战役,赣南苏区始得稍安。二是乐宜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本当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地区推进,以策应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无奈力所不逮,“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当然,这里也反映出身居全党最高领导的博古,谋事论事的全局立场。
博古列举军事战略上的弱点的第二个事实,倒是充分体现了他对游击战争、游击部队、游击区域的高度重视。 “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博古接着上文说的这几句话,则反映了他对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伍的肯定与推崇。在谈到目前苏区党面临的紧急任务时,博古又强调说: “我们要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不但要在苏区周围组织挺进队深入白区游击,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游击区域使敌人腹背受敌。要记得游击队的积极活动,是主力红军在决战中获得胜利的要素之一”。这进一步确立了游击队伍、游击战争在反“围剿”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足见,后来一些人说什么博古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其实不足信。博古反对的,仅仅是打一处、抢一处、丢一处的流寇式的“游击战”、游击习气。
在政治方面、其他工作方面的错误和弱点,博古认为 “更大更多”。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曾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与工农群众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日常斗争,提高他到更高的阶段,使他们能够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胜利汇合起来”。在反帝运动中,没有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组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中,有轻视经济战争的观念,不善于与黄色工会作正确斗争,而扩大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其次,对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的面貌揭发不足。再次,是没有很迅速的克服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
博古关于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错误和弱点的总结,反映了他自觉接受、遵循国际路线和国际指示的思想特点,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统一战线,关心工农经济状况等),也有 “左”倾色彩 (排斥“第三势力”即所谓 “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等)。这在当年中共从属于共产国际、而后者对前者掌控太多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够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或许正是他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