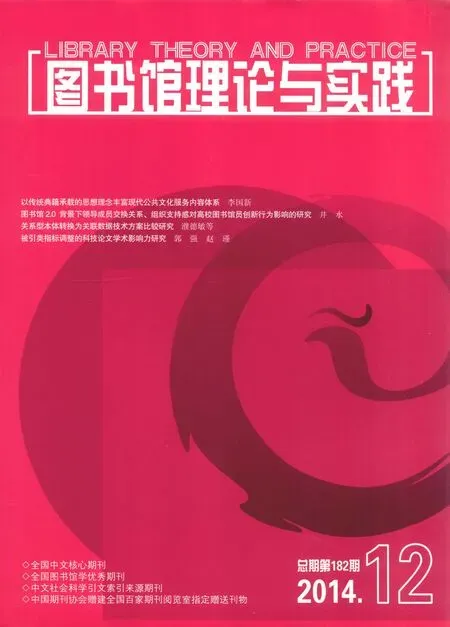《国史经籍志》论略
●李权弟,张金铣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9)
《国史经籍志》论略
●李权弟,张金铣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9)
《国史经籍志》;焦竑;类例;价值和影响
《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书目之一,其编撰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变革和创新,以其体例严谨、类例详悉、著录丰富等显著特点和驳正前人谬误的学术批判精神,恢复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明清之际和清代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肯定和广泛重视,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日益得到彰显。
焦竑编撰的《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一部书目,在明末和清代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国史经籍志》的研究变得相当薄弱,仅有零星的论述和介绍。本文拟对《国史经籍志》的编撰、类例及其价值和影响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对时下认识此书有所助益。
1 《国史经籍志》的作者及编撰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澹园、龙洞山农,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祖籍山东日照市大花崖村。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代史学家、思想家、文献学家和藏书家。万历十七年(1589),举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后为皇长子讲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主持顺天府乡试,因所取人选中“文多险诞语”,为人弹劾,贬谪福宁州同知。万历二十七年(1599),焦竑辞官归里,从此闭门家居,专心治学著书和讲学,并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被誉为“巨儒宿学,北面人宗”。[1]黄宗羲这样评价焦竑:“先生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2]由此可以想见焦竑当时会通三教的思想领袖地位。
焦竑为人生性疏直,敢于抨击时政之弊,因而不为当政者所喜。其思想解放,富于进取,与当时的大思想家李贽颇为一致,二人交往甚密,成为终生挚友。焦竑师事耿定向、罗汝芳等当时著名学者,又笃信李贽之学,为学不拘泥于儒学,大胆冲破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主张“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3]“囊括三教,熔铸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4]承接和发展了晚明“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运动,走向了那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峰巅。
焦竑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于文史、哲学,治学严谨,不入俗流,建树独特;著述宏富,除自撰者,尚有编纂、评点之书,计有八九十部之多。其中,《国史经籍志》颇具影响。《国史经籍志》的编撰与明代万历年间进行的官修本朝史书活动直接相关,是此次修史的主要成果之一。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向明神宗奏请纂修本朝国史,并力荐焦竑专领其事。史馆成立后,焦竑先仿照《隋书·经籍志》的体例,撰写了《国史经籍志》六卷初稿,耗时两年零十个月。万历二十五年(1597)史馆停罢,焦竑不久弃官归家,再无机会利用政府藏书。离京后,他历经五年才最后定稿,万历三十年(1602)由其门人陈汝元首次校刻行世。
在《国史经籍志》定稿的过程中,焦竑可利用的书籍只有私家藏书,主要还是自己的藏书。焦竑喜好集书、抄书和刻板印书,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是当时南京地区私家藏书的典型代表,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明史·文苑·焦竑传》载:“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据晚清学者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卷三所引《澹生堂藏书训》云:“金陵焦太史弱侯,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尤人所难。”焦竑作为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其丰富藏书为他从事目录之学创造了他人无可比拟的独特条件,也为他成就《国史经籍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国史经籍志》的编撰一反成规,并非记录一代藏书和一代著述之盛,迥异于过去正史艺文志的体例,而是采取了通记古今著述、不分存佚的方法。其著录书籍,时代及先秦迄明,主要以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为基础,参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明代前中期的诸家书目,并充分利用了政府藏书和家藏丰富的图书。因而,焦竑撰写《国史经籍志》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著录相当丰富。
2 《国史经籍志》的分类体系
焦竑十分推崇郑樵,赞同其“类例不立则书亡”的观点,因而《国史经籍志》的编撰旨趣和分类方法是仿取《通志·艺文略》之例,以四部分类,类各一卷。又分经为十一目,史为十五目,子为十六目,集为六目。此外,还冠以制书类一卷,将明太祖以来的诏令制书置于儒家六经之上,从而突破了传统书目各类目的排列顺序,这是焦竑首创,表明他对反映当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包含“文武之道”著述的高度重视。焦竑对图书的归类还追溯到晋人荀勖《中经新簿》所创立的四部分类法,他在《国史经籍志·序》中说:“今之所录,亦准勖例,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御诸书则冠其首焉。”可见,焦竑是综合使用了荀勖的四分法和郑樵的细分法,对图书分类倾力颇多。
焦竑总体继承了郑樵《通志·艺文略》的著录体例,《国史经籍志》采用三级分类法,甚至有的分到四级类目,目录明晰,分类细致。全书共分五个大部,52小类,322属。其一、二级类目如下。
制书4类:御制、中宫御制、敕修、纪注时政;经部11类:易、书、诗、春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经总解、小学;
史部15类:正史、编年、霸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时令、食货、仪注、法令、传记、地理、谱牒、簿录;
子部16类:儒家、道家、释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医家、艺术家、类家;
集部6类: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
焦竑在二级类目下设有更多的三级类目,少者2属,多者29属。值得注意的是,焦竑在子部的“天文家”类下的三级类目“天文”、“历数”,又分别设有四级类目。“天文”属下有7种:天象、天文总占、天竺国天文、星占、日月占、风云气候物象占、宝气;“历数”属下有5种:正历、历术、七曜历、杂星历、刻漏。这是焦氏的又一发明,为古代书目中所鲜见。此外,焦氏对郑氏的类目也做了较多的增删和变通,并不拘泥于旧目。例如,“易”类删“拟易”目;“书”类删“古文经”、“集注”、“义训”“小学”、“逸篇”、“续书”、“逸书”诸目;史部增设“时令”、“食货”、“仪注”类;子部增设“名家”类,道家增“诸经”、“杂著”,释家增“经”“律”、“论”、“义疏”、“偈”、“杂著”等,这无疑丰富了古代书目类例的内容,为史志书目开辟了新天地。焦氏还在经史子集四部前新增制书类,这是《通志·艺文略》乃至历代史志书目所没有的。
由上可见,《国史经籍志》的分类体系既继承传统,又多有改革,类例设置颇为详细,图书归类总体恰当,便于因类求书,并体现出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应当指出的是,《国史经籍志》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著录格式不太统一,著作时代、方式时有时无,标目格式多有变化,不免丛杂;某些类目设置不甚恰当,过分琐碎,如五行家分29属;对部分图书的归类不当,缺乏考订,如把算数之学列入小学而为“数”类;有的书籍重复著录,如《唐马总通历》十卷、《宋孙光宪续通历》十卷,二书在史部编年类运历、纪录两目重出。
3 《国史经籍志》的体例结构
《国史经籍志》有总序即焦竑自序,经、史、子、集四部48类之后有47篇小序(集部“诗文评”无小序),加上制书类一篇大序,五部共有49篇序。这些序含有相当多的学术内容,阐述所统部类的范围、性质、分类宗旨和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焦竑结合前人和自己的研究,提出对某一学术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他的博洽和独断之学。例如卷二《尚书》类序云:“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盖左右二史分职之。秦置尚书,禁中通章奏;汉诏命在尚书,主王言,故秦汉因以名官。《七略》曰,尚书,直言也。而以为上古之书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错书二十八篇,汉魏数百年间,诸儒所治仅此耳。至东晋梅赜增多二十五篇,即所称壁藏书也。考《汉志》有古经十六卷,以其后出,别于经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考,猥以晚晋杂乱之书定为义疏,而汉魏专门之学遂以茀废。近吴幼清叙录一出,乃悉还伏生之旧,而赵子昂、归熙甫之流,各著为书,靡不悬合。盖涣然有当于心。夫古书淆于后人至不可胜数,其文辞格制之异,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尝深疑之而未及是正,今学官既有著令,学士大夫往往循习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遗,掇拾于故老者,尽乱于伪人之手而不觉,可胜惜哉!故于胪列诸家而特著其事,俟广石渠、白虎之义者有所考镜焉。”[5]焦竑以史家笔法梳理了古文尚书之流变,努力廓清后世流传的古文尚书之非,辨学术考源流的精神灿然可见。《国史经籍志》各部类小序之作,是焦竑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各部类冠以序说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隋书·经籍志》之后消失已久的这一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影响了其后史志目录的编撰。
《国史经籍志》的著录内容主要有书名、卷数、著者,间或有著者时代、著作方式及简注。例如卷二《尚书》类:“《古文尚书》十三卷,孔安国传”;“《尚书纬》三卷,郑元注”;“《尚书义疏》三十卷,(梁)蔡大宝”。[5]简注主要是注释著述的内容、主旨、时代、篇卷变动、书名由来、著者事迹等有关情况。例如,地理类都城宫苑目:《学士院新撰目》一卷,注曰“宋初设军镇及宫殿名”,这是注著作内容;制书类:《昭鉴录》五卷,注曰“训亲藩”,此为注著述主旨;传记类名号目:《小名录》五卷,注曰“记秦汉至隋人”,这是注时代起讫;法家类:《慎子》一卷,注曰“四十二篇隋唐分十卷今亡九卷”,此为注篇卷之分合。[5]这些注释灵活多样,简明扼要,对所著录书籍的内容或形式作补充说明;注释质量高、范围广、针对性强,不失为后世各家书目的范例。
《国史经籍志》还附录《纠缪》一卷,论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宋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目录学著作,或指出其著录重复,或勘正其讹误,或改正其分类。由此可见,焦竑对史部范围内的簿录之学颇有研究,表明他编写《国史经籍志》是建立在批判前人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彰显了450年前郑樵《通志·校雠略》中研讨目录学的学风,继承和发展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纠缪》的撰写带有辑考性质,尽管后人指责其“乖史志之体”,但它充分体现了焦竑鲜明的学术自觉精神,更增强了《国史经籍志》的学术性,对后来校雠目录著作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4 《国史经籍志》的价值和影响
我们衡量一位古代学者的成就,主要看他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国史经籍志》采取通记古今著述、不分存佚的著录方法来编撰,使其集古今存佚全阙之书为一目,成为明以前历代著述的总书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较系统的中国著述史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丰富材料。同时,还为后人从著录中探究著述源流和古今学术变化、检索图书、因类求书提供了便利,这是《国史经籍志》的价值所在。
《国史经籍志》在万历二十五年编成,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在缙绅之间传抄流行,荐绅之家“转相缮写,而长安纸价为之腾贵”,[6]万历三十年刊行之后,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在晚明学人中深受好评。而清代学者对《国史经籍志》的评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明史》纂修者和四库馆臣为代表,采取诋毁态度;另一种是以金门诏、钱大昕、章学诚诸家为中坚,予以大力推崇。这种分歧固然有学术的因素,即与如何看待《国史经籍志》存在的不足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焦竑的思想学说与清朝的官方意志有冲突所致。
四库馆臣等人批评《国史经籍志》著录文献“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过分夸大其通记古今图书而不问存佚、缺乏考订等缺点,全盘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此等持论有失公允,明显带有偏见。其实,四库馆臣刻意贬抑焦竑的真正原因在于:“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于杨慎之《丹铅录》矣。”[7]这是指焦竑的学说有损于世道人心,这种攻击已然超出学术讨论层面。焦竑思想进步,精神独立,又与被视为“异端”“离经叛道”的李贽有莫逆之交,不为清廷所喜,《国史经籍志》受到四库馆臣等人的诋毁和冷落,已是在所难免。
与四库馆臣等人的观点相反,清代一批学者如金门诏、钱大昕、章学诚、周中孚、伍崇曜等人则分别从不同方面肯定了《国史经籍志》的学术价值,此书足为后人借镜之资。金门诏对《国史经籍志》的体例和分类甚为推崇,称赞其“类聚群分,灿然明备”,[8]并表示要继承焦竑的良法遗意,以《国史经籍志》为基础,仿其体例,增补内容,编撰《明史》“经籍志”:“兹准竑志,详加参考,并取竑以后所出之书悉增之。是犹班氏之准刘歆,魏征之准荀勖,其或不失前贤之遗意也夫!”[9]大致与金门诏同时,宋定国、谢星缠不仅借抄《国史经籍志》,还遵循焦竑的分类方法,对该书进行增补,编纂《国史经籍志补》。钱大昕则说《国史经籍志》是他撰写《元史·艺文志》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于焦氏《经籍志》……采获颇多。”[10]章学诚认为,焦竑“部次群书”,实有“知言之学”。他撰写《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直接受到焦氏《纠缪》的影响,并对之有切实的评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11]周中孚对焦竑所撰部类小序给予高度评价,强调其在史部目录著作发展上的历史意义,谓“弱侯能参之汉、隋志例,各于分目之后,作总论目一则,以畅发其大旨,是又《新、旧唐志》《宋志》所不及为者,所谓质有其文也,此则加于人一等矣”。[12]咸丰元年(1851),《国史经籍志》被编入《粤雅堂丛书》,伍崇曜点评此书道:“未尝不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也。”[13]以上诸家所言,充分证明《国史经籍志》在清代学者中受到相当的重视,反映出清代学者不仅广泛使用《国史经籍志》,而且对该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诚然,他们对《国史经籍志》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在肯定其优长的同时,也批评了该书的错讹之处。总体来看,《国史经籍志》在清代得以广泛流传并产生积极影响,表明其学术价值是得到公认的。
《国史经籍志》尽管遭到四库馆臣等人的有意贬低,但客观上对清朝官修史书还是提供了诸多借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清修《明史·艺文志》就是从焦竑通记古今著述而带来不足的做法中吸取经验,采取了记一代著述的方法;清高宗敇修的《续通志·校雠略》“参以先儒之论说而折衷之”,[14]以引用焦竑之说为最多,直接吸纳了《国史经籍志·纠缪》的成果,其内容几乎全部被援引,成了《续通志·校雠略》校雠汉、隋、唐、宋四朝之艺文志、经籍志的主体内容;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焦竑的四部三级分类著录方法,并规复小序之体。可见,从内容到形式,《国史经籍志》都对清朝的修史活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国史经籍志》作为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著作,是继郑樵之后唯一通记古今、详分细目的书目,弘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对于我们了解古今学术源流和概况,研究史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焦竑以一己之力,近十年之功著录先秦至明代中后期的文献,并有所创见和革新,其学术贡献和学术气概值得充分肯定。至于该书的不足,我们不应苛求古人。
[1](明)焦竑.澹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19.
[2](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本.
[3](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M].中华书局排印本.
[4](明)焦竑.澹园续集[M].金陵丛书本.
[5](明)焦竑.国史经籍志[M].丛书集成初编本.
[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M].明万历三十年陈汝元函三馆刻本.
[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744.
[8](清)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M].丛书集成初编本.
[9](清)金门诏.金东山文集[M].清乾隆年间刻本.
[10](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江苏书店出版,1983:346.
[11](清)章学诚.校雠通义[M].丛书集成初编本.
[12](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民国嘉业堂本.
[13](明)焦竑.国史经籍志[M].粤雅堂丛书本.
[14](清)嵇璜,等.续通志[M].光绪浙江书局本.
G257.33
E
1005-8214(2014)12-0075-04
李权弟(1966-),男,安徽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民进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发表论文20余篇;张金铣(1965-),男,安徽庐江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发表论文70余篇。
2014-03-05[责任编辑]宋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