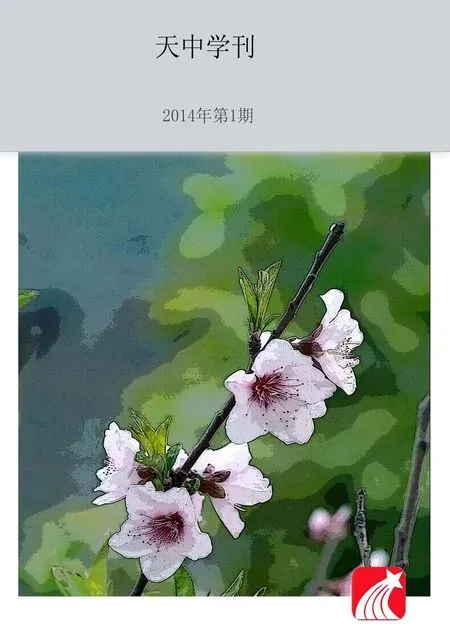武梁祠汉画像叙事艺术探微
李征宇
武梁祠汉画像叙事艺术探微
李征宇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图像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媒介,汉画像在图像叙事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作为汉画像代表的武梁祠画像在叙事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尤其令人瞩目。根据叙事学理论,从时间性与空间性两个维度分析武梁祠画像,能够对其叙事艺术上的成就有所体认。首先,叙述者通过单幅画像的构建、群体画像的安排以及榜题的运用对叙事时间进行了充分地把握;其次,三种类型画像的不同位置安排和历史人物图像的有意选择也体现叙述者对叙事空间的把握。从叙事学角度观照汉画像可以为解析它的艺术魅力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图像;汉画像;时间性;空间性
叙事的起源相当久远,几乎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叙事的载体十分丰富,罗兰·巴特指出:“对人类来说,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1]2所以说,图像,包括绘画、彩绘、电影、连环画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叙事媒介。从史前的叙事历史来看,人类曾运用多种图像形式以达到叙事的目的,比如岩画、结绳、刻契等。正是有了这些材料的佐证,人类的史前历史才能被后人追溯与理解。
中国的汉画像具有类似的功用,根据内容,汉画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反映社会生活的图像;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像;表现祥瑞和神话故事的图像;刻画自然风景的图像[2]25。作为一种艺术图像,汉画像广泛而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同时从汉人对于历史图像的偏好,也可看出他们对往昔史事的看法。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对此曾有概括:“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v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3]5
作为一部具有恢宏气象与忠实特性的“艺术之书”[4]59,同时也是“一部绣像的历史”[3]6,汉画像带有浓厚的叙事性。首先,它的叙事形式十分丰富,既有单张画集中表现某一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又可以用多张画以连续的形式表现比较复杂的事件,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出现了三维的空间形式:既有单张或者多张画,又结合某些雕塑、祭品等,共同叙述一些特定的事件。其次,它的叙事空间也十分广阔,有的体现于平面绘画上,还有一些将整个祠堂、墓葬,甚至宫廷全都纳入叙事中来。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始建于东汉桓、灵时期的武梁祠画像是汉代画像艺术的巅峰之作,其石刻画像内容丰富,雕制精巧,取材广泛,集雕刻、绘画、文字于一身,曾被称为“汉画像石之王”。武梁祠画像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峰,在叙事上同样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微观上看,其内容涵盖了汉画像艺术中的绝大部分题材,尤其是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像和表现祥瑞、神话故事的图像特别丰富,不管是单幅画像,还是组合画像,都带有强烈的叙事性;从宏观上看,与一般祠堂不同,武梁祠经过了祠主武梁本人设计,其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叙述体,包蕴了设计者特别的叙事目的。笔者尝试以叙事学的方法,通过对武梁祠画像叙事风格的探析,管窥汉画像在叙事上的成就,从而为解析汉画像的艺术魅力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一、时间性
从本质上说,叙事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叙述者必须在时间的轨道中叙述事件的过程,虽然叙述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顺叙、倒叙、插叙等,但整个叙述过程仍然是一个线性的流程。“一般来说,一个叙述体是一个包含两重时间序列的转换系统,它内含两种时间:被叙述的故事的原始或编年时间与文本的叙述时间,通常两者分别被称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5]63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往往呈现不平衡、不同步的状态,所以叙事时间往往成为叙述者重要的叙事话语与叙事策略。作为武梁祠的叙述者也就是设计者,其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则集中体现在单幅画像构建和群体图像的安排上;榜题形式的运用也有考虑叙事时间的成分。
首先是单幅画像的构建。如果说在文本的叙事中,叙述者最重要的工具是语言,叙述者对叙事时间的把握主要表现在对语言的安排上,那么在图像叙事中,叙述者最重要的工具则是画面,其对叙事时间的把握表现在构图方式上。以单幅画像而言,最能展现叙述者对叙事时间把握的构图方式是对“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把握。
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了“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观点。他认为,在艺术实践中,往往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艺术创作局限于某一顷刻,所以艺术家应当挑选全部“动作”中最耐人寻味、最富于想象力的那一“片刻”。他说:“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也就一定愈相信自己看到了这些东西。在一种激情的整个过程里,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能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较软弱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步。”[6]24也就是说,这个顷刻具有最大的艺术张力,艺术家抓住了这一点,就能够使观者既能看到过去,又能看到未来。这样的图像,能够使观者看到产生时间流动的意识,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
早在东汉时期,工匠就已经开始熟练运用这种意识进行创作,他们紧紧抓住事件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利用图像进行叙事。武梁祠中不少反映历史传说的画像石图像就是如此,如位于武梁祠后壁的“鲁义姑姊”画像。据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可知,鲁义姑姊是鲁国国都郊外的一位妇女,齐鲁交战,她准备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侄子逃往山中避难,齐军快马赶到,鲁义姑姊丢下自己的儿子,抱着侄子逃走。齐将见状,为其节义所感,遂止兵。鲁君听说此事后,称其为义姑姊。武梁祠画像在表现这个故事时,放弃了绝大部分情节而着重表现面对即将到来的齐军,鲁义姑姊毅然丢下自己的儿子,抱住侄子准备逃走的瞬间。画像的大部分空间都被代表军队的一辆马车和对抗的齐鲁士兵占据,鲁义姑姊和她的儿子、侄子被压迫到画面的最右侧,从画面上看,似乎齐军马上就要冲到他们面前,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这幅画面最精彩的地方在于用极简洁的笔法表现鲁义姑姊纠结而辛酸的心情,画面中鲁义姑姊已经抱起侄子,准备抛弃儿子逃难,工匠用一个向右倾斜的身形说明鲁义姑姊正准备逃走的动作,然而工匠又把她的头图绘成向左观望的样式,我认为这个的动作有两个作用,一是代表鲁义姑姊在观察齐军的动向,另一个则是表现她在看儿子最后一眼。整个画像加上榜题把“鲁义姑姊”故事的前半部分表现得十分清楚。观者通过对画面与榜题的阅读,可以感受到两军交战的激烈场面以及鲁义姑姊在做选择时的纠结与辛酸,整个画面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包蕴着丰富的内容。这幅画像能够达到如此效果,与工匠对“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把握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武梁祠左壁的“梁节姑姊”画像、后壁的“李善遗孤”画像以及西壁的“曹子劫桓”画像等,都体现出汉代工匠选择决定性片刻的技巧[7]81。
其次是对群体图像的精心安排。武梁祠中位于后墙以及两侧墙壁上的历史人物图像,被一条贯穿整个祠堂内部的装饰带分为上下两层,每一层又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与中国传统书籍的写法与读法相似,其中图像的排列顺序和阅读顺序均是从右至左、从上到下。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在观看祠堂原建筑中的画像时都须从上层开始,从右壁、后壁到左壁,然后又回到右面起首再从第二层开始。”在循环往复中,完成整个阅读过程。
上层图像分为两部分,上部最开始是从上古到夏的11位帝王,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开始,以夏朝的末代君主桀作结,紧接着是7位生活在周代的列女。下面一层则是从东周时代的曾参开始,到东汉时代的赵徇为止,共17个人物。他们的身份比较复杂,包括孝子、忠仆、义士、贤兄等。这些人物明显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的,特别是11位帝王,如果参照司马迁《史记》的分类,他们实际上代表着从上古到夏的“帝纪”,如果再加上从东周到汉代的列女及“孝子”“义士”等,这些图像实际表现的是从上古到东汉时期的历史。观者在观赏这些图像时,就像是在阅读一本从上古到东汉时期的史书一样,这样的叙事方式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史记》。巫鸿指出武梁祠画像在历史叙事上与《史记》有四个共同点:描绘了从人类产生一直到汉代的中国“通史”;通过精心挑选的人物来浓缩历史;这些人物根据他们的政治关系、生平德行以及志向等分为几个系列;祠堂的设计者武梁出现在所有图像最后,如同司马迁以《太史公自叙》结尾《史记》一样[8]171。我们无法明确武梁在进行设计时是否受到司马迁的影响,但是这种宏阔的叙事观念确实在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一脉相承,司马迁以其非凡的笔触构筑了一个气魄雄大的历史宇宙,而武梁则将这个宇宙具象化,从整体结构上实现了对《史记》世界的对应。
这些图像绝非随意挑选的,它们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用以表现人类历史过程的人物,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瞬间,每一个人物都代表着一段历史或者是从那段历史中流传下来的一种美德。在这种连续的历史观念的指引之下,武梁祠画像的叙事过程得以完成。
再次是榜题形式的运用。武梁祠中的榜题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的榜题,用以标明人物的身份或事件,处于主流,比如“鲁义姑姊”“鲁秋胡妻”“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等;另一类则是榜题内容与榜题载体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榜题的内容与形式得到了统一,二者成为一个组合图像,其功能得到丰富,比如将11位帝王的画像分成10个单独的部分(伏羲、女娲共为一体),又以9根柱子隔开,柱子上分别刻有对每位帝王的颂赞式的榜题。然而这9根柱子并不仅仅只有承载榜题的一种作用,一方面它将11位帝王分隔到10个大小相似的方框内,另一方面它其实还有卷轴画或连环画中界框的作用。看起来由于分隔,使这11位帝王完全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空间之内,他们之间的联系似乎被完全打破了,可实际上,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紧密的联系。巫鸿通过画像衣冠的样式、人物的动作和姿态分析了帝王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这11位帝王画像的图像语言有意地表现了历史演进的过程和规律性[8]179。这样的分析当然极富启发意义,然而当我们从艺术的角度观察古帝王系列画像,同样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
古帝王系列画像位于武梁祠右壁(西壁)山墙之下画像的最上一层,其上为一条贯穿整个祠堂内壁的装饰带,其下也有一条窄带将其与下层的孝子故事画像相隔离。从整体上看,古帝王系列画像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画像系列,只处于右壁,而不是像列女或者孝子故事一样,横跨两块墙壁,甚至跨越两层;二是与其他画像相比,古帝王系列画像的表现形式也独具一格,11位帝王的画像均为单体图像,且用界框将每个图像隔离出来,榜题位于界框(柱子)上,这样的形式不仅在武梁祠画像中,就是在至今所有出土的画像石中也仅此一见。
从形式上看,界框似乎打破了各个帝王画像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这样的形式恰恰达到了一种非动似动的艺术效果[9]94。在后世的卷轴画或者连环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界框的存在,比如著名的长卷《韩熙载夜宴图》,就借助各种屏风进行分隔,以此开启了中国画对于屏风的一个特殊运用传统——分割画面。观者依次观看系列画面,对不同的界框进行整合,在此过程中故事通过观者的能动整合而渐趋完整,当观者阅读完整个画面,一个连续的故事也由此出现。所以,屏风作为一种界框虽然截断了画面,却因为观者的能动参与反而使故事得以更加完整,叙事过程得以全部完成。武梁祠11位古帝王画像中的界框所起到的作用与此类似。
所以,特殊的图像形式与附着在其上的文字信息,以及画面人物独特的服饰衣冠、动作姿态,三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将古帝王系列画像铸造成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不管是在图像形式的构建上,还是在古帝王图像的实际排列上,都体现了历史的流动性。巫鸿是通过对画面人物独特的服饰衣冠以及动作姿态的解析,证明武梁祠汉画的排列与司马迁《史记》之间的相似性,体现了汉代史家的一种进化史观。而从艺术史的角度,通过解析特殊的图像形式与附着在界框上的文字信息,同样可以证明这个结论。三者的完美结合,使历史的流动性信息得以充分传递,使观者最大程度地接受,从而实现了叙事效应的最大化。
二、空间性
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墓葬往往都承载着多重文化意蕴,尤其是在极度重视墓葬的古代中国,郑岩指出:“墓葬可以被理解为安置死者肉身的处所;可以被理解为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结合着相关仪式所构建的诗化的‘死后世界’(至少是其中一部分)。”[10]97在这个诗化的“死后世界”中,时间与空间往往糅合在一起。在期望永生和“事死如生”思想指导下修筑的汉代墓葬,时间上的永恒往往需要通过空间性的艺术,比如雕塑、绘画等形式表现出来。
不管是作为“拟绘画”或者“拟雕塑”,汉画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空间艺术,其赖以依附的场所——墓穴和祠堂,也是一个空间处所,所以汉画像在进行叙事时,同样绕不开空间。武梁祠汉画像在叙事上的空间表现首先体现在其对三种不同类型画像的位置安排上。从复原的结果看,武梁祠是一座单开间的小祠堂,内部不过一人多高,在狭小的空间内,祠堂内壁刻满了图像,虽然图像的数量达到了一百多个,却丝毫不显杂乱,这完全有赖于设计者对图像位置的精心安排。祠堂的图像按照不同属性,可以分为祥瑞图像、神仙图像以及历史人物图像,三种不同类型的图像分属屋顶、山墙和墙壁,“这三个部分实际上代表的就是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8]92。
屋顶的祥瑞图代表着至高无上的上天,它正通过不同的征兆来对人间进行警示。西王母与其代表的仙境则代表着汉人所向往的地方,而西王母在演变过程中更是逐渐成为如同后世观世音一般救苦救难的神祇,这使她在汉代的地位仅次于上天。至于墙壁下面的人类世界,正是东汉人对于自身的一种认识。武梁祠的设计者在其间既回顾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又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道德的一种态度。这三种类型图像以及它们所处的位置代表汉人对于当时宇宙的认识,这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
武梁祠汉画像在叙事上的空间表现还体现在对历史人物图像的选择上。武梁祠墙壁上有榜题的人物画像多达44组,人物的身份涵盖君王、忠臣、志士、列女、孝子、刺客等各个阶层,人物生活的时间从上古到东汉时期,跨度达几千年。从时间性来看,帝王、列女、孝子、义士等图像的线性排列展现的是从上古到东汉时期的历史;从空间性来看,每一组人物的“在场”都经过了设计者的精心挑选,以图像的形式无言地阐发和传达设计者的思想。
中国的古代墓葬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埋葬死者遗体的地下空间,包括墓穴以及陪葬品等,另一部分则是后人进行祭祀的地上空间,包括封土、礼仪建筑以及雕刻和石碑等。祠堂属于地上空间,是一种礼仪性的建筑,主要用于缅怀或祭奠。对古人而言,墓穴的理想状态是一旦封闭,永不开启,这与祠堂有本质的区别。祠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它面向的是家族的后人,后人在这里与逝去的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德行,并通过墙壁上的图像受到教育,体会前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墓穴只属于死者,那么祠堂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死者与生者共同拥有。
实现这种共同拥有的途径是祭祀,东汉祠堂的一些铭文和文献都说明了祠堂是祭祀的重要场所[2]104。祭祀是一个后人与祖先进行交流沟通的机会,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并不是单向的,因为古人认为祭祀时祖先神灵是在场的,所以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1]2467,《礼记·祭义》则描绘了祖先在场的情景:“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11]1592后人通过献祭向祖先表达怀念之情,那么祖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与后人交流的呢?武梁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那就是通过祠堂中精心选择的图像来传达自己的思想。
作为一位儒生,武梁通过“精心挑选的历史模范人物,教导他的遗孀、子孙、亲戚和仆人们按照正确的儒家的规范行事”[8]243。比如位于武梁祠后壁及左壁的七幅列女故事画像,根据题榜及图像本身可知,这些故事均出自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其中梁高行、楚昭贞姜的故事出自卷四《贞顺》,而鲁义姑姊、鲁秋胡妻、梁节姑姊、京师节女、齐义继母则出自卷五《节义》。此外,刻于左壁下方的钟离春故事同样出自《列女传》,出自卷六《辩通》。《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刘向编撰《列女传》的原因:“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12]1957刘向编撰《列女传》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古代妇女美德与恶行的描述,表达其对女主专政、外戚专权的不满以及对于刘氏江山的担忧。或许刘向觉得仅仅用书写的方式仍然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甚至把这些故事图绘下来,据其所著的《别录》可知他“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13]175刘向的原意是想要通过对这些古代妇女的赞或贬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过由于这些人物的行为符合当时儒家的道德标准,所以他想要彰显的道德以及想要批判的恶行得到了汉人的认同。
《列女传》收录近百名女子,按照她们的行为与品德,分成“母仪”“贤明”等7个不同部分。那么为什么武梁祠的设计者偏偏只从《贞顺》与《节义》两卷中挑选人物呢?这与这些人物本身所具备的品德密不可分。从篇卷的名目即可知,这些妇女所共同拥有的美德是“贞”与“节”,这两点被汉代儒家视为妇女最重要的品德,自然也被儒生武梁所推崇,所以这七幅经过严格选择的列女图像最终以群体性的姿态出现在武梁祠墙壁上。与此类似,还有代表汉代至高无上品德——“孝”的16位孝子图像,代表“忠”的6位刺客图像等。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图像承载着不同的意蕴,成为武梁祠画像的一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成的叙述体,传达出设计者对于良好品德的表彰与向往。无独有偶,东汉王延寿用赋的形式描述了建造于西汉景帝时期灵光殿的建筑和殿内壁画,并指出了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不管是武梁祠还是灵光殿的图像,它们绝非仅仅作为一般视觉对象而存在,而是承载着巨大的道德说教功用。
可以想象,当武梁等人的后人来到这个祠堂中进行祭祀活动时,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祖先,还有祖先留下的具象的图像。这些图像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在本身具有神秘气息的祭祀活动中,它们的教导作用将变得更加明显。
武梁祠汉画像造型充实饱满,风格古朴雄大,内容丰富多彩,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高度。可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遥远的图像,那些附着在它们身上复杂的文化意蕴,如设计者对于美德的推崇、对于永生的渴望等,都将被无情隐没。只有从多个角度审视这些图像,才能透过那些直观形象的画面、易懂简洁的艺术语言领悟丰富的汉代文化精神,才能更加完整地领略到这些穿越千年的艺术品的非凡魅力。
[1][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李发林.山东汉代画像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2.
[3]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曹意强.艺术与历史——哈斯克尔的史学成就和西方艺术史的发展[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5]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德]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全集: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7]李征宇.顷刻与并置:汉画叙事探赜[J].理论月刊,2012(2).
[8]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9]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文学评论,2012(2).
[10]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艺研究,2011(1).
[1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唐]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杨宁〕
The Narrative Art of the Stone Image of Wuliang Temple in the Han Dynasty
LI Zheng-yu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China)
As an important media of narration, the Han-dynasty-stone-image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the image narrative studies. The images in Wuliang Temple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an-dynasty stone image in the narration. According to narrative theory, we are able to recognize the achievements of narrative of Wuliang Temple’s images if we analyze it from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aspects. First, the narrator grasped the narrative time by constructing single portraits, arranging group portraits and the using of inscription. Second, the narrator mastered the narrative space by arranging different places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portraits and the choosing of historical figures. It provides a new possibility to explain the Han-dynasty stone images’ charm from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mage; Han-dynasty-stone-image; temporality; spatiality
2013年度长江大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3CSZ002)
李征宇(1984―),男,湖南长沙人,讲师,博士。
2013-05-29
J205
A
1006−5261(2014)01−00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