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望之下
王宪
愿望之下
王宪
YUANWANGZHIX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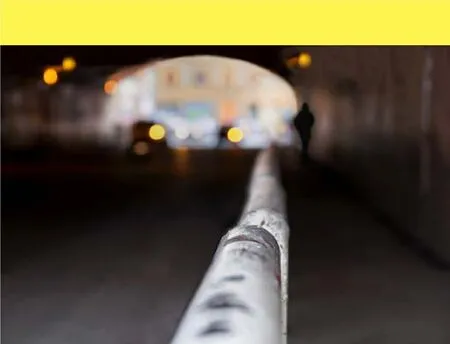
吃完饭,荣志国照旧不管邻居曾打“110”告他扰民的事,把两个音箱移过来,让喇叭对准窗外。音频信号在电子屏幕山状起伏时,拐把子楼围起的楼院再次变成巨大的音箱,响起他爱听的歌。
荣志国双肘架在窗台上,望了望开阔的天空,又从制高点六楼往下看缩小了的一切。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尽管天天一个人在家不说不笑永远一个表情,皱巴着像块破布,却弥漫着他自己非常知道的滋味。这是他一天当中唯一能够感到快乐的时候——他从小就爱听歌。
看了一会儿没看见她,回头看墙上的钟。确认钟点儿没错后,又往下看。看了很久还是没看见她,脑袋空白起来,视线里是干巴起来的街道、车库灰石棉板的顶盖、圆了的树冠,还有路过的女人。女人和以前一样,远远走来时是脸,走过之后是身段。他这样看过她很多次,不同的是过程没这么快,总是她走来时向声响的高处望那么一眼,脸没了后是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很黑。还有只有从垂直角度才能显出的曲线。她的腰身一点也不笨拙,该是没那种往下淌的赘肉,常进行什么有氧锻炼。她一步步走进他早知道的拐把子第一洞,影子一闪在楼洞里消失。他不知道她家住几楼,有没有朝院内的窗户。他把手够过去,拧了一下调音旋钮,让声音再大一点。
这天中午荣志国很失望。第二天中午仍然很失望。接着好几天还是这样。尽管他从没想和她怎么样,但也不愿意是这样——中午听歌的时候,他喜欢有歌也有和歌一样的人,两样同时存在。他喜欢让和歌一样的人知道他在听歌,也像他看见她一样看见他。
荣志国的女儿还是天天来电话,还是在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女儿问他晚饭吃的什么,然后叮嘱一些话。到了星期六,又提去南湖公园门口看那像晒衣服似的在绳上挂的征婚广告纸片片的事,表示她并没放弃帮父亲找对象,仍在努力。
荣志国啊了啊,声音透着几分愉快,但没听。他已经习惯了,心里停着两年前就有的定位。他失败很多次,大哥二哥也不能动摇他对问题的看法。他说二婚和一婚不一样。他说他遇上的人就是这样:条件不好的,一见面就是结婚这个问题。不能和她结婚就别接触,也不知道过去吃过什么亏,所以才这么警惕,题目优先,一定要在那样的承诺下进行每一次接触,对每一次的接触承担责任;条件好的,关注自己财产的安全性,不说不想结婚,说咱们这个年龄结婚还有什么用,就那么和你泡着。骂人讲话,和你睡行,结婚不行。而条件处在两者之间,本来是数量最多最适合他谈谈的人,他却一个没遇上。他说那些两者之间的人,不是觉得自己条件不好,就是觉得自己条件很好,没人觉得自己属于两者之间又好又不好,可以有两者之间的态度。
荣志国越来越觉得是时间上出了问题。想了两天,地点也被想出问题,之后问题老了。他不中午放音响了,十点多钟下楼来,在院内一坐就是小半天。有时他往大门口看,有时他快乐地和看车库的老三说话。话特别多,也能爆发一下笑声,只是之后就有了对比,蒙上疲倦的脸,比他自己一个人坐着时还呆。他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等得状态低迷起来,很快像块石头,被稀里糊涂扔在那儿。
到了星期六这天,荣志国看见她从拐把子第一洞出来,走近他。他把脸压低,看见她的高跟鞋。她走过去后,他抬起头看。在她背影从院门口消失时,一切忽然显得太快。他浑然不知地站起,跟了过去。
在街口小杂货店,她让店主帮她试灯管好不好使。她说是她家卫生间的灯,不亮好几天,不知是灯管坏了,该买灯管,还是镇流器坏了,该买镇流器。她说她拆不下来镇流器,只能这样试着来。她说不管哪个坏了,她都在他店买。可惜店里没试的设备。在她打算到店主说的灯具店去试时,荣志国靠了上去,说:“我可以帮你试试。”
回到院内,荣志国突然和老三大声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没带她上自己家,只说“我得上楼回家试”。她点点头,说她在这儿等着。他转过脸,对老三说:“她家的灯可能坏了。”
荣志国下来时告诉她灯管没坏,“下步该试试你家的镇流器坏没坏。”他手里拿着镇流器。他把他家的镇流器卸下来,打算安在她家的灯座上,看她家的镇流器坏没坏。
她说:“灯管没坏,就是镇流器坏了。”要去买镇流器。
荣志国说:“灯管没坏,也不见得就是镇流器坏了。”说完补充一句他认为很有思想的话:“世上的事,并不是不是白的就是黑的”。
去她家试的结果,发现是她家电线与电线的接头断了,但胶布没掉,从外表一点看不出来。
荣志国回家取胶布,回来鼓捣几下,灯就亮了。
她不好意思地看着荣志国。她说他的模样一点也不像会的人。她的目光落在他的近视镜上,说想不到他这么明白,一时自我批评的话也多起来。角度不同,说法不同,当中却少不了一个意思,在数叨往事中表现出他是熟人,认出他是那个天天中午放音响的人。
荣志国慌了,赶紧说听音响和听人唱歌不一样,声小不行,没立体声的感觉。
她很随和,也帮荣志国说类似的话。原来她懂点音乐,年轻时考过市歌舞团。
她送荣志国出门时,荣志国说:“我是‘老初三’,下岗前在大厂当机械维修钳工。机械维修钳工是万能工。”就跟她讲万能在哪儿,并介绍他接触过新中国第一批进口的原苏联车床,还有捷克产的绕弹簧机。他说那种制造电器开关小弹簧的机器十分精密,全厂就两个人能修,他是其中一个。
她有点听明白了,不再机械点头,目光亮着看荣志国。
荣志国和她开门唠了好一会儿,唠得很好,突然问:“你中午不回家吃饭了?”
她说:“有时在外头吃。在外头吃省事。”
荣志国心安理得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从此听歌可以与看她分离,中午没看见她就没看见,晚上掐着下班时间在院门口等她。
她很愿意和荣志国打招呼,也常因家里一些类似买灯管买镇流器都不一定对的事,停下脚步问他。第一次问时,也要说他那句不是白的也不见得就是黑的话。后来再这样说时,就是让他去她家实际看看的理由了。
第一次从她家往回走的时候,荣志国情不自禁用他跑调的声音,哼哼他老在中午放的一首邓丽君,一路都是不同于过去中午远远看她一眼的滋味。
干完活坐下休息时,她主动向荣志国介绍她的家境。内容很快超出范围,提起便停不下。她女儿出嫁了,在北京,最多一年回来一次。她没丈夫。前夫有外遇。不是一般的外遇,和一个女青年整出了孩子,还是双胞胎。是那女青年坚持留的结果。她只好在算计中被离婚。
荣志国说她前夫可真不怎么的,愤怒地抨击着那个他并不认识的男人。
她很高兴,说一看就知道荣志国是个很正直的人。
荣志国热了脸,没一会儿说:“也不是我正直。他太不知道好赖,守着你这么好的女人,却不知道好。要是我……”他迅速停下了话。
她还是认真了,不再看荣志国,那样低着头,就等着他自己走了。
荣志国说着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算是告辞,走了。
她没再找荣志国帮忙。
荣志国中午不再放音响。
到了9月,院内个个楼洞贴出暖气试水的通知。
荣志国中午从六楼看她从楼下走过,看了两天终于挺不住了,去她家问暖气有没有问题。他说如果有问题不修好,发水冲了楼下就得赔。
她没让荣志国检查她家的暖气,只说不漏。
荣志国厚着脸皮出来。
第二天一早,她上楼来找荣志国,说她家暖气有个地方漏,去年用瓶子接,一星期半瓶。
荣志国说只会越漏越大,一下开裂也有可能,“去锅炉房报修吧。”
她望着荣志国,站在不动地儿。她说去年锅炉房就不给她修。当初家里装修图好看,她前夫把大六零铸铁暖气片全拆了,换了好看不好用的簿铁皮暖气片,设备已属她家私自改装,只能自己负责。
荣志国说:“那我去看看吧。”
荣志国呆呆地站在那里。暖气挨着床,中间没下脚的空儿。
她催荣志国看。
荣志国趴在床上,用她的小化妆镜,反射着看。到底在第四片朝里的柱面上,发现了褐色水迹,水迹最上端有一个当初靠油漆密死的洞眼儿。这种坏很难修。无法拆下那一片换新的。也不能焊,怎么也是里面没防腐涂层,挺不了几天。整组换要花五百多块,但也不能和现有的那些暖气协调。即便一个牌子,新的也不可能和几年前生产的颜色、式样完全一样。
在参建各方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下,2018年1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白耀华亲自按下启动按钮,盐环定扬黄工程更新改造项目首座泵站机组空载试运行一次性成功,各项试验技术指标符合国家规范。
荣志国坐下来,沉着脸抽烟。
她给荣志国沏上茶,又出去一趟,买来一盒好烟,让他抽她的烟。
荣志国冒汗了。
荣志国想了很久,去水暖配件店买了个三寸管喉箍,又向老三要了一块自行车内胎。他拆下暖气,垫上内胎,用喉箍紧住漏点。重新安装时,把暖气调了个儿,喉箍朝墙。
她问喉箍花了多少钱,越听没多钱越问。
荣志国说:“就两块,实在要给,这盒烟我就揣着了。”
她笑了。
荣志国也笑了。
荣志国还是那样笑笑。
她只好像承认自己问了也不懂只能永远傻下去似的笑笑,然后就夸荣志国修得一点也不影响美观。
荣志国说:“不仅是不影响美观,防护面积大,哪儿漏这儿也漏不了了。”
荣志国喝完她沏的茶,才离开她家。
四天后的中午,她从荣志国的音响走过时,扬起脸朝他笑,开口和他说话。随即自己也发现了问题,就把双手在嘴上架出喇叭。
荣志国还是听不见,但比听见更明确。他大幅度地朝她点头。他知道他的活很为他作脸,试水时一点没漏。
这天晚上,荣志国待着待着就想到她的床很暄,床单有种不知是什么牌洗衣粉留下的味,全是趴在上面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但试水成功后有了。只是没一会儿,心里忽然又很不是滋味。他很不高兴当初她故意不告诉他漏。他忍不住从这方面挑她的理儿,纠缠起待人礼貌不礼貌的问题。他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像鱼泡儿。
第二天,荣志国早早下楼等她,见了说:“有点事需要说说。”
她说:“进屋说吧。”

王 宪,辽宁沈阳人。发表短篇小说多篇。短篇小说《鬼道》获《芒种》小说奖,《后果》被《短篇小说选刊》转载。长篇小说《自己》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互联网上发表长篇小说《红山古玉》。
荣志国跟在她后面,进了她家。她打开厅里暖色调的吊灯,让他在沙发上坐下,转身沏来一杯茶,放在茶几上,拉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她说“说吧”,随即忍住马上要笑出来的脸,一下变得比笑好看。她就那样看着他。
来之前想好的话,荣志国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拿起茶杯,吹了吹,烫着喝了一口。“其实没事,只是吃完饭出来走走,想上你这儿坐坐。能让我进来坐坐就挺好了。”他咧开嘴巴,特别傻乎乎地朝她笑了一下。
她的目光暗淡下来,随便唠了两句别的,就来说事。“我还以为你找我是要帮我好好弄弄暖气。暖气改装后一直不如以前,家里不再养花就是因为这个。”她讲那年花是怎么被冻死的。冻死的花是蝴蝶兰。她的脸在惋惜中皱皱,充满了伤感,更像蝴蝶兰开花时也去不掉的那份柔弱。
荣志国指出不懂的人为家好看爱弄出的问题,陪她唠几句,很快没心了。停停就说:“你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也不否认我这么说是有目的的。你也能从院里人知道,我现在一个人,是自由的。”之后,坐在那里有着自己感受不完的狼狈,红了整个脸。
她笑起来,只一声停下,特别正经起来。她说“是有这个自由”,说了两遍,然后什么也不说了,停着一副很呆很呆的呆相。
荣志国说:“我一直对你印象不错。我愿意和你往来。”
她更低头。
荣志国说了很多话,说完悄悄看她一眼,赶紧端起茶杯喝茶。
时间好像过了一辈子,她才开口。先是对自己说似的,“有的事儿,是倒不回来的”。后来又说,“我们不合适”,声还是不大,好像只想让自己听见。
荣志国说:“怎么不合适?”
她又不说话了。
荣志国不管她了,一定要说心里最后一句话。“从今以后我就对你好,你怎么对我我就不管了。怎么对我都行,把我骂走也行,我愿意。”
她说:“那有什么好处呢?不会有好结果!我不会和你怎么样,一开始就不是那种感觉。”
荣志国说:“那也行,那就朋友,朋友行了吧?我就真心待朋友,你可以没一点负担。”
她说:“朋友也不行。那样的朋友存在不了。朋友朋友就朋友出别的事,最后还不如一般仇人,也一辈子忘不了。”
荣志国讲不过她了。他又喝茶。很快肚子特别饿,汗从脸上流下来,擦也止不住,水唧唧的。他想起人在饿时不能喝茶,越喝越饿,可他已经喝了两杯。他说:“你得做饭了吧?”站起走出来,免得自己一会儿更不像样。
沉默一个多月,这天她匆匆来找荣志国。挨她家那洞的二楼邻居被盗了。小偷半夜踩着满是冰雪的楼洞遮雨台,打开二楼邻居厨房塑钢窗户的锁扣爬了进去,之后又从这家阳台窜到另一家,一家家窜,偷了三家。
荣志国急忙跟着她去她家。她家的窗户,离所有可攀登的地方都很远,有铁罩栏。他说:“你家没事。”
她露出镇定之色,就说刚才警察挨家走,看了她家也说没事,但她怕警察水平不行,根本看不明白存在的问题。
荣志国哦了哦,没有说话。
她坐下来,又立刻站起,忙着给荣志国沏茶。唠一会院里的闲事停下说:“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你帮忙。”
荣志国说:“绝对没问题,朋友不在仁义在。我说的是真的。”
她的脸还是红了。
荣志国让她拿来笔纸,写下他家的电话号。“半夜打也行。什么事也比警察来得快。派出所离你家半站地,我离你家不到一百米,还算上了两个楼梯。”
她把纸用电话压住,之后脸一直很红很红。
拐把子楼存在了三十九年,上百户人家常头疼上下水要修,暖气要修,电要修,门窗要修,封闭阳台的水泥墙面也要修。而她家因为有荣志国出现,好办多了,她想着备好茶好烟再阿庆嫂一点就行了。
荣志国给她修了两次,动了心眼儿,再换件时,故意不换坚固耐用的,让它差不离就坏。不过是有选择的,不属于会带来危险的关键件。而且买得也便宜,大都是大东旧货市场的东西。她很高兴,告诉他她厂效益不好,不开档案工资,她每月只能领到八百块。
这天,荣志国接完女儿电话,电话又响了。她让他马上过去。
她家的门半开半关着。她在厨房正拿毛巾往水管活接头上捂,脸上头上挂着水珠。她的眼睛紧紧盯着手。她的指缝蹿着毛巾挡不住的小水柱。
旁边还有一个男人,穿得西装革履,端着比碗大不到哪儿去的不锈钢盆,在下面接水。满了就从她另一侧狂奔几步,往卫生间陶瓷洗面池里倒,再回来接下一盆,弄得一路是水。
她发现荣志国时,几乎是埋怨的口吻,“看怎么办吧。”
荣志国不再愣着。削好木楔,拆下活接头,顶住四分粗的水管。
三个人坐下来,她特意介绍一下荣志国,说他住在这个院,是她老邻居。然后介绍那男人是她同事,安技科的工程师。事情是工程师引起的。他从厂里弄了个漂亮的不锈钢水龙头,换下她家厨房的旧水龙头。他关了入户阀门,拆旧水龙头时,拧动了与旧水龙头相连的水管;准备缠麻重新加固时,又拧动了与水管相连的三通,之后又是一段水管、一个活接头松动了,一直坏到进阳台接胶皮管子的接头,整个暴露在厨房外墙的管线都必须重新安装。好不容易全部弄好,打开阀门,发现活接头也裂了。再去关阀门,阀门也关不上了。
她讲刚才发生的事,工程师不时晃晃头,后来开了口。告诉荣志国哪哪都不行了,碰哪哪坏,就感叹亏得阀门坏在开的位置上,还可以照样用水。又转过脸,往阀门那看了一眼。
荣志国对工程师说,每家都有每家的特点,动哪儿都必须先看好,开个会研究几天也不为过,否则非沾包不可。拆她家的水龙头时,用管钳子扶着点水管就好了。他说那个像不锈钢一样亮的活接头,材质是锌铅的,不动保三年,动就可能立刻报废。说完,掏出烟,叼上一根。随即看眼工程师,又抽出一根,双手递了过去。
工程师说他不抽烟,之后就端起茶杯吱喽吱喽喝起来。喝完一杯,拿暖壶续上热水。
荣志国抽第二根烟的时候,工程师喝第二杯茶。他和她唠了一会儿入户阀门应该借社会停水时换。工程师又往杯里续了满满的热水。他的手握着杯把,大拇指在上面一下一下动着,很有时间把玩似的,就那么陪着。
荣志国下了决心,一定要等工程师走他再走,就和她唠别人家发水泡汤的热闹。他越来越专心不起来,借着笑,拿眼睛往那边看。后来不想看了,可频率还在增加,目光不可控制地往那边移。再后来,他停下话,什么也不说,只看着工程师,干脆就是明晃晃的态度,就是想让他知道他在看他,充满一触即发的味道。
可是,一点力量也没有,工程师还是那样坐着,那样友好地看着他,那样喝着茶,温和、懒散、不可动摇,就是不走。他只能再找话说,也开始觉得嘴越来越笨。他不说了,也不走,一个劲抽烟,弄得一屋子烟气。
工程师移动整个脸,夸张地看眼墙上的钟,对她说:“要不我先把鱼收拾了?”就去了厨房,只有半个屁股还露在门框上。
荣志国身上悄悄冒汗。他坐不住了,说:“我衣服可能透了……”站起往外走。
回家没待一会儿,荣志国再次下楼,站在胡同对面一棵大树后,紧紧盯着院门口。直到院内一片漆黑,也没看见工程师出来。他心里酸酸的,浑身无力,蒙着世界末日的感觉。
后来他想,就不该走,就该好好地饿他们一顿。他知道工程师喝了不少茶,饿起来只能比她更饿。他一夜没睡,之后好几天还在这样后悔。
一直没社会停水,没机会换阀门。这事在一个女人心里是个挺大的事儿,她打电话问荣志国有没有别的办法换。她的声音还是过去的声音。对他的称呼,因为接触多了,叫他志国。
荣志国说:“让我想想。”
荣志国没想出好办法。在她第二次提这件事时,决定还是顶水干,然后浑然不知地脱口而出,“现在你家就你一个人呀。”
电话空了一下,回答就她一个,又说也是该再找个人一起给荣志国打下手。
荣志国说:“得得,我可不要什么工程师。我可不要样子货!……”他把那个工程师从水平到做派狠狠说了一顿。放下电话,愉快地下楼,向她家走去。
阀门换得相当成功。她顾不上收拾,招呼荣志国坐,端来茶,她早沏好了茶。
荣志国双手接住,尽管不渴,还是喝了一口。
她去擦地,荣志国坐在那儿抽烟。抽完嘴里干了,想起喝茶。他拿起茶杯,迅速放下。他呆呆地望着茶杯,又往角架上看。角架上果然有他记忆中的茶杯,一共五个。他心里好些了,可片刻后又不行了。尽管她家不止一个茶杯,但不能说明他用的这个,就不是工程师那天用的。
上来一股劲,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了。他看角架上的茶杯,又看他用的这个。那天他根本没注意工程师用的杯子在细节上有什么特征,不知道哪儿有磕碴、哪儿有划痕。
没等荣志国进一步证明是不是一个茶杯,获得自己想要的结论,就已经是看哪个,都想起工程师那肥厚油腻的嘴唇贴在上面——那一瞬间,他特别忘不了自己从第一天在她家喝茶,用的就是这样的杯子,用了一次又一次;特别知道工程师不可能是在换水龙头那天第一次来,那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而每次来用的也是这样的茶杯,也用了一次又一次。一种滋味停在嘴上,他下意识地抹了一把嘴,之后却忘不了另一张嘴,更加不得劲。
她家有需要荣志国帮忙干的活,不用上楼,打个电话就能找到他。他只能什么也不说地过去。有的时候,干着干着活,工程师就来了,根本不是他想避开就能避开的事。有的时候,工程师没出现,却一直有马上就会进门的感觉糊在他的脑门上。工程师用过的茶杯,也继续被用来为他沏茶,就那么摆在桌面上,然后是认真劝茶的话。他的感觉一次不如一次。
后来,即便在自己家,荣志国也有了变化。他有了电话一响就看号的习惯。看见屏幕上那串熟悉的数字时,更是一阵阵紧张。他呆呆地望着那号。可是,他永远拧不过铃声,还是一次次接了。他的声音也和过去一样,竭力不表现出一点异样。她有往他家打电话的权利,号是他给她的。他没有不接电话的权利,不是许诺过她怎么对他都行吗。
女儿来了几次后说:“爸,你怎么蔫巴巴的?”
荣志国说:“我没怎么!”声一下高了。
女儿问他怎么现在中午不放音响听歌了,比“110”来的那天还老实。
荣志国不吱声了。
女儿又说他气色不好,说了很多,说老一个人生活不行。当晚女婿来了电话,让岳父去他家住。说他家冬暖夏凉,说他会做好几样味道很地道的粤菜,说他儿子好玩,逗逗外孙,当姥爷的多有意思。
荣志国住进女儿家。很快发现,那些邀请他去住的话,不过是些热情洋溢的词语。这天,趁白天他一个人在家,留了个纸条,带着东西走了。
回家第一件事,荣志国拿起电话告诉她他回来了。
她惊讶地说:“你上哪儿了?”
荣志国说:“出去一趟,上女儿家住了几天。”
她说:“那挺好,老待在家是不行……”打听起荣志国女儿家的条件。
荣志国介绍女儿家的条件怎么好。
日子继续着。
她家继续有活。
荣志国继续帮她干活。
责任编辑 李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