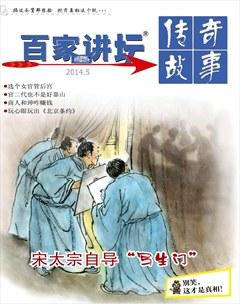边角料
明朝男人很“浪漫” 佚名
翻开《金瓶梅》,妓女似乎无处不在。西门庆和朋友喝酒玩乐在妓院,过生日在妓院,谈生意也在妓院,喜庆时也请妓女到家里弹唱助兴。事实上,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后,民间开始变得富裕,妓女也随之增加。嘉靖到崇祯年间,甚至有人举办各种选美大会,品评名妓,设定“花榜”,依次是:状元、榜眼、探花……明代的妓女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西门庆过生日时叫来了妓院新秀郑爱月,众妻妾们好奇地对她评头论足,郑爱月的鞋子、头饰都很时髦,连向来对自己衣饰品位自负的潘金莲也“不耻下问”。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明代妓女在许多方面都比家里的老婆有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不只表现在容貌、穿着上,还表现在文化水平上。以西门庆家为例:大老婆吴月娘虽然出身官宦,却不识字。郑爱月虽然出身妓院,但受过专业训练,不但会弹曲唱词,还能欣赏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男人上妓院与其说是去消费女色,不如说是去追逐“浪漫爱情”。
宫猫也要分品级 包光潜
据史料记载,明代宦官机构名目繁多,光叫“房”的就有几十个:御酒房、猫儿房、豹房等。猫儿房是管理宫猫的机构,不仅要管理好大量的宫猫,还要在众多宫猫中选拔佼佼者,献给皇帝。皇帝喜欢的自己留下,其他的则赏赐给皇亲国戚。这些宫猫和人一样,分三六九等,公的叫某小厮,母的叫某丫头,得到皇帝和后妃们特别宠爱的,还会赐名封号。有了职衔的猫就叫某管事,享受特别待遇。由于宫猫主人的官衔不同,这些猫管事们也就有了大管事与小管事的之分。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公猫被阉割后,一般叫某老爷。猫老爷在宫猫中享受一定的待遇,地位很高。如果官猫得到皇帝的恩宠,那就了不得了,生前风光,死后哀荣。
道士促生西厂 李国荣
紫禁城坚如磐石而又防守严密,宫禁制度面面俱到且处罚严厉,但破禁之事还是时有发生。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道士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许多太监对他奉若神明,常引他入宫游玩,还带他登万寿山观景。有的宫女为了能得到皇帝的临幸,也请李大师作法。李子龙在装神弄鬼之余,竟与宫女通奸,直到被锦衣卫拿获,才和多名太监一起被枭首示众。这件事使明宪宗深感锦衣卫和东厂力量不足,于是设立西厂,派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统领。汪直由此发迹,祸乱朝纲。
广州自古就开放 王月华
宋朝年间,广州已有十万外商聚居在西门外,政府专门给他们划了块地,叫做“藩坊”。
因為待遇不错,很多外商到广州后就不愿回去了,赚钱后买房买地,再雇几个昆仑奴,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这些人定居下来后,自然要生儿育女,于是这些“外来娃”的教育就成了朝廷关注的问题。虽说宋朝政府的态度要远比清朝开放,但让帝国的下一代与蛮夷后代同室求学,仍然是主政者不能接受的。为此,广州特意开办了“藩学”,专门招收外商子弟。由此可见,广州开办国际学校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至千年以上,广州的开放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书商售书有妙招 李鹏
为了更好地招揽客户,书铺会尽其可能地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例如,清代福州南后街的书铺,看书、购书悉听尊便,甚至备有笔砚供熟客抄录。乍一看,此举岂不会使得消费者不再买店里的书了?其实不然,精明的销售商以此聚集人气,吸引更多的爱书者到店里来,久而久之,图书销量自会增加。
清代琉璃厂卖旧书和碑帖的书铺招待顾客更为周到:到处是檀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暧炕上小憩,吸烟谈心。书店伙计和颜悦色,绝无慢客举动。买与不买、给现钱或者记账都行。但这类书铺主要经营珍稀古本,对此有兴趣且有购买能力的,都是高端客户。不过,一般的书铺也有高招:弄来前几科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试卷贴在墙上,吸引众多士子前来观看。这样一来,店里自然热闹,图书销售量也相应增加。
不仅琉璃厂书铺如此,北京其他地方的书铺也都如此,即使天天去看书,看上大半天,或连续看几天,掌柜、伙计也不会厌烦。偶尔买下一两部,下回来就会被当成老主顾,享受到“奉承恐后”的待遇。
参加饭局是件苦差季 李开周
唐朝时,李蔚去拜访韦昭度,看门的骗他说韦大人不在家,李蔚只好回去了。走到半路上,知情人告诉李蔚,这是韦大人故意让他吃闭门羹。李蔚大怒,发誓要跟韦昭度绝交。韦昭度听说后,赶忙摆了一桌宴席,请李蔚前来喝酒,向其赔罪。李蔚到了韦家大门口,想起之前的事,说啥也不进门,韦昭度只好跳着《杨柳枝》舞亲自出门迎接。
韦昭度官高位尊,跳舞迎客似乎不太雅相,但这在唐朝很流行。在大型宴席上,唱歌跳舞是必有的环节和必备的礼节,主人请客人就座时要跳舞,给客人敬酒时要跳舞,客人也要唱歌跳舞来答谢主人。好在那时候舞蹈动作不太复杂,就算学不会,也可以跟大伙明说不会,站起来使劲道歉,然后自罚三杯。
比较起来,还是宋朝时赴宴省心,因为主宾都坐着喝酒,唱歌跳舞的差事全交给家里的歌伎或者外面的乐队了。但是那些擅长写诗填词的宋朝士大夫们并不省心,歌伎们整天唱老掉牙的曲子,早唱厌了,听说席上有填词高手,比铁杆粉丝见了偶像都兴奋,会请他们写新词助兴。
乾隆南巡为治水患 姜涛
1736年,乾隆下旨令淮扬在京任职官员据实陈奏治水意见,以备采择。可见乾隆一开始就注重河工。
乾隆第一次南巡经过车逻坝时,见到车逻坝泄水尤盛,想到淮水归江,要增加东西湾人江口门,开挖太平河。第二次南巡时,他谋划先降低洪泽湖的水位,接下来定淮水入江为急办工程,先后连续多年,终于使归江口门达到107丈,归江河道具备了排泄淮水的价值,无疑对减轻里下河水患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实施了他的“抽薪之计”,修订水情调度水则,减少淮水排向扬州的泄量,令河臣恪守此法,终于使里下河赢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不被水淹。
后来乾隆听说淮扬运河好久没有疏浚,河床逐渐淤高,不仅有碍漕运,水大之年还致泛滥,遂传谕两江总督、总河逐段查看测量,要他们一面组织开挖,一面上报。
由此可见,乾隆南巡一是为了治理长江水患和利用黄河水利,同时沿运河南下,查明漕运;二是为了解农田谷物情况并视察民情,而并非纯粹游山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