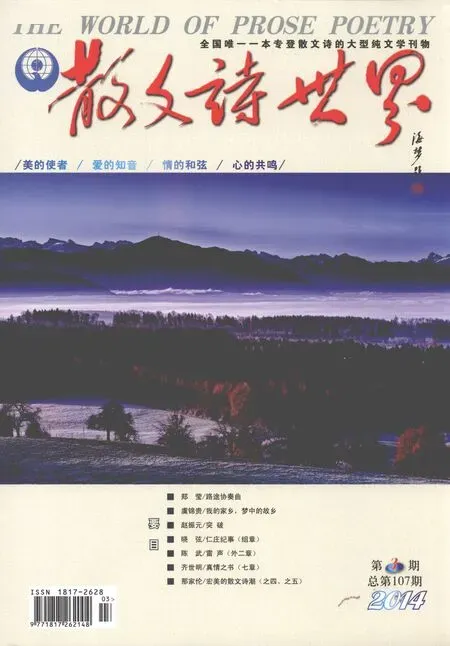仁庄纪事(组章)
浙江 晓 弦
实力方阵璀璨的星群
仁庄纪事(组章)
浙江 晓 弦

撒野的风筝
风筝在屋后的麦地里撒野,闻到爆竹的硝烟味,却越发地野了。
一缕酒香的鱼肉味,一缕桂香的兔肉味,一缕温馨的炊烟味,在村庄的转角处合谋。
夕阳西下,她们要劝风筝快快回家;
风筝接住了身后那排欧式公寓的窗户里,十三岁的二姐从初中教科书里,猛地抬起的眺望。甚至,他还闻到不远处“和谐号”高铁银蛇样高贵的喘息;
那只壮硕的花狸猫,捧着一根狗骨头,在他身后喵喵叫着。风筝骂它吃饱了撑着,无聊!
风筝只想念头上的蓝天和脚下的麦苗。可风筝怎么也不明白——那块适宜于滚铁箍、砸洋片、踢王和骑单车的水泥晒场,大红的推土机把它当成了作业本,狠狠地揉成了一团。
莫非,推土机也在上小学低年级,也不想在节假日写没完没了的作业?
五谷杂粮的起义
乡亲们,让我说一通胡话吧!
你们看,水稻在锈迹斑斑的水田,任凭再怎么苦苦地回忆,也想不起怀孕这桩千古大事;
小麦与大麦一个德性,春风不来,故意沉醉在一场所谓甜蜜的密谋里;
高粱像村里喜欢假冒品牌香水的小娘子,只要有脸色酡红的有钱人上门,不再脸红,也不再想心事似的低下头,抻长辫子或扭衣角。
坏就坏在土豆,这看起来土头土脑的家伙,还未开春就长出粉红的芽来。他把蚕豆豇豆赤豆毛豆这些豆字辈的同仁,一一数落,一一洗脑,一一苦口婆心个遍。
他还伙同老成的胡萝卜和不再纯情的小萝卜头,把在情事里不能自拔的莲藕,从黑淤泥里一一勾引出来,给她们黄金的启蒙,说什么地球同此凉热。说什么跳槽下海东山日出的时节已经到来!
掂量过五谷杂粮的水泥晒场是无奈的,一下子堆满了村庄最粗的黄桷树和黄羊树,堆满豁了牙的风车锈了马达的手扶拖拉机。
终于,五谷杂粮在一个暖冬集体起义,她们万众一心发誓:绝不沾染古老的晒场,不哭诉不后悔临走不扔一句感激半句感恩,就失散在一个看似黎明的黄昏里……
考古一个村庄
考古学家像个仙人,在村庄龟裂的大晒场运足气,借古道热肠的线装书的浩浩乎洋洋乎,说这是一个贵妃一样典藏的城池。
像在默写村庄的天文地理,他在村庄仅存的一面灰色土墙上,用碳笔一一记下:道路、城墙、楼台、学宫、府衙、道署、寺庙、水塘、沟渠、牌坊、古树、闸前岗、府前大街、田螺岭巷、花园塘巷。
他像熟练的甜点师,将芝麻葱花疏落有致地撒在烧饼上。
他还记下村庄的胡须,眉毛,嘴巴,鼻梁,额头,青春痘,美人痣,记下男人醉生梦死的花翎的官衔,和欲望喜悦的红荷包。
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五百年前……他把这张烧饼烤得焦黄诱人。
他说一千年前,小村是位香喷喷馥郁郁的处子,眼神清澈,肌肤水滑,丰乳肥臀,腰如丁香;
他是岁月的间谍和时间的特务,他现身村口,就带来一出精彩的谍战戏,令用心者感叹,用眼者唏嘘,用情者春心萌动。
考古家如是说
所有的人和事,都无法摆脱土地最初也是最后的召唤。而尘土,炊烟一样从地狱十八层汩汩升起。
生活的悲欣交加,无非是像糅合于土里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像慈悲的千手千眼的观音或现世宝,轮回再现。
世事的潮起潮落,沙器样崛起的大大小小的建筑,无非是在土地的胸脯上,再施以一层毛茸茸的尘土;
然后,新的尘土又被时间召回,又重新夯实,等结出灰黄壳儿,又有新土一掬掬堆来……
鲜血与呼吸,生命与挣扎,光荣与耻辱,全以壁画或者芯片的形式,镶嵌在大地的裙裾上,形成村庄的处女地。
卡车载着千年时光绝尘而去
装古董的车辆,在村口一辆接一辆;
挖土机咆哮如雷,裂缺霹雳,丘峦崩摧,轻巧地把千年的黑暗一片片开启。
土壤的橙红、浅黄、浅灰、灰黑、深黑,依次从地下炊烟一般升起。
厚薄不均的黄土层,吸引了真真假假的考古家,一个花香酒气、纨扇笙箫的年代,被硬生生地割开。
时间的废墟里的一只玉琮,一片碗底,一枚石镞,呼应着酒的香,花的色,剑的张。或者,一场风花雪月,一次例行的朝觐,和一个甜蜜的谄媚。
只知是明清的、宋代的、汉唐的,却不知是张子和的、许遥光的,苏轼的和王羲之的,是《嘉禾月河序》或《菩萨蛮•梅花洲八景图》的。
所有的事物,泥土里簇新和真实着,各个朝代的人物摩肩接踵——烧火,织布,写状,饮酒,耕作,书生琅琅,显现出时间纵深里片片华美。
大地幸运地接受一场场篡改,荣枯起伏,落花流水。
绝尘远去的运古董的车辆,一路撒落“有事,请拨137××××××××”的白纸片,像刀片,像雪泥鸿爪,撕扯起村庄车辙样的新老伤口。
一个傻子在立交桥口
每天上班过立交桥,总能瞅见一个傻子,在桥堍,用左手打老式的“大哥大”,右手高举一块“×××处长欺侮我小姨”的木牌。
这是早上的好时光,上班族把各式车辆,缓缓驶入流线型的立交桥口。
只有他,穿一件被卸掉肩章的老式军服,做一个忠诚的守桥人,呆滞的目光,如胸口被风雨浸渍的那块灰亮的衣衫。
一辆又一辆轿车,把车门摇紧,躲避他,仿佛他是永远的H7N9感染者,或者是一句灵验的诅咒——
执法疲劳的协警,蹬残疾车的老哥,收废品的大妈,骑单车的情侣,一个个把头转向天空,仿佛天上有青春的鸽子在召唤他们。
但那几个协警,过后会转过头,瞄他一两眼。骑单车的情侣,又恢复打情骂俏。
只有一个喜欢写散文诗的,呆呆地默视他,竟然忘记自个出来什么的干活。
有知情人悄悄靠近我说:“这个死要面子的老汉——木牌上写的小姨子,其实是他的原配妻子!”
我本是一座土得掉渣的土城
说来奇怪,喝了这么长久的自来水,在都市的五光十色里打摸爬滚几十年,身上的泥腥味,却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缘由莫非是,从小打赤脚在田野疯癫捉泥鳅掏螃蟹,喜欢吃野荸荠啃野芋艿嚼新鲜多汁的野茅针,交多了草鹅草鸭小羊小猫这帮狐朋狗友,放学要割满一篓狗尾巴草捞满整筐东洋水草,身穿棉土布衣裳蹬麦糊儿黏的千层底。
甚至,我还记起了最爱五谷杂粮的陋习,特喜欢土八拉几的土豆高梁和米酒。
我本不是净过身的太监,而是一座天生设防的土城——我头颅的城门,亮起土味浓烈的两只红灯笼。我有单薄的胸腔和猥琐的容颜,并不宽厚的嘴唇,一张启,便是一串野葡萄样的绍兴土话。我笨拙的四肢在七彩的城池里,老是辨不清方向,心里渴望一阵清亮的蛙鸣和水鸟亲切的教导,盲人一样将我认领。
一个人的河
她的青葱的一生,与这条河有关,河的拐来弯去,河的清澈与混浊,河咳出的泡沫的灰白和暗藏旋涡的铜绿,都深深地、深深地装扮了她的多舛的命运;
甚至,一帘帘低垂的河畔柳丝,一枝枝湖笔样保持谦谦君子形象的芦苇,一丛丛扭起柔腰的少女般的水草和红菱,一阵阵起自麦田的似有似无的白毛风,全是她难以逾越的羁绊和难逃的劫数;
薄薄秋日里,那双空留在河滩的绣花鞋,到了春天,像两尾搁浅在沼泽地的红锦鲤,或者,两只迷失在茫茫人海的小舴艋,世俗的桃花汛,越来越急;
涨潮的日子,从抹了油的媒婆嘴角渐渐溜走。花样年华的你,一瓣瓣凋落于季节的尽头。你背负生命的十字架,河水一样渐行渐远,终于消失在黎明淡淡的血色里。
只有那些白鹭在河滩歇脚,远远望去,像诗人随意丢弃的白球鞋,仿佛在等一个赤足披发的白晰裸女,哗地从河里起身,迅捷地穿上它,然后随光线飞去。
河水麦芒一样的光亮,急急照亮了,黄昏难抑的羞色。
爱在天梯间
认定了这座大山是爱的归宿,自天际垂下的粉色的拯救之路,像披了云霓的挽联,需要一步三磕,才能读懂月亮的心经;
认定了这座大山是羞于交媾的欢喜佛,是密宗的自由极地,是高耸于天际的爱之无字碑;
这是一场痛苦而漫长的朝拜,在时间的天平上,影子注入影子,步履叠加步履;
一座大山,一对男女,像梁祝遇到着火的春天,化蝶是必然的归宿。在翻越三千多级血染的台阶后,将爱之蟒,牵进一个哥德式的地堡,那深深的冬眠里。
此刻倘有雷霆,必是为爱加冕;此刻如有暴雨,必为忠贞的青蛇显形。
爱太软,盘踞在针芒的一滴玉露,得了真经,然后滴水石穿于古老的时光岩,滴出一条蛇蜕样虚拟的天路;
而灵动的机关,鼓动一场埋伏万年的纵横捭阖的突围,以兑现一宵千金的承诺。
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林子
我看见的一个林子,其实只有四枝春天的白桦;
我看见两对灵动的桨,或者,四把追打春光的桨,她们优美地划动在林涛的呻吟里。
哦,我看见灵动的桨影,和桨影里战栗不息的灌木,和灌木丛下赤热的山峦。
早春薄薄的雾岚,为她们抹上一层又一层弯弯曲曲的羞涩和光晕。
我还看见,一条明亮的小溪,和溪水旁啃草的一群青春的山羊。
甚至,我还看见律动着站起来的海,以及,一场堆满雪浪花的时间的海啸。
2013.12.30完稿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