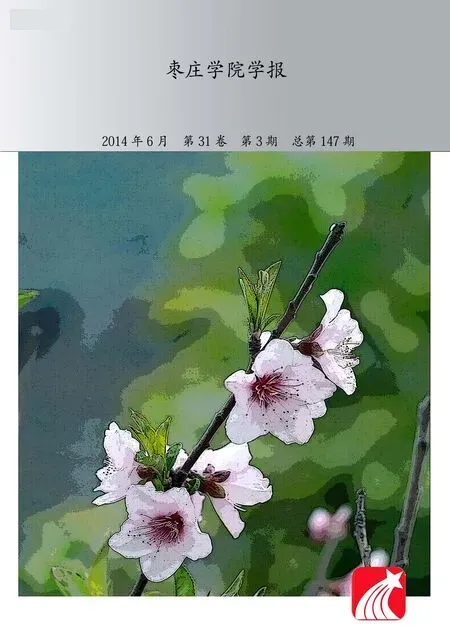“和”与嵇康音乐美学思想
车坤
(青岛大学 音乐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嵇康,魏晋时期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声无哀乐论》与《琴赋》为其阐述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前者思辨性强,集中阐发了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后者融入了嵇康平生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实践经验,兼具理论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嵇康缜密完整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体现出嵇康籍以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
一
研究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不能脱离生活时代及其时代的哲学思想。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P177)这个时代玄学的出现给人的存在提供了思想上的解放和超脱。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是庄学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它的中心课题是要探求一种理想人格的本体,极大的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带有“人的觉醒”的重要意义,“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2](P114)个体的人格理想追求在内在的自我精神上超越了有限达到无限,追求自然之道,在理论阐述上则以思辨为用。
《声无哀乐论》通过“秦客”与“东野主人”的八次辩驳,深入探讨了音乐的本体、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问题。嵇康认为: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
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
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
嵇康从唯物主义元气论的立场出发,认为构成乐的实质的根本性的东西,也即乐的本体,是从宇宙天地而来。五色五声产生于天地阴阳五行的变化,而声的善与不善,就如味存在于天地之间,有其不变的本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琴赋》中也多有提及:如“宣和情志”“清和条昶”“性洁净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摠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和”最初有调和、中和之意。在中国美学史中,它往往与各种思潮联系密切,政治、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礼记·乐记》中“和”之天地、阴阳之气交融汇合,已有道家思想融合在内。“和”简单来讲即和谐、自由、自然、本真,在哲学层面上指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宇宙生成的法则和规律。具体体现在,就自然而言是阴阳协调;就禀赋阴阳二气而生的人来讲,则强调人的精神上要具备“和”的气质和特征,要恬静、清远、要融于自然,天人合一;就音乐来讲,则首先要声有自然之和,也即音乐艺术的媒介和各种形式因素之间要有和谐统一的组合规律。《琴赋》以音乐的载体——琴为描刻对象,分三方面细细摹情入理。开篇就是追溯琴之家世本源,制琴的梧桐“讬峻岳之崇冈,批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以昊苍,夕纳景于虞渊兮,日晞干于九阳,经千载以待价兮,寂神躓而永康”。梧桐来自大自然,吸取日月之精华,含天地之灵光,所以琴音天成,以和为体,为自然之道。从音乐组成来讲,声是一个个的音组成,音源自物体振动的快慢,形成声音之高低。音与音的搭配组合,有其自然性和规律性,人为的改变则会使声音突兀难以入耳。所以音的组合同样要求和谐自然,合规律性;音乐的创作上则强调冲和、清远、恬静、脱俗的意境之美,这意境具体体现在“若乃高轩飞观,广夏闲房,冬夜肃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灿,缨徽留芳。于是器冷弦调,心闲手敏,触摠如志,唯意所拟,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尧,终咏微子,宽明弘润,优游踌躇,拊弦安歌,新声代起,歌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最终达到的是与宇宙自然的和谐永恒。所以,音乐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而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至此,嵇康所谓声无哀乐,便是一番思辨后的必然结论。
二
儒家乐论强调“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看重音乐的社会功用,是维护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一种实用的载体。《声无哀乐论》起篇以秦客发难,强调声有哀乐。而嵇康争锋相对强调声无哀乐,这就涉及到声与哀乐之间的关系问题:声既然无哀乐,然则声又是如何让人感觉到哀乐的呢?也就是音乐与情感的关系是怎样的?客观事实是,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却能实实在在引发情感的波动,或喜或悲。按照逻辑思维推理下去,这显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按照嵇康的理解,音乐与情感首先具有对应关系,而非必然等同关系。他说:
声之与心,明为二物
然皆以单复、高卑、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
情感是纯主观的存在,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悲哀、如欢乐,大体上这是人心中最为普遍的情绪反应,而人们给不同的事以不同的名,而不同的物以不同的号,哭泣叫做悲哀,歌唱称之为快乐,但人们讲到快乐,就是说唱歌奏乐吗?但名、实不同,事物之名与本体不同,唱歌是名号,是人为赋予,具有社会性;哀乐是情感本性,为心理产生,具有生理性和个体性,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歌哭是人情感表现的外在现象,哀乐是人情感的内在本质,而不能以歌哭的现象来简单认定声有哀乐。
嵇康以酒为例来说明:“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酒本身没有哀乐之情,只有酒味的芳香与否,酒香可以使人情感发生变化,但酒香本身却不是情感。所以酒香仅仅是一种味外之旨。
在音乐审美心理上,不同的音乐可以引起大致相同的情绪反应如“躁、静、专、散”等,但音乐欣赏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脑力活动,则包含着复杂多变的心理和情感体现的。音乐创作者因感而发,用心去创作,好的音乐固然包含了作者的深情,但欣赏者如何通过音乐作品而体验到其中所要传达的情,却是因人而异、复杂多变的。所以,嵇康说:
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则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
所以尽管音乐创作要有感而发,用心表现,但就欣赏者而言,则不见得会与创作者的情感体验保持一致,甚至因风俗不同,而出现听到哭泣而感到欢乐、听到唱歌感到悲戚。这也正应验了我们常说的,悲伤会让人哭泣,但高兴极致也会哭泣一样,所谓喜极而泣是也。这是同一种情感可以表现为多种声音的例子。
人由于主体差异所在,必然会造成音乐欣赏时理解的多样性。嵇康认为人们欣赏音乐时涕泪纵横的原因在于悲哀的情感早已蓄积于内心,接触到和谐的音乐而后流露出来“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后显发”音乐成为欣赏者情感引发的审美中介,这实际上隐含了现代接受美学中关于“期待视野”的一个主题。
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首创的“期待视野”认为,在文学阅读之先,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在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具体落实到文学阅读活动时,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期待作品能够表现出切合自己意愿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趣味。艺术欣赏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虽然期待视野讲的是文学阅读,但在音乐欣赏的接受心理上也是适用的。欣赏者的心路历程,他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历史、现在、未来……等等方面的体验和认识、把握和思索,全都融合在对音乐的欣赏和接受中,在音乐的震撼中,唤醒并巩固那些属于个体无意识甚至隐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情怀与深层体验。当音乐与这些情感体验达到契合时,欣赏者才会动容,才会接受并推崇。退后一步讲,即便没有这样的心理体验和把握,哪怕对于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婴儿来讲,对于让成人感到悲哀的乐曲,在他那里也许是让他很高兴的声音,反之亦然。这大概是音乐的节奏、高低、平缓、躁静契合了他幼小心灵的心理需求,让他产生了安全感或者不安全感的缘故。
音乐引发情感还具有不确定性,也即音乐的无常性:
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主于喜怒,亦无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
曲用每殊,情随之变。“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
正因为“触类而长,所致非一”,所以它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表现种种思想激发种种情感,从而体现出音乐的巨大魅力。它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情感,不偏执、不拘泥,而是使欣赏者能从有限的声音感受到无限,情感得以升华,心灵得以净化,回归到万物生命自然自由和谐本真的本性与存在状态。钱钟书论及嵇康《声无哀乐论》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两者的内在联系:“西方论师(Hanslick)谓音乐不传心情而示心运……嵇康《论》于千载前已道之”[3](P290)“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吾国则嵇中散《声无哀乐论》说此最妙……奥国汉斯立克音乐说一书中议论,中散已先发之”。[4](P72)音乐不是任何具体的情意,所以才能涵盖一切情意。
三
嵇康强调音乐以和为美,满足个人审美需求,追求理想的人格和人生,获得精神的独立和自由。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从儒家社会功用角度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琴赋》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
而移风易俗不是音乐的必然功用。所谓移风易俗只是社会世道衰弊之后的事。嵇康还特意把仲尼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做了全新的解释:古代王者承受清净无为的天道,用以治理万事万物,必定崇尚简易的教化,实行无为政治,君王清净于上,臣子顺从于下,玄妙的教化默默通行,所以,天人都通达顺畅,百姓安逸。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这样的情景下,自然会有平和的心情充实于内部,平和的气氛充盈于外部,于是和谐的音乐出现了,太和的音乐反过来又感染、引导人的平和的神气,迎合人的自然情性,使人心依顺“道”理。所以愉悦的心情表现于乐器,博大的神气显露于乐声。这样子世人同受感化,不言而信,不谋而成,和悦相爱,世间一片美好光明。这就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道理所在。这就说明平和的内心是音乐的根本,这是一种顺应天地万物自然生长从而自由发展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理想境界,所以,“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风俗固然是美好的,而音乐是“和”的外在表现,当音乐与诗、舞并和各种重要的社会政治利益活动密切结合时,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担当协调人伦关系、使人性雅化的职能,但这种职能并不是音乐自带的,而是当政者为维护君臣、长幼、上下、尊卑等社会关系而强加给音乐的,带有政治和道德色彩。这样的音乐已经不是嵇康心目中美好的音乐,所以他说:“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这一点与他一以贯之的声无哀乐论是相互补充的。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琴赋》所阐发的观点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高峰,在音乐美学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他使音乐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转而成为承载宇宙自然和谐统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强调创作者心态的澄怀虚静,欣赏者的平和洁净,都是要超越个体存在,超越有限,物我两忘,追寻那种琴声、音韵和人心浑然合一的玄冥,最终达到《琴赋》中提及的“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的境界。艺术的独立与个体生命的觉醒是并行的。由此而来音乐带来的魔力与人的魅力也浑然融为一体。
宗白华讲:“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5](P216)黑格尔讲:“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6](P182)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终将以里程碑般的光辉形象泽被后代的音乐美学。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钱钟书.钱钟书论学文选(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